《一日三秋》:走不出故事的城與人

云友讀書會:有書友自“云”中來,不亦樂乎?云友讀書會成立于2020年5月,是中國作家網(wǎng)在疫情中聯(lián)絡(luò)策劃的線上跨校青年交流組織。此讀書會面向熱愛文學(xué)的青年,通過線上學(xué)術(shù)沙龍、讀書分享、主題演講等活動,推動青年學(xué)人的文化與學(xué)術(shù)交流,力求以文會友,激蕩思想。云上時光,吾誰與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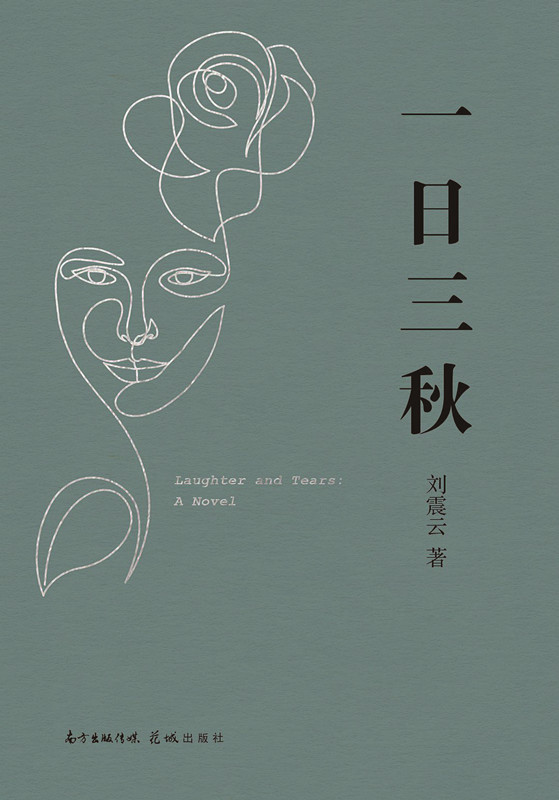
《一日三秋》是劉震云在《吃瓜時代的兒女們》之后四年磨一劍,為我們重磅呈現(xiàn)的一部頗具魔幻色彩的長篇小說,它以延津當(dāng)?shù)鼗ǘ飰糁兴褜ばυ挼膫髡f為線,鋪開了這一地方兩代人的悲歡。本期云友讀書會的四位朋友分別從小說中漫溢的白蛇元素、魔幻現(xiàn)實主義手法、“一日三秋”和“笑話”展開對話,為我們呈現(xiàn)進(jìn)入這個故事的多種維度。
@李楊:《白蛇傳》與日常生活的變形
劉震云的寫作路徑大致可分為兩條:一是寫世俗日常,以處女作《塔鋪》為起點,憑借《一地雞毛》確立“新寫實主義”代表作家的文學(xué)史地位,而《一句頂一萬句》可以說是此類寫作的集大成者;一是寫民間歷史,相繼出版的“故鄉(xiāng)”系列占據(jù)“新歷史小說”風(fēng)潮的一席之地。質(zhì)言之,前者注重日常生活經(jīng)驗的提煉、描摹與協(xié)調(diào),后者則以變形、夸張與戲仿的方式重新解讀歷史。在最新推出的《一日三秋》中,劉震云力圖“以日常生活為基調(diào),把變形、夸張、穿越生死和神神鬼鬼當(dāng)作鋪襯和火鍋的底料”,某種程度上或可視為其融合兩條寫作路徑的一次創(chuàng)新之舉。而完成此次創(chuàng)舉的關(guān)鍵,正在于對《白蛇傳》的個人化敘述。
《一日三秋》故事的開始,即安排豫劇《白娘子》中白娘子的扮演者櫻桃和法海的扮演者陳長杰結(jié)為夫妻,構(gòu)建起戲里與戲外的強烈反差。不過,戲里的演繹卻不斷滲透進(jìn)戲外,主人公明亮的乳名即來源于戲里“有出息”的翰林,而伴隨著李延生前往武漢拉開的故事主線,則與葬在亂墳崗上的櫻桃被強奸殺人犯逼著扮成白娘子“假戲真做”有關(guān)。貫穿全書近半篇幅的櫻桃靈魂的飄游,更是與《白蛇傳》脫不開關(guān)聯(lián)。從門市部墻上的《白蛇傳》海報,到明亮口袋里的折子戲劇照,直至被拋入江中,櫻桃化作的仍是戲中的白娘子。可以說,因一把韭菜自殺后,櫻桃始終是以戲中的白娘子形象出現(xiàn)并借戲“活了下來”。事實上,作者還有意打破戲曲與民間傳說本身的界限,肉身壓在亂墳崗等待陳長杰拯救的櫻桃,不免引人想起被壓在雷峰塔下等待法海釋放的白娘子。而被打撈上岸的櫻桃去到的,正是馮夢龍《警世通言》所記載的白蛇故事的發(fā)生時間——宋朝。傳說、戲里和戲外三個世界的跨越,充分發(fā)揮了小說作為虛構(gòu)藝術(shù)的魅力,而明亮對花二娘說的“負(fù)負(fù)得正”,則暗示著在文本閱讀過程中收獲的體驗與感悟是真實美妙的。這樣辯證看待虛實真假的思維方式,延續(xù)著劉震云在“故鄉(xiāng)”系列中有關(guān)文學(xué)與歷史關(guān)系的思考。
作為歷代相傳的“集體共享型”故事,《白蛇傳》中的白蛇處于“人是什么”與“人應(yīng)當(dāng)是什么”相對立的情境之中,也即本能欲望與社會觀念之間存在沖突。對此,書中借陳長杰之口一語道破:“《白蛇傳》的戲眼,是下半身惹的禍。”而支撐文本主體內(nèi)容的明亮與馬小萌的情感困境,恰與《白蛇傳》中白蛇所處境遇形成對照。馬小萌之所以被逼上吊,同明亮逃往西安,后又遭孫二貨羞辱威脅,直到晚年兒子鴻志仍因為其出頭與同學(xué)大打出手,都與借錢不成的香秀曝光她在北京做過五年妓女的事情有關(guān)。明亮選擇接受馬小萌的過往,但兩人的婚姻關(guān)系卻不容于延津的世俗道德,一如許仙接受了白娘子的蛇妖身份,卻難逃法海以人妖殊途為由鎮(zhèn)壓白蛇于雷峰塔下。不同于民間傳說的是,在激烈的矛盾沖突之外,日常生活更是由無數(shù)的平淡時光構(gòu)成,而這份時間的力量足以淡化或消解觀念的碰撞。不難見出,劉震云借《白蛇傳》隱喻了《一日三秋》所要展示的人生困境的主題,又以日常生活書寫暗示著走出困境的可能性。
1924年9月24日,雷峰塔的倒塌,為反傳統(tǒng)人士提供了想象的空間,一度成為五四知識分子推翻封建秩序的隱喻。魯迅即在《論雷峰塔的倒掉》中有言:“現(xiàn)在,他居然倒掉了,則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為何如?”及至田漢創(chuàng)作于20世紀(jì)中葉的革命現(xiàn)代戲中,法海所住寺廟成為腐朽制度的象征,承擔(dān)著剔除封建糟粕的歷史使命,延續(xù)著五四以來的反抗與斗爭意識。而在20世紀(jì)末的電視劇《新白娘子傳奇》(1992)和電影《青蛇》(1993)中,文本里的情與欲得以放大,滿足著大眾有關(guān)情比金堅或紙醉金迷的世紀(jì)末幻想。到了2021年,劉震云推出《一日三秋》,在革命與欲望的敘事之外,將《白蛇傳》的戲曲與日常生活書寫相融合,以夸張變形的方式重新演繹白蛇傳說,實現(xiàn)了寫作風(fēng)格的突破與自我的超越。
@趙志軍:魔幻中原的意義指向
剛才李楊談了《一日三秋》與《白蛇傳》的同構(gòu)性,他對故事的琢磨很細(xì)膩,我想接著談?wù)勑≌f打破魔幻、現(xiàn)實邊界的手法在文本層面的意義。大概可以斷言,多數(shù)讀者對劉震云會用此種形式重寫人們已然熟悉了的河南沒有準(zhǔn)備,這大致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作為中原核心的河南在中國文化中長時間表征著一種正統(tǒng),所謂“子不語怪力亂神”,儒學(xué)所倡導(dǎo)的積極入世的現(xiàn)實精神已成為我們關(guān)于河南的一種格式化想象,一種排斥與壓抑巫神鬼怪話語的固化印象;二是作為“新寫實”小說的代表作家,劉震云的作品一貫延續(xù)著一種冷靜的、刻意風(fēng)干了溫度與水潤的語言風(fēng)格,生活總是以破碎、干扁、缺乏價值的“本原”樣態(tài)呈現(xiàn)。《一日三秋》神話與現(xiàn)實、夢境與日常互相穿梭滲透的魔幻現(xiàn)實格調(diào),無疑與我們慣性的河南印象及熟知的作家風(fēng)格形成了不小的反差。這種反差又恰恰說明,這部作品在河南的地方書寫與作家的生存思考方面有著特殊意義。
關(guān)于地方書寫。魔幻現(xiàn)實主義這一形式的產(chǎn)生及流播(被邊緣、民族、地方、宗教書寫借用)本身代表著被壓抑的聲音以非正常方式進(jìn)行突圍的嘗試,故此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被規(guī)約為中國傳統(tǒng)(甚至正統(tǒng))之表征符號的中原(河南),在慣常的文化表述中被抽象與單一化了,這不僅掩蓋了其本有的斑斕色彩,更使得作為中國部分的河南(中原)很少被視為“地方”,而是整個中國或正統(tǒng)中國的不再被天馬行空地想象與創(chuàng)造的模板,以致河南形象總體上比較刻板、單調(diào)。《一日三秋》里的延津小城非常難得地恢復(fù)了“河南地方”本來面目,無論是戲里戲外糾纏人間的地方豫劇《白蛇傳》、夢里夢外界限不清的賣羊湯的吳大嘴、記憶與現(xiàn)實里真切卻又模糊的賣棗糕的奶奶,還是傳說與現(xiàn)實難以界明的花二娘、溝通陰陽兩域的算命人老董,都顯示了民間文化及民間話語本身的巨大豐富性。圍繞著老董的,也不再是“不語怪力亂神”的負(fù)載著文化包袱的“河南人”,而是一群我們所熟悉的現(xiàn)實又迷信的市井俗人,他們使抽象的“河南”不再正統(tǒng)、陌生。在延津人夢中尋找笑話的花二娘的地方傳說,也讓延津成為與眾不同的“獨一個”。即是說,經(jīng)由魔幻現(xiàn)實手法對地方符號的廣泛勾連,《一日三秋》使中原(河南)擁有了鮮明的地方性。
關(guān)于生存思考。魔幻現(xiàn)實主義手法對彌漫于個人、族群命運之上的無形禁錮進(jìn)行形象描繪和具體解釋的努力,無疑是對于人此在生存的變形化觀照,這種逸出現(xiàn)實邏輯的觀照并不指向問題的最終解答,而是以喚起對于存在的注意為目的。在劉震云以《一地雞毛》為代表的新寫實小說中,許多人物在嚴(yán)肅、破碎的現(xiàn)實中沒有波瀾地消磨生命,人的存在被籠罩于意義缺失的平面的物理牢籠中,除去袒露人及其生活、歷史、社會的殘酷本相,作家似乎對精神崇高、靈魂救贖等范疇缺乏興趣。但在《一日三秋》中,人物對前世、今生、來世間因果的執(zhí)著,至少證明了作家對筆下人物的精神性存在有了呈現(xiàn)與解釋的欲望。無論是將《白蛇傳》中角色關(guān)系與現(xiàn)實人物關(guān)系的倒錯作為諸多人物悲劇宿命的源起,還是將明亮與馬小萌今生的相守解釋為前世恩怨的延續(xù),抑或是老董基于來世光明的愿望而有的種種善舉,都是作家對人的種種生存予以“同情之理解”的嘗試性解釋,這使得本來仍然破碎、冷靜的故事在敘事行進(jìn)中逐漸擁有了難得的溫情。以此觀之,《一日三秋》或會成為劉震云創(chuàng)作譜系中的某個關(guān)鍵轉(zhuǎn)折,如果這種對存在進(jìn)行解釋的努力能在今后的創(chuàng)作中得到延續(xù)的話。
當(dāng)然,劉震云已經(jīng)明言,穿越生死的神鬼敘事只是為了將六叔的畫鋪陳為一個完整故事,這些突破了作者預(yù)設(shè)框架的意義或許只是“作為內(nèi)容的形式”在作家創(chuàng)作中潛在進(jìn)行的自我意義生成,但這種“偶然性”無疑也表征著前述重要轉(zhuǎn)折的可能到來,對此我們可以在劉震云將來的創(chuàng)作中進(jìn)行驗證。同時也須指出,作家一貫的寫實風(fēng)格與魔幻現(xiàn)實手法的捍格,確實造成了這部小說諸章節(jié)風(fēng)格、氛圍的不一致,一些頗具戲劇性的線索(如兩個孫二貨)之未能充分打通,也給小說留下了不小的遺憾。
@崔濤:“一日三秋”的宿命
李楊就《白蛇傳》隱喻指出的人生困境主題與趙志軍就生存思考提及的人物悲劇宿命,我認(rèn)為都可以在“一日三秋”的表達(dá)中獲取線索。雖然小說已經(jīng)指明,這既是“一日不見,如隔三秋的意思,這在人和人之間,是一句頂一萬句的話”,也更是“人和地方的關(guān)系,在這里生活一天,勝過在別處生活三年”。但吊詭的是,這種對人以及對地的親切感在小說中卻被無情地拆解了,以致“一日三秋”本身成為一個反諷的“笑話”,進(jìn)而呈現(xiàn)出籠罩在各類人物身上的無力掙脫的宿命感。
這首先體現(xiàn)在花二娘與延津及延津人的關(guān)系上。三千年來,延津人都知道花二郎已死于延津,但無人對花二娘坦承,使其在等待中困于延津并望(忘)延津之外。延津人為之付出的代價則是世世代代都要在睡前準(zhǔn)備笑話,以備花二娘于夢中索取,否則會有生命之虞。這宿命般的“三秋一日”,于花二娘而言是“一日三秋苦日短”,對延津人來講卻是“一日三秋苦日長”。其次,“白蛇”櫻桃的命運也是如此,戲里戲外終究受厄于“法海”陳長杰之手,甚至死后也受困于“笑話”不得輪回,困頓解脫全不由己。除與明亮短暫的共處外,“一日三秋”的親切感對櫻桃來說幾乎不存在,戲中的宿命與延津人的苦途成為她人鬼一生的羈困。
似乎所有突破或調(diào)和宿命的希望都匯聚于明亮身上。但即使定居西安,他也未能逃脫花二娘夢中索取笑話的苦運。他的一生,仍在隱隱地延續(xù)著父母一代的《白蛇傳》故事繼續(xù)演繹,幼年拯救櫻桃暗合“許仕林救母”,成人后與長舌頭的蛇妻馬小萌的結(jié)合然后背井離鄉(xiāng),成功后重返延津面對的卻是物是人非故人凋零。他在延津、武漢和西安三地的空間轉(zhuǎn)圜中盡量調(diào)適以圖沖破宿命的牢籠,但終究沒能逃出延津人的困局,“故鄉(xiāng)一日勝過他鄉(xiāng)三秋”的親切感只能在夢中編織。對記憶有選擇地過濾與篩選不過是一種徒勞的自欺,本意味著親切感的“一日三秋”最終在諸般希望破滅后呈現(xiàn)出一種荒誕的反諷意味。
延津人的“一日三秋”承載著“神界鬼界、戲里戲外、歷史當(dāng)下、夢里夢外和故鄉(xiāng)他鄉(xiāng)”的多種宿命與困境,展露的正是人對命運的無奈和屈從。作者剝開日常生活“一地雞毛”的表象,將神鬼世界融入了跌宕起伏的人途,但故事背后仍是那波瀾不驚的一江宿命池水,仍是那無形之力不動聲色地對生活與人性的擠壓。
@丁永杰:“幽默”背后的關(guān)懷
劉震云對“幽默”有自己獨到的見解。2020年底,劉震云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談到“幽默”,認(rèn)為真正的幽默是不幽默的,應(yīng)該關(guān)注笑話背后的道理、道理背后的道理。新作《一日三秋》便是對“笑話”“幽默”本質(zhì)的進(jìn)一步思考和延伸。
不妨看一下《前言》中的幾個鏡頭:“見他畫中,月光之下,一個俊美的少女笑得前仰后合”;“又見一幅畫中,畫著一群男女的人頭,聚在一起,張著大嘴在笑”;“其中一只盤子里,就剩一個魚頭,魚頭在笑”,甚至“畫中的閻羅也在笑”。花二娘在延津人夢中尋找笑話這條線索貫穿整部小說,但不難發(fā)現(xiàn),全書幾乎沒有一個能讓花二娘真正滿意的笑話,連最會講笑話的人也是如此。如果說《一句頂一萬句》《我不是潘金蓮》《吃瓜時代的兒女們》等作品中確實有許多令讀者忍俊不禁的片段,《一日三秋》則幾乎沒有什么能令讀者發(fā)笑的情節(jié)。三千多年來,花二娘找尋“好笑”的笑話而不得,明亮為求生講述的妻子在北京的“事情”,這藏在內(nèi)心深處難以言說的痛楚,卻成功逗笑了花二娘,其間的分裂和悖論令讀者心頭顫動。
《一日三秋》交代了兩代人的生存軌跡。上一代人進(jìn)入讀者視野沒多久,便籠罩在了死氣沉沉的生活中。陳長杰和櫻桃在縣豫劇團(tuán)演戲的時候風(fēng)光無限,劇團(tuán)解散后就陷入一地雞毛的生活,以至櫻桃因為一把韭菜上吊自殺;李延生在婚后不久就變得沉默不語;吳大嘴整天不茍言笑,最終被“心事”壓死……這一代人的一生大多被“笑話”捉弄:老來不得志的陳長杰自認(rèn)“把自己活成了笑話”,李延生也同樣感嘆“我算把自己活成了笑話”。劉震云將“笑話重返于延津”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憂郁少年明亮早早輟學(xué)去“天蓬元帥”飯館學(xué)習(xí)廚藝,卻意外地為后來的身份轉(zhuǎn)變創(chuàng)造了條件。馬小萌靠自己不光彩的“事情”攢下了10萬元錢,卻為自己和明亮換取了生活轉(zhuǎn)機。上一代人櫻桃、吳大嘴未能躲過的來自花二娘的笑話考驗,也被明亮看似巧妙、實則充滿“矛盾性”的幽默笑話消解掉了。想必,這就是作者在小說中試圖給我們尋找面對人生的態(tài)度與方法。
這讓我不由想起沙夫茨伯里關(guān)于“幽默”的論述:幽默是對真理的最佳檢驗方式,也是防范狂熱、偽善與教條頑固(bigotry)的最佳手段。在他看來,經(jīng)不住打趣的主題必然可疑,假正經(jīng)經(jīng)受不住一個笑話的考驗。“幽默”不僅僅是單純博人一笑的“笑話”,它往往和“真理”有著一種難以言說的曖昧關(guān)系。劉震云擅長在這部小說中著力營造一種“幽默感”,但與其說作者在通過兩代人的故事幫我們追尋“失去的幽默”,不如說他是在強調(diào)每個“幽默”的小人物都應(yīng)當(dāng)被予以關(guān)懷。
(本文發(fā)于中國作家網(wǎng)與《文藝報》合辦“文學(xué)觀瀾”專刊2022年2月21日第8版)
- 塵界 魔界 天界——評《一日三秋》[2022-02-18]
- 劉震云:寫長篇是一場“不勻速的長跑”[2022-02-07]
- “滿紙荒唐言”與“一本正經(jīng)話”[2022-01-09]
- “笑話”點透人生[2022-01-02]
- 從“走來”之處“走出”:黃開發(fā)散文的行旅體驗與記憶書寫[2021-11-24]
- 滿紙荒唐言,一把含笑淚——劉震云《一日三秋》讀札[2021-11-18]
- “噴空”里外觀——簡論劉震云《一日三秋》[2021-11-15]
- 一笛涼月難思量——《一日三秋》讀記[2021-1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