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歌:新文學中“最現代”的狂飆社作家
“高氏三杰”中的高歌
“五四”新文學乃至整個現代文學30年,小說特別是短篇小說,從傳統向現代轉型,從幼稚到成熟到強大,走過了一條艱難探索、銳意創新的道路。山西作家對短篇小說文體情有獨鐘,在這一文體的演變、發展中,作出了重要貢獻。中國現代短篇小說的建樹、成就,較充分地反映在兩套浩大的、權威的叢書中,一是茅盾、魯迅等編選的《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小說一二三集)、二是巴金、康濯等作序的《中國新文學大系》(1927—1937、1937—1949短篇小說卷)。山西作家有8人、11篇作品入選。分別是:
李健吾《終條山的傳說》《死的影子》;
高歌《生的旋律》;
青苗《馬泊頭》;
趙樹理《小二黑結婚》《福貴》《傳家寶》;
西戎《喜事》;
束為《紅契》;
西虹《英雄的父親》;
馬烽《金寶娘》。
如上作家作品,絕大部分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唯有高歌是既不知其名也不知其作的。
高歌是高長虹的胞弟、“狂飆社”的重要作家。高歌是中國新文學中“最現代”的小說家。
在山西盂縣以至陽泉市,流傳著“高氏三杰”的傳奇。指的是盂縣清城鎮西溝村一個耕讀之家的“弟兄仨”:高長虹、高歌、高遠征。這是一個書香家庭。祖父是晚清秀才,執教為生。父親是副榜舉人,曾先后在天津、河北的兩縣任承審員和代理知事。祖上家業殷實,后來日漸破落。高長虹1898年出生。1914年以優異成績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學”,同年遵父母之命與鄰村王巧弟結婚,高長虹稱自己的婚姻是弟兄悲劇的“第二幕”,后因參加反對閻錫山的政治活動而與校方沖突退學回村。1924年至1929年,他先后在太原、北京、上海,與高沐鴻、段復生、高歌等,發起并組織“狂飆運動”,出版刊物、書籍,開展演劇活動,并作為魯迅倡導組織的莽原社重要成員,傾力協助魯迅編輯《莽原》月刊。但后來高魯發生沖突,二人分道揚鑣。1930至1937年,為了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和現代科學、經濟學,他遠涉重洋到日本、德國、法國、瑞士等國。抗戰爆發后的1938年,他急切地回到中國,在武漢進入全國“文協”,又到重慶,投身抗戰文化宣傳運動。1941年他徒步奔赴延安,受到革命根據地高規格歡迎,但他自由知識分子的思想、行為、創作,與根據地格格不入,甚至與毛澤東發生沖突。1945年之后,他流落哈爾濱、沈陽,被東北局宣傳部當精神病患者養起來,1954年去世,享年56歲。高遠征,高長虹三弟,1907年出生,自小聰慧好學,1923至1927年就讀于太原進山中學。這是一所深受新文化、新文學影響的學校,也是一所馬克思主義較早傳播的學校。1924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并擔任學校黨支部宣傳委員,在組織、宣傳工作中很有成績。1926年,由家里包辦與清城鎮農家姑娘潘金妮結婚,是高家兄弟婚姻悲劇的“第三幕”。同年,他與學校進步同學,組織文學社團“石燃社”,創辦《石燃》副刊,共出版六七期,發表大量文學作品,可惜均已散失。他從小喜愛文學,才思敏捷,頗受高長虹偏愛,在《狂飆》周刊發表小說二篇。《慈母》寫“我”回家探親,母親對三個兒子的掛念,情真意切,高長虹讀后“眼淚奪眶而出”。《生活》寫一所學校清晨的日常情景,一位青年教師對陳腐的教育規訓的思索與反叛,采用了意識流手法。1927年他與幾位同學赴武漢參加北伐,先入賀龍的學生團,再入葉挺部隊,參加了南昌起義,后在挺進廣東途中被國民黨軍隊包圍而英勇犧牲,年僅21歲。


高歌、高遠征、高長虹
高歌排行第二,1900年出生。他是“五四”新文化、新文學哺育成長的文學青年。從小深受兄長高長虹的影響,喜歡讀書、熱愛文學。1913年13歲時,由家庭做主同本縣胡家溝15歲的村姑胡巧娘結婚,是他們兄弟婚姻悲劇的“第一幕”。他很是不滿,但也無可奈何,妻子為他生了兩個兒子。1917至1922年,他就讀于太原“山西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其間正逢“五四”運動,他與一批進步青年研讀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茅盾等的著作,“議論國是,研究新文學”。1922年畢業后,回到盂縣在縣一高任國文教師,他在課堂上講授新文學作家作品,節假日在學校操場上搭臺唱戲,演出他改編和創作的進步戲曲,頗受鄉親們歡迎,但也被舊派校長所反對、所壓制。他是狂飆運動的骨干、功臣。1924年他跟高長虹在太原創立了狂飆社,隨后高長虹赴北京開展狂飆運動,他緊跟到北京,在魯迅任教的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讀書。他一邊協助高長虹開展工作,一邊開始了小說創作。在高長虹的引薦下,他結識了魯迅,開始交往,其間拜訪魯迅14次,寫信9封,魯迅回復2封,贈書一次。還結識了張稼夫、呂蘊儒等文化人士。1926年他受高長虹之托,接編《弦上》周刊,一直編到停刊。同年秋赴上海,協助高長虹編輯上海《狂飆》周刊和“狂飆叢書”。1928年他從杭州回到上海,與高長虹重振狂飆,成立出版部,出版書籍,創辦機關刊物《狂飆運動》,擔任《世界》周刊編輯,狂飆運動搞得有聲有色。他曾經兩度離開狂飆社,一次是1925年春,北京《狂飆》周刊停刊,高歌與向培良、呂蘊儒赴河南開封創辦《豫報》副刊;另一次是1927年,應潘漢年之邀,與向培良一同赴武漢編輯《革命軍日報》副刊《革命青年》。時間都不長,最后又回到高長虹身邊、狂飆社大本營。1930年,高長虹離國赴日,高歌在上海處理善后事宜,并參加革命活動,加入中國共產黨。狂飆社隨之解體星散。他追求革命最終卻成為一介平民。1930年他因參加革命而被國民黨逮捕,關入蘇州“反省院”,出獄后失掉黨的組織關系。抗戰開始后,他在重慶隱姓埋名,在一些私營小企業,靠自食其力生活。建國后依然滯留重慶,在市勞動局、計委等部門做普通干部,孤身一人,不再成家,于“文革”前后去世,享年60余歲。
世事如夢。天妒英才。“高氏三杰”都是人才、天才,都選擇了文學,但卻走了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他們在短暫的人生中,綻放出燦爛的生命之花。
在文學創作上,高長虹是全才,各文學文體皆擅。而高歌專事小說,短、中、長篇小說。雖也有詩歌、散文、評論,但很少。他的創作集中在1924年到1930年6年間,共發表短篇小說43篇,中篇小說4部,長篇小說1部,翻譯作品兩部。建國前集輯出版的有:《清晨起來》《高老師》《壓榨出來的聲音》《我的日記》《野獸樣的人》《加里的情書》《情書四十萬字》,翻譯作品:《奧特賽》《依里亞特》。1993年北岳文藝出版社出版《高歌作品集》(上、下)。共10種,實算130多萬字。1984年上海文藝出版社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集一》(1927—1937),收入《生的旋律》;2015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山西新文學大系》(第六卷),收入《生的旋律》《生的一瞥》《佚秋老人》。
高歌博采現代,銳意求新,成果豐碩,無疑是“五四”新文學中最前衛的現代派作家,但他在當時乃至后世,讀者甚少,更無專門的評論文章。就筆者所見,只有狂飆社專家董大中的《高歌創作論》,文中說:“高歌這些作品的主要特色是看不懂。1925年高長虹在北京版《狂飆》和其他報刊發表了第一個豐收季的一系列作品后,魯迅在給許廣平信中說,高的作品‘晦澀難解’。跟高長虹比起來,高歌這些作品,才真是‘晦澀難解’。高歌這種風格的作品,即使在狂飆同仁中也得不到好評。藉雨農在致高沐鴻并轉長虹信中說:‘高歌的作品,我不能懂,尤其是《清晨起來》。總之,我是不高興這類作品的。’高歌這些小說在五四以來的小說創作歷史上,直到新時期,都極少見。幾乎沒有人寫同樣的小說。它是一個獨特的品種,是一種‘狂叛品’。”[1] 高歌小說為什么會出現“看不懂”“無反響”的結果呢?筆者以為原因有三個方面。一是太現代。作家效仿西方現代主義方法與手法,過分激進,走得比同時代的眾多現代派作家更遠,超越了讀者的審美認知和能力。二是不成熟。當時的高歌只有二十多歲,文學修養和訓練還不夠,對現代主義文學的接受生吞活剝,還沒有實力轉化成純熟的藝術。三是粗淺化。狂飆社辦的是“同人”刊物,他們是為刊物而寫作、為生存而寫作。環境惡劣、時間緊迫,很難靜心、從容寫作,往往是草率上陣、倉促成文,甚至出現粗制濫造的情況,致使一些很好的題材、構思,也難以打造出精湛、優美的篇章。這是需要我們注意和理解的。
“五四”新文學時代,各種各樣的文學社團蜂擁而出,每一種都有自己的思想理論和文學主張。譬如鄉土小說派是以啟蒙現實主義為宗旨兼容現代主義和浪漫主義的;譬如創造社是以浪漫主義為追求汲納現代主義的;譬如新感覺派是以弗洛伊德學說為基礎并采用意識流方法的。那么狂飆社就是取法德國“狂飆突進運動”的思想與精神,主張文學表現“個性”“自由”,倡導“超人哲學”“返回自然”。袁可嘉指出:“‘五四’后期出現的狂飆社,其得名更與德國表現主義同名刊物有直接的聯系。向培良的戲劇集《沉悶的戲劇》顯示出無政府主義者的奮斗和反抗,其中之一《生的留戀和死的誘惑》中的勇士一病一死成了主人公的反抗方式。《晴嫩》的表現主義色彩更濃,簡直是‘性解放’的形象化。像表現主義者一樣,向培良認為戲劇應該是‘人類的心靈深處和靈魂底隱微的藝術’。……有的學表現主義的手法,用人物作為一種品質的代表,如高長虹的《一個神秘的悲劇》的人物就以A、B、C、D來代表,情節是一條抽象的線索——由劇中人在不同時期的愿望、情緒和意念組接起來。”[2] 這就是說,狂飆社的文學宗旨是以表現主義為主的。1927年高歌在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他的第一本小說集《清晨起來》,他在封底的“廣告”中稱:“世界的文藝潮流,已脫去陳腐羅曼主義與寫實主義,漸漸從象征主義走到表現主義了。我國的文藝運動,尚不出于羅曼與寫實兩道。即近日轟傳的唯美主義,也不過羅曼主義之一支流。‘狂飆’的文藝態度,本在打破一切流派,而直造藝術之堂奧。其所辟途徑,且有侵越象征、表現之勢。”[3]這段話并沒有被學界廣泛關注,但卻恰好表現了狂飆社作家的文學思想與創作觀念,他們不滿足于現實主義、浪漫主義,而要打破陳腐的創作思潮,開辟表現主義、象征主義等更現代的創作道路。

《高歌作品集》(上下),北岳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
以現實的社會人生為“基點”
“五四”新文學,是中國傳統文學向現代文學的一場偉大轉型。那些學養豐厚、高瞻遠矚的思想家、文學家,如陳獨秀、胡適、魯迅、茅盾等,在譯介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的同時及隨后,也引進了更復雜、更新穎的現代主義。其實在那些杰出作家那里,雖有自己奉行的文學思想與創作方法,但往往是兼容并蓄的。現實主義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現代主義也綻放出璀璨的藝術之花;但后者常常因“水土不服”而被質疑、批評。狂飆社作家如高長虹、高沐鴻、高歌等,顯然是尊崇現代主義的,現代主義的多種流派、方法,在他們那里得到了充分發揮。但他們并沒有割斷現實主義或者說也離不開現實主義,特別是在寫故鄉、家庭、親人的作品,寫自己在城市的生活、經歷的作品中,他們會不由自主采用現實主義寫作方法。現實的社會人生成為他們創作的“基點”,他們由此出發,在觀照城市、知識分子時,就有了一個堅實的基礎或坐標。他們像當時許多作家那樣,用小說書寫人生、自我,因此這些寫實小說,就有了自敘傳特征。然而,由于他們對現實主義的輕視、偏見,使他們缺乏對現實主義的研究、訓練,導致他們的這類創作難以精深、純熟。
高歌奔赴北京時,還是一個24歲的青年,此后又去上海打拼,去武漢謀生,尚不到30歲。從偏遠的山區小縣,到大都市闖蕩,與花花世界的隔膜,對故鄉親人的想念,不時涌上筆端。《破碎的生命》描寫的是一幅溫暖、感傷的鄉村圖畫。“我”是一位知識青年,內心里充滿了“空虛”“茫然”。站在自家的打谷場邊,看到衣服破爛的老長工,因被東家開除而悲痛,“我”同情他讓他再來干活,他誠惶誠恐,感激涕零。一伙女人在羊圈旁剝玉米皮,其中有“我”喜歡的女子,她“水晶般”的眼睛,讓“我”熱血奔涌。幾十只羊擠來擠去,羊倌和他的兒子在那里忙碌著,讓“我”浮想聯翩。作家在樸素、散漫的描繪中,表現了一位進步青年對底層民眾的關切,對鄉村姑娘的深情,對故鄉、家庭的依戀,對自我命運的思索。是一篇富有詩意的現實主義小說。在《潑辣的女人》里,作家寫了一位敢于反抗、罵人的中年媳婦的形象;在《欲擒之死的報告》中,寫了十六七歲的欲擒的突然而亡。都反映了作家對底層小人物的同情、憐憫。家里的親人,更是高歌不斷回憶、描寫的對象。寫父親的有兩篇。《父親的像》寫“我”、哥哥、父親三人,在北京一個公園休憩、游園。美景之中,涼篷底下,父子三人飲茶、聊天,說些“精力可貴、時間可貴和將來可貴的話”。公園小路上,父子三人相扶相攙,緩緩漫步。后來,父親一人站在小山頂,默默佇立,在兩個兒子的眼里:如“化石”一樣“模糊”地“壁立”著。他們的父親中過舉人、當過縣官,他期待兩個兒子走“學而優則仕”的道路,但卻選擇了一條渺茫的文學、革命的路。此時他們一定有很多話說,又難以開口、談攏。在這一幅靜默的圖畫中,父親的期待、教誨,兒子們的愧疚、主見,可謂此時無聲勝有聲。《父親病了》用詩一樣的語言,描寫“我”得知父親生病后的焦急、思念之情。寫母親的有三篇。《襯衣》寫“我”在外漂泊,得空回家,母親和弟妹們的高興,都爭著要把剛買的每人一件的襯衣讓給“我”,表現了一種母愛、親情的溫暖。《母親的心血》用詩的語言,書寫了母親為家庭、為兒女付出的巨大心血。《走回了家里》寫母親病逝,“我”回家奔喪,家里人與人關系的微妙變化,“我”的悲痛欲絕和內心的空洞。所有這些寫父親、寫母親的篇章,都具有濃重的真實感、紀實性,是地道的現實主義作品。
高歌把自己在城市中的一些經歷、生活,用日記的形式寫進了小說,同樣具有現實主義特征。1925年春,《狂飆》周刊因種種原因停刊,在魯迅的支持下,高歌與向培良、呂蘊儒赴河南開封創辦《豫報》副刊。副刊在5月4日面世,到這年秋天,因政局變幻而停辦,高歌又回到北京。小說《五天》記敘了這段經歷中最開始的情景:“我”與灰衣服朋友乘坐火車從北京到鄭州又到洛陽,城市中的混亂、緊張局勢;土匪一般的兵士入室搶劫,把“我”和二弟關進監獄,灰衣服朋友設法保釋了我們。逼真地寫出了當時河南的社會情景。小說中寫到一個細節:在車站“我”向賣食品的孩子買了兩碗元宵,沒來得及付錢車開了,孩子追車大罵,“我”覺得像搶了人一樣內疚。高歌在給魯迅的信中寫了此事,魯迅即刻回信說:“‘以為自己搶人是好的,搶我就有點不樂意’,你以為這是變壞了的性質么?我想這是不好不壞,平平常常。所以你終于還不能證明自己是壞人。看看許多中國人罷,反對搶人,說自己愿意施舍;我們也毫不見他去搶,而他家里有許許多多別人的東西。”[4] 這真是一件有意義的小事。青年作家高歌耿耿于懷的事情,魯迅那里卻看得云淡風輕。魯迅從孩子的角度又轉向高歌的角度。買東西不付錢形同搶人,但你并非故意,因此是平平常常的事情。而那些貪官、富豪,并無搶人,家里卻全是他人的東西、財富。這又怎樣解釋?想來高歌讀了魯迅的回信,一下子就豁然開朗,如釋重負了。在這一來一往的通信中,我們看到了高歌的單純、善良,魯迅的慈祥、善教。中篇小說《我的日記》,寫的是“我”在杭州的一段漂泊經歷:城市風景區的游覽,與朋友喝酒、聊天,對美麗、聰慧女子的愛戀與想象,噩夢中軍士破門而入的開槍,對狂飆運動的反思與期望…… 零零碎碎,真是一本生活的流水賬,缺乏應有的藝術提煉與構思,但也呈現了作家當時的一種生存與精神情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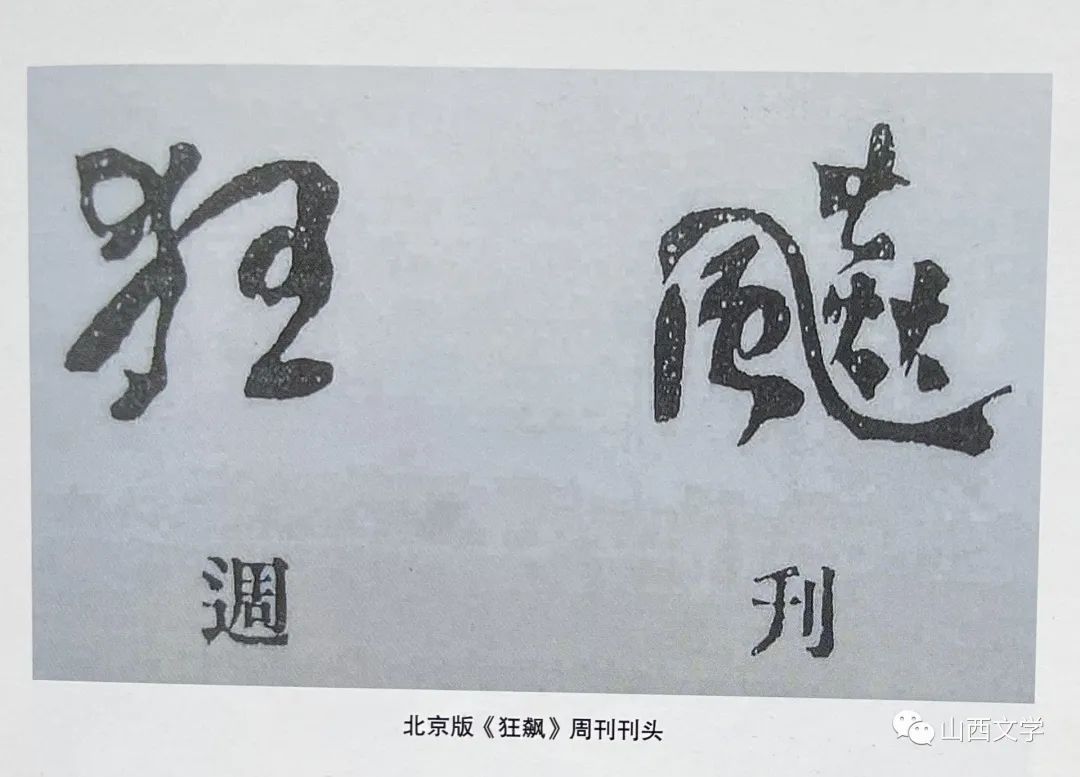
《狂飆周刊》刊頭
董大中在文章中說:讀作家后期的幾部小說,“我有一個感覺:作者在對生活的描寫上,走了一條由遠及近,由虛到實,由幻覺到直感,一步一步把我們引向更加親切、更加真實的道路。”[5] 這里指的是高歌1928—1930年創作的《加里的情書》和《情書四十萬字》,前部創作于1928年9月到12月,后部創作于1928年1月到1930年5月。兩部小說內容有所不同,但又有很多重疊的地方,前部是包含在后部之中的,可以當作一部長篇小說。1927年,高歌到杭州修養、寫作,結識一位安徽女子,女子已有丈夫、兒子,但婚姻不如意,跟父母親等住在一起。高歌在西湖與她相遇相戀,沉浸在一種愛情的漩渦中。狂飆運動的受挫,人生前途的未卜,使他在愛情中得到了某種慰藉。整部小說由作者“加里”寫給情人“利那”的數百封信組成。寫“我”對利那的摯愛、關心、尊敬;寫“我”對未來兩人生活、工作的籌劃、安排;寫“我”中途回上海狂飆社的文學活動、編輯工作;寫“我”對兄長高長虹的牽掛、支持;寫“我”對國家局勢、命運的分析、認識…… 但大部篇幅是書寫“我”與情人的交往、相愛,“我”對純真愛情的抒發、歌頌,充滿了“我的親”“我的愛”這樣的詞句。小說表現了一個進步青年對自由愛情的追求,對知性女子的尊重,有著濃郁的“五四”文學韻味。在現實主義的描寫上,又借鑒了抒情、議論、意識流等手法,顯示了作家對現實主義的開放、變革。但是,在中國革命走向復雜、艱難的時代背景下,高歌閉門造車寫這樣一部小資“情書”,顯得不合時宜。同時,由于高歌對現實主義小說藝術表現的陌生,使他這部小說乃至不少寫實小說,顯示出雜亂、膚淺的傾向。

上海《東方雜志》
表現主義、象征主義的創作傾向
袁可嘉在《歐美現代派文學概論》中說:“在現代主義的諸多派別中,表現主義文學對‘五四’新文學的影響是較為顯著的。” [6]魯迅、郭沫若、茅盾等,不僅評介了這些現代主義思潮,而且在創作實踐中借鑒了一些現代主義創作方法。高長虹是狂飆社中的批評家,不僅寫詩歌、散文、小說,也寫文學評論。他廣泛涉獵西方現代文學理論,對表現主義、象征主義、弗洛伊德學說以及意識流等都作過評述,同時運用在自己的創作中,這對高沐鴻、高歌等人的創作有很大影響。有論者認為高歌小說很像高長虹小說,正是他吸納了相同的現代表現方法的自然結果。高歌的小說分兩個時期,前一個是1924—1926年,后一個時期是1926—1929年,他始終在探索現代主義寫法,但后一時期顯然比前一時期成熟了許多,出現了小說精品。當然,那種現實主義小說乃至現實與現代兼容的小說,他也在堅持寫作。運用什么樣的創作方法,有時是作家的主觀選擇,但更多的時候是題材自身的選擇。
高歌是1924年進入北京,與高長虹創辦《狂飆》周刊時開始創作的,大部分作品發表在《狂飆》周刊和《莽原》半月刊上。1927年由上海泰東圖書局集輯出版小說集《清晨起來》。《愛之沫》是作家的處女作,寫“我”和朋友小黑子,在如黑夜般的白天奔跑,闖進一個小屋子,見到一位老婦人和一個少女,少女正是“我”要找的人,而老婦人送“我”一件小巧的禮物。在這一幅朦朧、多彩、變幻的圖畫中,用“我”的行動,象征了一個知識青年對人生、命運特別是愛情的尋找。而變幻的天象、神秘的老婦人和少女,“我”與少女的一見如故,無不是作家的主觀幻覺、想象、理想,典型的表現主義藝術手法。《愛的報酬》同樣以“我”為主人公,寫房屋像遭受地震一樣淪陷到地層中,“我”救援了一位死去的年輕女子,用“我”的愛喚醒了她,但她又回到地底的房間,把“我”拒之墻外。“我”是一位覺醒的知識青年,年輕女子是困在底層社會的普通民眾,她雖生而死,“我”的救援使她再生,但她依然被困苦海,“我”與她之間隔著高大的壁障。很顯然,這是一個象征情節,象征了底層民眾特別是婦女的命運,象征了知識分子與民眾的關系。房屋的塌陷、女子的死而復生,又完全是作家主觀幻覺、想象、夸張的情景,顯示出表現主義的強大力量。《解剖》是一篇精短而奇特的小說。“我”變成了一個人體解剖師,但用的是筆,一點一點地切開人的頭顱、眼睛、耳朵等。在切開人的大腦時,竟發現人的大腦下層刻著“神”與“人”兩個字。細細想來,悟到這依然是一種象征,解剖師工作象征了作家的創作,作家就是要解剖、揭示人的生命肌理、精神世界。而人的本質是“神”與“人”的交織、博弈、統一。解剖師的行為、過程的描寫,又用了荒誕手法。不管是寫知識分子對人生、愛情的尋找,還是寫知識分子與民眾的關系,抑或寫作家對人的解剖、認識,都表現的是“五四”新文學,知識分子對社會、人生的啟蒙、批判的重大主題。但有一部分小說,由于作家對所寫題材的隔膜、對表現方法的不精,造成了晦澀難解的現象,混淆了散文、詩歌與小說之間應有的界限。如《愛之傭》《看小孩的時候》《活尸》《蒼蠅的世界》等。
“五四”新文學伊始,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引進、借鑒,幾乎是全盤照搬。高歌對各種現代表現方法,更是來者不拒。譬如荒誕手法。《人鳥》中描寫了一只像人的大鳥,又刻畫了一只麻雀變成會飛的魔鬼,在空中搏斗,情節極為荒誕。譬如意識流。《月夜》寫一位業余寫作者,躺在出租房的小床上,面對生存的困難,前途的黯淡,他的悲傷、孤獨、期望的一系列意識和潛意識活動,寫得細膩而深切。譬如對人的“力比多”的表現,當時借鑒弗洛伊德學說,表現人的性意識是一種風潮。高歌在短、中、長篇小說里,都寫到了主人公的性本能、潛意識。如《人和人的開幕》,用自由詩的語言,散文的結構,刻畫了兩個年輕人在寬大的床上,從擁抱到愛撫到做愛的畫面,汪洋恣肆地抒發了自由之愛、青春之美、生命之美。但作家這些寫性的文字,并無肉欲之感,而是迸發出精神的超越性。譬如組合方法。《征途》寫“我”的“英雄夢”,在夢中做了統兵元帥,招兵買馬、攻城略地。想象大膽、奇特、夸張,既有荒誕手法,又有意識流技巧,顯示了作家想象的奇異,才氣的豐沛,手法的多樣。但這一類小說,有的存在著情節怪誕、瑣碎,意蘊模糊、晦澀,語言冗雜、粗糙的現象,給讀者的閱讀、理解,造成諸多障礙。
狂飆社研究專家言行說:1928年“狂飆運動出現了有史以來一個高潮期。……這時期,高歌的創作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7]此時的高歌正處在創作的噴發期、成熟期。短、中、長篇小說并舉,現代主義、現實主義共進。特別是在現代主義創作上,逐漸變得開闊、豐富、深沉起來。后來出版的重要文學選本,選入的都是他這一時期的作品。《生的一瞥》與前一時期的《愛之沫》,都表現的是青年“尋路”的主題,但顯然豐厚了許多。“我”從酒店出來,帶著醉意前行,耳邊響著低聲的對話:“哪里去呀?”“向前走!”“我”看到兩個年幼的孩子向前走。看到農民在河邊辛勤的勞作。“我”被淹沒在河里,有人把“我”救起。在一個房子里看到一個赤身女孩,她拉著“我”說:“我來救你”。小說用這樣的情景,象征“后五四”時代知識青年的艱難“尋路”,表現“遺棄了舊的路而走新的路”,那種迷惘、恐慌、無助的精神狀態。其中有幻覺、有夢境、有意識流,都運用了表現主義手法。而那個赤身女孩,代表了一種自由、純真的愛情。《佚秋老人》塑造的則是一位老人的形象。高高的石橋,橋下是河水魚兒,橋畔是綠地鮮花。一位盲眼老人,以橋為家,在上面靜坐、吟唱、舞蹈。這是一幅多么寧靜、優美的圖畫。作家運用了浪漫主義手法。依戀老人的是一個年幼的孩子,陪他說話、聽他講故事,充滿天倫之樂,但孩子總是被媽媽生硬地叫走。這就是世俗的人情冷暖。出現在老人身邊的,還有一位身份不凡穿軍裝的女人,從朦朧簡略的敘述與交代中,可以猜測他們曾經是夫妻,盲眼老人有著光輝的歷史和很高的地位,但現在他愿意過這樣的生活,不愿跟女人回到現實中。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是獨特的、高峻的,但思想意蘊是朦朧的、深遠的。佚秋老人象征了一種孤獨、沉靜、超然的人生境界。作家用抒情、空白、聯想、想象等表現主義方法,創造了一幅老人與世界的永恒圖畫。《生的旋律》由“我”的意識流為“隧道”,展示了“我”的人生經歷、精神變遷。“我”與父親、母親、哥哥的關系;家人與長工對“我”的打壓;“我”在昏暗的上海弄堂的行走、探尋,“在灰白色的世界中想象著我的光明”;“我”無辜地被兵士抓捕,又被押到法庭審判,而審判者中竟有“我”的父親。看來作家的內心深處,是把父親當作敵對的舊勢力的;在法庭上“我”為自己辯護:“我沒有罪”“戀愛神圣”“我是人類的主人”,體現了一個青年的革命理想和堅貞性格。“我”在黑暗的監牢中見到了如“小鹿”般的女朋友,我們驚喜、擁吻,商議著如何越獄、逃走。作者堅信黑暗終將過去,革命總會成功。愛情永存,前途光明。作家雖然寫的是“我”的人生與精神,但又濃縮、象征了無數革命青年的人生與精神。作品以意識流方法為主,又自如運用了幻覺、想象、抒情等多種表現方式,使作品成為作家的一篇代表作。
“后五四”時期的現代主義創作思想與方法,經歷了一個引進、實踐、反思的曲折歷程。一方面它使中國的現代小說,變得豐富而強大,另一方面又暴露出諸多自身的缺陷。狂飆社作家高歌、高長虹等,在推進中國小說的現代性方面,作出了可貴貢獻。但他們對現代主義思想與方法的生搬硬套,對這些創作方法的不加改造,草率運用,又使他們的創作固守模式,難有突破。曲高和寡,應者寥寥。1930年代之后,他們所以中斷了小說創作,一方面是由于左翼文學、革命文學的沖擊,另一方面則是現代主義創作方法很難適應時代與讀者的需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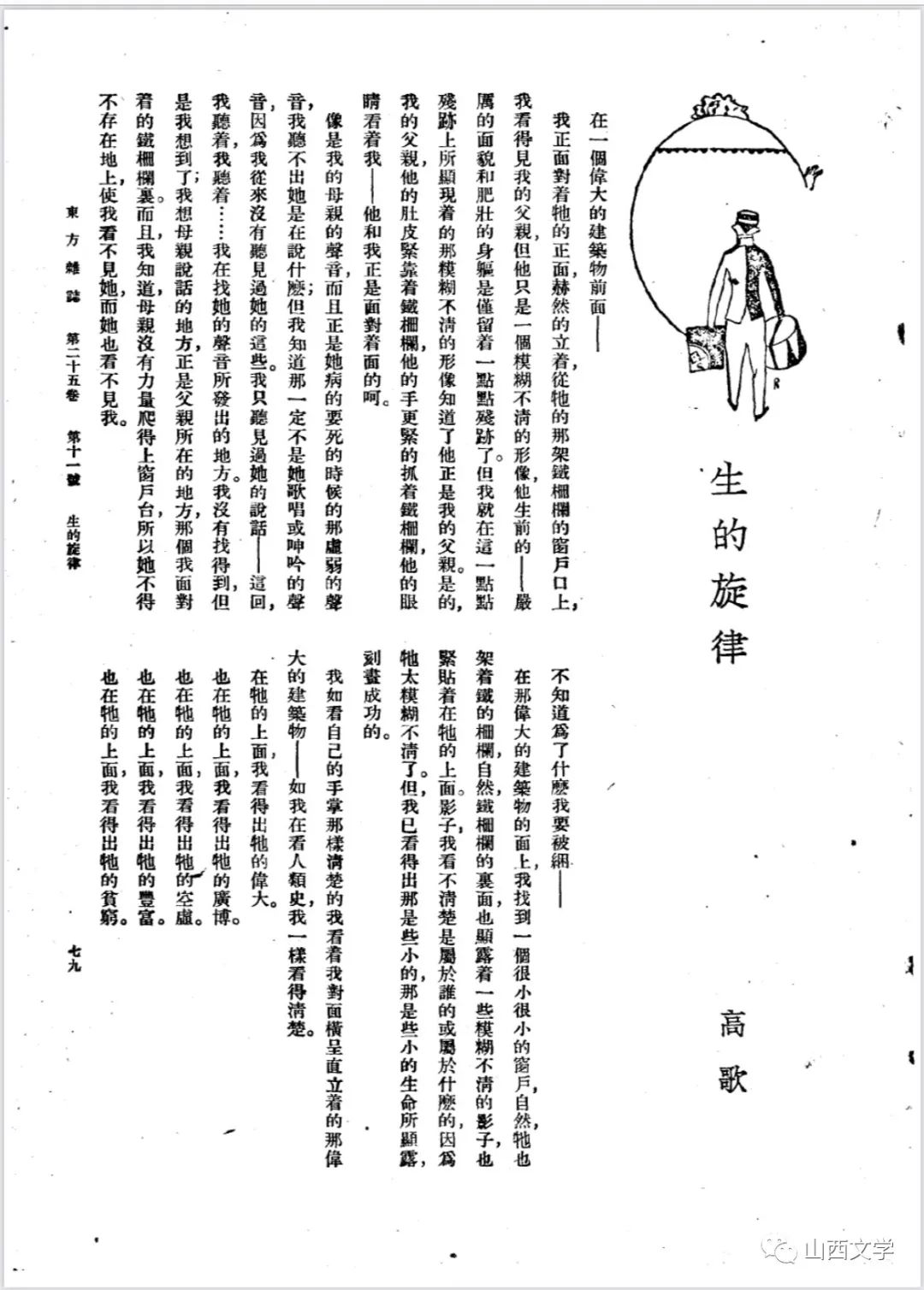
高歌《生的旋律》,《東方雜志》1928年第11期
多種創作方法的兼容
“五四”新文學的主潮,既不是那種純粹的現代主義創作,也不是那種正統的現實主義創作,而恰恰是在現實主義基礎上又融入了現代主義元素的形態。魯迅、茅盾、郁達夫等的小說,都具有這樣的藝術特征。而浪漫主義小說、新感覺小說等,處于支流位置。狂飆社作家的小說,自然屬于現代主義。他們期望超越現實主義,但并不能擺脫現實主義,因此在一些情況下就采用了兼容并包的方法,即努力把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結合起來。高長虹說:“現實主義的藝術,不是那樣容易產生的。熟習(悉)生活,熟習(悉)語言,技術精巧,觀點正確,這些條件,缺少了一樣都不很妥當。……走現實主義的路,這就是成功的起點。”[8]當然這是作家后來的理性認識,并不能代表創作,但有這樣的意識,就是可貴的。高歌的小說創作,一方面表現出對現代主義的執著追求,另一方面也表現出對現實主義的努力依傍。即在現實主義的基礎上,有限度地融入古典主義、現代主義表現方式,形成一種可稱為現代現實主義的創作樣式。
變革敘述視角,大量運用第一人稱“我”,也使用第三人稱“他”,乃至運用第二人稱“你”,使高歌小說在敘述上變化多端。敘述視角問題,在中國古典小說中就是一個重要問題,但直到進入現代,才變得清晰、科學起來,受到了作家的高度重視。譬如《第一次上火線》,是作家創作的惟一一篇寫戰爭題材的小說。作品寫“我”這個北方青年,不能忍受平庸、寂寞的生活,參加了“革命軍”,開赴南方k城,參加戰斗,想不到這場仗竟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我”在戰場上的恐懼、亂想,一位友軍士兵的無辜喪命等。小說是以第一人稱為視角,更便于寫出戰爭的真實,“我”的內心的真實。但作家又設置了一個“你”的視角,即“我”的朋友“你”,“我”用寫信的方式向“你”傾訴,“我”與“你”共同對話、交流。這樣就使小說的敘述有了一個對象、焦點,使“我”的敘述更真誠、可信、感人。譬如中篇小說《野獸樣的人》,是一部自敘傳小說,以“我”為主人公和敘事人,描述了文學青年的“我”在上海的打工生活和內心世界。“我”的生活是艱難的,沒有固定職業,靠寫作維持生存,住在“狹的囚籠”般的租房里。在“我”的眼里,大上海是混亂、墮落的。奢華的大街上,“男的是士兵,女的是娼妓”。環境的壓抑,常常讓“我”有恐懼感、虛無感,因此渴望上戰場,轟轟烈烈地活著。“我”向往美好的愛情,在飯店解救一個被欺辱的年輕女子,做了一件“英雄救美”的好事,但美好的愛情只是一個泡影。街上到處是像野獸一樣的警察、士兵。這些畫面、情景、人事,由“我”親身經歷,親口講出,顯得格外真實、生動、深切。在這一基礎上,又運用表現主義手法,突出了“我”的主觀感受、想象。如把黑夜和白天混淆,老感覺有人闖進屋向“我”開槍,“我”被關進監獄,巧遇女朋友救“我”逃出…… 高歌多次想到、夢到被抓捕、進監牢,這是當時許多進步青年經常遇到的厄運。1929年他真的遇到了這樣一場悲劇。這些非現實的描寫,不僅沒有損害小說的現實主義特征,反而強化和豐富了小說的現實性。只是作家在對情節、細節的描述中,不夠節制,顯出一種自然主義傾向。
借鑒詩意化方法,賦予生活、人物以詩情畫意,使高歌小說有一種憂郁、抒情的審美特色。中國古典小說、西方現代小說,都有詩意化寫作傳統,這種方法在浪漫主義文學中達到一種極致。高歌信奉主觀色彩強烈的表現主義,因此詩意化就成為慣用方法。譬如《春天的消息》寫于1927年,此時北京《狂飆》周刊停刊,他和高長虹都處于焦慮中,在這樣的情境中,為了激勵自己他創作了這篇詩一樣的小說。作品寫“我”活了25歲,卻一直生活在冬天,沒有度過一個春天。作品中的“你”既是一位靈動、清純的女性,又象征著自由、美好的春天。等到春天突然來臨,“我”欣喜若狂,毅然投入春天的懷抱。作品用了大量詩句、排比句,歌頌春天、梅花,歌頌女性、愛情,表現了作家對春天的渴望,對前途的信心。譬如前面所述的《佚秋老人》《生的旋律》,前篇寫石橋與老人有一種靜穆、悠遠的藝術美,后篇寫“我”的人生與精神,有一種憂郁、激越的抒情味,可謂高歌詩意小說的精品。
運用荒誕手法,強化小說的戲劇性、吸引力,也是高歌常用的創新手段。譬如《剪刀》,描寫丈夫與妻子的日常生活。丈夫在屋里悠閑踱步,妻子幾次進來問:“早上,吃什么?”丈夫始終緘口不言,最后妻子進來手拿一把剪刀,突然撲通倒在地上,丈夫依然在踱步。最日常的生活中卻出現了荒誕情景,妻子是用剪刀自盡了?還是向丈夫跪下了?作品留下了懸念。再如《死尸》中,“我”得了怪病,身體冰冷如同死去,臉色未變尚有意識。家人把“我”入殮棺材,就在封棺釘釘時,“我”醒來跳出棺材。這是農村發生的荒誕故事,作家寫進了小說中。這些情節確實是荒誕不經的,頗有吸引力,但作家還沒有去發掘背后的內涵。
取法意識流方法和手法,展示人物紛繁、洶涌的心理與精神活動,是高歌小說最主要的藝術特征。意識流既可當作整體的創作方法,即完全表現一個人的意識世界,也可當作局部的創作手法,即部分地插入人的心理活動。高歌在小說中兩種方法都使用,前者容易形成現代主義小說,后者往往構成現實主義小說。中篇小說《高老師》是作家一部重要作品,較充分、完全地刻畫了一個現實主義人物形象。作家寫高老師的日常生活,飲食起居;寫課堂講課,師生互動;寫逛街交友,吃飯喝酒;寫想念母親、與弟妹們交往;寫參加革命組織,醞釀暴動起義;寫突發疾病,倒在講臺。這些都是忠實的現實主義描述。但作家在現實主義的基礎上,更鼎力寫了他的意識與無意識活動,精神與靈魂世界。他生活在一種矛盾重重的心理與情緒中,他“愛好的東西,同時也是他所憎惡的東西”。包括環境、職業、他人、自己等等。他痛恨城市、學校、領導,但又離不開城市、學校、工作。他成為“燃燒著氣憤和激昂的烈火”的人。他悄悄地了解民情,發動工人去斗爭,暗中制造炸藥,要在暴動中“搗毀這個城”,然后去建設一個“新的中國”、“新的世界”!他被群眾奉為暴動領袖。但他卻倒在了講臺上。作品中的情節、細節,人物的想象、回憶、幻覺、意識流,統統攪和在一起。顯示出一個貧困、激憤、矛盾、抗爭的革命知識分子形象。但從現實主義人物的尺度要求,這一人物顯得模糊、表象、凌亂,缺乏應有的有機性、立體感。
現實主義與古典主義、現代主義,在創作方法和表現形式上的嫁接、兼容,并不是幾種不同類型的“主義”的簡單相加、拼接,而是在更高層面上的一種打碎重組、再造。高歌有些作品的兼容是成功的,有些則是不那么成功的。他在情節組織、人物塑造、語言錘煉乃至標點使用上,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難以創造出更多獨特、完美的小說文本。但這些不足以掩蓋他在小說內容和形式上的天才探索與創新,是需要我們格外珍視和研究的。

“高氏三杰”故居
注釋:
[1]董大中:《高歌創作論》,《狂飆社紀事》,北岳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165頁。
[2]袁可嘉:《歐美現代派文學概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頁。
[3]高歌:《清晨起來》,上海泰東圖書局1927年版,封底。
[4]魯迅:《魯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70頁。
[5]董大中:《高歌創作論》,《狂飆社紀事》,北岳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168頁。
[6]袁可嘉:《歐美現代派文學概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頁。
[7]言行:《高歌小傳》,《新文學史料》1993年第3期。
[8]高長虹:《高長虹全集》(第四卷),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年版,第464頁。
作者簡介:段崇軒,1952年生,山西原平人。1978年畢業于山西大學中文系,歷任山大中文系教師、《山西文學》月刊社編輯、主編,山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山西文學院一級作家。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理事。1978年開始從事中國當代文學及文學評論研究,著有長篇傳記《趙樹理傳》(合作),評論集《生命的河流》《邊緣的求索》《地域文化與文學走向》,專著《鄉村小說的世紀沉浮》《馬烽小說藝術論》,散文隨筆集《藍色的音樂》等十多種。專著《中國當代短篇小說演變史》,入選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有多篇作品獲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優秀成果獎、趙樹理文學獎等獎項。
- 臺靜農:白頭猶自在天涯[2022-08-05]
- 陳平原:“演說”如何呈現[2022-07-19]
- 老舍在青島創作《駱駝祥子》[2022-07-15]
- 王道:沈從文編音樂教材[2022-07-12]
- 《語絲》體制之形成與北京的報刊出版[2022-07-08]
- 《捧血者——詩人辛勞》新書首發式暨學術研討會在內蒙古文學館舉辦[2022-06-23]
- 趙普光:不“冷”不“熱”的子善先生[2022-06-21]
- 中國現代作家書信的“公”與“私”[2022-06-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