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絲》體制之形成與北京的報刊出版 ——關于“同人雜志”與“小周刊”

《語絲》創刊號首頁
一
1924年10月下旬,由于排好的稿件(即魯迅《我的失戀》一詩)突遭晨報社代理總編輯劉勉己抽去,原《晨報副刊》主編孫伏園憤而辭職。在與周氏兄弟分別商議后,他與章廷謙(川島)、李小峰等人決意不依附任何報社,邀集友好,另創新刊——此即現代中國著名的同人刊物《語絲》誕生的故事。時至今日,結合幾種相關報刊、書信、日記等材料,其間的諸般事實及先后次序已可得到較為明了的還原。
孫伏園于10月23日出晨報館,當夜“在川島處住一宿”,后兩日分別拜訪周作人、魯迅,[1]議定出版一種“周刊或旬刊”。[2]25日,川島開始向胡適等人寫信尋求支持和贊助。[3]11月2日晚,孫伏園、周作人、錢玄同、江紹原、李小峰、章廷謙、顧頡剛等七人在東安市場開成北樓聚會,“語絲”之為刊名,“周刊”之為體制,與會者每人出資八元,都在此會上確定。[4]首期稿件很快收齊,11月12日在《北京大學日刊》上登出了目錄和定價,預告將在“本月十七號出版”。[5]又據川島回憶,同人們和承印該刊的北大自設印刷所約定,每周一出版的《語絲》須提前兩日印好,[6]因此它實際上15日就送到了魯迅(應該還有周作人)家中。次日,孫伏園等又從魯迅處收得十元為“刊資之助”。[7]
《語絲》之出刊既然肇始于同人們對孫伏園突遭報館上級“侵奪文字之權”的不忿,[8]作為對應的制度性后果,該刊成為“同人雜志”幾乎是一種必然選擇。和同人們各自分擔出版費用的出資方式相匹配,在投稿方面,他們也享有平等的權利。同人的“內稿”,編輯無權取舍,一般來稿必登;[9]而對于外來的稿件,則如周作人在發刊辭中所宣稱的:“至于主張上相反的議論則只好請其在別處發表”,體現出一定的團體意識。[10]
清末民初以來的報刊,根據運營模式,大致可分為商業報刊、機關刊物和同人雜志三種。商業報刊多由書局報館出資承印,為撰稿者發放稿酬,注重名聲和經濟方面的利益追求;機關刊物,提供經濟支持的贊助者多為學會、團體機構或某一政黨,出言發聲常為某種特定立場的顯示;同人雜志則較少或不依賴外界的經濟支持,同人集體出錢維持刊物的運營,因此較有文化理想的追求,而不甚在乎經濟回報,撰稿者往往也沒有稿酬可拿。[11]不過,此三者并不總能平行和均衡地發展,而往往隨著政治經濟“大環境”和團體內部“小環境”的變化此消彼長。
《語絲》尚未正式面世時,周作人致信胡適,對辦刊宗旨略作解釋,謂:“‘慨自’《新青年》《每周評論》不出以后,攻勢的刊物漸漸不見,殊有‘法統’中斷之嘆,這回又想出來罵舊道德、舊思想,(即使王永江為內務部尚書也不管他,)且來做一做民六議員,想你也贊成的吧。”[12]雖然語帶戲謔,但他以攻擊“舊道德、舊思想”為使命,自覺將《語絲》放在新文化人自辦的含有“文明批評”色彩的所謂“攻勢的刊物”的脈絡之中,以接續其未竟之業的意思是很顯然的。
從第3卷起改在北京編輯的《新青年》月刊,走的雖然是同人雜志的路子,卻是借助上海群益書社的力量印行的。[13]與此相近的是1923年胡適、高一涵等人籌辦《努力月報》,也由商務印書館應允承辦。借助書局成熟的業務運作和較為充分的資本,新文化人的見解主張得以行遠,書局報館也因此聲名益彰。只是這樣的合作能夠成立,一來需要刊物的主持者與書局高層有極好的私交,方能獲得充分的信任和自由;[14]二來主辦者須得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和象征資本,才能以較強的議價能力抵制住出版方過度的商業訴求,維持住刊物的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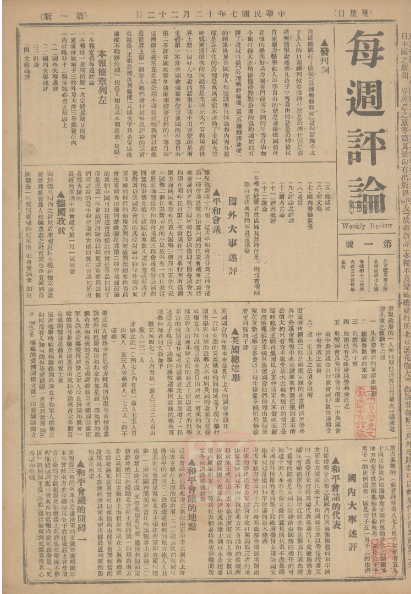
《每周評論》創刊號首頁
繼《新青年》月刊而起,創辦于1918年底的《每周評論》周報,較之以上兩刊,其同人雜志的性質更為純粹,這很大程度上是由它的出版周期決定的。它的組織者、撰稿人和《新青年》為同一班底,同人集股出資,[15]自行租社址、跑印刷、作校對,[17]初始目的就是為了補《新青年》出版周期較長,側重輸入學理,難以對現實政治形勢作出及時反應的不足。[16]其時和新文化人有合作關系的商業書局多遠在滬上,不宜承辦短周期刊物,而《每周評論》編輯部設在陳獨秀的北大紅樓文科學長辦公室,發行所在宣武門外的涇縣會館,地點較為集中,組織小而靈活。其時在北京辦報并不繁難,印刷方面還能借重李大釗和《晨報》印刷所的關系。[18]后來胡適、丁文江等人的《努力周報》特為“談政治”而辦,和《每周評論》的旨趣有一定延續性,運作方式亦類似。
從《新青年》到《每周評論》和《努力周報》,看似只是外在的體制和形式的更動——由長周期(月刊)/“長文章”變為短周期(周刊)/“短文章”,由他人出資承印的商業報刊與同人雜志的“雜糅”,轉型為“花自己的錢,說自己的話”的完全的同人雜志——卻和文章風格及言說姿態由穩健平易的“闡明學理”向直言不諱的“批評事實”變化隱然相關。在此背后持續鼓蕩著的精神動力,大概是在京新文化人們試圖尋覓、借助,甚至干脆自造一個“獨立正直的輿論機關”,以實現對“混沌思想”進行“澈底批評”,[19]終至于影響和改變社會的夙愿。和商業報刊或機關刊物相比,同人雜志或許才最符合這種不斷擺脫各種束縛、追求充分言論自由的理想。因此,肆言無忌的同人雜志與京中政治管控經常處于緊張對峙的狀態,自是意料中事。1919年8月,《每周評論》即因言論“含過激派臭味”,為京師警察廳封禁。[20]作為另一份立意“談政治的報”,[21]《努力周報》于1923年10月第75期后,再未繼續出刊,雖有胡適南下,病體未復的考慮,但這月曹錕以“賄選”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一事,造成了京中政治空氣空前惡化,也是令胡適感到“我們談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謂止了壁了”,“決意把《努力》暫時停刊”的一大原因。[22]前事尤其提醒人們注意北洋軍閥當政時期干預言論出版的方式和特征——即與政局的治亂翻覆相對應,當局在言論管制方面也缺乏穩定一貫的政策,常隨一時政象的轉移而時緊時弛,或存或亡。
和30年代南京國民政府逐漸發展出的一套較為細致精密的書刊審查手段不同,北京當局一般很少在書刊出版前作文字內容層面的干預,而往往直接訴諸對生產、流通等具體環節的干擾和破壞。[23]1922年胡適創辦《努力周報》時,不但社址房東受到壓力,還須一再向警察廳進呈申請,聆受訓誡,方得通過;[24]1924年曹錕當政時期,警察廳對《胡適文存》《獨秀文存》,乃至一些非政論性書刊,均由“便衣偵探把一張禁書的書單傳給各書攤”,以非正式的方式破壞銷售。[25]報刊在向外埠寄發的過程中,也常有遭到扣留的情況。[26]到了1926年,張作霖入主北京,更為粗暴和常見的形式,則是直接搗毀報館書局,將主事者或捕或殺。[27]1919年的《每周評論》,1920年的《新社會》旬刊,都被當局以各種理由封禁。[28]邵飄萍于1918年創辦《京報》,次年報社即因抨擊安福系內閣被封。邵喬裝逃滬,僅以身免,俟安福系失勢,乃卷土重來,將報紙復刊;然奉軍進京后仍遭槍決,《京報》及旗下各類副刊亦隨之瓦解冰銷。[29]他的例子最能見出20年代北京的言論空間因主政的軍閥派系之作風差異而頻繁地舒張和緊縮的狀態。其轉變之急劇,往往能從“百家爭鳴”一夜變為“萬馬齊喑”或相反。就像邵飄萍曾在直系、奉系、皖系以及馮玉祥的“國民軍”的勾心斗角中,一次次“利用軍閥間的矛盾靈活機警地獲得了安全”,[30]京中每一次政治變亂所造成的法統中斷和大權旁落,都為知識人的言論出版騰出了空間。
在《語絲》創刊前,《新青年》同人已于1920年前后發生分裂,該刊隨即遷滬,成為一份純粹的政黨刊物,《努力周報》也壽僅年余而夭。在所謂“五四退潮”后的蕭條年月,京中由新文化人主辦,獨立發行的小型刊物并不多見,依附于商業大報而存在的報紙副刊成為他們發表言論的不多的重要渠道之一。這些大報社——如孫伏園所供職的晨報社——多有深厚的政治背景和人脈資源,能為旗下刊物提供一定程度的庇護;而綜合性副刊多載學術、文藝等“非政治性”內容的特點,也是它能夠存活較久,未遭取締的重要原因。
《晨報副刊》原由《晨報》第七版(偶爾移至第五版)獨立出來。該版在1920年7月孫伏園接編之前,由李大釗、張梓生先后負責編輯,不載新聞和政論,以與報紙正張相區別,代之以“名著”“論壇”“小說”“藝術談”等“嚴正的學術性的文字”,也間有“浪漫談”等略具趣味性的欄目,顯示出與《北京日報》的《消閑錄》、《新聞報》的《快活林》等早期純以滑稽消閑為格調的副刊,兼有繼承與改造的雙重關系。[31]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孫氏被稱為“中國現代報紙副刊的革新者”。或許可以說,《晨報副刊》和其他數種同類型大報副刊,同時兼具商業報刊、同人雜志和機關刊物三者的部分特性。就其版面形制和出版方式來說,它本身就是商業大報的一部分,或以普及性的科學知識和趣味性的文藝材料娛樂具有一定知識水平的受眾,或將報社青睞的政界要人和文化精英的講演社論置諸篇首,增加分量。另外,它又因主持者孫伏園等人的思想傾向、編輯方式和以大學為基礎形成的關系網,而能夠超越于北京出版界在繁榮和蕭條之間的擺蕩,為周氏兄弟、胡適、林語堂等新文化人提供一塊較為穩定的發表園地。[32]在《語絲》創辦前,《晨報副刊》實際上是魯迅、周作人、錢玄同等曾經的《新青年》同人從小說、翻譯到論文、雜感等幾乎所有類型文章的輸出之地。
不過,“投資者—經辦人”這對既相互利用又彼此制約的關系,在這里依然存在。《晨報副刊》從報紙正張中獨立出來,從1921年10月12日起“擴充成為四開一張的小報”,是在當時的報社主持者蒲伯英(殿俊)的建議下實行的。“晨報附刊”的名字,即是他提議孫伏園請教魯迅而得,而“晨報副鐫”仿漢磚字體的四字報頭也為蒲氏所題寫。可見兩人上下級之間,合作頗形融洽。[33]然而蒲伯英至1922年便不再擔任編輯事務,自次年2月更不履及報社,[34]晨報社乃由創社元老之一、民初進步黨議員劉崇佑(崧生)負責,其堂侄劉勉己為代理總編輯。報社上層的人事變動,影響遂漸及職員、職權乃至報刊的面貌。

1921年10月12日《晨報副刊》首頁
由于報紙副刊較為曖昧的身份特征,它與報紙的正張是否必然需要保持一致的傾向性或分明的主從關系,原無一定,端看報社的具體管理制度,以及主持者的辦事作風和人際關系。如1933年曾為天津《大公報》主辦《小公園》副刊的陳紀瀅認為,副刊“一定是配合報紙本身的一種文字輔佐物”,與報紙新聞應當“言論一元化”;[35]《京報》館主邵飄萍則直陳,他“援助學術團體”創設副刊而不加干涉,正是使“一方面可以發表研究之興趣,一方面可以增加報紙之聲光”,雙方“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互助互利”之舉。[36]就《晨報》及其前身《晨鐘報》而言,它長期被目為“研究系”的機關報,但《晨報副刊》在孫伏園主持下,并未體現出特別鮮明的黨派色彩,[37]可見他對《晨報副刊》的編務,享有充分的自主權,而孫氏對此也習以為常,才會將劉勉己對自己原有職權的干涉引以為“生平未有的恥辱”。[38]在《晨報》新高層的眼里,孫伏園與其說是知根知底的職員,倒更近于自帶關系的傭兵。
在“抽稿事件”發生前,孫伏園應該就已感受到了社內風向變動的征兆——是年7月,孫氏離京南下,《晨報副刊》由友人李小峰代編。李小峰受周作人文章的啟發,刊登了自己所寫的“徐文長玩弄刀筆、包辦訴訟,因此被稱為惡訟師的故事”。其時劉崇佑為聞名京津的大律師,《晨報》頭版常年登載著他的廣告,看到這些文章,“以為是對他有意的諷刺,在幾次集會上表示了不滿”。[39]劉氏叔侄與晨報館俱有魯迅所謂的“深關系”,非尋常職員可比。也許正是意識到自己獨編副刊,不受掣肘的局面不再,孫伏園遂決心請辭離館。
論者常結合晨報社的政黨背景,將“抽稿事件”的發生解釋為兩種對立的政治勢力或思想立場之爭表面化的結果。如李小峰在1956年就結合1925年徐志摩受陳博生等人邀請和陳源的鼓勵,接編《晨報副刊》一事,將此事描述為給徐志摩“騰位子”而實施的蓄謀已久的排擠,顯然是歷經與“現代評論派”的論爭后,“倒放電影”而得出的在當時“政治正確”的敘述,查無實據,不足為憑。[40]平情而論,此事最為直接的原因,是孫伏園在原本較為融洽平等的上下級關系中享有的副刊編輯權力,突遭新上級“侵奪”,為其自尊所不能堪。此事再一次揭示,報刊本身的主張和言論表達,除了受到大的政治社會環境影響外,受報館或書局一類“小共同體”的意志和趣味的作用或許更為直接。
放棄《晨報副刊》這一傳統的發表園地,固然擺脫了報館的束縛,但也意味著失去了穩定保護,直接暴露在北京陰晴無定的政治氣候中。不過湊巧的是,《語絲》的誕生正逢京中發生了繼1917年張勛復辟又遭驅逐后最大的一場政變。孫伏園至遲于1924年10月24日出晨報館,而在10月23日當天,原本奉令出京迎擊奉軍的馮玉祥突然班師回京,發動政變,推翻曹錕政府,接管了北京。短短十數天內,馮氏接連發布“主張和平之通電”,驅逐清廢帝溥儀出宮,電邀孫中山北上議政。經過一系列政治變動后,段祺瑞受各方推戴,組織臨時政府,自號“執政”,表面上與全民共憤的“武人當政”相切割,作出了“改新政治,與民更始”的開明姿態,[41]京中氣氛一時轉為“安謐”,[42]輿論界和文化界也呈現出輕松活躍的狀態。曾為曹錕政府封禁的日報復活,也帶動了幾種定期刊物的產生。景梅九《國風日報》的解禁,使高長虹等人主辦的《狂飆》周刊和《世界語周刊》得以附于該報而問世;[43]而12月13日創刊的《現代評論》,雖籌備“已經半載”,于此時“才獲出版”,亦不為無因。[44]繼而至次年3月6日《猛進》周刊、4月24日《莽原》周刊等“定期小刊物”先后出版,此時的出版界,已被論者評為“風起云涌,熱鬧不可一世”了。[45]誠如高長虹所言:“這一次的政變與北京的出版界是很有關系的,政變以后,定期刊物很出了幾種,除五四時期外,怕沒有再那樣熱鬧過吧?”[46]尤有意味的是,胡適創辦《努力周報》,正值第一次直奉戰爭如火如荼之際,該報之停刊又與曹錕賄選有關。而《語絲》創辦于第二次直奉戰爭告終和曹錕倒臺之時,兩份同人刊物的起訖,恰成一組有意味的對照。《語絲》創刊之始,從組稿、排印到發行,純系同人自操自辦,雖未知其創刊時向有司立案的詳情,但顯然未受刁難,可謂得時。不僅如此,此事的另一直接后果,就是再次激活了新文化人譏彈時政、針砭世風的傳統,給這些應時而生的刊物多少都打上了一層政治性的烙印。就以《語絲》后來的對頭《現代評論》而言,從長期籌備到最終出刊,主持者預先宣傳其色彩和定位,就經歷了由包含“性愛,影劇,文學,藝術,政治,社會,新聞,寫真照像,上海俄羅斯及日本之通信”等內容的“大雜燴”式的“現代周刊”,[47]到刊名有明確指向性,以“本著獨立的精神,發表無顧忌,無偏黨,無阿附的言論”為標榜的《現代評論》的轉變。這當然是創辦者們潛察政局、應時而變的結果。對于刊物的誕生與當下時局的關系,他們這樣描述:“現在他不先不后,正當干戈始戢,百廢待興的時候,哇的一聲,產生出來,他應當覺悟他的責任是很重大的了。”[48]
《語絲》的情形與此類似,它雖然是同人們舊有發表園地的一件替代品,卻沒有簡單成為《晨報副刊》的“縮小版”,而是很快表現出對時政議題的熱衷和討論焦點的凝聚。用周作人一年后總結這一階段時的話說,對于“溥儀出宮,孫中山去世等等大事件”,語絲同人都“大談而特談”,只是談論的方式與“以政治為職業”的專家有別而已。[49]在這里,他所隱隱針對并試圖與之相區別的,自然是以政法領域學者為主體的“現代評論派”諸人。但他亦承認兩派所評論的都是關乎時政的話題,只是范圍有廣狹之別、立場有正側之殊而已。這批均以評論性文字名世的周刊的興起,都受惠于同一歷史進程——北京的言論出版空間,因為“最為杰出的一場政變”而空前地打開,[50]抑制同人雜志發展的最大阻力一時不復存在,以往被壓抑在新文化人內部,從思想立場、政治派別到性情志趣、教育背景等各種方面的差異,也同時得到釋放,甚至很快就在新的言論場域中展開了激烈的派系斗爭。
在此意義上,孫伏園離開《晨報副刊》而另創《語絲》一事,雖然只是偶發性的,卻由于隨后發生了反映著在京新文化人分化重組的一連串事件,而被人們追溯為此過程的開端。在后見之明的映照下,此事之驟起仿佛也成了某種必然性的顯現。孫伏園離職數日后,章廷謙就在給胡適的信里,將事情解釋為“兩種勢力不相容的緣故”,已有指人事沖突為派系傾軋之意;[51]魯迅1929年底回憶此事時,也抓住劉勉己的歐洲留學背景加以強調,為孫伏園的去職找到了更為深遠的“答案”。[52]田露、邱煥星等研究者則對幾個當事人的人際交往、文學品味等信息加以“索隱”,認為此次沖突根源于“雙方對文化理念和政治態度的不同”。[53]在筆者看來,局中人的猜想固然近于臆度,后來者的“誅心”亦似求之過深。相較引發此事的原因,其導致的后果或更值得重視。
二
晚清以來,現代印刷裝訂技術漸入中國。初時書、報外觀尚難區分,經過一段時間的演變,兩者漸相分離,可以視作裝幀樣式的兩種典型。[54]僅以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情況而言,前者文字量大,籌備周期較長,開本小(32開較為普遍)而頁數多,一般很少分欄;后者即事而生,每日翻新,開本大(一般為4開)而頁數少。在印刷技術上,兩者其實沒有本質區別。除了圖畫的印制需要使用銅鋅板外,文字均為鉛活字凸版印刷:先排好若干版面,匯為一整個印張大小,而后上機過紙刷墨。不過書籍還需加以裝訂,即將整個印張折疊為較小的版面,數冊堆疊,折縫一側為書脊,刷膠釘釘,包上封面,切去毛邊,方為成品——此即所謂“平裝”。[55]報紙則只需折疊,不必粘合裝訂,亦無封面。切邊后,每張紙可單獨取出并攤開,于是在版面間形成了可供刊登廣告和啟事的中縫。
作為定期刊物的雜志,隨出版周期之長短和文字量的多少,其形制在“光譜”兩端之間移動。一般來說,出版周期較長的刊物,月刊如《新青年》、《新潮》、《小說月報》,季刊如《淺草》,動輒數百頁,有封面,每頁少分欄,除了開本常取16開,較書略大外,其余均與書無異。而有紀念性質的年刊年鑒,常取硬面精裝,則完全就是一本書了。日刊、周刊、旬刊和半月刊等短周期雜志,每次能征集的文字量小,頁數不多,不易裝訂,故常取折疊的形式,有時干脆不加封面,實近于報紙一系。戈公振認為,時人“區別報紙與雜志”,“多從外觀著手,如報紙為折疊的,雜志為裝訂的”,是一種“皮相的見解”,站不住腳。[56]除了他從內容著眼列舉的幾條理由外,短周期雜志常常只折疊而不裝訂的樣式,本身就和報紙難以區別,應該也是原因之一。
據周作人日記,1924年11月2日首次同人聚會時,《語絲》作為“小周刊”的形制就被正式確定下來,此后周作人也多以此稱之。[57]這個詞恰當地描述了該刊的形制特征及其整體視覺效果。《語絲》面世時為16開的冊頁,每期一般4張8版,實際上是由一大張2開紙折疊兩次而成。它的特殊之處在于不切邊,拿到手之后,需要親手將底部的折痕裁開——這甚至造成了一些讀者的困惑:留學歸國后加入“語絲社”的林語堂,對于《語絲》、《猛進》和其他“無論那一種一大張八頁的刊物”,聲稱“運用”了“最高的腦力”和“幾何的分析”,還是搞不懂裁切的方法,得不出正確的版面閱讀順序,以至專門寫信向主編周作人詢問。其原因就在于他是用讀一般“中文書籍”或“西洋書”的方法來看待它們的,而沒意識到這種裝訂形式更接近報紙的譜系。這也意味著“小周刊”一類的短周期雜志,雖然已有《新社會》旬刊、《向導》周刊、《燕大周刊》等為前導,其形制仍未在一般讀者的觀念中得到普及,直到1925年前后“《京報副刊》,《語絲》,《莽原》,《猛進》等出世以后”,[58]才真正風行起來。

1921年孫伏園攝于北京
魯迅、川島回憶,《語絲》面世之初的具體事務性工作,如“編輯、校對、接洽稿子、跑印刷所等事”,主要由孫伏園、李小峰和川島承擔。三人同為北大畢業,年齒輩分相近,私人關系也很親密。川島時任校長辦公室西文秘書,兼哲學系助教,暇時輒來幫忙。[59]李小峰其時沒有穩定收入,和孫伏園同為新潮社干事,常在北大一院的社內聚會,印制文藝叢書,料理后期社務,[60]所出勞力較多,后來以“新潮”“語絲”二社的出版物為基礎,組建了北新書局。[61]孫伏園在報界經驗最為豐富,先后為《國民公報》和《晨報》編輯過副刊,為三人之主腦。盡管他不久后就在荊有麟和魯迅的推薦下改任《京報副刊》主編,[62]精力有所分散,但如果說在《語絲》形制的奠定過程中,他發揮了較大的作用,應該是恰如其分的。
在12月5日《京報副刊》的創刊號上,孫伏園專有一文談他在決定刊物形制時的參照和考量,想來創辦《語絲》時就經歷過一回這樣的過程:
現有的日報附張或小報大抵有四種式樣。第一種《自由談》,《快活林》,《小時報》等無論矣;時事新報的《學燈》,北京晨報的副刊代表第二種;《向導》及民國日報的《覺悟》代表第三種;北大研究所的《歌謠周刊》,以及《綠波》,《狂飆》等代表第四種。第四種最好,可惜印刷工人和讀者兩方面都不大習慣,所以只好暫緩采用。二三兩種之間,第二種似乎較好,但篇幅太大,合訂時翻閱非常不便。所以我們決定采第三種。但又頗以《覺悟》每行的字數為太多了,或者太費閱者眼力,所以兼采《語絲周刊》的短行制。
不過,還有一層要先向閱者聲明的,現在還有許多人看不慣《覺悟》和《語絲》一類的式樣,拿到手以后,倒來倒去的看了半天,終于看不出個所以然。現在我在這里鄭重聲明,《京報》的愛讀者的案上,大抵不至于不備一把小刀的罷,那么請君先裁開而后翻閱,便什么問題也沒有了。[63]
基于形制的類同,“舊文學”性質的休閑小報、經過改良的日報副刊以及新文學團體主持的周刊,都被孫伏園放在“日報附張或小報”的系統里。出于新文化人的價值偏見,他先“理所當然”地摒除了第一種,將比對和選擇局限在新文化出版形成的“小傳統”內部。“第二種”的代表,8開本的《晨報副刊》雖然已較它所依附的4開大報為小,在孫氏看來,仍然太大而不適于在合訂成冊后翻閱。“第三種”和“第四種”的諸刊物在開本和頁數上差別不大。所不同者,“第四種”的三種刊物文字皆為橫行,這也許就是為孫伏園所欣賞的原因,但他也意識到這一特征在排印技術和閱讀習慣方面可能遇到的阻力,于是只剩下“第三種”——1922年9月創刊于上海的中共黨刊《向導》周報,和《民國日報》的副刊《覺悟》。兩者在當時均為16開小冊,文字豎排,內頁版面分兩欄。[64]盡管如此,孫伏園猶嫌分欄少,每行字數多,“太費閱者眼力”。在對開本大小、文字方向、版面設計都進行了細致篩選之后,剩下的卻是不在上述列舉之內,大小為16開,每期8頁,文字豎排,頁分三欄的《語絲》。在此,報紙副刊和“小周刊”的形制差別幾乎完全泯滅了。也可以說,《語絲》的形制,本身就是孫伏園和同人們在既有技術條件下,對刊物各個層面的形式要素都作了精心選擇的結果。
回溯《新青年》同人既往的辦刊經驗,《每周評論》和《努力周報》為周刊,均從日報中脫化而來。前者在《晨報》印刷所制版和印刷,其形制亦與《晨報》大體相同,只是每版由4開縮小為8開。每期僅一大張,中縫印有廣告,每版依長邊分成四欄,文字豎排,“國外(內)大事述評”“社論”等常規欄目填充了版面的大部分。《努力周報》形制全襲《每周評論》。此二刊原以評說時事、針砭政象為宗旨,宜乎出之以正大的儻論和短小的時評,和報紙更具親緣性。如果將《每周評論》看作一份報紙的話,那么一般安置在中后版面的“隨感錄”“新文藝”等欄目便類似報紙的副刊——而副刊的源頭正是寓“附于報尾以補版面之不足”之意的“報屁股”。[65]
某種程度上,1919年停刊的《每周評論》可以看作次年獨立出來的《晨報副刊》的先聲。后者也是4開紙單張對折為4版,每頁四欄的報紙形式,排版和欄目安置卻大為靈活,雖仍有“講演”“譯述”“科學淺說”“衛生談”等常設欄目,但分布較為錯落;“小說”和“戲劇”往往能占據至少三分之一的版面;在此二者之間,由“雜感”“論壇”“詩”等短小靈活的欄目加以調劑。編者偶爾也會創設一些以風格命名的新欄目(如連載《阿Q正傳》的“開心話”),甚至有了因人設欄的情況(如周作人的專欄“自己的園地”)。在當時的中國報界,匯于一個總題之下,每篇各自獨立的“專欄”還是個新鮮物事,是需要編者加以特別介紹的。[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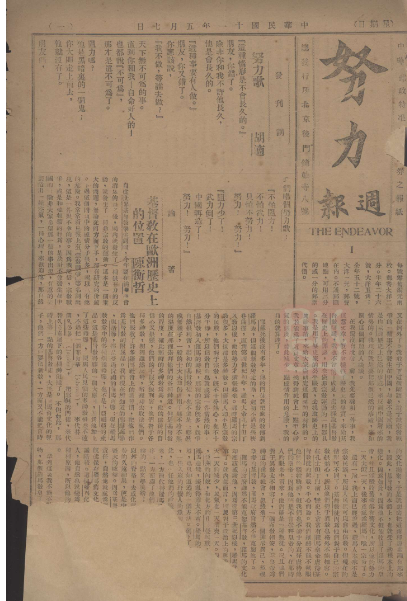
《努力周報》創刊號首頁
其實早在未出晨報館之時,孫伏園就不以《晨報副刊》的既有形制為滿足。他雖然一貫表示峻拒《申報》的《自由談》、《新聞報》的《快活林》等早期報紙附張的滑稽風格,卻又繼承了它們予讀者以趣味和放松的真精神。他認為,日報副刊“以趣味為先”乃是“中外報紙的通例”:“外國報中稱為文藝部,自然是以趣味為主,中國報中如自由談,快活林,小時報之類,雖然趣味比較惡劣,有時反弄得極無趣味,但這是他們不知道什么是真的好趣味的緣故,應該原諒原諒他們”。作為對它們的揚棄,新式報紙副刊應當成為“高等娛樂的場所”。同時他也很清楚,《晨報副刊》以及同等地位的《時事新報·學燈》和《民國日報·覺悟》都沒能做到這一點。他的辯解是,在中國“教育不發達”的“特殊情形下”,副刊不得不負擔起向讀者普及常識的責任,“兼談哲學科學”等“專門或普通的學問”——其矛頭所指,自然是“講演”“譯述”“科學淺說”等較為嚴正枯燥的欄目。而且副刊形制一經確立,便有其歷史的延續性,輕易難以變更,他于是期待出現專門的雜志來分擔這些內容,以“使我們日報的附張卸除這個重擔,仍舊回復原來的地位”。向副刊中“時時打算孱入有趣味的材料”,是他試圖在局部做出改變的編輯策略。[67]
孫伏園所感得的問題在出版界有相當的普遍性,戈公振亦謂:“當此社會設備不完美之時,凡有文字知識者,舍讀日報副張以調節其腦筋外,幾別無娛樂之可言。”他也認同報紙副刊應具有能令知識分子“調節腦筋”的娛樂性,“以文藝為基礎”,引起讀者“研究之興味”。[68]而另一方面,有專門興趣的作者和讀者,也不會以在駁雜的綜合性副刊上占一小小篇幅為滿足。為適應此需求,一些出版形式應運而生,比如報紙副刊開始出現日刊、周刊、旬刊的分化。《晨報副刊》自1923年6月1日起增開《文學旬刊》,由王統照主編,作為文學研究會的機關刊物和發表園地,直接于出刊日替代原本《晨副》的版面。1925年4月1日劉勉己代編《晨報副刊》時,又增插《藝林旬刊》和《新少年旬刊》,10月1日起干脆將副刊編輯部分為日刊部和周刊部。日刊即徐志摩主編的《晨報副刊》,將板式由依長邊分四欄改為依寬邊分三欄,取消了欄目名稱,猶如拆除了房屋內固有的墻面,代之以無差別的隔板,遂打破了原先各種話題、學科或文類在一期之內都能占一席之地的均衡狀態,使文字漸如水流,依主題和氣質的相似而趨歸一處,綜合性大為減弱。原本占據三分之一版面、專業性較強的文字則依主題的不同,分別匯入周刊部的《國際》《社會》《家庭》三種周刊,此三刊由“正張各部部長分任撰述”。[69]其后,徐志摩又將自己經手后文藝性漸強的日刊版面騰出來創辦《詩鐫》和《劇刊》兩種周刊,更是依文類越分越細了。可見主事者雖不同,調整形制,增強副刊的獨立性,減弱其中的“正張”色彩,順應文字“以類相從”的專業化趨勢的見解則一。故戈公振觀察稱:“且特殊之報紙,如政治學術團體之機關報等,以及普通日刊報紙之副張,均往往含有雜志的濃厚色彩,可見二者漸相接近。”[70]
也就在這時,頗多附于日報出刊的“小周刊”開始涌現于北京出版界。它們多由文藝或學術團體和報館直接聯絡,再由后者代為印刷。如1924年11月9日高長虹等人在《國風日報》出版的《狂飆》周刊和《世界語周刊》,石評梅等人在《世界日報》辦的《婦女周刊》(1924年底)和《薔薇周刊》(1926年),《京報》旗下的《莽原》(1925年)《國語周刊》(1925年)及包括《文學周報》《民眾文藝》《戲劇周刊》《電影周刊》等在內的所謂“七種周刊”等。它們不但各有興趣和主張,從內容上不復能看出和報館以及報紙正張的關聯,而且形制也較為自由,不必再與報紙正張完全一致。甚至可以像《莽原》那樣,只有一部分附于《京報》發送,其他則單獨出售。[71]這既強調了作為報紙副刊的周刊本身的獨立價值,也是為了將來好裝訂成合訂本,作二次出售的考慮。這或許反映了一種普遍的閱讀感覺和收藏習慣,即出版物的外在形式越近于書(開本減小,體積增厚)和遠于報(以片紙發布即時消息,隨事而消),其內容和思想也就越具有值得永久保存的價值。
盡管在形制上頗為相似,和這些專門性“小周刊”相比,《語絲》仍有其獨特性。從作者構成上來說,它最初的十六名撰稿人多以和孫伏園的私人關系聚集在一起,橫跨兩個代際,各自的興趣關懷和擅長的創作體裁不盡相同,[72]不像那些多由境遇相似的文學青年組成的緊密小團體一樣,有前衛的藝術訴求或一致的政治主張;[73]其“雜而不純”的性質,倒更接近《晨報副刊》《京報副刊》一類無既定主題的駁雜日刊。另外,這些作者的背景大都偏于文藝,不務科學、經濟、政法等“專門之學”,是以《語絲》也不必承擔大報副刊那種普及科學和常識的任務,反而最合于孫伏園對一份“理想中的附張”的期待,在更高的層面上實現了從“副刊”向“小報”的復歸。[74]有趣的是,周作人晚年向友人介紹《語絲》,就謙遜地將它形容為:“該刊物系是報紙半張八折,亦是平常小報,就是專門譏刺打架,遂至浪得虛名耳。”[75]在孫伏園這里,從《晨報副刊》到《京報副刊》的變化和《語絲》的誕生是同步的。看似外在的形制問題,關系著他作為一個資深新文化報人、副刊編輯的媒體自覺。
或許是由于遵循著相似的原始編輯設想,在內部版面的設計上,《語絲》和《京報副刊》一樣,每頁分出三個橫欄,使每行字數減少到20,閱讀起來更為輕松;取消了具體的欄目名稱,各種主題和體裁的文字看似隨意地相互接續。在如此有限的版面內安排花色繁多的文章,足以使編輯排版的匠心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更重要的是,這直觀地傳達出一種擁擠、擾攘卻又前呼后擁、充滿生機的視覺感受,也就放大了文字中存在的譏誚、唱和或辯難——這些都是《語絲》的讀者時常予以反饋的。而作者本身也是讀者,隨著身份的往復轉化,由感受催生的文字又會再次投入版面。副刊編者們不約而同地意識到,文字的簡短、文章間迅捷的切換,往往與輕松、活潑、有新鮮感、具刺激性的閱讀感受相連。[76]
不難理解,在這樣的氣氛之下,《語絲》上刊登最多也最受歡迎,最終在文學史上留下印記的文體為什么是短小的雜感、簡潔的評論,以及含蘊深長的散文詩,而非動輒橫跨三五頁,需要連載數期的小說、劇本或學術論文。這種經過改造的副刊形制,本身就潛在地表示了對不同文體或迎或拒的差別態度。孫福熙回憶,他和同學“凡初接到《新青年》時,就翻閱書的末尾,先看隨感錄的文字”,此后重新翻閱,讀的也多是這部分。其原因就在于它篇幅的簡短,“使讀者不為時間與精神所限”,留下的印象反而“與別的長篇論文的地位一樣輕重”。[77]從這個角度來講,《語絲》整體都帶有“隨感”和“速寫”的風味,懷著“名山事業”的撰著心態為它供稿的寫作者恐怕是不多的。
堪作對照的是,同為“小周刊”的《現代評論》,只是頁數增加了一倍,每頁分兩欄而非三欄,以傳統的方式穩定地劃分欄目,大體遵從先“時事短評”和政治經濟論文,后“小說”、學術文、“書評”和通信的較為雍容的排布,廣告登在刊物的首尾頁面而非中縫,就遠于小報副刊的靈活隨意,而近于月刊雜志的堂皇寬綽,生成了和《語絲》截然不同的視覺效果與閱讀體驗。由于它每期都給創作安排了固定場地,文藝性也大為增強。魯迅就注意到,“《現代評論》比起日報的副刊來,比較的著重于文藝”。[78]《現代評論》的成員構成頗為復雜,初始撰稿班組主要包括綜合月刊《太平洋》社社員創造社的部分成員,后來還“容納了十多個觀點不同的社團流派的作家作品”。[79]該刊嚴格的欄目劃分,某種程度上也是為了使興趣和主張迥異的實力人物們能夠“各司其職”而作的制度分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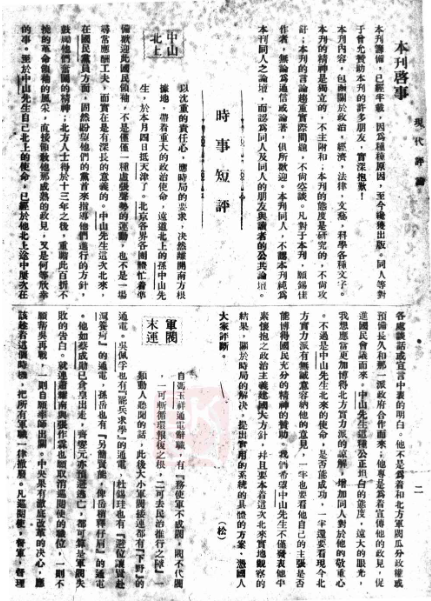
《現代評論》創刊號內頁
另外,前已言之,《語絲》由位于北京大學第一院地下室內,北大出版部附設的小印刷所承印。此處原為印刷教學講義而設,同時也接外活。孫伏園和李小峰等作為后期新潮社的主要成員,和此處多有接觸。[80]在《語絲》之外,同樣由此處承印的刊物,前有1922年底北大歌謠研究會創辦的《歌謠周刊》,后有1925年創刊,由北大教授徐旭生等人主辦的《猛進》周刊。在《歌謠周刊》的排版由直行改為橫行之前,三種刊物形制上的一致性是顯而易見的:均為16開小冊,每版依長邊分為三欄,文字外加黑框,頁眉處印有刊號、日期和版面序數,廣告登在中縫處,文字豎排印刷。但一貫之中也有些關鍵的分別。《歌謠周刊》作為一份專門性較強的學術刊物,姑置不論;《語絲》和《猛進》倒是常被放在一起比較論列的。兩者最大的區別在于頭版的樣式:《語絲》的頭版,錢玄同題寫的刊頭、地址、報費、廣告費等信息居于右上,簡明的目錄格居于左下,其余為頭版正文,形制全同副刊;《猛進》的頭版更像是封面,自上至下,分別由巨大的魏碑體報頭、日期刊號、疏朗的目錄、通信處和其他訂購信息構成,直到第25期,才出現將內頁正文摻入封面的情況。同時內頁也被“時事短評”“虛生專欄”“通信”等固定欄目切割開來,體現了掙脫報紙和副刊,模仿、靠近月刊等長周期刊物的努力。從這一點來說,《猛進》的形制恰在《語絲》和《現代評論》之間。有趣的是,魯迅就認為,從內容和風格來說,《猛進》多“論一時的政象的文字”的特征近于《現代評論》,但就其愛發“很勇”的反抗性議論一點來說,又和《語絲》站在同一陣線。[81]刊物的形制和風格之間,竟存在如此有意味的對應關系。后者固然不僅為前者這一單一因素所決定,但多少可以說明,在“日報副刊—小周刊—長周期雜志”的演變光譜中,刊物的形制并不是全然外在,與內在的文章肌理、論說風格——或逕言之曰文體——水米無干的“儲藏室”式的存在。
《語絲》于1926年5月31日出到第81期時,進行了“特別改良”,變為小32開的狹長小冊,有論者謂:“這種版式非常奇怪,在刊物中可說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82]每期凡16頁,頁分兩欄,加添封面封底。多出的頁面上,除了刊名、刊號、目錄之外,便是書刊廣告,以及北新書局招股、遷址、促銷一類的商業信息。我推測,《語絲》此次改版,最大原因當是原先的小報形制只有中縫能夠刊登商業信息,已成難以突破的常規,對于成立不久、亟須通過宣傳以張大自身的出版方北新書局來說不敷應用,干脆另起爐灶,使此時行銷已廣、聲名赫赫的《語絲》一刊潛在的商業價值得以發揮。如此說成立,那么一些研究者認為到了上海時期才對該刊起“干擾”作用的商業考慮,[83]其實早就影響到這份看似純粹的“同人雜志”的形式層面。
“同人雜志”與“小周刊”是人們用來界定現代刊物體制的常用詞,借助這些標簽,人們仿佛就能輕捷地把握住一份刊物的面貌。然而在詞與物的罅隙間,豐盈的歷史信息和物質形式細節過于輕易地流失了。抽象的“共相”背后,是無數變動不居、各如其面的“殊相”。具體到每份刊物,其體制和形態并不是天然和透明的,而是在時代風會、讀者趣味、物質技術等條件的制約下,以及代代相延、迭有翻新的出版實踐中,不無偶然地生成和被選擇,而后具體微妙地參與到該刊面貌的建構中來。換句話說,以《語絲》而論,雖然它的誕生只是數日間的事,但是使它得以成為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樣子的或遠或近的結構性潛流,早就在涌動著了。
注釋:
[1] 《周作人日記》中冊,鄭州:大象出版社,1998年,第407、408頁;
[2][7] 《魯迅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533、535頁。
[3][51] 1924年10月25日章廷謙致胡適函,《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194頁。
[4][8] 《顧頡剛日記》第1卷,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548頁。
[5] 《思想文藝定期刊語絲周報第一期目錄》,《北京大學日刊》1924年11月2日第1567號。
[6] 川島:《憶魯迅先生和〈語絲〉》,《魯迅回憶錄(散篇)》,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魯迅研究月刊》選編,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269頁,原載《文藝報》1956年第16號。
[9][52] 魯迅:《我和〈語絲〉的始終》,《萌芽月刊》1930年2月1日第1卷第2期。
[10] 《發刊辭》,《語絲》1924年11月17日第1期。
[11] 陳平原:《思想史視野中的文學——〈新青年〉研究(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2年第3期。
[12] 1924年11月13日周作人致胡適函,周作人:《與胡適書二通》,《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鐘叔河編訂,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509頁。
[13] 汪原放:《亞東圖書館與陳獨秀》,上海:學林出版社,2006年,第32–34頁。
[14] 商務印書館欲承辦《努力月刊》時,對胡適等人不計較“紅利”而取“友誼的幫助”態度,顯然與商務高層的張元濟、高夢旦等人和胡適的友誼是分不開的。見1924年9月8日胡適致高一涵信稿,《胡適來往書信選》,第188–189頁。胡適與商務的長期關系,參見陳達文:《胡適與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與商務印書館》,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第573–600頁。
[15] 據金毓黻回憶和周作人日記,起首由同人各出現洋五元,其后“每月助刊資三元”。見李家勇:《〈每周評論〉的經營初探》,《工會論壇》2010年第6卷第1期。
[16] 張申府:《憶守常》,《張申府文集》第3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03頁。
[17] “看《新青年》的,不可不看《每周評論》。1 《新青年》里面都是長篇文章。《每周評論》多是短篇文章。2 《新青年》里面所說的,《每周評論》多半沒有。《每周評論》所說的,《新青年》里面也大概沒有。3 《新青年》是重在闡明學理。《每周評論》是重在批評事實。4《新青年》一月出一冊,來得慢。《每周評論》七天出一次,來得快。”(《新青年》1918年12月15日第5卷第6號)
[18] 《李大釗書信集》,周芳、李繼華、宋彬編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72頁。李大釗曾任《晨鐘報》(《晨報》前身)總編輯。
[19] 胡適:《〈努力〉的問題》,《晨報副刊》1924年9月12日。
[20] 《北京每周評論被封之因果》,《申報》1919年9月5日。
[21] 胡適:《我的歧路》,《努力周報》1922年6月18日第7期。
[22] 胡適:《胡適之的來信》、《一年半的回顧》,《努力周報》1923年10月21日第75期。
[23] 參見張克明輯錄:《北洋政府查禁書籍、報刊、傳單目錄(1912年7月–1928年3月)》,《天津社會科學》1982年第5、6期。
[24] 《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420、436、487頁。
[25] 阮旡名:《文字之獄的黑影》,《中國新文壇秘錄》,上海:南強書局,1933年,第8–14頁。
[26] 魯迅在1927年9月說:“這半年來,凡我所看的期刊,除《北新》外,沒有一種完全的”。他推測,沒收可能發生在許多城市,北京自為其一。(魯迅:《扣絲雜感》,《語絲》1927年10月22日第154期)
[27] 羅志田指出,民國初年的北洋政府“大體尚秉承著歷代朝廷對讀書人的‘忍讓’”,至20年代中后期,張宗昌、張作霖等人乃一反舊則,“隨意捕殺記者、學生,嚴重損毀了北洋政府的統治基礎”。(羅志田:《北伐前南北軍政格局的演變,1924–1926》,《激變時代的文化與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53頁)
[28] 《新社會》旬刊于1920年5月1日出版第19號后不久,因涉嫌“反對政府”遭封禁,辦事員亦被逮捕。見鄭振鐸1920年5月20日致張東蓀函,《時事新報·學燈》1920年5月25日;鄭振鐸:《〈中國文學論集〉序》,《中國文學論集》,上海:開明書店,1934年,第2頁。
[29] 見《東陽文史資料選輯》第2輯“邵飄萍史料專輯”所收諸文。(《東陽文史資料選輯》第2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東陽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1985年)
[30] 杜鐘彬:《邵飄萍傳略》,《東陽文史資料選輯》第2輯“邵飄萍史料專輯”,第29頁。
[31][33] 孫伏園:《三十年前副刊回憶》,《20世紀中國著名編輯出版家研究資料匯輯》第3輯,宋應離等編,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55、365頁,原載《文藝報》1950年第16期。
[32] 馮鐵著、史建國譯:《作為文學園地的報紙副刊——以〈晨報副刊〉(1921–1928)為例》,《江蘇教育師范學報(社會科學)》2011年第27卷第6期。
[34] 《蒲伯英啟事》,《晨報》1923年6月30日。
[35] 陳紀瀅:《我們需要怎樣的副刊》,《中國報紙的副刊》,王文彬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36–39頁。
[36] 飄萍:《“七種周刊”在新聞學上之理由》,《京報副刊》1924年12月10日第6號。
[37] 田露:《20年代北京的文化空間:1919~1927年北京報紙副刊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94頁。
[38] 伏園:《京副一周年》,《京報副刊》1925年12月5日第349號。
[39] 李小峰:《魯迅先生與〈語絲〉的誕生》,《魯迅回憶錄(散篇)》,第287–289頁,原載1956年10月11日《文匯報》。關于此事,孫伏園和周作人都只回憶到劉崇佑對周作人所作《徐文長的故事》的厭惡,似不及李小峰所述直接具體而近情理。(伏園:《京副一周年》,《京報副刊》1925年12月5日第349號;豈明:《答伏園論“語絲的文體”》,《語絲》1925年11月23日第54期)李小峰所作《徐文長的故事》,刊《晨報副刊》1924年7月12日,署名林蘭女士。
[40] 李小峰:《魯迅先生與〈語絲〉的誕生》,《魯迅回憶錄(散篇)》,第286–288頁。田露亦有相似的看法(《20年代北京的文化空間:1919~1927年北京報紙副刊研究》,第85–92頁)。徐志摩受邀接編《晨報副刊》事,見徐志摩:《我為什么來辦我想怎么辦》,《晨報副刊》1925年10月1日。據此文,黃子美和陳博生力邀徐志摩接編《晨副》,事在1925年3月,而1924年黃子美建議徐辦副刊,只是“隨便說起”,且未明言此副刊就是《晨副》。
[41] 燕樹棠:《法統與革命》,《現代評論》1924年12月13日第1卷第1期。
[42] 1924年11月28日周作人致俞平伯函,《周作人俞平伯往來通信集》,孫玉蓉編注,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年,第20頁。
[43] 廖久明:《高長虹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6頁。
[44] 《本刊啟事》,《現代評論》1924年12月13日第1卷第1期。
[45] 軒:《一年來國內定期出版物略述》,原載《唐山》旬刊,轉引自伏園:《一年來國內定期出版物略述補》,《京報副刊》1926年1月18–31日第388–401號。
[46] 高長虹:《走到出版界》之《1925,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高長虹全集》第2卷,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年,第194頁。
[47] 《北京大學日刊》1924年11月21、27日第1574、1579號。
[48] 《現代評論出版了!》,《北京大學日刊》1924年12月11日第1591號。
[49] 豈明:《答伏園論“語絲的文體”》,《語絲》1925年11月23日第54期。
[50] 此語為北京的英文報紙《北京導報》(Peking Leader)1924年10月26日文章中對“北京政變”的評價。見莊士敦:《紫禁城的黃昏》,陳時偉等譯,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7年,第297頁。
[53] 田露:《20年代北京的文化空間:1919~1927年北京報紙副刊研究》,第85-92頁;邱煥星:《導火線:魯迅〈我的失戀〉撤稿的背后》,《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16年第1期。
[54][56][68][70]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第331、6、228頁。
[55] 王淮珠編《書刊裝訂工藝》,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88年,第21–22頁。
[57] 《周作人日記》中冊,第408頁。周作人在致俞平伯、胡適的信中,以及在一些文章中,都以“小周刊”來指稱《語絲》。(周作人:《與胡適書二通》,《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第509頁;1924年11月28日周作人致俞平伯函,《周作人俞平伯往來通信集》,第18–20頁;豈明:《答伏園論“語絲的文體”》,《語絲》1925年11月23日第54期)
[58] 林玉堂:《語絲的體裁》,《語絲》1925年11月23日第54期。
[59] 袁良駿:《川島先生生平著作簡表》,《川島選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136–142頁。
[60][80] 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文史資料選輯》第61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第123、86頁。
[61] 北新書局成立于1925年2月間。(《北新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招股章程》,《語絲》1926年10月9日第100期)初由李小峰、孫伏園合辦,后來孫因事退股,事權財權遂漸集于李小峰及其親屬之手。見陳樹萍:《北新書局大事記》,《北新書局與中國現代文學》,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第237–240頁。
[62] 荊有麟:《魯迅回憶斷片》之《〈京報〉的崛起》,《魯迅回憶錄(專著)》,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魯迅研究月刊》選編,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183–189頁。陳子善推測,荊有麟向孫伏園傳達邵飄萍的邀請,約在1924年11月24日前后。(陳子善:《〈京報副刊〉影印本序》,《新文學史料》2016年第3期)
[63] 記者:《〈京副〉的式樣》,《京報副刊》1924年12月5日第1號。
[64] 《民國日報·覺悟》1919年創刊于上海,1931年停刊。在如此長的出版時期內,形制有多次變更,此處僅言1924年底時的情況。
[65] 吳永貴和林英注意到,《每周報刊》相對于過去的報刊,已有了“一個重要媒介形式創新”:“一張四開紙的對疊,省卻了裝訂的工序,簡約易行,內容不必太多,貴在趨時,滿足人們對報紙的時效性期待;同時各欄目板塊燦然分明,主題指向明確,篇幅短小精悍,重在說理,滿足人們對期刊的縱深性要求。”他們認為,該形制產生了輻射性后果:繼起的《語絲》《努力周報》《湘江評論》等刊,“都有著與《每周評論》面孔相似的文本樣貌”。(吳永貴、林英:《〈每周評論〉的媒介空間與評論維度》,《中國編輯》2018年第2期)
[66][67] 記者:《編余閑話三則》,《晨報副刊》1922年11月11日。
[69] 《學藝部啟事》,《晨報副刊》1925年9月30日。
[71][81] 1925年5月30日、3月31日魯迅致許廣平函,《魯迅著譯編年全集》第6卷,第241、146頁。
[72] 這十六位“長期撰稿”的作者是周作人、錢玄同、江紹原、林語堂、魯迅、川島、孫斐君(斐君女士)、王品青、章衣萍、吳曙天(曙天女士)、孫伏園、李小峰、馮沅君(淦女士)、顧頡剛、春臺、蔡漱六(林蘭女士)。見川島:《憶魯迅先生和〈語絲〉》,《魯迅回憶錄(散篇)》,第286頁。
[73] 姜濤:《從綠波社到無須社——“文學青年”的聚合、位置及人格造型》,《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國的文學與青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14–150頁。
[74] 記者:《理想中的日報附張》,《京報副刊》1924年12月5日第1號。這篇文章里譏諷的“老實不客氣的討論無線電的學問”,指的應該就是當時陳秉騏在孫的老東家《晨報副刊》連載的《無線電通信距離之研究》,可見孫伏園創辦《語絲》和《京副》,從一開始就是以《晨副》為他者的。
[75] 1960年12月13日周作人致鮑耀明函,《周作人與鮑耀明通信集》,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6頁。該函未署年月,此書編者認為寫于8月,誤。
[76] 孟超認為,副刊應以“風趣、輕松、短小精悍、引人入勝的筆調”來傳達思想和談論問題;卜少夫比較中日報紙的差別,認為日文報紙“無論在戰前以及戰時,都比我們的紙面上所顯示的要活潑生動得多”,其原因“也沒有什么特殊之處,除多用銅鋅版,編排花式多一點以外,那就是文章短與題目多。”胡喬木則認為,副刊上的文章“寫得愈長看得越少”,甚至將“短些!再短些!”的寫作號召與“群眾觀點”聯系到一起。見孟超:《副刊的趣味性》,卜少夫:《副刊的形式與內容》,胡喬木:《短些!再短些!》,王文彬編:《中國報紙的副刊》,第34、47、59–60頁。
[77] 春苔:《閑話與草畫》,《北新》1926年11月3日第13期。
[78] 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魯迅全集》第6卷,第253–254、258頁。
[79] 黃裔:《追本溯源:重探現代評論派》,《中國文學研究》1991年第4期。
[82] 史蟫:《記語絲社》,《文友》1943年7月15日第1卷第5期。
[83] 趙林:《多元語境制約下的〈語絲〉周刊》,《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35卷第3期。
(轉載自“論文衡史”微信公眾號)
- 《捧血者——詩人辛勞》新書首發式暨學術研討會在內蒙古文學館舉辦[2022-06-23]
- 趙普光:不“冷”不“熱”的子善先生[2022-06-21]
- 中國現代作家書信的“公”與“私”[2022-06-06]
- 馮至:一個沉思者的精神超越與生命探求[2022-05-18]
- 中國現代文學經典重釋的路徑探究[2022-05-16]
- 徐玉諾的真性情[2022-05-07]
- 姜濤:凱約嘉湖上一只小船的打翻[2022-04-24]
- 新女聲:晚清白話報章與現代女性意識的萌芽[2022-04-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