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桃不必拒舊符 ——在《學(xué)衡》創(chuàng)刊一百周年之際訪張寶明教授
1922年1月,《學(xué)衡》雜志在南京創(chuàng)刊,輾轉(zhuǎn)十年后,終因內(nèi)外交困而停刊。三十年后,有人請(qǐng)《學(xué)衡》雜志主編吳宓撰述創(chuàng)刊始末,得其回復(fù):“《學(xué)衡》社的是非功過(guò),澄清之日不在現(xiàn)今,而在四五十年后。”
時(shí)值《學(xué)衡》創(chuàng)刊百年,張寶明教授以《學(xué)衡》典存昭示“斯文在茲”(《斯文在茲:〈學(xué)衡〉典存》,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為我們重審學(xué)衡派的是非得失、思考學(xué)衡派的當(dāng)代啟示提供了一個(gè)機(jī)會(huì)。《中華讀書(shū)報(bào)》就此專(zhuān)訪了張寶明教授。
中華讀書(shū)報(bào):您先后主編《新青年》讀本多種與《斯文在茲——〈學(xué)衡〉典存》,呈現(xiàn)近代中國(guó)兩股截然相對(duì)的思潮,有著什么樣的考量?
張寶明:有兩點(diǎn)考量。第一,《學(xué)衡》宛如一艘沉潛多年且漸行漸遠(yuǎn)的“人文集結(jié)號(hào)”,百年了,是時(shí)候打撈了!而且需要我們耐心地打撈與梳理。作為近代中國(guó)“人文方舟”的《學(xué)衡》,如何評(píng)價(jià),我們需要跳出“總把新桃換舊符”的傳統(tǒng)窠臼。班固《西都賦》有言曰:“方舟并鶩,俯仰極樂(lè)。”
第二,很多同仁看到這個(gè)編選本后會(huì)想:開(kāi)始轉(zhuǎn)向了?其實(shí)不然。長(zhǎng)期以來(lái),我將《新青年》作為研究對(duì)象,而且編選過(guò)三種不同形式的《新青年》讀本。我研究《新青年》的過(guò)程始終有一個(gè)揮之不去的“影子”,就是《學(xué)衡》,它是《新青年》的伴生物。所以,走進(jìn)《學(xué)衡》是必然的。
過(guò)去,我們?cè)鵀椤缎虑嗄辍肪庍x本擬過(guò)一句話的宣傳語(yǔ):“不讀《新青年》,就難以讀懂近代中國(guó)。”如果回到《學(xué)衡》,完全可以說(shuō):“在這里,讀懂中國(guó)與世界。”《學(xué)衡》有很多牽掛,與《學(xué)衡》相遇也就有了一層牽掛的牽掛。
就這套書(shū)而言,首先要感謝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六點(diǎn)分社倪為國(guó)先生的約稿。沒(méi)有倪先生的執(zhí)著,就沒(méi)有今天這個(gè)“斯文在茲”之“典存”的面世。而就本人而言,做這套書(shū)有三個(gè)“心動(dòng)”的因素。一是《學(xué)衡》在當(dāng)年文言文大勢(shì)已去的背景下,以“舍我其誰(shuí)”的氣魄主動(dòng)擔(dān)當(dāng)起挽大廈于將傾的文化復(fù)興責(zé)任,充分彰顯了“文不在茲乎”的悲壯,充盈著滿滿的人文悲情;二是《學(xué)衡》以“明其源流”的方式向“與日月同輝的經(jīng)典致敬”,貫穿著“理解”“認(rèn)同”“同情”之人文溫情;三是《學(xué)衡》在“家事國(guó)事”的關(guān)懷中,更有“天下”“世界”的視野和胸懷,流布出人文承諾的多情。這“三情”合起來(lái)看,不能不說(shuō)《學(xué)衡》的文字是20世紀(jì)以來(lái)彌足珍貴的文化資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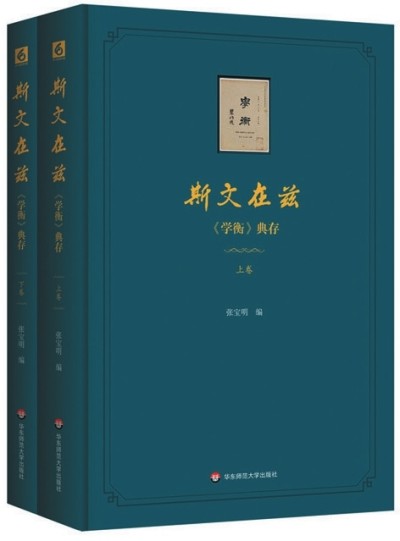
《斯文在茲——〈學(xué)衡〉典存》,張寶明編,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21年8月第一版,398.00元
中華讀書(shū)報(bào):請(qǐng)問(wèn)您說(shuō)《學(xué)衡》留下的文字可以幫我們“讀懂中國(guó)與世界”的含義是什么?西學(xué)東漸潮流影響下的學(xué)衡派同樣在“睜眼看世界”,卻表現(xiàn)為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者,您覺(jué)得該如何理解這一反差?
張寶明:我們必須看到一個(gè)歷史事實(shí),《學(xué)衡》的擔(dān)綱者都是學(xué)業(yè)有成的海歸。他們懷揣赤子之心回到祖國(guó)。按常理,無(wú)論是留學(xué)東瀛還是留學(xué)歐美,一定是以“他山之石”的心態(tài)面對(duì)世界,在中西文化的情理中做出伯仲、軒輊的判斷。然而,學(xué)衡派面對(duì)當(dāng)年的“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吶喊,始終保持了一份冷靜與警惕,不忘守護(hù)自家本色。這個(gè)本色是不以他者為“喜”,亦不以“己”家為“悲”,而是在喜憂參半、憂樂(lè)圓融中建構(gòu)起中西互鑒、古今匯通的文化通約,他們?cè)诒J刂髁x的標(biāo)簽下承載著以“退”為“進(jìn)”、以“守”為“攻”的開(kāi)放維新之道。
與新青年派中的“萬(wàn)事不如人”“悔過(guò)自新”甚至全盤(pán)西化不同,學(xué)衡派的內(nèi)省從一開(kāi)始就呈現(xiàn)出呵護(hù)文化、維護(hù)遺產(chǎn)的自覺(jué)特征。固然,新青年派知識(shí)同仁也有過(guò)“取法乎上得乎其中”“矯枉必須過(guò)正”的自我開(kāi)脫,但總的文化傾向上卻不能不說(shuō)與《學(xué)衡》諸君的文化揀擇是格格不入的。就《學(xué)衡》的“中正”而言,今天看來(lái),它更為符合人類(lèi)文化發(fā)展的基本規(guī)律。正是這一點(diǎn)上,我們看到了《學(xué)衡》所呈現(xiàn)的開(kāi)放,不是“去中國(guó)化”,更不是“全盤(pán)西化”。進(jìn)一步說(shuō),即是在不分軒輊、難為伯仲的基礎(chǔ)上,打通域界、族界與國(guó)界,以與人類(lèi)文明共同體的心態(tài)漸行漸近。這顯然也是一種求真經(jīng)、悟真道并“止于至善”的文化心態(tài)。
順便說(shuō)一句,《學(xué)衡》與《新青年》在中國(guó)要走向現(xiàn)代化的意識(shí)上都表現(xiàn)出極大的自信,《學(xué)衡》的自信表現(xiàn)為內(nèi)斂的、低調(diào)的、謙和的自信,具有深沉優(yōu)容、從容淡定、大氣寬容的人文氣息。它的自信來(lái)源于深層底蘊(yùn)中的內(nèi)涵與鑲嵌在骨子里的硬核,是一種自然而然的輻射與散發(fā)。這里,我們可以稱(chēng)其“有節(jié)(制)的自信”。《新青年》的自信則表現(xiàn)為張揚(yáng)的、高調(diào)的、外傾的色彩,時(shí)不時(shí)流布出激進(jìn)、超能的積極銳氣。對(duì)此,我們可以稱(chēng)之為“無(wú)制(衡)的自信”。歸根結(jié)底,在學(xué)衡派眼中,勸諭人類(lèi)節(jié)制乃是文化的應(yīng)有之義。
在學(xué)衡派看來(lái),從事新文化運(yùn)動(dòng)者就是挾西方文化以令國(guó)人的典型“自信”者,這一以西方文化為上的新青年派恰恰不是“自信”,而是“他信”。在“信他”還是“信己”這一選項(xiàng)上,學(xué)衡派的文化心態(tài)呈現(xiàn)的乃是一種厚重、穩(wěn)健、中正的消極自信。骨子里的自信流布在創(chuàng)刊號(hào)的簡(jiǎn)章上:“昌明國(guó)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píng)之職事。”由此而來(lái)的文化“懷柔”同樣能贏得八方來(lái)朝的“遠(yuǎn)人”格局。“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說(shuō)的就是這一文化景象。
中華讀書(shū)報(bào):《學(xué)衡》以倡導(dǎo)新人文主義為主導(dǎo),請(qǐng)問(wèn)新人文主義與人文主義有什么區(qū)別?進(jìn)而請(qǐng)問(wèn),《學(xué)衡》倡導(dǎo)的新人文主義與《新青年》主導(dǎo)的人道主義有什么不同?
張寶明:首先,我想糾正一個(gè)觀點(diǎn),《學(xué)衡》倡導(dǎo)的是人文主義,而非倡導(dǎo)“新人文主義”。“新人文主義”作為一個(gè)名詞并沒(méi)有被學(xué)衡派所提及,而是后人在概括白璧德的人文主義思想時(shí)所提出的,因此也就不存在人文主義和新人文主義的區(qū)別。如果硬要作出區(qū)別,也可以說(shuō)是時(shí)代價(jià)值觀念的滲透而已。在本質(zhì)意義二者還是源流合轍、一脈相承。
事實(shí)上,倒是如你所說(shuō),值得一提的還是《新青年》與《學(xué)衡》因?qū)umanism的不同理解、譯介與倚重而出現(xiàn)的分庭抗禮之思想張力。文言與白話之爭(zhēng)其實(shí)是這兩種思想譜系話語(yǔ)權(quán)爭(zhēng)奪的外化。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中,通過(guò)新青年派與學(xué)衡派的詮釋發(fā)揮,人道主義與人文主義成為“Humanism”兩大主流譯法,而新青年派與學(xué)衡派也依據(jù)“人道主義”與“人文主義”成為“五四”時(shí)期并峙的思想雙峰。
回到“五四”的歷史與文化語(yǔ)境,由于人道主義在反對(duì)封建意識(shí)形態(tài)的過(guò)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啟蒙意義,因此,它從一開(kāi)始就天然地受到新文化倡導(dǎo)者的擁戴。對(duì)人道主義的重點(diǎn)引介,新青年派是從人本身,從人的生命價(jià)值出發(fā)的,他們對(duì)于勞苦大眾不幸的同情,重心不是政治與經(jīng)濟(jì),而是源自于對(duì)人的價(jià)值和尊嚴(yán)的喪失的關(guān)注。“思想藝文改造”呼喚“人”的到來(lái),與“人的運(yùn)動(dòng)”“人的覺(jué)醒”“人的發(fā)現(xiàn)”等“人”同氣相求。一時(shí)間,人道主義成為文學(xué)革新運(yùn)動(dòng)中最為堅(jiān)挺的主心骨,也是新文學(xué)家和思想先驅(qū)“言必稱(chēng)”的啟蒙工具。
然而,那些為新青年派尊崇的人物在學(xué)衡派看來(lái)卻是一些不安定的靈魂,認(rèn)為他們?cè)谒枷肷戏謱僮匀恢髁x、浪漫主義和實(shí)驗(yàn)主義,是西方近代以來(lái)人道主義的拼盤(pán)。于是,以批判人道主義著稱(chēng)的人文主義大師白璧德在學(xué)衡派的推介下登場(chǎng)。白璧德堅(jiān)守的是一種調(diào)和、克制、收斂的規(guī)訓(xùn),反對(duì)偏激、過(guò)度或極端的做派。學(xué)衡派中的吳宓、梅光迪以及后來(lái)的新月派作家梁實(shí)秋等在美國(guó)留學(xué)期間深受其影響, 最終成為其忠實(shí)信徒和傳播者。吳宓曾對(duì)人道主義與人文主義進(jìn)行了言簡(jiǎn)意賅的比較,“人道主義主張兼愛(ài),與人文主義 Humanism 之主張別擇而注重修身克己者截然不同”。沿著白璧德的路線,學(xué)衡派認(rèn)可的藝術(shù)立身之“古典”“中庸”“自制”,帶有一定的“發(fā)乎情止乎禮”意味。
中華讀書(shū)報(bào):記得您曾在一篇文章中這樣描述20世紀(jì)思想文化史上兩個(gè)重要學(xué)派的差異:“學(xué)衡派,為靈魂尋找故鄉(xiāng)的仁人;新青年派,為故鄉(xiāng)尋找靈魂的志士。”能否對(duì)此做進(jìn)一步的解讀?
張寶明:這個(gè)問(wèn)題其實(shí)在本質(zhì)上是一個(gè)路徑依賴(lài)與選擇問(wèn)題。新青年派與學(xué)衡派都懷有為中國(guó)現(xiàn)代化之路尋找出路的同氣相求之抱負(fù),只是在那個(gè)時(shí)代救世濟(jì)民、救亡圖存之路應(yīng)該怎么走,何謂正道的問(wèn)題上存在分歧:一方高歌的是“歸家”,一邊引吭的是“遠(yuǎn)方”。換句話說(shuō),新青年派是要在打破傳統(tǒng)以后的重組,舊派是要在傳統(tǒng)基礎(chǔ)上的意義尋繹。無(wú)論是文化觀念的對(duì)峙還是文學(xué)理論的交鋒,都是圍繞文化的整合方式進(jìn)行的。
“打倒”或說(shuō)“推倒”之后“建設(shè)”,這是新青年派慣用的話語(yǔ),也是他們內(nèi)在的邏輯。他們認(rèn)為固有的文化中的大部已經(jīng)失去保護(hù)“吾人”的功能,所以我們需要來(lái)一個(gè)徹底的覺(jué)悟,在換血式的“革命”中尋繹到讓我們仰仗的新文化。這個(gè)覺(jué)悟是“徹底”的,并從中悟出對(duì)舊文學(xué)、舊文化、舊倫理、舊政治等等一切之“舊”的家當(dāng)破壞、顛覆的必要性。“要擁護(hù)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duì)孔教,禮法,貞節(jié),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hù)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duì)舊藝術(shù),舊宗教。要擁護(hù)德先生又要擁護(hù)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duì)國(guó)粹和舊文學(xué)。”從今以后的“新”方案,乃是科學(xué)的、民主的“政治”,科學(xué)的、民主的“藝術(shù)”,科學(xué)的、民主的“文化”,科學(xué)的、民主的“文學(xué)”。冠以“科學(xué)的”“民主的”頭銜就可以暢通無(wú)阻。“科學(xué)的”“民主的”修飾詞就讓他們要立意的內(nèi)容煥然一新。而凡是“新”則必然優(yōu)于“舊”、勝于“舊”。
與新青年派不同,學(xué)衡派諸公更樂(lè)意從原典上尋繹精神世界的皈依。在他們看來(lái),只有這份文化的“背景”才厚重,只有這份文化的“定力”才可靠。在“可愛(ài)”與“可信”之間,他們更傾向于后者。他們認(rèn)為四書(shū)五經(jīng)已經(jīng)成為經(jīng)得起檢驗(yàn)的元典,《詩(shī)經(jīng)》《離騷》等千古流傳的文學(xué)作品已經(jīng)深入人心。這些經(jīng)典乃是文化積淀、深層結(jié)構(gòu),不是那些隨風(fēng)飄蕩的時(shí)髦、可愛(ài)之流可以比擬。而這一切,又都?xì)w結(jié)為對(duì)文化之“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信奉,對(duì)文學(xué)教化育人功能的領(lǐng)悟。
在學(xué)衡派,有規(guī)訓(xùn)才能對(duì)其他人的自由和權(quán)利給予足夠的尊重和保護(hù)。這里就形成了是以個(gè)人為本位還是以群體為本位的差異,也產(chǎn)生了強(qiáng)調(diào)責(zé)任還是權(quán)利的分歧。歸根結(jié)底,雙方在思維方式上,一個(gè)是發(fā)散、外傾的、“積極的”、高調(diào)的;一個(gè)是收斂、內(nèi)傾的、“消極的”、低調(diào)的。在前者,個(gè)性的張揚(yáng)、話語(yǔ)的擴(kuò)張是其根本特征;在后者,自我的規(guī)訓(xùn)和內(nèi)心的自律構(gòu)成了主體。“學(xué)衡派”的收斂、內(nèi)傾、“消極”不是不要進(jìn)化,不是反對(duì)創(chuàng)造。他們主張創(chuàng)造是在傳統(tǒng)意義資源基礎(chǔ)上的創(chuàng)造,不是無(wú)中生有,而是“有”中生有:在“因襲”的平臺(tái)上發(fā)揮,在“摹仿”的前提下創(chuàng)造。當(dāng)然“因襲”不是“抄襲”,“摹仿”的目的也不是停滯于臨摹和仿真,目標(biāo)還是要推陳出新。這是一種以退為進(jìn)的守成戰(zhàn)略。
新青年派不能容忍這樣的一種不死不活的惰性,他們主張個(gè)性的張揚(yáng)和發(fā)散,積極、激進(jìn)地超越,是要在“前無(wú)古人”“后無(wú)來(lái)者”之空前絕后的邏輯上抽刀斷水。于是,推翻、推倒、打倒、革命之類(lèi)的詞匯不絕于耳。以西學(xué)取代中學(xué),以白話取代文言,以自由體取代格律體,以“她”替代“伊”,“此國(guó)人所以混淆迷亂而不能自已者也”。然而,“吾華為數(shù)千年禮儀之邦,其間因風(fēng)俗禮制人倫維系之久長(zhǎng),故節(jié)制的、個(gè)人的、消極的倫理道德,莫不完備”。這里所謂的“節(jié)制的”即是說(shuō)規(guī)訓(xùn)和收斂;所謂“個(gè)人的”即是內(nèi)傾和內(nèi)化;所謂“消極的”即是謙遜的、低調(diào)的,為規(guī)避驕囂、魯莽而設(shè)。在這樣一個(gè)“莫不完備”的文化面前,我們?nèi)舨患艺渥詳?shù),反“舍近求遠(yuǎn)”豈不是“棄家雞而愛(ài)野鶩者也”。在這樣的一個(gè)思維邏輯下,我們看到:當(dāng)新青年派在白話文凱旋之高歌縈繞于耳之際,也正是低調(diào)之學(xué)衡派自命清高、“舍身成仁”的悲壯之時(shí)。
中華讀書(shū)報(bào):我們還注意到,您在《斯文在茲》序言中將學(xué)衡派與新青年派的糾葛喻為“紳士”對(duì)抗“猛士”。歷史上,“猛士”們引導(dǎo)了中國(guó)的啟蒙與革命,“紳士”們的作用又該如何評(píng)價(jià)?
張寶明:我們知道,《學(xué)衡》創(chuàng)刊的1922年已經(jīng)是白話文大獲全勝、《新青年》凱歌勁吹的時(shí)代。1921年,經(jīng)過(guò)《新青年》的鼓與呼,民間與官方多年的互濟(jì),北洋政府一紙公文將居于“廂房”的白話文移至華夏“堂屋”,史稱(chēng)新文化運(yùn)動(dòng)。正是在這個(gè)意義上,我借用魯迅先生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這句話來(lái)概括新青年派的精神氣質(zhì)。
相對(duì)于“猛士”,以守成為基調(diào)的學(xué)衡派同仁則有一種“明知山有虎”之責(zé)任擔(dān)當(dāng)。他們冒著“不識(shí)時(shí)務(wù)”之嫌,可能會(huì)成為社會(huì)的笑柄,甚至被看成不自量力、螳臂當(dāng)車(chē),但在他們溫文爾雅的“斯文”背后透露了對(duì)華夏文明的堅(jiān)守。
針對(duì)《新青年》諸君看似策略的“矯枉必須過(guò)正”與“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心理,《學(xué)衡》同仁有一種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憤懣。對(duì)文白之爭(zhēng)中“不容討論”的做法、新舊之辯中的“絕無(wú)調(diào)和之余地”的做派,以及由此而來(lái)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之非此即彼的思維定式,他們口誅筆伐。
在《學(xué)衡》那里,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中反對(duì)調(diào)和、折中,倡導(dǎo)“過(guò)正”的偏執(zhí)言行,完全違背了人類(lèi)文明進(jìn)程中規(guī)約、揀擇、中和、謙卑的人文向度。不容討論、不容調(diào)和的下一步就是“舊的不去新的不來(lái)”的破舊立新思維。立新不必破舊,新的只有在過(guò)去積累的基礎(chǔ)上才能推出。因此,當(dāng)新文化同仁以西方文化作為壓倒式價(jià)值觀來(lái)取代擁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國(guó)文化時(shí),學(xué)衡派同仁告誡他們,正道的人文發(fā)展觀應(yīng)該是互助、互鑒、互濟(jì),在并行不悖中協(xié)力前行,作為共同體的人類(lèi)多元與多彩的文明不應(yīng)是誰(shuí)打倒誰(shuí)、誰(shuí)壓倒誰(shuí)、誰(shuí)消泯誰(shuí),“我者”與“他者”、“新”與“舊”共存更為符合并立競(jìng)進(jìn)的文化格局。
中華讀書(shū)報(bào):《學(xué)衡》核心人物吳宓先生曾在20世紀(jì)60年代斷言:“《學(xué)衡》社的是非功過(guò),澄清之日不在現(xiàn)今,而在四五十年后。”您認(rèn)為這在今天得到印證了嗎?
張寶明:吳宓先生的斷言,隱含著一個(gè)問(wèn)題:只有當(dāng)歷史認(rèn)知到《新青年》派的不足,重新檢討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得失,《學(xué)衡》的意義才會(huì)顯現(xiàn)出來(lái)。《新青年》與《學(xué)衡》的對(duì)峙帶給近代史一種張力,其意義在于:要建構(gòu)形成一個(gè)政治共同體、一個(gè)學(xué)術(shù)共同體、一個(gè)倫理共同體都非一日之功。這種歷史張力一直延續(xù)到今天。從這個(gè)意義上說(shuō),《新青年》和《學(xué)衡》在很多方面是相互發(fā)明、互為補(bǔ)充的。
百年后的今天,重讀《學(xué)衡》,我想說(shuō)的是,《學(xué)衡》不但不是民主、科學(xué)的阻礙者、反對(duì)者,相反倒是民主、科學(xué)的積極擁躉。在他們保守的名聲下,其顯示出的開(kāi)放視野絲毫不亞于《新青年》。就家國(guó)情懷和世界胸懷來(lái)看,也可以說(shuō)有過(guò)之而無(wú)不及。只是他們以中國(guó)傳統(tǒng)的“過(guò)猶不及”的維度來(lái)丈量著自己前進(jìn)的腳步而已。
中華讀書(shū)報(bào):好的,還有一個(gè)問(wèn)題。吳宓先生曾言:“舊者不必是,新者未必非。”新舊問(wèn)題應(yīng)該說(shuō)是《新青年》與《學(xué)衡》爭(zhēng)執(zhí)最大的焦點(diǎn)所在。今天我們?nèi)绾卫斫膺@一說(shuō)法的意義?
張寶明:這個(gè)問(wèn)題問(wèn)得非常好,尤其是在當(dāng)下。何者為新?何者為舊?這不是一個(gè)楚河漢界的問(wèn)題。新舊可以對(duì)峙,但并不必然意味著替代。從《詩(shī)經(jīng)》上“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詩(shī)句、孔老先生的名言“君子和而不同”,聯(lián)想到從古希臘就開(kāi)始的箴言“弓”與“箭”的關(guān)系,再到德國(guó)哲學(xué)家卡西爾關(guān)于“對(duì)立造成和諧”的“六弦琴”關(guān)系解讀,都能佐證這一點(diǎn):新,不意味進(jìn)步;舊,不意味落伍。梁實(shí)秋曾這樣直截了當(dāng)?shù)卣f(shuō):“文學(xué)并無(wú)新舊可分,只有中外可辨。”對(duì)此,吳芳吉、曹慕管、吳宓都專(zhuān)門(mén)撰文予以辨析。他們認(rèn)為,嚴(yán)格意義上“新文學(xué)一詞,根本不能成立”。周作人有一個(gè)“新舊”說(shuō):“新舊這名稱(chēng),本來(lái)很不妥當(dāng),其實(shí)‘太陽(yáng)底下何嘗有新的東西?’思想道理,只有是非,并無(wú)新舊。”真正有意義和價(jià)值的東西,本來(lái)就并不需要打上“新”的標(biāo)簽來(lái)增值,更不會(huì)因?yàn)闀r(shí)間的久遠(yuǎn)而失色,反之亦然。
在學(xué)衡派諸君看來(lái),對(duì)“吾國(guó)文化”中“可與日月?tīng)?zhēng)光之價(jià)值”的經(jīng)典視而不見(jiàn),這無(wú)異是文化上的“自殘”。舍近求遠(yuǎn)不如近水樓臺(tái),真正的人文之道在中國(guó)本土悠長(zhǎng)、光輝。在喜新厭舊、厚今薄古成為常態(tài)之日,吳宓“舊者不必是,新者未必非,然反是則尤不可”的判斷,不能不說(shuō)是學(xué)衡派留給我們的珍貴遺產(chǎn)之一。
- 汪榮祖:另一種新文化運(yùn)動(dòng)[2022-02-14]
- 國(guó)史大義、宗綱所在:學(xué)衡祭酒柳詒徵的史學(xué)精神[2022-02-11]
- 黃克武:嚴(yán)復(fù)、林紓與學(xué)衡派[2022-02-07]
- 柳門(mén)高足景昌極[2022-01-29]
- 劉伯明:理解學(xué)衡派的另一線索[2022-01-26]
- 倔強(qiáng)的少數(shù):學(xué)衡派在東南大學(xué)[2022-01-25]
- 《新青年》與“精神股份制”打造的金字招牌[2022-01-17]
- 許紀(jì)霖:不合時(shí)宜的堂吉訶德[2021-1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