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晨曦時(shí)刻的兒女”燭照我們內(nèi)心

20世紀(jì)70年代末,沈從文在黃永玉位于京新巷的家中。 出版社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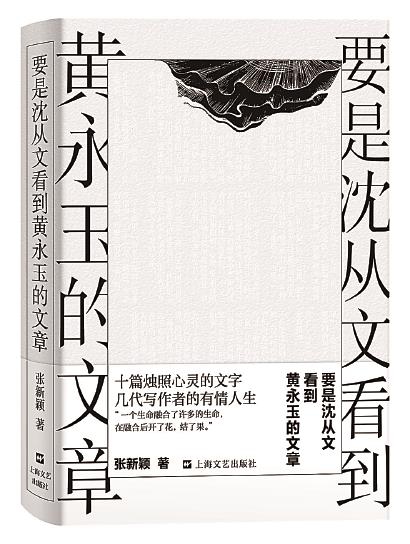
《要是沈從文看到黃永玉的文章》張新穎 著上海文藝出版社
“一個(gè)人寫(xiě)作時(shí),他最直接的對(duì)象并非他的同輩,更不是其后代,而是其先驅(qū)。是那些給了他語(yǔ)言的人,是那些給了他形式的人。”
學(xué)者張新穎引用布羅茨基的這番話,為黃永玉的寫(xiě)作作了一個(gè)注腳:在停不下來(lái)的懷念中,黃永玉通過(guò)寫(xiě)作來(lái)喚回他的表叔沈從文。而他寫(xiě)作《要是沈從文看到黃永玉的文章》一書(shū),又何嘗不是?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張新穎對(duì)黃永玉、沈從文的解讀,以及對(duì)那些“晨曦時(shí)刻的兒女”的寫(xiě)作源泉的追溯,之于當(dāng)代文學(xué)創(chuàng)作有著重要意義,也滋養(yǎng)著當(dāng)下的讀者。而那些關(guān)于生、死、愛(ài)的文學(xué)母題的探討,更是讓我們獲得一種內(nèi)心的燭照。
他是一個(gè)“多情”的人
我們的談話像流水,流過(guò)許許多多的人、許許多多的事
讀書(shū)周刊:您很多年前就開(kāi)始研究沈從文先生,先寫(xiě)了《沈從文的后半生》,后來(lái)又寫(xiě)了《沈從文的前半生》。如今寫(xiě)黃永玉,沈從文與黃永玉既是表叔侄又是知己,所以您關(guān)注黃永玉可以說(shuō)是自然而然的事吧?
張新穎(復(fù)旦大學(xué)中文系教授,文學(xué)批評(píng)家,《要是沈從文看到黃永玉的文章》作者):是的,也是一種機(jī)緣巧合。2014年8月,我受到李輝老師(作家、出版策劃人)的邀請(qǐng),去參加黃永玉老先生的90歲壽宴。我以前沒(méi)有見(jiàn)過(guò)黃先生,這么好的機(jī)會(huì),我怎么會(huì)錯(cuò)過(guò)?黃先生一見(jiàn)面就和我聊起《沈從文的后半生》,他說(shuō):“事情我大都知道,但還是停不下來(lái),讀到天亮,讀完了。原先零零碎碎的東西,你完整寫(xiě)出來(lái),就固定下來(lái)了。”
宴席第二天,我又和黃先生聊天,從上午10點(diǎn)一直聊到傍晚。黃先生的記憶力好得驚人,我們聊到他那時(shí)正在寫(xiě)的自傳體長(zhǎng)篇小說(shuō)《無(wú)愁河的浪蕩漢子》,聊到他的家鄉(xiāng)、他的家人、他的老朋友,當(dāng)然也聊到沈從文,我們的談話像流水,流過(guò)許許多多的人、許許多多的事,我把他的話幾乎原汁原味地還原成了一篇文章。
讀書(shū)周刊:您怎樣解讀黃永玉?
張新穎:我還是從《無(wú)愁河的浪蕩漢子》說(shuō)起吧。黃永玉走到哪里寫(xiě)到哪里,出現(xiàn)什么就寫(xiě)什么。他的記憶清晰而完整,實(shí)為罕見(jiàn),我想是因?yàn)樗?jīng)歷的人、事、物,在他看來(lái)都和他密切相關(guān),他對(duì)這些都有感情。
這話聽(tīng)起來(lái)沒(méi)有什么意思,其實(shí)卻很關(guān)鍵。因?yàn)橛洃浟Τヌ焐牟糠郑€有后天的運(yùn)作,譬如你為什么記住了這件事而沒(méi)有記住那件事,就是一種選擇和舍棄。這就是黃永玉的特別之處,他不篩選,凡是出現(xiàn)在他生命中的,都和他的生命產(chǎn)生關(guān)系,由關(guān)系產(chǎn)生感情。所有的經(jīng)歷,不僅是好的,也包括壞的,都能夠被吸收利用并轉(zhuǎn)化為生命的養(yǎng)分。
讀書(shū)周刊:所以可以見(jiàn)出黃永玉的一個(gè)特質(zhì),是“多情”,對(duì)于事物的多情。
張新穎:是的,就是他自己說(shuō)的“對(duì)世界的‘多謝’”。而他的過(guò)目不忘和他的多情,正是不竭的創(chuàng)作源泉。
他就是他書(shū)中的主人公,實(shí)打?qū)嵉赜媚_走路,一步一步踩在堅(jiān)實(shí)的地面上,有分辨力,有主心骨,有實(shí)的經(jīng)驗(yàn),過(guò)真的生活。就如同書(shū)中序子的父親告誡的:“心腸要硬一點(diǎn),過(guò)日子要淡一點(diǎn),讀書(shū)要狠一點(diǎn)。”
讀書(shū)周刊:這句告誡,對(duì)我們也深有啟發(fā)。
張新穎:黃永玉的家人、家鄉(xiāng),都是他的一筆寶貴“財(cái)產(chǎn)”,給他打下人生的底子。
黃永玉年輕時(shí)來(lái)到家鄉(xiāng)之外的世界,在人、事、物的對(duì)比和參照之下,他才有意識(shí)地認(rèn)識(shí)并肯定家鄉(xiāng)的不同之處,而那個(gè)家鄉(xiāng)打底的自我,也逐漸清楚地顯現(xiàn),被自覺(jué)地認(rèn)識(shí)、自覺(jué)地肯定。然而他的精神世界并沒(méi)有在這里打圈圈,正如“無(wú)愁河”是一條大河,其豐沛的源頭讓它更加寬闊和長(zhǎng)遠(yuǎn),也讓受它滋養(yǎng)的人敞開(kāi)生命而不是封閉生命。
對(duì)我們都有所啟示的是,對(duì)新鮮事物、對(duì)未知世界,黃永玉懷有強(qiáng)烈的好奇,他的心態(tài)時(shí)刻敞開(kāi),這體現(xiàn)在他的文學(xué)中、他的木刻創(chuàng)作和繪畫(huà)創(chuàng)作中。
他筆下的沈從文,善良從容
他欽佩表叔精神層面的堅(jiān)韌,欣賞表叔從容不迫的人生姿態(tài)
讀書(shū)周刊:黃永玉這樣一個(gè)“寬廣而好奇”的人,又怎樣評(píng)價(jià)他的表叔沈從文呢?
張新穎:沈從文是黃永玉寫(xiě)得最多、寫(xiě)得最豐富生動(dòng)的一個(gè)人物。黃永玉不時(shí)在文字中流露,他欽佩表叔精神層面的堅(jiān)韌,欣賞表叔從容不迫的人生姿態(tài)。
黃永玉寫(xiě)沈從文,不愿意用溢美之詞,更不愿意將其拔高至如偉人一般高聳入云。他筆下的沈從文,善良,從容,懂得欣賞美,沉溺于創(chuàng)造,盡管平實(shí),實(shí)際上卻樹(shù)起一個(gè)高高的人生標(biāo)桿。
讀書(shū)周刊:在他眼里,表叔更像是一顆星星。
張新穎:黃永玉寫(xiě)過(guò),他(沈從文)不過(guò)是一顆星星,一顆不仰仗什么而自己發(fā)光的星星。黃永玉明白沈從文說(shuō)過(guò)的話——我從來(lái)沒(méi)想過(guò)“突破”,我只是“完成”。他覺(jué)得沈從文“非常非常的平常”,他的人格、生活、情感、工作和與人相處的方式,都在平常的狀態(tài)運(yùn)行,“他就像水那么平常,永遠(yuǎn)向下,向人民流動(dòng),滋養(yǎng)生靈,長(zhǎng)年累月生發(fā)出水滴石穿的力量。”黃永玉還曾在沈從文的陵園刻了一塊石碑,上頭寫(xiě)著:“一個(gè)士兵,要不戰(zhàn)死沙場(chǎng),便是回到故鄉(xiāng)。”我想黃永玉覺(jué)得他和他的表叔,都是“戰(zhàn)場(chǎng)”上的“士兵”。
讀書(shū)周刊:黃永玉有一部紀(jì)念湘西山水和人物的長(zhǎng)篇散文《太陽(yáng)下的風(fēng)景》,文末有一段話令人難以忘記,忍不住想讀一讀:“我們那個(gè)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們產(chǎn)生奔赴他鄉(xiāng)的獻(xiàn)身的幻想。從歷史角度看來(lái),這既不協(xié)調(diào)且充滿悲涼,以至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歲時(shí)背著小小包袱,順著小河,穿過(guò)洞庭去‘翻閱另一本大書(shū)’的。”這兩個(gè)人都對(duì)漂泊情有獨(dú)鐘,他們身上是否有很多相似的特質(zhì)?
張新穎:沈從文隨著軍營(yíng)在湘西山水里浸染個(gè)透,然后獨(dú)自一人告別家鄉(xiāng),前往北京;黃永玉也早早離開(kāi)父母,到江西、福建一帶流浪。
可以說(shuō)他們很相似——在漂泊中成長(zhǎng),在漂泊中尋找打開(kāi)藝術(shù)殿堂大門(mén)的那把鑰匙。也可以說(shuō)他們有很大不同——沈從文到達(dá)北京之后,就基本確定了未來(lái)的生活道路,并且在幾年之后以自己的才華引起了徐志摩、胡適的青睞,從而一個(gè)湘西鄉(xiāng)下人在以留學(xué)歐美知識(shí)分子為主體的京派文人中占據(jù)了重要的一席之地;黃永玉則是不同的,由于時(shí)代、年齡、機(jī)遇和性格的差異,他還不像沈從文那樣,一開(kāi)始就有一種既定目標(biāo),他比沈從文的漂泊更為頻繁,眼中的世界也更為廣泛。而在性情上和適應(yīng)能力上,他也許比沈從文更適合漂泊。
重新理解那個(gè)文學(xué)世界
沈從文的文學(xué)和他的文物研究,都是他“有情”的表現(xiàn)
讀書(shū)周刊:有一個(gè)一開(kāi)始就想問(wèn)的問(wèn)題,這本書(shū)的標(biāo)題很有意思,似乎是一個(gè)設(shè)問(wèn),想要通過(guò)“要是沈從文看到黃永玉的文章”這個(gè)假設(shè),去尋找一個(gè)答案、解決一個(gè)問(wèn)題,但讀完后似乎又覺(jué)得不是這樣,您究竟想通過(guò)這個(gè)假設(shè)表達(dá)什么呢?
張新穎:布羅茨基說(shuō)過(guò),一個(gè)人寫(xiě)作時(shí),他最直接的對(duì)象并非他的同輩,更不是其后代,而是其先驅(qū)。是那些給了他語(yǔ)言的人,是那些給了他形式的人。黃永玉也說(shuō),他感到周圍有朋友在等著看他,有沈從文、有蕭乾在盯著他,仿佛要對(duì)對(duì)口徑,他每寫(xiě)一章都在想,要是他們看的時(shí)候會(huì)怎么想。“比如如果蕭乾還活著,我估計(jì)他看了肯定開(kāi)心得不得了。表叔如果看到了,他會(huì)在旁邊寫(xiě)注,注的內(nèi)容可能比我寫(xiě)的還要多。”
讀書(shū)周刊:從這個(gè)意義上來(lái)說(shuō),這個(gè)假設(shè)有著極其現(xiàn)實(shí)的重要性。
張新穎:是的,這個(gè)假設(shè)其實(shí)不是針對(duì)已逝的人,而是針對(duì)活著的人,針對(duì)活著還要寫(xiě)作的人,要讓活著的人把它展開(kāi),用寫(xiě)作展開(kāi),并持續(xù)地伴隨著寫(xiě)作。讓它成為寫(xiě)作的啟發(fā)、推動(dòng)、支持、監(jiān)督、對(duì)話,變成寫(xiě)作的動(dòng)力機(jī)制中特殊的重要因素。
讀書(shū)周刊:那么是不是可以說(shuō),當(dāng)下我們?nèi)ビ懻擖S永玉、討論沈從文,對(duì)當(dāng)代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也很有意義?
張新穎:可以這么說(shuō)。沈從文的文學(xué)世界,比“人”的世界大。五四運(yùn)動(dòng)以來(lái)的文學(xué)世界,基本是“人”的世界,而沈從文的文學(xué)里的“大”,在于他的世界的“大”。城市人、讀書(shū)人對(duì)“人”的理解,只是在人的世界中理解人,而他卻放在一個(gè)比“人”更大的自然的世界中去理解和感受。
比如說(shuō),在沈從文的筆下,“自然”從來(lái)不是一個(gè)背景,而是作品的一部分。他始終認(rèn)為,自然背景其實(shí)遠(yuǎn)遠(yuǎn)大于人事變動(dòng),時(shí)代的巨變也總能“被土地的平靜所吸收”。你讀這段話——“工作完畢,各自散去時(shí),也大都沉默無(wú)聲,依然在山道上成一道長(zhǎng)長(zhǎng)的行列,逐漸消失到丘陵竹樹(shù)間。情形離奇得很,也莊嚴(yán)得很。”任何書(shū)中都不曾這么描寫(xiě)過(guò)。
沈從文也不寫(xiě)帝王將相、才子佳人,而是寫(xiě)一條河,寫(xiě)河邊生存的人們,寫(xiě)那些人家忽視的、遺忘的人和事。這些東西就是歷史深處的、有情的。我想這是因?yàn)樵谏驈奈目磥?lái),恰恰是普通人的生存和命運(yùn),才構(gòu)成“真的歷史”,在通常的歷史書(shū)寫(xiě)之外的普通人的哭、笑、吃、喝,遠(yuǎn)比王朝更迭中的大事件、大人物,更能代表久遠(yuǎn)恒常的傳統(tǒng)和存在。
讀書(shū)周刊:我們可以不斷去重新理解沈從文的文學(xué)。
張新穎:把沈從文放在整個(gè)20世紀(jì)中國(guó)巨大變動(dòng)的歷史過(guò)程中,去重新理解他的文學(xué),理解一個(gè)“得其自”的文學(xué)家,如何轉(zhuǎn)變?yōu)橐粋€(gè)痛苦的思想者,又如何在精神的嚴(yán)酷磨礪下成為處于時(shí)代邊緣卻深入歷史文化深處的實(shí)踐者,這是十分有價(jià)值的事。
讀書(shū)周刊:沈從文晚年的身份,由一名文學(xué)家變成了文史研究者,這種轉(zhuǎn)變是否也有一種“時(shí)代的必然性”?
張新穎:他的文學(xué)和他的文物研究,都是他“有情”的表現(xiàn),都是對(duì)別人忽略了的普通人的“有情”的關(guān)注。
他的文物研究做的都是很多研究者不屑于去關(guān)注的東西,衣服、綢緞、花紋、珠飾、“花花朵朵、壇壇罐罐”等,都是普通匠人制作的、百姓生活中用到的普通文化產(chǎn)品,這些物品無(wú)關(guān)乎帝王將相們的文雅或驍勇。他能從中看到普通人的生活,體會(huì)到普通人的情感。他對(duì)此是一往情深的。他看到銀鎖銀魚(yú),會(huì)想象到小銀匠一面因事流淚一面用小鋼模敲擊花紋;看到小木匠和小媳婦的手藝,能發(fā)現(xiàn)手藝人的情緒與作品之間的某種緊貼或者游離。
讀書(shū)周刊:真是“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沈從文的文學(xué)作品和文物研究中的審美趣味與追求,長(zhǎng)遠(yuǎn)地影響了后來(lái)的創(chuàng)作者。
張新穎:自20世紀(jì)80年代沈從文被重新“發(fā)現(xiàn)”以來(lái),一些作家懷著驚奇和敬仰,有意識(shí)地臨摹揣摩。另外還有一種情況,比如當(dāng)代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極具代表性的作品,1992年的《活著》、2005年的《秦腔》和2011年的《天香》。其作者余華、賈平凹和王安憶,在當(dāng)代文學(xué)中的重要性和影響力自然不必多說(shuō),需要說(shuō)的是,他們3位未必都愿意將自己的作品和沈從文的傳統(tǒng)扯上關(guān)系,也未必有意識(shí)地向這個(gè)傳統(tǒng)致敬,卻意外地回應(yīng)了這個(gè)傳統(tǒng)、激活了這個(gè)傳統(tǒng)。
有意思的地方也恰恰在這里。不自覺(jué)的、不刻意的,甚至是無(wú)意識(shí)的關(guān)聯(lián)、契合、參與,反倒更能說(shuō)明問(wèn)題的意義,他們與沈從文的思想和作品的互相認(rèn)證,讓我很感興趣。
讀書(shū)周刊:如果眼光略微偏出文學(xué)呢?
張新穎:偏到與文學(xué)關(guān)系密切的電影,侯孝賢受沈從文影響不小,這一點(diǎn)侯孝賢本人也多次談起過(guò);還有賈樟柯,賈樟柯不僅受侯孝賢電影的影響,而且由侯孝賢的電影追到沈從文的文學(xué),其早期電影《小武》《站臺(tái)》《三峽好人》等,也可以看到沈從文的影子。賈樟柯從中獲得的教益不是枝枝節(jié)節(jié),而是事關(guān)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基本性原則。那一條曲折的路徑,描述出山重水復(fù),柳暗花明,若展開(kāi)談,又是一個(gè)大的話題。
晨曦時(shí)刻的知識(shí)分子
經(jīng)歷苦難后內(nèi)心的透明燭照,在文學(xué)中展示出生命的自救能力
讀書(shū)周刊:您還寫(xiě)過(guò)一些人,包括賈植芳、路翎、穆旦、蕭珊、巫寧坤等,為什么要去追溯這些知識(shí)分子的人生軌跡?
張新穎:他們幾位大致可以看作一代人——出生在20世紀(jì)一二十年代,到三四十年代已經(jīng)成長(zhǎng)或成熟起來(lái)。他們不同于開(kāi)創(chuàng)新文化的一代,也不同于之后的幾代。他們區(qū)別性的深刻特征,是新文化晨曦之際——這個(gè)短暫的歷史時(shí)段——非常重要的兒女,帶著這樣的精神血脈和人格底色,去經(jīng)歷時(shí)代的動(dòng)蕩和變化,去經(jīng)歷各自曲折跌宕的人生。他們的故事自然交織進(jìn)20世紀(jì)中國(guó)的大故事。與此同時(shí),他們并未泯然其中,而是一些難以抹平的個(gè)體。
讀書(shū)周刊:和關(guān)注沈從文的方式相似,您會(huì)特別去關(guān)注他們的至暗時(shí)刻,他們的焦灼與痛苦,那些光鮮以外的東西。這是為何?
張新穎:他們是劇烈變動(dòng)時(shí)代的參與者,被賦予一些完全被動(dòng)的身份。可是,除了承認(rèn)時(shí)代的力量之外,還有沒(méi)有可能通過(guò)自己的努力,去超越受害者這樣一個(gè)被動(dòng)的身份,自己來(lái)完成另外一個(gè)身份?我特別關(guān)注他們?cè)诰唧w歷史情境里的個(gè)人選擇,這種選擇,大到翻譯家巫寧坤要不要回國(guó),小到他走進(jìn)北大荒時(shí)行囊里放進(jìn)的兩本書(shū)——英文的《哈姆雷特》和馮至編的《杜甫詩(shī)選》。
讀書(shū)周刊:您在追溯“晨曦時(shí)刻的兒女們”時(shí),最大的發(fā)現(xiàn)是什么?
張新穎:我發(fā)現(xiàn),“人”是可貴的,是很難被完全摧毀的——這個(gè)不能夠被完全摧毀的東西讓人激動(dòng),讓人覺(jué)得寶貴。就好像我讀路翎晚年的作品,特別是他那一首首長(zhǎng)詩(shī)和短詩(shī),我由衷地感受到了精神透過(guò)重重迷障散發(fā)出的動(dòng)人光輝,那是一種經(jīng)歷苦難后內(nèi)心的透明燭照,他在文學(xué)活動(dòng)中所展示出的生命自我救治能力和創(chuàng)作潛力,差不多是與生俱來(lái)、與身俱在的。
現(xiàn)代以來(lái),中國(guó)發(fā)生了很多大事情,大部分普通人是被潮流裹挾著走的。當(dāng)然不能要求普通人有那么大的定力,但越是這樣,越是顯出他們的可貴,他們能和潮流保持距離的品質(zhì),對(duì)我們來(lái)說(shuō)是缺乏的。
讀書(shū)周刊:您寫(xiě)到巴金家里的“文學(xué)聚會(huì)”,穆旦、巫寧坤、楊振寧等中國(guó)留學(xué)生在芝加哥大學(xué)國(guó)際公寓里的“小組討論”,還有您一次次在您的研究生導(dǎo)師賈植芳先生書(shū)房里的聊天,這些聚會(huì)對(duì)于年輕一代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會(huì)產(chǎn)生什么樣的影響?
張新穎:很難講直接影響到創(chuàng)作,但會(huì)直接影響到作家的生命,由他們的生命再影響到創(chuàng)作。在巴金家里,黃裳、汪曾祺、黃永玉他們都是一群小青年,雖然巴金不跟他們講話,但也是一種精神的影響。
人需要這樣的“小環(huán)境”,這種環(huán)境帶來(lái)一個(gè)向上的文明的力量。所謂“文明”,就是人要對(duì)人好,人和人有一個(gè)向心力,不只是搞文學(xué)的,每個(gè)人都渴望一個(gè)好的小環(huán)境,小到家庭大到朋友圈子,一個(gè)可怕的社會(huì)就是把這些都掃平了,只有一個(gè)巨大的抽象的集體生活。
心靈空間的拓展之路
讀書(shū),使個(gè)人就不再是孤單的個(gè)人,心靈不再是孤單的心靈
讀書(shū)周刊:誰(shuí)都追求精神和心靈空間的拓展,可是,怎樣達(dá)成呢?
張新穎:讀書(shū)是特別重要的一條路徑,讓個(gè)人狹窄的心逐漸變大,變得豐富多彩,變成一個(gè)大的心靈宇宙。
有一種理想的閱讀方式,是通過(guò)沉浸于偉大的著作,領(lǐng)略歷史上和現(xiàn)實(shí)中人類所思、所求的廣闊和豐盈,從而在自己和整個(gè)人類之間建立起息息相通的生動(dòng)聯(lián)系,使自己的心臟隨著人類心臟的跳動(dòng)而跳動(dòng)。這樣,個(gè)人就不再是孤單的個(gè)人,心靈就不再是孤單的心靈,人生也會(huì)越來(lái)越充實(shí)。
但是不要指望心靈一下子就擴(kuò)得很大,這是一個(gè)漸進(jìn)的過(guò)程,每走一步,都會(huì)帶來(lái)不同的感受,每到達(dá)一個(gè)目標(biāo),都會(huì)處在不同的境界。
讀書(shū)周刊:您讀書(shū)處在哪個(gè)境界?
張新穎:《莊子·寓言》里,有一個(gè)人對(duì)另外一個(gè)人說(shuō)到進(jìn)入“道”的順序,我覺(jué)得讀書(shū)的順序也一樣: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lái),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
“一年而野”,“野”就是粗狂、放縱、打開(kāi),剛開(kāi)始要有一個(gè)大的局面,放縱自己去打開(kāi)局面;“二年而從”,是從一種“野”的狀態(tài)回來(lái),降心而從;“三年而通”,這個(gè)“通”,其實(shí)貫通了“野”和“從”后的一個(gè)比較平衡的狀態(tài);“四年而物”,這個(gè)階段能夠排除內(nèi)心干擾而及物,和外面的世界發(fā)生關(guān)系。我自己只能體會(huì)到“五年而來(lái)”這個(gè)階段,“來(lái)”到我這里,使我的心靈充實(shí)起來(lái)。
讀書(shū)周刊:什么書(shū)是您說(shuō)過(guò)的“書(shū)中的恒星”?
張新穎:極少數(shù)的書(shū),是無(wú)以計(jì)數(shù)的書(shū)的中心,許許多多的書(shū)圍繞著它們,吸取它們的光輝和熱量,共同構(gòu)成了人類精神的浩瀚星空。舉個(gè)例子來(lái)說(shuō),在現(xiàn)代中國(guó),魯迅的著作就是這樣的核心書(shū)。
有一個(gè)故事,是大學(xué)者陳寅恪對(duì)人說(shuō)的。他小時(shí)候去見(jiàn)歷史學(xué)家夏曾佑,老人對(duì)他說(shuō):“你能讀外國(guó)書(shū),很好;我只能讀中國(guó)書(shū),都讀完了,沒(méi)得讀了。”陳寅恪非常驚訝,以為他老糊涂了。中國(guó)書(shū)怎么可能讀完呢?過(guò)了很多年,等到陳寅恪也老了時(shí),他才覺(jué)得夏曾佑的話有道理:中國(guó)古書(shū)不過(guò)是那幾十種,是讀得完的。
是哪幾十種?沒(méi)有留下記錄。但學(xué)者金克木寫(xiě)文章說(shuō),有10部古書(shū)是漢代以來(lái)的小孩子上學(xué)就背誦一大半、一直背誦到19世紀(jì)末的,它們是:《易》《詩(shī)》《書(shū)》《春秋左傳》《禮記》《論語(yǔ)》《孟子》《荀子》《老子》《莊子》。這10部書(shū)若不知道,唐朝的韓愈、宋朝的朱熹、明朝的王守仁的書(shū)都無(wú)法讀,連《鏡花緣》《紅樓夢(mèng)》里許多地方的詞句和用意也難以體會(huì)。再往下,史書(shū)讀《史記》、文學(xué)書(shū)讀《文選》。一部書(shū)通讀了,讀通了,接下去越來(lái)越容易,并不那么可怕。
讀書(shū)周刊:這使我又想到沈從文和黃永玉,您說(shuō)過(guò),成就他們叔侄的,不僅僅是經(jīng)歷,倘若沒(méi)有超過(guò)常人的讀書(shū),是沒(méi)法想象的。
張新穎:黃永玉在《無(wú)愁河的浪蕩漢子》中,說(shuō)到少年序子讀的書(shū),比如:《榕村語(yǔ)錄》,康熙宰相李光地著,他居然有時(shí)也用白話文,可惜不見(jiàn)學(xué)者提起他;《普通地質(zhì)學(xué)》,是達(dá)爾文的徒弟萊伊爾寫(xiě)的,讀熟了它,走到哪里都清楚腳底下是什么巖頭、眼前是什么性質(zhì)的山;《人類和動(dòng)物的表情》《貝爾格艦上的報(bào)告書(shū)》都是達(dá)爾文寫(xiě)的,比《進(jìn)化論》有意思;盧梭的《愛(ài)彌兒》,很有味道和見(jiàn)識(shí),只可惜譯文拗口,仿佛3斤新鮮豬肉讓人燉糊了……
沈從文15歲開(kāi)始當(dāng)兵,隨部隊(duì)輾轉(zhuǎn)。有誰(shuí)能想象,這個(gè)每月只有三四元錢(qián)的小兵,包袱里有一本值6元錢(qián)的《云麾碑》,值5元錢(qián)的《圣教序》,值兩元錢(qián)的《蘭亭序》,值5元錢(qián)的《虞世南夫子廟堂碑》,還有一部《李義山詩(shī)集》,他自己寫(xiě):“這份產(chǎn)業(yè)于現(xiàn)在來(lái)說(shuō),依然是很動(dòng)人的。”
讀書(shū)周刊:較之那一代人,您對(duì)現(xiàn)代人閱讀的前景樂(lè)觀嗎?
張新穎:我不是特別悲觀,每一代人的偏好會(huì)有變化,形式也會(huì)有變化,但是大家還在讀。
值得注意的是網(wǎng)絡(luò)時(shí)代對(duì)閱讀的影響。如今的孩子是伴隨著可視媒介成長(zhǎng)的,他們也許從未培養(yǎng)起對(duì)于書(shū)本的深厚感情。但網(wǎng)絡(luò)無(wú)法代替讀書(shū),書(shū)的“品相”“色香”“神韻”“意味”,書(shū)頁(yè)翻動(dòng)時(shí)發(fā)出的聲音,眼光和文字碰觸的感受、對(duì)一本新書(shū)的驚艷、與一冊(cè)老書(shū)的重逢等,都有至關(guān)重要的意義。不管怎樣,如果你有孩子,不妨讓他知道,讀書(shū)是多么好的事。
- 沈從文與天津往事[2022-06-15]
- 王道:沈從文早期的美育計(jì)劃[2022-05-30]
- 傅漢思與沈從文——跨越半世紀(jì)的恩與報(bào)[2022-05-26]
- 筆尖下的江河——《從文自傳》創(chuàng)作與出版始末[2022-03-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