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下與古典間再建一座別樣宮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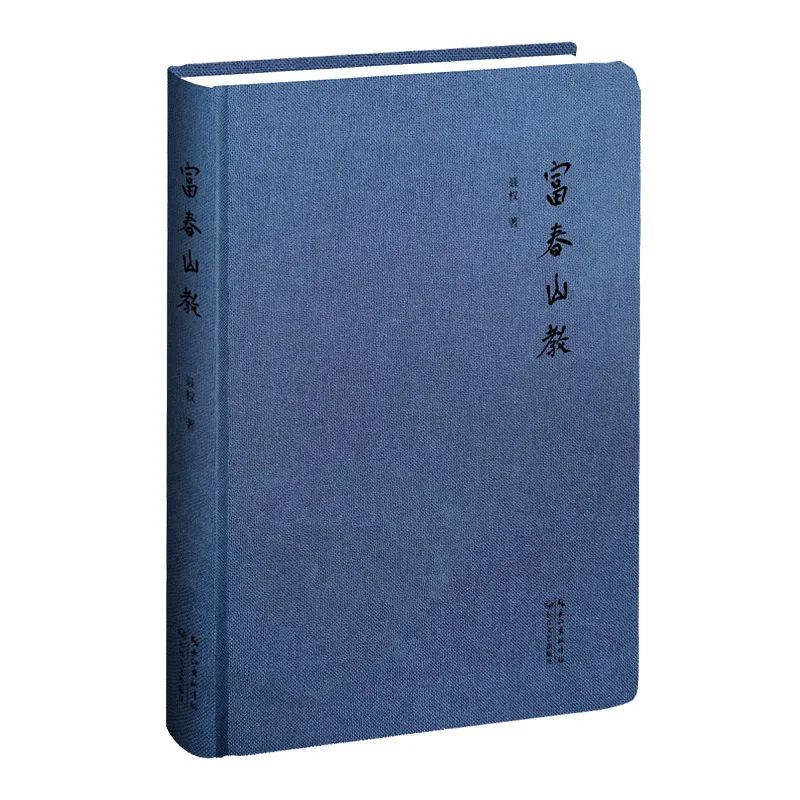
《富春山教》
聶權 著
長江詩歌出版中心
雷平陽:馬爾克斯的自傳叫《活著為了講述》,可對詩人而言,講述為了發現,為了進入語言的心臟。你的新詩集《富春山教》大抵上也有著這個思路。據此,對講述或說敘事,你有何體悟?在探險式的講述中你又是如何保持了持續性思考的狀態并且去到了你所設定的終點上?
聶權:在開始對談之前,我想先向平陽大哥你致以敬意,在很多方面,包括敘事方式進入當代詩歌并且進行全方位拓展這一方面,我個人以為,你是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和意義的。你在一個對談中說,一方面,甚至可將敘事認定為詩歌的力量、節奏和空間之源;另一方面,《擊壤歌》和《詩經》中有著大量的敘事篇章,詩歌的敘事來得更古老。很奇怪,在當下仍然有不少人在排斥敘事,認為敘事會影響到詩歌的本質。我覺得如你所說,敘事方式是詩歌寫作的源頭之一。敘事方式合于詩歌的本質,合于人類表述情感的需要。詩言志,我們的生活和生命,絕大部分是由事件組成,如果刻意摒棄敘事方式的進入,生活、生命、情感的相應部分都沒有辦法進入到詩歌中去,一個只愿意去用抒情方式去寫作的詩人,他的詩歌世界相對于他的生命世界,是有很大缺失的,是不完整的。所以,我也是愿意將敘事作為自己寫作的重要方式之一,并且與抒情找尋盡可能恰當的平衡或者反差效果。
怎么樣講述,是一件會讓我著迷的事。講述的方式,如自然本身,億萬溝壑、億萬山水、億萬江河、億萬星辰,各有其形,各有走向、態勢、空間、差距、引力、排斥、回旋、滾卷、沖撞、氣形,摸索、觀摹、借形、擬勢于詩歌之中的過程,猶如探求一個比現實世界更瑰麗奇偉更變化無窮的世界里的種種神秘。我一直不愿意自己的下一首詩歌與自己從前的作品有重復處,這其中就包括講述的方式,宇宙無盡,詩歌世界及技藝無盡,求有異于自我及他人之新、變、創造、平中之奇險、奇崛或自然,對自我的不斷的變化,可能有意無意間有與你說的持續性的思考的狀態契合。
雷平陽:我有一首短詩《臉譜》,從想寫到寫成,短短五行,耗掉的時間是五年。意圖、語感、情緒的挑選令我苦不堪言同時又興致勃勃。它的寫作過程讓我確信:現代詩的寫作所謂“一揮而就”已經類似于神話,只有那些得到神靈支持的詩人能夠蒙福,更多的詩人也許得像做一項浩大的工程那樣選項、確定目標、規劃、預算、繪圖、備料、施工、裝修,缺一不可,費盡移山心力方能完成。一場自己與自己的戰爭,有時是自己與鬼的戰爭,有時是自己與真理和美學的戰爭,有時還是自己與語言的戰爭,而且還得像所羅門王建造神殿時聽不到鐵器的聲音那樣去展開。那么,你可否談談這種設定式詩歌的寫作意味著什么?我們詩歌將“有感而發”的詩教傳統導入工程式一般的綜合系統將會面臨怎樣的結局?
聶權:多年前,我曾和劉年、王單單多次討論研究過你的許多詩歌可以在他人心中留下深刻印象難以磨滅這一特點的原因,聽了《臉譜》的創作過程,更多了些明悟。你的創作和讀書一樣,都是艱辛而類似于浩大工程的。聞一多提倡在感情冷卻下來再進行創作。我在近三十歲時,對他的這種觀點是存疑而不以為然的,但是,現在,越來越傾向于一種如你所說的目擊神遇后的設定、計算、遙想、觀望、摹形、察微、搭建、構架、理氣、凝神、出擊、起舞等等準備后的由心而生的自然生發。在一定意義上,聞一多說的“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著腳鐐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是有道理的。當然,這種“鐐銬”在當下應該包含更豐富的詩歌技藝與規律。在近些年,我也漸多如你寫作《臉譜》等作品的經歷和感覺,只是從構思到創作時間要短了許多。我有一首不起眼的小詩《暗襲》,寫因被刀切傷想起遠方的母親,母親在廚房要躲避多少這樣明晃晃的暗襲,期間每次在廚房都會想到一樣在廚房的母親,想到詩人毛子和津渡兩首寫廚房特別動人的詩歌里的句子,在近一年之后,才寫了下來。王昌齡《詩格》中說:“夫置意作詩,即須凝心,目擊其物,便以心擊之,深穿其境。如登高山絕頂,下臨萬象,如在掌中。”我覺得設定式的寫作對于成熟的寫作者來說是可取的,它是一種成熟詩人的能力,將“有感而發”的詩教傳統導入工程式一般的綜合系統,我個人覺得并不沖突,這種做好艱巨工程樣的內心構建與設定與由真心、真情自然生發的平衡,是可以同步處理的。我期待一種境界與能力,瞬間如歷經千年,在很短的時間里可以完成這種內心的浩大工程,而在更短時間內完成一首詩。
雷平陽:卡瓦菲斯有不少詩歌書寫現代性史跡,施奈德翻譯又由柳向陽轉譯過來的寒山子詩歌,對我的啟示性很大,古代語境與現代語境的轉換,帶來了無數的新詞語和閃亮的美學空間,模糊的只可意會的精神奇觀得到了準確的落實同時又引出了新的謎語。從中既可窺見傳統詩歌端莊的背影又能發現一個個未來的思想幽靈。一段時間以來,你著迷于此,基于什么樣的想法和追求?
聶權:接通過去、現在和未來,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現在正在琢磨這個問題,也可能會去做進一步的嘗試。這一點讓我著迷。與之相應的隱約的追求是,詩人是不是也應該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精神,可以將當代歷程有效地放置于時間與詩歌長河的坐標系中。于所處時代完成繼往開來,應該是寫作者的責任和使命。當然,這只是一種愿望。
雷平陽:在殿堂和遺址上再造一座殿堂,現實生活中從來都是常態,在詩歌寫作中則是冒險。我一直推崇李白的詩歌《夜宿山寺》“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視其為神品。即使用白話隨口翻譯過來,都是一首石破天驚的現代詩,但我連模仿它的勇氣都沒有。你的詩作中不乏舊典,除了出新之需而外,是否也有著對現實進行詩意審判的需要?
聶權:對李白的有些詩,我也有過類似的感覺,曾經有兩年,我一直在反復閱讀、揣摩如李白《靜夜思》“床頭明月光,凝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及杜甫有些看似極簡單的神來之作,并且隱約覺有受益。
希尼說,詩是文化的自我回歸。即連外國詩人,也很重視文化的傳承,而白話詩當下流行的方向已經使用典等古人常用之法不大可能較多出現,這其實也構成了新詩的一種局限。我理想中的詩歌形態,是無事不可入、無物不可入的,新詩當下的語言狀態和方向,已不能滿足這樣的體系。用舊典承襲積淀,有出新之需,有回歸,也有期望調和新與舊的平衡而更有長足之力前進,從這三方面來說,是有想要糾偏于現實狀況的想法的。
雷平陽:現實和它帶來的戰爭以及戰爭留下的景象和心象,一直是書寫者案頭的一只怪獸,直接寫它或以虛構的方式呈現它,目的都是為了找出它的成因、欲望和天命,探究它的精神內核并由此開顯其體制中眾神與眾生的內在現實和前往未來時的行姿,直面與虛構之爭并沒有什么意義,但寫作者所處的精神高度、神賜的寫作蠻力和對未知的知道欲,往往會成為寫作成果的檢驗尺碼。你的上一本詩集與《富春山教》之間明顯存在著一道裂痕,前者親近現實而后者疏離,這是否可以理解為是現在的文本疏離過去的文本?文本之間的疏離隱藏著什么樣的秘密?這種疏離是必須嗎?
聶權:《富春山教》和我的上一本詩集相隔五年多,三分之二都是近兩三年的新作,五年間生活、生命狀態,關注點,審美傾向、趣味,體悟,體察,思考結論,看待世界的方式,處世態度等都發生了轉變,作為生命的一個重要部分,詩歌也發生了相應的改變,如果說有什么秘密的話,那就是個體生活、生命本身的不足對外人道的悄然改變。我覺得這種疏離是必須的,它是一種調整自己的改變,通則變、變則通自古而然,階段性的通與變不斷交嬗方有前進。之前特別關注現實,緣由之一是以為詩歌當能對現實、人心、靈魂、精神建設起到作用,庶能體現詩歌“言之寺廟”的重對人心、人性起作用的本質,在群體性接續于《左傳》等書中體現出來的先秦時代可以詩歌為規則,規勸、教化、溫潤浸入靈魂、干預現實與人心、化世風的傳統于萬一的過程中,起到一名寫作者微渺的作用。現在的改變與疏離不代表否認了這種道路,于精神走向上,是一致并且希望終將以更好的姿態回歸的。
雷平陽:因為誰也無法接近事物的真相,很多時候我都會把現實生活中的很多事件歸于虛構。在我的一篇近作《游泳的人帶來恩賜》中,開篇就是:“凡是虛構都有教育世界的資本。”對這個觀點,你怎么看?再說,寫作者以現實去看靠近虛構的真理,或以虛構無限逼近現實的真理,兩者之間你傾向于誰?是否有第三條道路?
聶權:從寫《云南記》起,你就在做以虛構來“教育”世界的努力,而且構建了一座宏偉的詩歌精神宮殿。在這一方面,我覺得自己未必有發言權,因為沒有將虛構無限逼近現實的真理的方向完全落實于寫作。我在2008年至2015年之間做的嘗試,當屬以現實去靠近虛構的真理這種方向,當時的觀念是將生活、生命原來的面貌呈現,不多增一分,不多減一分,紙上山川、河流、人事、情感與現實中的比例不差分毫,一點都不拔高,也不降低,從生活和生命本身發掘詩意,而后的實際檢驗與自我反思證明,這種道路輕視了藝術性。所以在2015年之后,我也努力找尋現實與虛構的平衡。我可能傾向于探求二者之間的平衡、打破平衡和再造平衡,如此循環往復,不斷接近“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的無盡真理與真相。
雷平陽:不久前,讀到韓少功的一篇文章《優質的漢語正離我們遠去》。他說:一種優質的語言并不等于強勢語言,并不等于流行語言。優質語言一是要有很強的解析能力,二是要有很強的形容能力,”而二者正在這離漢語。我觀察,在寫作者中間,自覺地想為漢語做貢獻的人的確已經很少有了,口語化和翻譯體化的大環境中,有著解析力和形容力的語言少之又少,人們有意無意地信靠了強勢與流行,根本去不到或回不到漢語本體之上,似乎很少有人再睜大了眼睛仔細地查看他寫出來的每一個字和字的本意及可能性,說什么和寫什么,仿佛都是由另一個大腦所指揮,自來水一樣就流了出來。讀你近期的作品,明顯發現你的語言有了不小的變化,越來越準確,也越來越具有古意,我是否可以認為在語言學上你有復古的傾向:復古的傾向與在白話之基礎上重新“發明”一種漢語,兩者誰更有意義?如果選擇在白話文基礎上認真地去找回漢語的解析能力和形容力,讓漢語“活潑潑的”,我們又該如何去做?
聶權:是的,如你這樣自覺為漢語貢獻的人極少或者心有余而力未足,這是憾事,我一直期望通過當下大家的共同努力,呈現出又一個詩歌盛世,而今看來,僅從語言的建設、創造與貢獻而論,暫時還不足以撐起這個詩歌盛世的龐大構架。這種強勢與流行中的一部分,我能不能理解為白話詩百年來的部分的無效發展?白話詩的出現,是適應時代發展的,是非常正確的,但是過度的口語化以及對于傳統漢語沉淀的有意遠離,是對我們民族的語言傳承、底蘊有極大傷害的。矯枉過正,則猶不及。一端過重,一端若無,天平必然無法成立。江海尚不擇細流,我們有什么理由摒棄我們數千年的重要傳承?這兩年,從寫了《師說》起,汲取古典文學語言,將文言與現代口語融合,是我有意的嘗試,是有著回頭望的復古的傾向的,而令我欣喜的是,近一年多,自己竟然真的突有寸進,找到了比較適合自己表達所長的方式。我覺得在白話的基礎上,與源頭性的語言、與文學史中的一代代先賢的積淀融合、創造,重新“發明”一種與時俱進的適應當下文學與生活表述的語言體系,是更有意義的;讓漢語“活潑潑的”,感覺我們應該做到:認真讀《現代漢語詞典》,鉆研每個字的本意、引申義以及在詩歌表述中的可能運用;認真讀《成語詞典》;認真讀二十四史;認真鉆研《古詩源》《詩經》《樂府詩集》、唐詩宋詞元曲的精華,探詢語言意象間的微奧;認真學習先秦諸子文章及其他歷代精華散文篇章,掌握文言能力;向西方詩歌學習語言意象間的空間與張力、生命意識、人性抒寫。操千曲而后曉音,觀千劍而后識器,在這樣的基礎上認真思考語言的源頭、多源流、當下形態的融合、體系性創造、重建并加以高強度訓練是有必要的。
雷平陽:中國古代詩人寫作喜歡用典,西方眾多的一流作家和詩人也總是喜歡在某個典的巴比倫塔上起飛。“出處”之于在紙上團團亂轉的寫作者來說,也許是把衣服釘在寺廟墻壁上的一顆木釘子,但很長時間以來,在漢語寫作中這仿佛變成了一件羞恥的事情,人們更迷信“來路不明”或“天外飛仙”。以我所在的云南為例,不同的民族留下了很多的創世史詩、英雄史詩和遷徙史詩,卻很少有寫作者從中去探寶,將其中的諸神和英雄塑造為現代性的某個形象,提煉出某種精神,歐洲和拉美地區的作家和詩人對此不遺余力。他們之于“出處”,尤信眾之于天國,我們為什么會如此錯過腳下土地,你有何看法?而且,我們不乏崇尚博爾赫斯、卡瓦菲斯和卡達萊這樣一些作家的作家,為什么他們崇尚的只是這些作家的寫作技藝,而沒有認真地去崇尚或效仿這些作家構造精神譜系的方法論?
聶權:生命世界和自己的詩歌是對應的,首先,是不是有很多詩人有自己的精神向度、精神譜系?如果有自己的精神譜系,相對成熟的寫作者不會不有所體現。另外,在現實世界里,為數不少的人都有難以想象的偏執,有的人甚至不認同自己的民族有文化,我曾在一次座談中接觸到這樣的現象:建議他們發掘自己的民族文化,而會后有人告誡我說得太大膽,這樣說有人會不高興。當然,錯過腳下根源,也跟個體的格局、觀念、感知力、思考力、發掘力、辯證力等均有關系;在我做編輯以來十多年,也聽到為數不少的人很固執地堅持,一生寫出一兩首、兩三首好作品已經足夠。稍作探討,竟至勃然變色。這也是出乎意料但確實存在的現象。觀念如此,何談找尋腳下根源、成體系和譜系?另外,可能也與部分優秀詩人的行走、閱讀思考深度、眼界格局、自我滿足程度、文化積淀與創新、貢獻意識有關。
雷平陽:古典或現在,其實任何一個詩人都是在重復永遠不變的責任:置身于某個時間段但又試圖抹去時間的痕跡,讓語言思想和個體知識及其情感獲得幻想中的永恒性。這種行為有著先知和巫師的氣質,也容易讓他們的旁視者產生此時即彼時的錯覺——把時間當成某種量身訂制的空間,進而忽視了詩歌由古典來到“現在”所必備的一個個時間刻度及其創造性。問題因此而變得很嚴峻:“古典”中的現代性如何去發現?‘現在”中的古典精神得以什么樣的面貌出場?也就是說,當我們完成了對寫作的永恒性的概念化認知之后,我們也許得站在未知的立場上對自己的工作進行嚴苛的審測,它是否合法、有效?在古典精神與現代性旨趣之間它是否破除了邊界并抬高了時間河床?對此,你有什么想法?當然,你完全可以把它理解成一次“重返的逍遙”,而我想知道的則是這次“重返的道遙”得有什么樣的前提條件?
聶權:是啊,這種責任和錙銖累積的寫作內容我也在思考。生命個體在古時、今時、未來的本質性特征都是相似甚至相同的,從生命、身體、心靈、人性、命運等方面來說,“古今無有不同”在相當大程度上是成立的。許許多多的古人智慧遠勝于我們,我們的智慧也未必輸于后人。我們難免以現代性的眼光去看待古人古事古典,而若以“古今無有不同”的觀念觀照古人古事古典,找尋到古今的共同點,“古典”中的內容的眾多現代性即可被發掘。打通古、今乃至未來的界限,對寫作者是很有意義的。“現在”中的古典精神以回溯、汲取、揚棄的態度,以貫通文史哲的基礎上,入得俗世得人間三昧而可跳得出來、無限接近生命真相與真理的個人面貌出現,在當下是必要的。杜甫、蘇軾等人能有恒久的影響,很大程度在于他們由深厚文化積淀而來的個人面目。現在還少有以個人面目影響到其他人的詩人,“古典”在生命中的缺失不可不說是一個重要原因;古典與現代的關系在各個時代應該是一種不斷構建平衡、打破平衡、再構建新的平衡的狀態,這樣才可以把古今邊界破除并通過一個時代的努力,為時間河床增加高度;“重返的逍遙”這五個字概括得好啊,這也是我理想中的寫作和生命的狀態。要做到“重返的逍遙”是很有難度的,從個人來說,要重返,必須先要深入了解重返的世界,要逍遙,必須“從心所欲不逾矩”。而僅僅個人做到重返逍遙,對時代而言也是無效的,想要有效地抬高時間河床,必須通過集體的努力。也確實已到了該集體糾偏的時候了,應該集體性地充分重視源頭、古典與新的平衡的不斷構建。
雷平陽:你的職業是編輯,選取稿件時有什么標準?作為詩人,而且是一位年輕的詩人,今后有什么寫作計劃?作為山西人,有沒有想過用漢語去虛構一座五臺山,或者虛構一座云岡石窟?
聶權:選取稿件時我習慣于條分縷析,看經手的作品于這些標準能做到多少:能體現詩人整體性的成就;有余味,能讓別人記得住;有根;語言有建樹;有創新,有開拓性甚至貢獻;有大格局、大氣象;師法自然;有深度生活、生命體驗;有歌的要素;具有詩言志的方式;氣息貫通、獨特、多變化;真情動人;結構布局的奇崛多變;對現實、人心起作用;體現作者選取題材的能力;有畫面感;可從日常生活中發掘詩意;可以探究平衡的奧妙;具有當代性;做減法,可以讓讀者深度介入;有精神來處和去處;溫暖的給人心靈出口的向度;有生生不息的氣息;能夠寫出微妙的感覺;有深厚的地域印記;見面目;見人性、神性;有時不妨以童真角度來看世界;有源頭和根本;有天然引力;向古典詩詞、文化、文學汲取養分。
作為山西朔州人,我為實際距離五臺山和云崗石窟相對近一點而有驕傲,但它們的底蘊太華美、莊嚴,我不敢冀望于比擬它們,但是希望能留下些如它們,或如遺址、或具有長久生命力的可以在時間中存在久一點的作品。
我夢想借有限小詩,寫宇宙浩蕩與幽微之氣象,夢想建構一個生命個體在探索自我生命意義的過程中所看到、所感知的、所體悟的宇宙,它與現實宇宙中的種種比例相當,它粗糙,有大概的輪廓,生命個體與群體、江河、山川、泥土、巖石、金屬、空氣的千變萬化、千差萬別的形態、悲歡、命運,都與現實中的不差分毫,這在個世界中的真相、秘密和核心,要我無限地去接近。它只是我理想中的或許大而無當的圖景,尚未展開一角,如果命運允許,我會做一嘗試。這也是我今后的寫作計劃。
對談者簡介:
雷平陽,詩人,1966年秋生于云南昭通。現居昆明。出版詩歌、散文集四十多部,曾獲人民文學獎、人民文學年度詩人獎、詩刊年度大獎、十月文學獎、華語傳媒大獎詩歌獎、鐘山文學獎、花地文學排行榜詩歌金獎、中國詩歌學會屈原詩歌獎金獎和魯迅文學獎等獎項。
聶權,1979年生,山西朔州人。1994年起習詩。曾獲“2010中國·星星年度詩人獎”、2016華文青年詩人獎、2017華語青年作家獎、第五屆徐志摩詩歌獎、第二屆金青藤國際詩歌獎、第四屆“紅棉杯”文學獎詩歌獎。有作品被譯為多民族文字及英、韓文。著有詩集《一小塊陽光》《下午茶》《富春山教》及韓文詩集《春日》。
- 對話:胡續冬與“九十年代詩歌”[2022-07-26]
- 書香永川·心靈故鄉——詩意永川川渝詩人創作采風暨龍遠信詩歌分享活動舉行[2022-07-20]
- 盧山:新媒體語境下詩歌破圈傳播的路徑探析[2022-07-20]
- 劉福春 李俊杰:詩與生活[2022-07-23]
- 楊碧薇:挺住意味著一切[2022-07-18]
- 2022深圳海洋詩歌季:大海與詩,在心中見遠方[2022-07-12]
- 啞石:我用職業與生活來“養活”身體里那個“詩人”[2022-07-12]
- 第八屆《絲路放歌 黃河詩會》在銀川舉行[2022-07-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