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yǔ)言和想象的停靠站 ——評(píng)渡瀾小說(shuō)集《傻子烏尼戈消失了》
主持人語(yǔ):
出生于1999年的青年作家渡瀾是漢語(yǔ)世界的后入者,她的母語(yǔ)是蒙語(yǔ),從小接受蒙語(yǔ)和漢語(yǔ)的平行教育。蒙語(yǔ)中人與自然渾融不分的境界,成為其作品齊物之境的基礎(chǔ)。小說(shuō)集《傻子烏尼戈消失了》充盈著奇妙比喻,以色彩、觸感、聲音、氣味的層層堆疊賦予文字以靈性。羅蘭·巴特將寫(xiě)作技巧稱之為“一種既固執(zhí)又迂回的言語(yǔ)活動(dòng)”,其迂回性體現(xiàn)于“無(wú)限多樣的停靠站”。渡瀾的跨語(yǔ)際書(shū)寫(xiě)就提供了這樣的“停靠站”,語(yǔ)言、思想、作者、讀者之間的對(duì)話迷離撲朔。“和光”組織了一場(chǎng)渡瀾小說(shuō)研討,“90后”“00后”讀者,試圖從意象、自然、語(yǔ)言、修辭、敘事等視角,打開(kāi)渡瀾作品廣袤馥郁的文學(xué)空間,牽引出游蕩其間的宇宙情懷。
——戴瑤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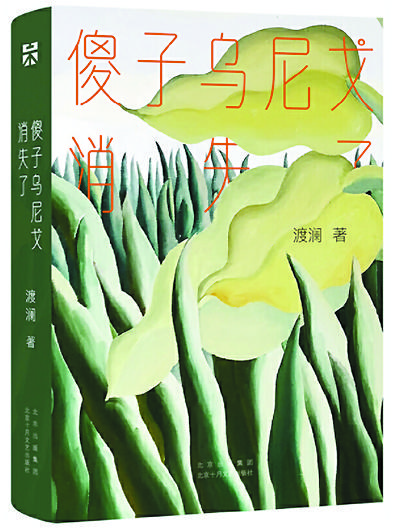
1.烏尼戈·自然力·童年
于明玉:動(dòng)物入侵、世界異變的迷離景象以尋常樣態(tài)踱進(jìn)讀者視野,將曾經(jīng)此在化、生活化的物象重新推回原型。無(wú)法落地的猜疑如“嘎樂(lè)”一般涌動(dòng):在布里亞特蒙古人的創(chuàng)世神話中,母親神額和·布爾罕分離天地之初即創(chuàng)造野鴨銜泥筑陸,《去看烏嘎跳舞》則以鴨子為言說(shuō)單位;薩滿教巫女作獸禽舞、著鳥(niǎo)羽服,遨游于天神/人族間溝通圣諭,又可作解喜鵲烏鴉對(duì)烏尼戈的親昵之態(tài)。在普魯斯特式“綿延”漫漶的時(shí)間里,動(dòng)物創(chuàng)世神、英雄勇士以持守遠(yuǎn)古文明的超現(xiàn)實(shí)形象返生,也建構(gòu)了民族記憶的初生場(chǎng)所。去儀式化的生態(tài)敘事恰與《沙鄉(xiāng)年鑒》所述“共同體”意識(shí)偶合——生命依扶關(guān)聯(lián),萬(wàn)有歸復(fù)于一,人與諸靈盡為穹廬懷抱的仔畜。
王奕寧:說(shuō)到共同體,我不禁想起了《沙鄉(xiāng)年鑒》中的這句話:“一個(gè)事物趨向于保護(hù)生物共同體的完整、穩(wěn)定和美麗時(shí),它是正確的;否則它就是錯(cuò)誤的。”雖然這句話看上去有些忽視事物模糊性的可能,但烏尼戈悲傷又溫潤(rùn)的包容與平和簡(jiǎn)直是這個(gè)共同體敘述的翻版。《傻子烏尼戈消失了》表面講述的是一個(gè)叛逆的、不溶于社會(huì)的孩童成長(zhǎng)史,但其中更引人深思的是故事背后蘊(yùn)含的自然思想。我認(rèn)為,烏尼戈是被人類不斷迫害的自然的縮影。他擁有“無(wú)限接近自然的美”,第一次出現(xiàn)時(shí)就布滿了人類的“腳印”,“我”將他拴在餐桌上的舉動(dòng)也體現(xiàn)人類對(duì)自然的征服與控制。烏尼戈包含世間萬(wàn)物,以及人類肉眼無(wú)法見(jiàn)到的物質(zhì)實(shí)體(松雞)。當(dāng)他遇到能夠?yàn)槿祟悗?lái)財(cái)富的俄日敦德日格勒的時(shí)候,命運(yùn)就難以遏制地沖向低谷。他被當(dāng)作取悅“致富機(jī)器”的寵兒,在“財(cái)富保安”的圍追堵截之中,它自身的資源與價(jià)值也在慢慢的磨滅與銷毀,直至滿身創(chuàng)傷。即使這樣,烏尼戈也沒(méi)有放棄人類,他向人類展示出了近似母愛(ài)的慈悲。可這種廣博的原諒卻沒(méi)有換來(lái)人類(小鎮(zhèn)居民)的一絲憐憫與猶豫,他們殺死了烏尼戈,將它燒得只剩在風(fēng)中蟄伏的灰塵。同時(shí),他們——人類——也因?yàn)槠群ψ匀坏臑跄岣甓艿搅藨?yīng)有的懲罰。一切來(lái)自于烏尼戈,也復(fù)歸于烏尼戈。隨著風(fēng)的凝聚與疏散,烏尼戈終將以另一種方式重組再現(xiàn)。
張暉敏:雖然小說(shuō)集觸及童年和自然這個(gè)常規(guī)議題,讀者卻難以在其中圈定傳統(tǒng)浪漫主義書(shū)寫(xiě)范式的烏托邦。我覺(jué)得渡瀾的書(shū)寫(xiě)不是回溯式的“減法”,而是時(shí)刻都在做著“加法”。族群記憶的差異首先使原型作用失效,過(guò)于冷靜和細(xì)膩的講述更讓童夢(mèng)的天真里帶上了殘酷——像是詳盡地描繪灰姑娘的姐姐們?nèi)绾蜗魅ツ_跟。而不期而至的消失、徒勞的尋找、失效的保護(hù)和無(wú)望的抗?fàn)帲偸窃诜乾F(xiàn)實(shí)的場(chǎng)景里喚起令人刺痛的現(xiàn)代情緒。美德、惡行、文明、野蠻、新生的芬芳糾纏著垂死的腐臭,截然對(duì)立的矛盾并置現(xiàn)形,又被童真邏輯彌合。“卮言”式的奇異魔力將讀者拉入陌生的草原,蓬勃的生命力超越了族群乃至物種的差異洶涌而來(lái),銜尾蛇般永恒流轉(zhuǎn)的時(shí)間里。童年這個(gè)蒼老的稚子被不斷粉碎重組,靜默地延伸向尚未展開(kāi)的將來(lái)。
王奕寧:我覺(jué)得渡瀾綺麗的夢(mèng)背后有“天人合一”自然哲學(xué)思想為其支撐。“自然界作為人類生命和一切生命之源,本身就是一種內(nèi)在的‘善’,這種‘內(nèi)在的善’所具有的非人工所能代替和改變的‘神性’,構(gòu)成人類所追求的生存世界的價(jià)值本原。” 烏尼戈就是這種善的顯現(xiàn)。像我上面提到過(guò)的,烏尼戈一直都是以一個(gè)可憐的被欺凌者形象出現(xiàn)的,但不管身體再怎么破碎與殘裂,精神再怎么恐懼與顫抖,他還是會(huì)抱著他最珍視的寶物——喜鵲向我們橫沖直撞地奔來(lái),好像完全不在意口袋里人們對(duì)他的唾棄與傷口中流出的血漬,只是不計(jì)回報(bào)地釋放“真心”的養(yǎng)料。這種真心和天地世界無(wú)二無(wú)別,是同一的。自然是不斷循環(huán)往復(fù)的、永久的存在,它是自由無(wú)邊的,而不僅僅是人類的囚徒與“供應(yīng)商”。雖然自然的生命意義與內(nèi)在價(jià)值需要人類的實(shí)踐與改造才能完成,但這種改造也應(yīng)建立在尊重自然的基礎(chǔ)之上。當(dāng)人類將自己過(guò)余的妄念移除,對(duì)自然抱有同理心的關(guān)懷,才能與自然一起融通,從而達(dá)到一切皆空的“天人合一”境界。
2.跨語(yǔ)際·詞語(yǔ)·修辭
張暉敏:渡瀾是很典型的跨語(yǔ)際寫(xiě)作,這一寫(xiě)作天然帶有陌生化的效果。她以囚犯“三角形”般的敏感謹(jǐn)慎,觸摸嶄新語(yǔ)匯,童年原初的開(kāi)放性于此刻回到了作者身上。在故事里,她偏愛(ài)書(shū)寫(xiě)對(duì)話,將新鮮的表達(dá)欲望傾注其中,每個(gè)出現(xiàn)的角色都固執(zhí)地展覽著獨(dú)屬的、情緒化的主觀世界。而讀者也不得不加倍謹(jǐn)慎地對(duì)待文本。一方面,詞語(yǔ)幾乎密不透風(fēng)地向讀者籠罩過(guò)來(lái)。過(guò)載的信息充斥著每一幀畫(huà)面,帶來(lái)難以聚焦的眩暈。而這些活的、不尋常的詞語(yǔ)又讓人反復(fù)停頓下來(lái),以免錯(cuò)過(guò)其中探出的細(xì)微觸角。
于明玉:難以想象的是,如此一個(gè)滌蕩素樸、駁雜斑斕的語(yǔ)言王國(guó),卻依舊鍥而不舍地值守客觀世界。符號(hào)如獒犬,寸步不離它畜群般的實(shí)存對(duì)象,在虛構(gòu)文學(xué)創(chuàng)作脫殼的當(dāng)下顯出一份澄清與忠實(shí)。蒙語(yǔ)慣性使得“艾日格”“烏日木”此類不轉(zhuǎn)譯的稱謂頻頻流出,直接暴露諸多詞匯的源頭正是向生活經(jīng)驗(yàn)取色,而在這一點(diǎn)上渡瀾同她的祖輩一脈相承,不過(guò)藍(lán)(青)色神符“長(zhǎng)生天”之宏大,已然退位于“烏珠穆沁熏皮袍色”之庸常。具體物象的擴(kuò)容,逐漸將隱形關(guān)系、微妙情緒、心理圖像搡出言辭洼地。
張林:聚焦詞匯,小說(shuō)中翻涌著大量密集而瑰麗的名詞。名詞作為存在物的名稱,如同一扇扇門(mén),背后站立著事物和事物的全部由來(lái)。烏尼戈從門(mén)里出來(lái),門(mén)也是柳澤真由娜夢(mèng)中的素描紙,它們是作者想象的造物,在一個(gè)個(gè)名稱里活筋動(dòng)骨,生長(zhǎng)后腐朽。
她詳細(xì)地命名事物,人名、地名多源自蒙語(yǔ)。蒙語(yǔ)名稱常帶有特殊含義,作者為少量名詞給予注釋,如烏尼戈意為狐貍,嘎樂(lè)意為火,這些意義在小說(shuō)系統(tǒng)里起了直接的或象征性的作用。但大部分并未加以解釋,并創(chuàng)造了如“吻驢的毒唇”等攜帶著并未言明的神話象征意味的詞匯,這些無(wú)法解碼的空白鍛造了一種想象的停靠,作為敘事的延宕,發(fā)散出無(wú)盡可能性。
王奕寧:我看到有人評(píng)論渡瀾對(duì)世界上事物總有一種天然呆的延遲感,但我更覺(jué)得她保護(hù)了青少年時(shí)期心態(tài)的敏感與豐沛。也正因?yàn)檫@,她的語(yǔ)言風(fēng)格才會(huì)既有稚氣孩童的柔和與諒解,又夾雜著歷經(jīng)磨練的成年人的犀利與深刻。小說(shuō)中設(shè)計(jì)了自帶含義的蒙古文名字,比如“鼬鼠之天敵”的烏尼戈,代表財(cái)富的俄日敦德日格勒,“招弟”的杜達(dá)古拉等等,這些名字組成了小說(shuō)中情節(jié)推進(jìn)的重要關(guān)卡。它們帶有對(duì)貪婪人性、落后習(xí)俗等文化內(nèi)核的諷刺,但又因?yàn)槭敲值木壒首兂闪艘环N帶有模糊感與距離感的獨(dú)特意象,使得這些諷刺少了些刻薄的感受,多了幾分跳脫靈巧的活潑,也為故事罩上了一層神秘色彩。
于明玉:是的,僅有她能像摩西分紅海一樣直抵本義彼岸。我梳理了一下小說(shuō)中的名字,狀貌逾常的莫德勒?qǐng)D寓意“智者”,性格怯弱的阿拉坦巴圖象征“如金子般堅(jiān)固”,甘狄克“花崗巖”、扎那“大象”、三丹“檀香”、索布德“珍珠”……隱秘的民俗事象符碼自異域文化的裂罅中向外窺探,裹挾神性與詩(shī)意。
張林:另外,在渡瀾小說(shuō)中,名詞常常并非單獨(dú)點(diǎn)狀出現(xiàn),而是通過(guò)修飾、并置或遞進(jìn)等關(guān)系聚合成束,他們的組合不是建立在理性邏輯之上,而是跟隨作者萬(wàn)物渾融的獨(dú)特思維,鋪展成奇詭斑斕的畫(huà)卷。索緒爾在《普通語(yǔ)言學(xué)教程》中提出語(yǔ)言本為“亂糟糟的渾然之物”,而渡瀾則將“渾然”帶來(lái)的獨(dú)特效果極致發(fā)揮,將不同性質(zhì)的名詞混用。她在充滿民族性與神話感的自然類名詞群落里插入現(xiàn)代性的科學(xué)類、工業(yè)類名詞,她將新幾內(nèi)亞桉樹(shù)和甲狀腺激素、分裂增殖、骺板軟骨并置,將羊奶、黑艾日格與氧氣、氮?dú)狻⒛蕷饣橛痴眨瑢⒔瘘S色葡萄球菌、小腸耶爾森菌與美人指、甜象草、炭火味道糅合。渡瀾也在充滿原始象征的詞語(yǔ)中嵌入屬于理性時(shí)代的抽象性、說(shuō)明性詞匯,如講述關(guān)于傻子烏尼戈的名字時(shí)提到了應(yīng)用于管理學(xué)、網(wǎng)頁(yè)設(shè)計(jì)等領(lǐng)域的KISS原則;刻畫(huà)生氣的鄰居時(shí),形象描繪其波濤洶涌的肚子,執(zhí)拗的腳,再加以總結(jié)為:結(jié)構(gòu)性的生氣經(jīng)驗(yàn)。這種特殊的用詞習(xí)慣或許與蒙漢雙系統(tǒng)學(xué)習(xí)經(jīng)歷有關(guān),蒙語(yǔ)塑造的萬(wàn)物有靈的思維方式已然純熟,當(dāng)新名詞進(jìn)入其語(yǔ)言系統(tǒng)時(shí),即被吸納為萬(wàn)物的一部分,這是一種豐富而非破壞。
李婧怡:修辭在渡瀾寫(xiě)作中占據(jù)著重中之重的位置,其中通感則占據(jù)主要位置。在文章中,五感仿佛統(tǒng)統(tǒng)混淆,聲音可以充滿痛感,人看起來(lái)可以像溫和的氣候,皮膚在恐懼時(shí)會(huì)散發(fā)出一股臭味兒……這種看似缺乏邏輯、不符合常識(shí)的搭配,賦予無(wú)形的東西以形狀,擊打有形之物直至其消散、彌漫在各個(gè)角落。小說(shuō)中人與動(dòng)物、人與自然、此物與彼物之間的界線消失了,一切都處于變形和無(wú)規(guī)律之中,世界在呼吸之間脹縮。小說(shuō)中撲面而來(lái)各種感覺(jué)——vibe——僅僅是一種氛圍。當(dāng)你無(wú)法從她的語(yǔ)言中獲得清晰邏輯與意義時(shí),不需要用常識(shí)和理論去規(guī)范和解讀,只需將自己浸沒(méi)其中。蓬勃的氛圍感推動(dòng)敘事,像層層海浪交疊著涌上沙灘。讀者隨之變幻成一條魚(yú),躍遷于水面。
張暉敏:感官之間傾斜流動(dòng),物種間的邊界也變得模糊。模糊始于命名的混雜,狐貍即是烏尼戈,烏尼戈即是那個(gè)衰老與新生間往復(fù)的男孩;嬰兒即是嘎樂(lè),嘎樂(lè)即是火,火同時(shí)是呼喚和警告,名稱虛弱地提示著它們的分別。千頭萬(wàn)緒間難以尋找到完整的邏輯鏈條,因此修辭也開(kāi)始脫離技法的層面,“擬人”和“擬物”都無(wú)法確切概括其間深層關(guān)聯(lián),隱藏其間的、完全詩(shī)化和抽象化了的意義等待著被發(fā)掘。
張林:大片明喻隱喻換喻夸張擬人翻飛漫溢,但她賦予這些修辭以非修辭的性質(zhì)。擬人以人類為中心,比喻基于事物之間的分別,夸張要首先認(rèn)證某種理性的現(xiàn)實(shí)。而渡瀾的文學(xué)世界卻并不刻意分別人與物、物與物的形態(tài),這一方面體現(xiàn)在人物塑造的未確定性,比如由日本黑烏鴉產(chǎn)下的柳澤真由娜,是“三十歲左右,頭發(fā)稀少的女性”,有乳房,嘴唇,卻也會(huì)掉落黑色羽毛,作者不明確其形態(tài)是人還是烏鴉,也不將其作為兩種形態(tài)簡(jiǎn)單疊加,仿佛一個(gè)人身上掉落羽毛是自然而然的,就像變成羽毛的三丹姐姐,是鳥(niǎo),還是人,不去區(qū)分。無(wú)須描繪本身便傳遞一種態(tài)度,即渾融齊物的宇宙觀,這與其說(shuō)是一種修辭(擬人、比喻),不如說(shuō)是寫(xiě)作者世界觀的呈現(xiàn)。至于看似是夸張修辭的部分,或許也是渡瀾想呈現(xiàn)的本來(lái)面目,烏尼戈身上兼具不同的人生階段,飛速變換,這是她塑造的獨(dú)特生命形態(tài);死也不是一種夸張,它輕易且自然,佛教稱涅槃滅除煩惱,度脫生死,死是寂滅的邊界,但在渡瀾筆下,死后依然言語(yǔ)不休,煩惱不斷,生死邊界就這樣消弭,夸張的修辭性質(zhì)也在分界線的消融中自行瓦解。
于明玉:作者曾不止一次地以候鳥(niǎo)、四季等一切循環(huán)往復(fù)之物為生死開(kāi)解:“我們的朋友烏尼戈永生不息——他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消失了。”這一有無(wú)相生、順其自然的哲學(xué)思維撕破“形”與“界”。《金甲蟲(chóng)》里一條匪夷所思的動(dòng)線——融化的雪、用胡子制作的門(mén)、馬鞭、山雀的啼叫——演示了聲響向色彩的更新;鼬鼠、汽車、火、舌頭、老虎、牛皮、鳥(niǎo)標(biāo)本等意象層出疊現(xiàn),在其私人辭典里蜿蜒出一套挾有幻覺(jué)氣質(zhì)的象征群組,并最終化為一聲張牙舞爪的恫嚇。事物人格化、謎語(yǔ)式的欲望書(shū)寫(xiě)、形象的變化與擬構(gòu),共同推動(dòng)渡瀾穿越“稠密地帶”,直抵“表達(dá)的真實(shí)”。
張暉敏:文集中來(lái)自不同民族的撫觸切碎詞語(yǔ)原本權(quán)威:交錯(cuò)的口語(yǔ)、書(shū)面語(yǔ)、“過(guò)大”和“過(guò)小”的形容詞,幾乎可以構(gòu)成一個(gè)微小卻嶄新的隱喻系統(tǒng)。因其承載了作者完整的思維過(guò)程,盡管能指和所指的關(guān)聯(lián)不斷受到挑戰(zhàn),文字的生命力卻沒(méi)有被削弱,反而愈加豐盈。文集獨(dú)特的修辭特征近于古典詩(shī)的“曲喻”,又因其篇幅和句式的不受限顯得格外放縱。萬(wàn)物有靈的世界里狂歡永不停息,陌生化的語(yǔ)匯帶著天然而野性的節(jié)奏激情,構(gòu)成了鮮明的辨識(shí)度,也為讀者的閱讀體驗(yàn)增加了質(zhì)感。
3.彎曲的敘事脈絡(luò)
張暉敏:與其說(shuō)是講故事,我覺(jué)得渡瀾更像是在寫(xiě)詩(shī)。非母語(yǔ)寫(xiě)作在文字中留下的中頓痕跡帶來(lái)了詩(shī)行般節(jié)奏。詭譎的邏輯鏈條,則使得文本免于落入起因—經(jīng)過(guò)—結(jié)果的線性敘事。小說(shuō)中童夢(mèng)色彩強(qiáng)烈的故事十分單純和儉省,沒(méi)有人試圖追問(wèn)卡夫卡的城堡是羅馬式還是哥特式,那么親吻公驢的生殖器誕下金魚(yú)也可以具備合理性。故事的結(jié)局并不難揣測(cè)。就像王子和公主總要生活在一起——壞脾氣的鄰居遲早自取滅亡,珍貴的羽毛必然遭到破壞,跳舞的烏嘎一定藏著謊言。但是讀者可以揣度故事的走向,承上啟下的規(guī)則似乎在照常運(yùn)作著,但只要稍不留神,便會(huì)從原本看似平滑無(wú)縫的情節(jié)之間重重跌落。徹底消化文本信息量不能一蹴而就,聆聽(tīng)者只能囫圇吞下這個(gè)草原吟游詩(shī)人的全部詭計(jì)。
于明玉:在渡瀾小說(shuō)里,情節(jié)是覆蓋語(yǔ)言富礦的薄土。一方面,主人公的種種舉動(dòng)缺少標(biāo)記明顯且邏輯自洽的行動(dòng)序列,讓觀客無(wú)從拾撿解讀焦點(diǎn)。而敘事脈絡(luò)也一再以凸字或U型的姿態(tài)出現(xiàn),毫不避諱其模式化與不完整性:起點(diǎn)往往會(huì)預(yù)設(shè)一個(gè)抽象、籠統(tǒng)的答案,而后泡沫樣的高潮弧線便兜轉(zhuǎn)升起(中途它幾近漲破),當(dāng)文字呱噪得漸次拱起紙張,故事卻滑向寂若死灰的烏有或溫情脈脈的永恒。“始”與“終”紛然落歸一線——目睹甘狄克慘死的風(fēng)止息于靈魂被燒盡的松林,去而后返的烏尼戈照拂每寸生命的酣眠,阿拉坦巴圖得知噪音真相的那一瞬,“整個(gè)世界陷入了一種驚人的寂靜”,似乎是急于將一切飄曳在外的余語(yǔ)都掐滅。
李婧怡:在我看來(lái),渡瀾的敘事并非以復(fù)雜緊湊取勝。以首篇《傻子烏尼戈消失了》為例,我們或許可以對(duì)其結(jié)構(gòu)作此解:相遇(出生)——誤解(挫折)——崩潰(死亡)——重逢(重生)。渡瀾在此為烏尼戈也為我們畫(huà)出了一個(gè)完滿的圓,它如一面嶄新發(fā)光的鏡子,反射出回環(huán)往復(fù)的時(shí)間觀與萬(wàn)物來(lái)去自由的生死法則,同時(shí)也映照出普通人的日日夜夜。面對(duì)這樣一種充滿無(wú)限可能性的敘事模式,我們可以秉承開(kāi)放的解讀理念對(duì)小說(shuō)內(nèi)容作出多種角度的解讀,例如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人與人的關(guān)系甚至人的異化等等。
于明玉:恰如雷蒙·凱諾所言,“盲目屈從于沖動(dòng)的所謂靈感,實(shí)際上是一種不自由。” 人物行動(dòng)的屢次失常同結(jié)構(gòu)形式的無(wú)限翻版,一起攪渾在渡瀾詩(shī)人般的創(chuàng)造中,也使文本的易讀性蒙塵。實(shí)際上對(duì)讀者而言,從開(kāi)局邁向結(jié)尾是困難的。大量信息從瘋轉(zhuǎn)事件中逸散,如過(guò)山車期間的風(fēng)聲與尖叫一般,達(dá)成了短暫的信號(hào)屏蔽效果,又在敘述完畢的那一刻迅速結(jié)網(wǎng)成罩。由此小說(shuō)集里充斥著異質(zhì)性的鬼影和漩渦,試探、狐疑與不信任竟成為了觀者的常態(tài),一個(gè)巨大的騙局悄然誕生——藍(lán)蜻蜓日迪接回了“智慧達(dá)達(dá)”,扎那失去了“三丹姐姐”,在自由意志席卷的林野中央,渡瀾平靜告訴我們,她所講述的就是這樣一件簡(jiǎn)單的事。
張暉敏:曲線敘事的方法,令民族、地域、文化的差異短暫閃現(xiàn)又消弭,因其生動(dòng)而并不令人覺(jué)得突兀。在詩(shī)化的、狂歡的自然之境,任何封閉閾限都可以短暫性被打破。敞開(kāi)的廣場(chǎng)上,只剩下欣喜的“孩童們”——人、獸類、或是其他生靈——留下的足跡。
和光讀書(shū)會(huì)簡(jiǎn)介:
大連理工大學(xué)中文學(xué)科“和光讀書(shū)會(huì)”成立于2018年6月,主持人戴瑤琴,“和光”定位是本碩貫通、“90后”及“00后”、文理交叉。“和光”已發(fā)表專輯《時(shí)代記憶與空間符號(hào)認(rèn)同的東北書(shū)寫(xiě)》《<大山里的小詩(shī)人>:翻山越嶺的希望之光》《<飛鳥(niǎo)和池魚(yú)>:錦鱗繡羽,水陸藏心》《<貝爾蒙特公園>/東京說(shuō):要頑強(qiáng)啊!》《<流俗地>:生于落俗,安于流俗》《<男孩們>:臍帶與魚(yú)線》《<流俗地>:俗地之光,豈能流逝?》。
- 小說(shuō)要寫(xiě)出生活的質(zhì)感[2022-06-24]
- 在小說(shuō)中呈現(xiàn)的現(xiàn)實(shí)有多“現(xiàn)實(shí)”[2022-05-27]
- 鄭在歡:我是周星馳的粉絲,喜劇是我的底色[2022-05-24]
- 陳鵬:六年,我們真誠(chéng)地為中國(guó)文學(xué)發(fā)展盡了一份綿薄之力[2022-05-18]
- 何平:文學(xué)批評(píng),首先要找到“現(xiàn)場(chǎng)”[2022-04-28]
- 林森:?作家應(yīng)開(kāi)拓新題材提供新結(jié)構(gòu)[2022-04-26]
- 想不通的事,就成了故事[2022-04-22]
- 現(xiàn)實(shí)生活自帶能量[2022-04-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