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料叢林中尋找接近魯迅的小徑
導語:2020年9月九州出版社推出《桃花樹下的魯迅》一書,在學界內外引起反響。魯迅研究專家、原魯迅博物館副館長陳漱渝稱作者黃堅是“魯研界外的高手”。黃堅為江西萍鄉人,定居南昌,曾著有《思想門:先秦諸子解讀》。現特邀兩位學者就《桃花樹下的魯迅》展開對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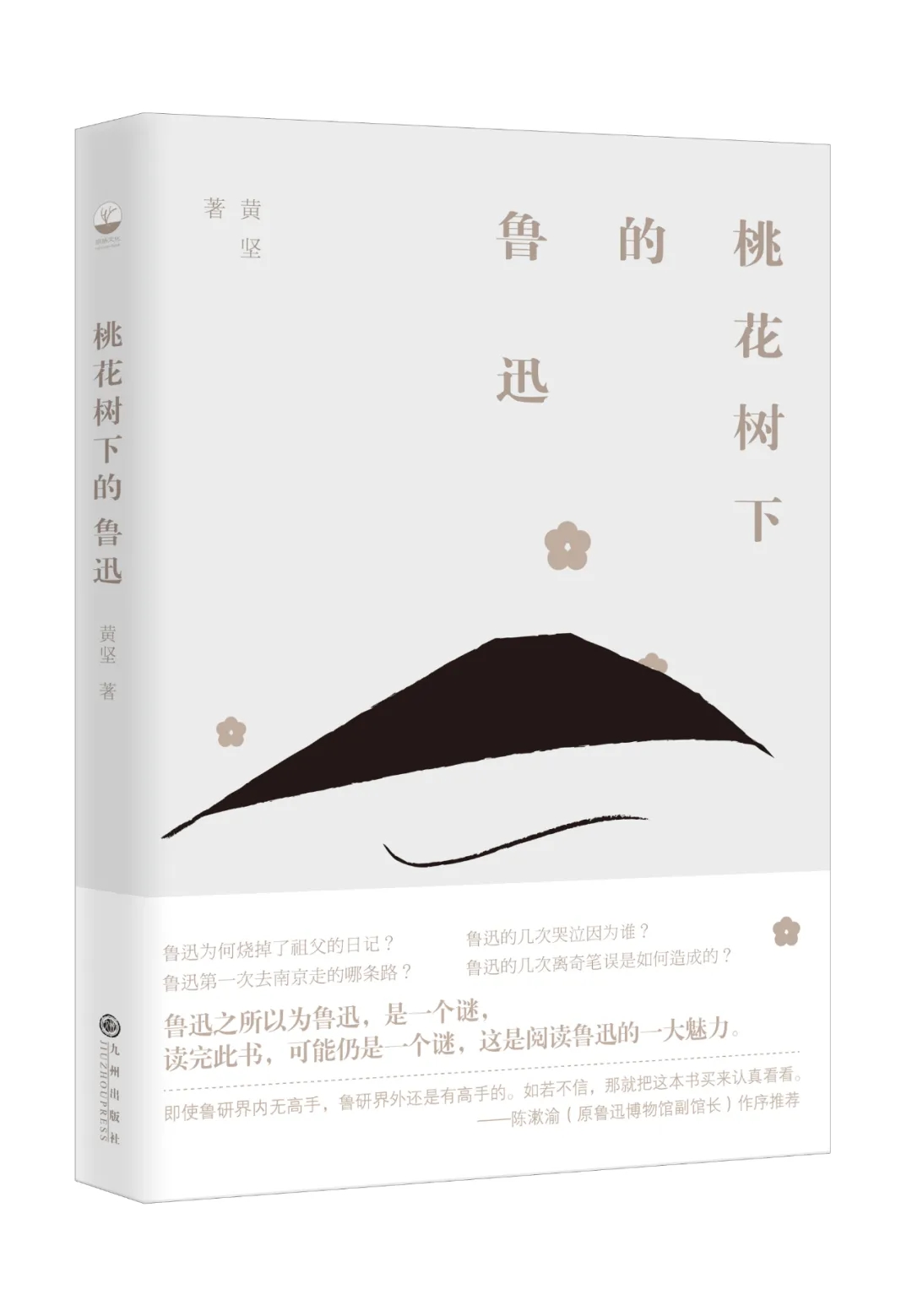
“人之子”魯迅
黃海飛:看到書名有點意外,“桃花”這樣一個指向“春天”“輕松爛漫”的意象在第一印象里似乎很難和魯迅聯系起來。如果讓您用一種樹來跟魯迅勾連,您會想到什么樹?
胡少卿:第一反應可能是棗樹,冬天的棗樹,黝黑,銳利。
黃海飛:是,大多數讀者第一印象是棗樹,就是魯迅寫的:“在我的后園,可以看見墻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作者獨獨挑出“桃花樹”,顯出對魯迅文字的熟稔,以及對于魯迅形象的別致意見。讀完全篇,發現桃花和魯迅的并列很有道理。作者是要揭示魯迅溫暖或生活化的一面。
胡少卿:努力寫出一個真實的活人。
黃海飛:作者抓住了魯迅生命中非常精彩的一些瞬間。他比較關注魯迅生命的兩端,一端是青少年魯迅,另一端是老年魯迅。為什么魯迅最后會突然想起桃花?當時已經是1936年4月15日,他給一個陌生的年輕人(顏黎民)回信,大約顏黎民在信中談到桃花。
胡少卿:從作者行文中我聯想到,這帶有一點回光返照的色彩。張愛玲的小短文《愛》里寫一個被拐賣的女子,到年老的時候,也總是回憶年輕時在春天月光中的桃樹下和一個鄰家小伙的偶遇。
黃海飛:是進入了生命晚年的一種狀態,書里作者也提到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讀魯迅晚年的作品,大概是1934年以后,能看到一個有點衰老、心力交瘁的魯迅,會有一種心疼的感覺,在上海的魯迅過得一點都不自在。在給朋友的信里,他說我很想出去,但沒有辦法,一方面是生活的壓力,同時也身不由己,他有很多活動,成為他的枷鎖。比如書中提到的酒,魯迅身體其實不能喝酒,但不斷地有招飲,必須去應酬。像《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這封信其實給了他生命最后一擊,加速了他的死亡。
胡少卿:這本書在市場上被歸入傳記類,其實它不是傳記。波蘭詩人米沃什說,傳記就像一個蚌殼的殼,真實的蚌的生命已經消失了,讀傳記只是收獲了一個殼而已。黃堅采取了一種比傳記更為迂回和游擊式的方法去靠近魯迅。他考察的角度不是俯視也不是仰視,是平視。他把魯迅當作一個普通人,一個跟我們一樣有喜怒哀樂、有缺陷的人來寫。作者選題的角度側重于生活和日常的方面,比如討論魯迅是否好酒、魯迅的哭泣、魯迅的遇險與避難、魯迅的筆誤等。魯迅的生命中不只有黑暗、尖銳、冷峻的東西,也有溫暖明亮的東西。黃堅說魯迅的生命是一面三色旗:“黑色代表歷史和力量,白色代表道德和幻想,紅色代表浪漫和溫暖,這樣才構成一面完整的魯迅之旗。”作者對魯迅的描述可以和蕭紅散文《回憶魯迅先生》相印證。蕭紅說魯迅是愛笑的,他的枕邊放著一張小畫,在病中常常拿出來看,畫上是一個穿長裙頭發飛散的女人在大風中奔跑,地上散落著玫瑰。這些細節體現了魯迅內心柔軟的一面。黃堅以前的著作《思想門》,把孔子當作一個普通人來寫。這本書的思路一樣。孔子跟魯迅算是我們樹立的兩尊雕像,黃堅努力想把這兩尊雕像復活為我們身邊的朋友。
黃海飛:本書確實對于過去刻板的魯迅形象進行了反撥,回歸到“人之子”魯迅。我們可以梳理下魯迅形象的變遷。魯迅生前,人們對于魯迅的評價是多元化的,有褒有貶。魯迅自己很清醒,他沒有把學生或朋友的過高贊譽太當回事。別人把他奉為“導師”或者“青年叛徒的領袖”,他是不要這些“紙糊的桂冠”的。很多人把魯迅跟高爾基相比,魯迅在書信里則自謙地說:“我那里及得高爾基的一半。文藝家的比較是極容易的,作品就是鐵證,沒法游移。”
胡少卿:當年劉半農想推薦魯迅參評諾貝爾文學獎,魯迅就回信說自己不配得獎:“要拿這錢,還欠努力……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
黃海飛:從魯迅逝世到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文革”中,魯迅的地位被抬得非常高,不斷“圣化”。“文革”以后開始反撥,出現了非議、否定魯迅的聲音。最為知名的就是21世紀初,王朔等發表的非議魯迅的文章。近十年來,確切地說是微博、微信興起之后,在社交媒體上我們看到魯迅的形象變得輕松、活潑,甚至略帶搞笑,受到了年輕人的追捧,成為流量的寵兒,如愛懟人的魯迅、吃貨魯迅、設計師魯迅。我稱之為“輕魯迅”。
胡少卿:課上講魯迅的時候,學生對魯迅在上海的生活狀況特別感興趣,說他屬于當時的高收入群體,生活方式很時髦,常去看電影,也很講究吃。還有一些研究者開始關注魯迅作為凡人的生理性的一面,如考證說他日記里記載的“夜濯足”是指自慰,而跟弟弟周作人反目的原因是偷看弟媳洗澡。
黃海飛:這就有點跑偏了,甚至可稱惡俗。但我們確實能看出這樣一個趨勢,近十年或者說進入21世紀以來,生活魯迅、作為人這一面的魯迅重新回歸,甚至占據了主流地位。黃堅這本書是在這個潮流之中的。
胡少卿:魯迅是普通人,但同時有他的非凡之處。黃堅努力去寫出現實的多面性。他在《魯迅的哭泣》這一章里記載魯迅的一次流淚,我印象很深。引用的是增田涉在《魯迅的印象》這篇文章里的回憶——因為魯迅說了許多中國政治方面的壞話,有個日本歌者在宴席上問他:你討厭出生在中國嗎?魯迅回答說:不,我認為比起任何國家來,還是生在中國好。增田涉看到魯迅“眼里濕潤著”。從這個細節里可以看出魯迅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他的怒罵和批判都是出于對中國的愛。他愛的不是哪個具體的政權,而是這片土地、土地上苦難深重的人們。這樣我們也就理解了,為什么他去世的時候,人們把“民族魂”三個字覆蓋在他的靈柩上。魯迅有很值得尊敬的一面,不能無限制地把他拉向瑣碎、日常,黃堅在寫作中是注意到了保持這種平衡的。
黃海飛:上面我提到的“輕魯迅”現象,是不是把魯迅看得太輕巧了?現在的年輕人不喜歡太沉重,刻意在回避這些東西,但魯迅沉重的一面反而更有價值。
胡少卿:那才是決定魯迅之為魯迅的地方。
黃海飛:您剛才提到的增田涉的回憶,我之前讀到那里也很感動。有人曾把魯迅和莊子做過比較,他們確實有一些相似點,比如,面冷心熱。
胡少卿:嗯,就是說話可能很毒,但內里是古道熱腸。
黃海飛:魯迅自己在文章里也提到了,他說我其實是不夠世故的,如果夠世故,我就不會說出來。正是因為對于民族和文化的熱愛,才會造成他的那種“峻急”。他的態度、立場、說話的方式是非常激進的。這也關涉到本書涉及的魯迅的兩面性問題。魯迅寫文章和在生活中其實有兩個形象,或者說有兩套說辭,這中間存在矛盾之處。黃堅老師敏銳地發現了,本書多篇文章都有涉及,比如《學潮中作為不同角色的魯迅》《魯迅自己的兩面之詞》,包括魯迅一方面是愛喝酒的,但他在給朋友的書信中自述卻稱不喝酒。不只是喝酒的問題,魯迅在很多地方都是以一種決然否定的語詞來表述的,但跟他生活中表現出來的完全相反。這時就要區分魯迅表達的語境是什么,是一種公眾話語還是私人話語。魯迅自己對公和私分得很清楚。
胡少卿:錢理群老師曾把魯迅的文字分成兩種,一種是“為自己的”,一種是“為他人的”。“為自己的”以散文詩集《野草》為代表,會去展露內心比較黑暗、像深淵的一面;“為他人的”包括他的小說集、雜文集,會比較多地給出信心和希望。現實本身就很矛盾、復雜,一個人的性格中也可能糾結了許多矛盾的東西,人不是單面的,作者沒有向哪一個極端強調,而是努力讓自己的寫作符合于生活的微妙和復雜,把握住了平衡。
見微知著
黃海飛:陳漱渝先生在序言中說,作者在寫這些“小文章”時下了“大功夫”,不少文章寫得都很“厚重”。作者很有問題意識,能在他人不疑處生疑,多問一個為什么。
比如魯迅與祖父周福清這樣一個選題,是過去魯迅研究界關注很少的。中國知網上從1981年至今總共只有19篇文章,而且大部分圍繞周福清的生平及科場舞弊案,對于魯迅和周福清的關系論述得不多。這個話題還具有開掘空間。
又如《魯迅第一次去南京走的哪條路》選取的也是一個鮮為人關注的話題,即魯迅第一次去南京求學的交通問題。這是已有研究的盲點。其姊妹篇《上海:魯迅第一次去南京的途經之地》以史料集錦的方式關注魯迅第一次去上海的經歷。過往研究魯迅與上海的關系主要集中于上海十年時期,近年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上海魯迅紀念館施曉燕老師的《魯迅在上海的居住和飲食》,關注的也主要是這一段。而對于1927年以前魯迅與上海的交集,學界關注較少。如本書作者在文章中指出的:“年青的魯迅和跟他一樣年輕的上海,在屢次的擦肩而過和相互注視與映照下,經歷了彼此的成長與蛻變。然而,這樣一種緣分關系,卻至今未被人們充分認識。”這里捎帶說一句,作者在文章中有一個精彩比喻:“假如把魯迅的一生,看成是一座現代雙塔斜拉橋,北京和上海,就是那兩座高高的雙塔,其在魯迅生命中所占的意義,是怎么評估也不過分的。”
胡少卿:作者不僅選題的角度比較清奇,而且帶有跨學科色彩,比如《魯迅第一次去南京走的哪條路》,綜合了地理學、社會史等多方面的知識來考證。
黃海飛:對!這篇文章討論魯迅為何舍近求遠,不走相對直線的運河路線,而要繞道上海、折向南京,以較為翔實的史料展現出晚清末年杭嘉湖蘇地區運河衰敗、治安糟糕、吏匪橫行的狀況,由此來解釋魯迅的選擇,合情合理。這是典型的“以小悟大,見微知著”,以魯迅走哪條路這樣一個很小的問題,展現出晚清末年江浙滬的交通史、社會史。又如在《桃花樹下的魯迅》這篇中,作者在討論魯迅和桃花這一意象時,突然宕開一筆討論中國文學史上對于“桃花”意象的評價的變遷,也展現出文學史和文化史的視野。
胡少卿:還有一處是典型的以小見大、由小及大。作者考證說魯迅跟他的祖父周福清在“寄望心太重”這一點上很相似,因為“寄望心太重,寄望太深”而性格“峻急”;峻急不僅體現在對周作人的懈怠“揮以老拳”,也體現在對自己的要求上,甚至體現在對自己身處的民族的期望上。這種解釋從私人生活引申到了魯迅的寫作風格。為什么魯迅的雜文里有很大的火氣,總是跟人論戰?就是因為“愛之深,恨之切”。這樣話題就拓展得深廣。這是典型的“小題大做”,一種很妙的做文章的方法。
全書帶有知識考古的色彩,作者像“史料偵探”一樣,在大量的史料里去尋找線索,并把這些線索勾連起來,試圖去復現一個多面而復雜的現實狀況。可以看出作者是熱愛魯迅的,但這種熱愛不等同于盲信盲從。作者要把他的熱愛建立在一個真實的地基上,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把前人對魯迅的講法的很多虛浮之處都夯實了。比如指出魯迅的筆誤,這是正常人都可能犯的錯誤,沒有必要去為了塑造一個完美的魯迅而去掩飾。以前通常說魯迅是革命家,但這只是一種籠統的說法。本書就去考證,魯迅對待學生運動的態度是什么?是很復雜的,魯迅有時候處于一個觀望的狀態、懷疑的狀態,有時候他甚至身處學生的對立面。通過作者對史料的梳理,可以看出魯迅對于熱鬧的群眾運動,多多少少是保持有一定距離的。還有魯迅對于自己在共產主義中國的遭遇的想象,顯示了魯迅預見未來的敏銳度。在《江、浙較量:巧合還是傳統?》一章,作者指出,魯迅跟論敵的論戰,有時會局限于地域上的某種偏見或既定想象,這其實是提示了魯迅思想中的弱點。
黃海飛:黃堅老師的研究是和學界在一個頻道同步共振。他肯定沒看過邱煥星老師的論文,但他關于魯迅與學潮的觀點與邱老師是一致的。
微妙感
胡少卿:在求真的基礎上,作者行文中還有許多文學化的、帶有靈性的成分,讓表述清晰而有美感,有點像黃仁宇描畫歷史的手法,也有點像本雅明的評論,在扎實的基礎上加入感性,試圖勾勒出歷史當中的微妙感,能看到明顯的才氣。書中提到魯迅筆名中的“迅”字,跟他年輕時在上海看見的輪船的速度有關。這個觀點以前似乎從來沒有人提出過。
黃海飛:這個我不太同意,這個判斷下得有點急了。“魯”這個字,大家沒有什么爭議,因為這就是魯迅母親的姓,魯跟周本來就是同姓的國家。而關于“迅”字則有幾種解釋,最為通行的說法是許壽裳先生的版本,他當面問過魯迅,魯迅回答說是“愚魯而迅速”的意思,我覺得這個是最合理的;第二種,黃堅在書中也提到了,歷史學家侯外廬先生說是“狼子”或“大力士”的意思,這是比較奇異的說法。作者在文章里面也不同意侯先生,并提出了一種新的假設,猜測“迅”字與魯迅青年時期對輪船速度很快的觀感相關,而且作者在書中還引用了鄧小平20世紀70年代末訪問日本時坐新干線的典故。
胡少卿:郭沫若寫過一首詩《筆立山頭展望》,是他在日本的時候,看見日本的港口停滿了輪船,感到很震撼。詩里將輪船冒出來的黑煙喻為黑牡丹,將其視為文明的象征,這是魯迅的同代人對輪船的震撼體驗,輪船在那時就代表著一種現代和進步的力量。
你剛才提到青少年時代魯迅和上海的關系之前研究得比較少。作者這里揭示了上海對少年魯迅、青年魯迅的影響。一個人很多事情,其實在他的童年、青少年時代都已經決定了,他在成年的許多做法,是對以前埋下來的線索的一次追溯、一次印證。作者推測魯迅后來取筆名為“迅”,跟他在上海所感覺到的輪船的速度有關。當然這本身是無法求證的,只能說是推測。如果這個推測成立的話,就意味著魯迅的“迅”這個筆名代表著魯迅對于中國現代化的迫切心情,希望中國也能夠加快速度,趕上世界文明的列車。“魯”有遲緩的意思,和“迅”正好構成一對反義詞。
黃海飛:不得不承認,作者很敏感,他能把這兩個東西聯系在一起,很有想象力。青少年魯迅這一塊的研究非常重要,但也是現在魯迅研究的一個薄弱點,因為這段材料很少。有一些學者正在做這一塊研究,比如河北大學劉潤濤老師,他就專門做魯迅的前半期研究。在這一點上,黃堅老師跟當下的學術潮流也是暗合的,他其實自覺或不自覺地就在潮流當中。
胡少卿:作者的寫作帶有某種文學化的想象,這個結論不是一個真憑實據的連接,而是帶有主觀發揮。
黃海飛:如果加上“可能”兩個字,就更嚴謹一點。其實作者后來也沒有下定論。
胡少卿:作者寫作的時候還是很注意把握那種微妙感的,他不完全說透,因為有些事一旦說透了就顯得特別俗。比如《桃花樹下的魯迅》這一章,一般提到桃花往往跟愛情、桃色新聞有關,而作者在這一章里也提到了魯迅在寫到桃花的時候,他興奮的心情可能與他和許廣平的戀愛有關系,但作者拒絕絕對地把兩樣東西套在一起,因為這個事情本來就是一種很微妙的東西。這章里面作者寫了魯迅的愛情,也寫到魯迅對桃花的興趣,但這兩者之間又不必然構成某種關系,所以這地方作者是點到即止,這樣的處理是很妙的。相對來說低端一點的作家,就容易把這個事情給坐實了。
黃海飛:作者確實很會寫文章。在閱讀本書的時候,我常常感嘆作者寫作的巧妙。作者善于設問,就像您剛才說的像一個史料偵探一樣,不斷地提問,然后回答,然后又提問,他這個技巧用得非常好,文章的結尾也結得好。過去人常說開頭和結尾是最難的,汪曾祺原先就談過沈從文的結尾非常好,其實汪曾祺自己的結尾也結得漂亮,結尾是能夠看出一個人的水平和才氣的。黃堅老師很多文章的結尾都結得非常漂亮。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第一篇的結尾收束,說是“就像周福清揮舞八角銅錘追打四七”。他很多的結尾都是這樣的單句結尾,很短促又很有力,有一種余味、余韻在里面。
胡少卿:作者努力揭示史料之中微妙的關系還有一處令我印象很深。在《魯迅一生中的避難和風險》這篇里,注解里有一句話:“從某種角度說,幽閉于深宮的光緒皇帝在十九世紀末的一次政治‘噴嚏’,卻成為二十世紀初文化思想魯迅誕生的‘第一推動力’。”是說因為光緒皇帝政治抱負不得施展很苦悶,所以把魯迅祖父周福清的科場舞弊案加以重判,而祖父的遭遇又影響了魯迅的成長,構成了魯迅的某種文化基因。這個地方有點像揭示史料和史料之間的蝴蝶效應,非常敏銳而有趣。
黃海飛:我聯想到柯林武德所寫的《歷史的觀念》。柯林武德也認為歷史是需要想象力的,要在觀念里面去推演歷史。無論是史料研究還是文學研究,想象力都非常重要。能把兩個看起來不相關的東西勾連在一起,并進行論證,如果成功了,那就是一家之言。我很認同陳漱渝先生在序言里說的,黃堅老師確實可以說是魯研界外的一個高手。
胡少卿:黃堅是民間學者,不屬于任何機構,也不屬于體制。不過他是有家學淵源的,他的五叔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黃宣民先生,曾擔任侯外廬先生的助手。黃堅做研究是出于興趣,就像作者介紹里說的,他“以研究與寫作為志業”。他不需要去考慮我怎么寫學術雜志才能發表之類的問題,而是按照“我覺得這樣寫最好,我就這樣寫”的方式來寫作。
黃海飛:是的,所以我們能夠看到作者很少受束縛。但是讓我很驚訝的一點在于其實作者是很遵守學術規范的。我看到書中不僅重要的材料都有注釋,甚至在一個地方使用了轉注,這是非常嚴謹的態度。當然,也有一點不足。我看了作者所列的“參考書目”,還有一些重要資料似乎也可以納入,如《魯迅生平史料匯編》《1913—1983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匯編》《回望魯迅叢書》等,尤其是《魯迅生平史料匯編》至少得加進去。
胡少卿:作者在《隨感與遐想:散說魯迅》這篇里提出一個概念叫“小化思維”,讓我有豁然開朗之感。“小化思維”是指,魯迅在解釋一些事情的起因時,會傾向于提供具體而微的細節。比如,魯迅說自己之所以棄醫從文,是因為看了有關日俄戰爭的幻燈片。而日本學者則考證說,他們不相信魯迅輟學是因為看了幻燈片。按照黃堅的“小化思維”概念,這可能是魯迅自己的一種文學化發揮;魯迅本人在《藤野先生》里講的“畫血管”的故事,就是他的自供狀:藤野先生說,你看你把血管畫歪了,魯迅說我這樣畫是因為這個位置比較好看。這個細節揭示了魯迅的思維方式:很多時候他在作品里那樣寫,是因為覺得那樣寫是一種比較好的文學選擇。他會為了美而犧牲一部分真,實際情況可能并非如他所寫。
黃海飛:黃堅對“畫血管”這個問題的揭示很有啟發性。他說畫血管的故事可以說是自我展示或暴露,甚至是一個隱喻。包括下文他又引了周作人的話,說魯迅好比是個盾,他有著兩面,雖然很有點不同,可是互相為用、不可偏廢。僅僅說魯迅形象是多元化的,這還比較淺,黃堅還看到了魯迅這樣一種矛盾交織的狀態。
胡少卿:魯迅《野草》的很多篇幅都是在表現這種既這樣又那樣的矛盾狀態,比如“影子”,徘徊于無地,又是在光明里,又是在黑暗里,如果完全光明了影子就消失了,如果完全黑暗了影子也看不見了,影子就是處在可進可退、左右為難的局面。魯迅對自己的概括是“歷史中間物”,“肩著黑暗的閘門”,這個形象也是這樣,一半身體在黑暗里面,一半身體在光明里面。黃堅引用林彪打仗時說的話:“沖下山去,和敵人攪在一起。”他說他在寫魯迅的時候,常常想起這句話。魯迅經常會反思自己,他不僅批判別人,同時也更深地去解剖自己。錢理群老師的魯迅研究特別強調這一點:魯迅揮向別人的刀子也更深更厲害地揮向自己。比如在《狂人日記》里,狂人批判這個社會吃人,但同時他會思考他自己是不是也曾經吃過人,“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魯迅不會像一些特別有道德義憤的作家,只會刀口向外,他的自我解剖、自我分析、自我批判,使他超越了許多同行。
“現代超前性”
黃海飛:魯迅其實很明了自己身上的黑暗,他下筆的時候不敢把心里的黑暗完全暴露出來。就像《藥》里面,添上一個光明的尾巴,加上一個花環,完全是為讀者考慮,或者說為青年考慮。黃堅推崇竹內好的一句話:“把魯迅冰固在啟蒙者的位置上,是否把他以死相抵的惟一的東西埋沒了呢?”如果把魯迅的形象單一化、凝固化,就喪失了魯迅的豐富性、矛盾性。我上學期給學生講《傷逝》,其中提到啟蒙的問題,我們會發現魯迅在那樣一個大家都在提倡啟蒙的時代,別人都在高呼戀愛自由、婚姻自由,他就比別人想得更透一步。他開始反思啟蒙和啟蒙者本身,質疑涓生作為啟蒙者是否合格,還有啟蒙的有效性問題,即我們是否做好了準備、我們有資格來啟蒙嗎?等等。最后發現是一個悲劇。
胡少卿:《傷逝》讓人思考:給你自由,你能用好嗎?讓你自由戀愛,你能做好嗎?魯迅不僅啟蒙,同時也超越啟蒙、反思啟蒙,意識到啟蒙的限度。所以,在現代社會啟蒙的神話破產之后,魯迅仍然是有效的。
黃海飛:再講一個例子,大一學生讀完《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以后也非常震撼,說完全沒有想到。那是1919年的文章,100多年前魯迅對于父母跟子女關系的思考,放在當下毫不過時。很多同學說現在許多父母還是原來那種觀念,還是說子女是要報恩的這樣一種態度。黃堅老師在書中提到魯迅當下的價值,用了一個詞叫“現代超前性”。魯迅到現在仍然沒有過時,可能是因為他揭示的是普世化的人性問題,是人性根本上的一些弱點。
胡少卿:魯迅寫的東西在以前被人們當作“國民性批判”來接受,但其中也蘊含了普遍性意義。比如說阿Q形象,很多國家的研究者發現他們國家也有阿Q,或者說他們的人性中也有阿Q的一面。阿Q的精神勝利法是一個人類的普遍性弱點,不僅僅是中國人的弱點。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魯迅才成為一個世界性的作家,他不僅展現我們自身的民族批判的一面,也展現人類性的一面。《野草》里對于內心深處黑暗、絕望情緒的描寫,是一種人類共通的現代感受。他引用裴多菲的詩句“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說的就是人類其實活在一個極大的虛無里。魯迅本質上是什么都不相信的,這種什么都不相信的絕望狀態,就是現代人的狀態。他和卡夫卡出生年相仿,他肯定沒讀過卡夫卡的書,但他像卡夫卡一樣,使用寓言的方式寫作,也寫人的各種“變形”,也生活在一個神圣世界瓦解之后的那種空虛和黑暗之中。他們的現代情緒是相通的。
黃海飛:魯迅自己一直都有世界視野。把魯迅的作用局限于“國民性批判”,是把他縮小了。其實他是一個現代作家,“現代”兩個字非常重要。
胡少卿:以前把他當成一個過渡期作家,他其實不是過渡的,而是在現代這個時段一直適用。魯迅本質上是個象征派作家,他的小說、散文詩是帶有象征含義的。他的小說其實都是些剪影,人物是一些寓言性人物,像詩一樣。李長之在《魯迅批判》里說魯迅的小說本質上是詩,魯迅本質上是個詩人、戰士——后來到沈從文才真真正正變成了小說家的方式。比如說短篇小說《長明燈》,小說中的那個瘋子完全是象征化的,他總是念念有詞,“熄掉它罷,熄掉它罷”,眼睛里射出狂熱。這個瘋子是一個象征的形象,不是個現實人物的形象。小說整個的場景特別荒誕,跟卡夫卡小說很像,是寓言式的。
黃海飛:可能也正是因為這樣,《長明燈》非常晦澀,南京師范大學的劉彬老師以前在《文學評論》上發表過一篇文章《從“吹燈”到“放火”》,解讀很精彩。您這么一說,這里面可能還有闡釋空間。
(作者單位:胡少卿、黃海飛,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文學院;記錄整理:張德地)

胡少卿,北京大學文學博士,對外經貿大學中文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領域為中國現當代文學、新詩,著有學術論著《中國當代文學中的“性”敘事(1978— )》、《駛向開闊的世界》等,詩集《微弱但不可摧毀的事物》,編有《顧城哲思錄》《殺像之意:廢名詩選》等,主編有“星空詩叢”等。
黃海飛,江西南豐人,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文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魯迅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