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惠雯筆下女性的家庭角色斷裂與情感置換:風(fēng)暴眼的沉默
近幾年,女性的生存地位不斷地被進(jìn)行討論和書寫,在職場上,大部分女性受到性別歧視已然是不爭的事實(shí),也有諸多職業(yè)女性為此發(fā)聲,強(qiáng)調(diào)在事業(yè)上的男女平等。但很顯然,家庭生活中的女性地位仍然被剝削和捆縛,而可怕的是,在這一點(diǎn)上,女性的聲音往往是微弱的,甚至就連女性本身都很難意識(shí)到她們在家庭生活中所處的地位,也正是因此,女性在無意識(shí)中被灌輸?shù)哪袡?quán)社會(huì)理念才更加尖銳和苛刻。
與今天職場中強(qiáng)調(diào)的男女平等不同,在家庭角色定位中,女性天然地被賦予了所謂“避風(fēng)港”的角色,事實(shí)上,這種看似溫和的比喻卻是對女性獨(dú)立想象的摧殘。在這些傳統(tǒng)的角色賦予乃至家庭定位上,女性的形象實(shí)際上是被扭曲了,這些情感的捆縛也充當(dāng)了男權(quán)社會(huì)下意識(shí)形態(tài)控制的工具,延續(xù)了男權(quán)支配欲望的觀念。

電影《82年的金智英》海報(bào)
2019年的韓國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實(shí)際上就對于這種女性長期被忽略和馴化的家庭地位提出了尖銳的探討。家庭生活的牢籠特性被從未有過的顯現(xiàn),而電影中女性對于女性被無意識(shí)的壓榨和剝削也引起了廣泛討論。事實(shí)上,同樣的關(guān)懷在張惠雯的小說中也早有顯現(xiàn)。
在家庭生活的書寫中,她展示了一種隔絕的荒蕪感,她筆下的女性形象緩慢而遮蔽,往往將自我構(gòu)筑成了扭曲空間下的詭秘泡影,在個(gè)體的場域中自我奔逃,但在自我空間之外,卻少有人能夠注意到她們的情感焦慮,這也就提出了對于今天家庭生活中女性的身份地位思考。
一、家庭生活中所覆蓋的牢籠屬性
在家庭的內(nèi)部空間中,女性往往被迫分置于封閉的狹小角落內(nèi),例如廚房、臥室等需要她們勞作的地方,在大部分時(shí)候,女性在家庭中承載著屈從地位,也就是不得不投身于煩瑣的布局工作之中,同時(shí),這些單調(diào)的勞作使得女性與外界隔絕,也就導(dǎo)致了她們不得不順從于瑣碎無序的工作,日復(fù)一日地自我壓抑。
事實(shí)上,在家庭空間的角度上來說,女性在這一封閉空間內(nèi)所奔波逃避的是男權(quán)社會(huì)的打擊和壓制,女性不得不從屬于這種壓制,并且成為男性財(cái)產(chǎn)的一部分,與世隔絕地歸屬于她們的配偶。關(guān)于父權(quán)和夫權(quán)的狀態(tài)其實(shí)大部分文學(xué)作品都有展示和書寫,因此,張惠雯也提出了一重全新的思考,那就是女性在成為母親之后所面對的自我妥協(xié)。
在父權(quán)制社會(huì)秩序下,女性的生存狀態(tài)是被不斷內(nèi)置和同化的,這也是張惠雯小說中所希望談?wù)摰膯栴},很顯然,在今天,我們很難再直觀地感受到“男尊女卑”的狀況,但實(shí)際上,性別歧視無所不在,性別的固化觀念也存在于家庭和職場生活中。
以小說《沉默的母親》[1] 來談,實(shí)際上,這是一部帶有強(qiáng)烈的東、西方糅合文化的作品,一個(gè)嫁到美國的中國女性,帶有亞洲文化中一切所謂的女性“優(yōu)良品質(zhì)”,她賢惠、顧家,同時(shí)不愛慕虛榮,這在任何一個(gè)男權(quán)社會(huì)下都被認(rèn)為是妻子的最佳人選,也正是因此,沃克先生幾乎是毫不猶豫地娶了這個(gè)女人。
作為旁觀者來審視這段婚姻不難看出其畸形與可笑,沃克先生作為丈夫和父親,也就是這個(gè)家庭中的絕對掌權(quán)者,他身上帶有強(qiáng)烈的自私自利色彩,他一面拿對中國妻子的要求——賢惠、保守、顧家、生養(yǎng)孩子等,來要求自己的妻子,一面又不肯付出中國家庭中常見的丈夫所需要負(fù)擔(dān)的,他計(jì)較每一份支出,同時(shí)不肯支付婚宴的錢,也不肯讓父母住入家中。
很顯然,這些捆縛和壓制在生活中都慢慢積聚成為了沃克太太的生活日常,然而,當(dāng)父親生病,她希望從丈夫手中拿到一些錢時(shí),她卻面臨從未有過的苛刻,丈夫舉出了一個(gè)又一個(gè)例子來拒絕拿出這筆錢,而長期在牢籠中生活而不自知的沃克太太也終于明白了自己生活的真相。
生活的真相仿佛一瞬間在她面前揭開了,那就是,她沒有自己的一分錢!而在這背后的更深層的真相是:在這個(gè)家里,她沒有任何決定權(quán),這里的什么都不屬于她,她在這里的意義就是生養(yǎng)一個(gè)又一個(gè)孩子!她一夜之間變得心如死灰。
同樣被生活的牢籠所扣住的女性還有《二人世界》[2] 中的“她”,小說自始至終都沒有給這些角色以命名,似乎也在暗示著,這種生活是同樣地鋪排在大部分女性的日常之中。事實(shí)上,小說中的“她”從某種程度上而言并不算是一個(gè)傳統(tǒng)的母親或是妻子形象,“她”不確定對孩子的愛,“她”無法做到對孩子全然付出,但又對丈夫的“不成熟”而感到慍怒,更與普通的父權(quán)文化不相符的是,“她”有一個(gè)情人。但小說也正是通過這個(gè)情人來展現(xiàn)出“她”在婚姻生活中的困頓和閉塞。
小說多次地提到了女性和男性面對新生生命的不同,對于“她”來說,她必須經(jīng)歷生活被男孩和家務(wù)填滿,必須經(jīng)歷時(shí)時(shí)刻刻的苦惱和瑣事,孩子擠占了她所有的空間,無論是物理上還是心理上,在這些麻木而瑣碎的事件里,她不再具有整塊的時(shí)間,必須習(xí)慣妥協(xié)于乏味的生活狀況。
但對于丈夫來說,他“始終如一。他是始終歡迎孩子到來的那個(gè)人”。他既意識(shí)不到妻子的改變,也不能夠做出有效的疏導(dǎo)。
女性在退居家庭生活之后,所面臨的不僅僅是經(jīng)濟(jì)狀況的流失,更是與外界的完全脫節(jié),同時(shí)也是自己人生的瑣碎與游離,因此,當(dāng)小說中的“她”開始拒絕情人的看望,以及“不再從他的電話里得到快樂和甜蜜”時(shí),她所面對的就是被改變的斷裂。
在小說的最后,她不再能夠從肉體的快樂中得到快樂,即便是在床上,也一次又一次想起兒子,同時(shí),她也賭氣似的向情人展示了她作為母親的一面,凌亂、邋遢、“懷著一種自毀的、夾雜著報(bào)復(fù)的快意想象他看見自己這副模樣的反應(yīng)”。從這里開始,無論是生理還是心理,“她”已然進(jìn)入了家庭的囚籠之中。

在生命個(gè)體的幽閉空間之下,生活是緩慢的、空間是逼仄的,與世隔絕的痛感不僅令女性和社會(huì)生活脫節(jié),就連和枕邊人乃至家庭生活中的其他人也產(chǎn)生了割裂,深刻象征著被遮蔽的捆縛與囚籠。我們今天所討論的家庭生活的牢籠屬性也就是在此,從東方的儒家思想來說,“女主內(nèi)”的思想深遠(yuǎn)地影響著家庭關(guān)系,在父權(quán)制的社會(huì)原則下,女性必須站在倫理角度中,以照顧家庭、服從人倫感情等來退居到生活的后方。
二、女性向內(nèi)坍塌與向外斷裂
沉默的囚籠過后,我們所需要探討的就是女性與外界隔離過后的纏繞與奔逃。當(dāng)女性在社會(huì)秩序與日常的生活秩序中產(chǎn)生齟齬之時(shí),即便是沉默,也會(huì)有爆發(fā)和崩塌的可能。事實(shí)上,張惠雯在她的女性題材小說中往往會(huì)談到女性在婚姻中的逃離。在這些作品中,女性很難從家庭生活中得到關(guān)心或者是尊重,只有男性無休止的冷漠和壓迫,因此,面對這種日復(fù)一日的痛苦,女性只能選擇逃離和反叛。
很顯然,尤其以東方社會(huì)秩序來看,男權(quán)社會(huì)馴化女性的一個(gè)核心就是婚姻家庭中的訓(xùn)誡,而在女性被迫退讓到家庭中失去自己的社會(huì)地位之后,她們的社會(huì)角色被綁架,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假設(shè)為隱蔽的奴性身份。一方面,父權(quán)制社會(huì)中,男性不需要對女性的付出表達(dá)感謝,所有在家庭中的付出都顯得理所應(yīng)當(dāng);而另一方面,女性卻需要對男性帶回來的錢財(cái)表示感謝,作為謀生者所存在的男性看起來具備了比女性更高的社會(huì)價(jià)值,女性的價(jià)值自然被忽略了。
當(dāng)兩性關(guān)系被放置到家庭生活中時(shí),還往往會(huì)出現(xiàn)一個(gè)婆婆的角色,事實(shí)上,這一角色代表著女性在父權(quán)制統(tǒng)治秩序中的縱向核心,在傳統(tǒng)觀念下,“多年媳婦熬成婆”,這一句就可以看出女性在傳統(tǒng)思想下的絕對附庸。即便“婆婆”的身份使得女性在老年時(shí)期具有了崇高的權(quán)力,但這一權(quán)力仍然是附庸于男性,同時(shí)也是指向了“兒子”,來作為“幫兇”壓榨兒媳。
在中國傳統(tǒng)婚姻的締結(jié)中,親子關(guān)系里的人們重視人倫,因此,女性對兒子的情感投射也就伴隨了對于兒媳的打壓和排擠,她們要求兒媳的絕對服從,同時(shí)也作為性別統(tǒng)治者的“幫兇”,強(qiáng)行把女性拉扯回到家庭生活之中,通過這種單向度的性別統(tǒng)治和年齡優(yōu)勢,來試圖滿足自己的情感以及權(quán)力需要。
因此,被壓榨的悲劇女性為了逃離這種囚籠的境況,一部分選擇了自我向內(nèi)的坍塌,一部分則選擇了向外的斷裂。從小說《沉默的母親》來看,小說中的沃克太太就是典型的自我坍塌者,當(dāng)她意識(shí)到自己“生活的真相”之后,在表面上,她仍然維持著得體和賢惠,照常做家務(wù),但同時(shí),當(dāng)著丈夫的面她食不下咽。但當(dāng)丈夫走后,“她像只老鼠一樣把去超市采購時(shí)順便買來的各種廉價(jià)零食藏在車庫里的那些空箱子里,然后在孩子們睡著,或是看電視,或是在樓上玩兒的任何時(shí)機(jī)里拿出來,像個(gè)得了吞咽強(qiáng)迫癥的人一樣貪婪地往嘴里塞著薯片、士力架、彩色軟糖、奶油曲奇餅……”
而在之后女兒的敘述中,母親在躁郁癥的心理疾病中走向了自我毀滅。她是一個(gè)沉默的少言寡語的順從者,她的可憐之處不僅在于她受到了所謂“賢良淑德”思想的荼毒,更在于她的無力抗?fàn)帯J聦?shí)上,她的抗?fàn)幎贾荒軓淖晕业臍缰姓故颈瘎 N覀兛梢韵胍姡绻@場夢沒有醒,沃克太太將永遠(yuǎn)是沃克先生沉默的、順從的妻子,但不幸的是,父親的生病以及沃克先生的冷漠將她飛快地從夢中醒了過來,她的不幸之處也在于此,她被操控了一生,但殘酷逼仄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也令她無法真正選擇覺醒,她能夠用以反抗的也只有生命,這正是她對于男權(quán)社會(huì)最為激烈卻也最為慘淡的反抗。
當(dāng)然,更值得一提的是,父親生病的這一情節(jié)構(gòu)建大約也是經(jīng)過了作者的思考,女性從父權(quán)文化中逃離,則被迫卷入夫權(quán)之中,而她的覺醒,也實(shí)際上是父權(quán)與夫權(quán)傾軋下的自我折磨。
而在小說《玫瑰玫瑰》[3] 中,作者則書寫了另一種向外的找尋與斷裂。島嶼上的女主人盛情邀請“我”去她家中做客,但當(dāng)“我”抵達(dá)這座島嶼,又接觸了她的生活之后,“我”才了解到看似廣袤空間下的逼仄與痛苦。
無性婚姻所造成的是一個(gè)女人在壓抑欲望之下的崩塌與恐懼,如果說《二人世界》《沉默的母親》等所講述的都是女性在親子關(guān)系中所遭遇的情感勒索,那么,《玫瑰玫瑰》[3] 則展示了配偶關(guān)系中的情緒匱乏。小說所借用的是無性婚姻中的復(fù)雜況味,有效書寫了女性在這種壓抑與自閉下的自我否認(rèn)。
在“我”的眼光中來看,這對夫妻是天生一對、是互相支持且相愛的,但婚姻之下,各自的痛苦就只有他們自己能夠了解,一方面,性愛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即代表著情感的缺失和孤立,女性無法從親密關(guān)系中獲得真實(shí)的溫暖;另一方面,在東亞文化的影響中,女性也必須壓抑自己的性欲望,因此,女主人只能選擇向“我”說出一切,即便是在自我處境全面坍塌的時(shí)刻,她也只能進(jìn)行斷裂的輸出,而非全然自我的找尋。全然鋒利的向外斷裂之下,小說呈現(xiàn)出了女性在孤獨(dú)時(shí)刻的靜默與錯(cuò)位,無法在家庭親密關(guān)系中獲得溫情的當(dāng)下,小說締結(jié)出了更為豐滿的情緒張力。
同樣的情感勒索還出現(xiàn)在了小說《雪從南方來》[4] 中,在此,家庭仍然作為了風(fēng)暴的中心,而有所不同的是,小說選取了男性作為風(fēng)暴眼,來回望兩個(gè)女性的掙扎和失落。小說所敘述的故事并不復(fù)雜:一個(gè)離異的帶著小女兒的單身男人,在遇見自己喜歡的人之后試圖讓愛人和女兒和平共處,但卻在年幼女兒的無知之惡下,失去了重新開始的可能。

事實(shí)上,這類故事的核心并不鮮見,繼父母與繼子女之間的矛盾向來是東方家庭中經(jīng)久不衰的書寫主題,然而,小說卻以一封郵件起始,試圖展示這對父女在長久的平靜生活下的暗流涌動(dòng)與風(fēng)暴迭起,柔弱的女兒是曾經(jīng)親手毀掉他愛情的劊子手,而被他誤解的徐寧也永遠(yuǎn)沒有了回來的可能。
另一面,徐寧的角色也值得被關(guān)注,在小說中,她實(shí)際上是一個(gè)溫厚的繼母形象,即便是面對他沒來由的指責(zé)和失控,以及小敏混沌的欺騙假裝之下,她所選擇的也是斷然離開:
“不用回答,什么都不用說!”她站起來說,拿一張紙巾擦掉臉上的淚,樣子像是如釋重負(fù),“我應(yīng)該早就明白的。我應(yīng)該早就想到結(jié)果會(huì)是這樣……”
在徐寧的世界中,她的如釋重負(fù)何嘗不是一種向外的斷裂,被主觀投射的繼母形象固然帶有陌生環(huán)境下先入為主的標(biāo)簽,同時(shí),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及時(shí)奔逃也引出了截然不同的思維模式。這種逃離是絕對支配過后的具象掙扎,也避免了她們成為家庭生活中的獻(xiàn)祭物品。
三、“心血來潮”下的女性自我博弈
作為移民作家,我們常常會(huì)談?wù)摰綇埢蓥┰谄湫≌f中所顯現(xiàn)的關(guān)于差異文化的認(rèn)同感與身份意識(shí),實(shí)際上,在其現(xiàn)實(shí)性的小說中,人物大多彌漫著一種困頓的身份焦慮。這也是小說敘述的核心之所在,而這種文化沖擊所帶來的是對于生存困境的討論和情感的捕捉,尤其以女性身份來談,她小說中的女性形象大多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身份焦慮,她們有著對于家庭生活的渴望,同時(shí),卻也具備對于未知遠(yuǎn)方的向往。
在這種欲望的割裂之下,小說呈現(xiàn)出對于移民生活的隱喻性寫照,尤其對于女性來說,她們所面臨的時(shí)常是雙重的困境。從家庭生活上來看,在張惠雯的小說中,大部分女性的移民大多與配偶有關(guān),因此,她們的奔赴實(shí)際上是從原生家庭中離開,去往另一個(gè)地方重建家園,這毫無疑問是一種生命際遇的漂泊和游蕩。同時(shí),她們也需要面對常規(guī)的靈魂的漂泊和探索,在生活之中,她們的生命歷程是真實(shí)而又隱蔽的,小說關(guān)注了女性的內(nèi)心情感,將她們無根的茫然加以深刻的書寫和展示。
在前文中我們講述了關(guān)于女性意識(shí)在家庭生活中的被囚禁狀況,實(shí)際上,家庭的囚籠化深層次的是對于夫權(quán)乃至男權(quán)思想的反抗,而在張惠雯另外幾部小說中,她則剔除了這種對于抵抗或者是直觀的交鋒,而是在凝視的角度下,體現(xiàn)女性主義的博弈與追求。這種凝視往往來自女性在親密關(guān)系之外所開拓的另一重情感,作為情人或者“紅顏知己”的她們,在這種關(guān)系中開辟了自己作為女性的另一面,也正是從這種看似錯(cuò)誤的遺憾感情中,小說將女性的覺醒意識(shí)推到了高潮。
從小說《關(guān)于南京的記憶》[5] 來談,第一人稱“我”的情感是復(fù)雜而動(dòng)蕩的。張惠雯巧妙地借用了移民的身份,來展示女性的雙重情感困境。一方面,“我”習(xí)慣了和男友的生活,也不準(zhǔn)備對這種生活加以改變,但“他”的出現(xiàn)卻改變了這種局面,同時(shí),“我”的這種小小的精神出軌,也使得“我”對自我情感有了更加深刻的認(rèn)知。
這可以看作是女性在長久恒定親密關(guān)系中的一段小小的“心血來潮”。而事實(shí)上,這種“心血來潮”并非情感的流失,而可以看作是女性對于婚姻乃至愛情的旁觀和浮靡,對于“我”來說,這種“不同尋常的友情”是女性決絕后的身份找尋,被糾正的錯(cuò)誤在多年之后令人神傷,也正是出于某種不可追的懷戀。
早在柯萊特的小說《面具后的女人》[6] 中,就有對這種“心血來潮”的描繪:“她會(huì)像丟棄葡萄皮兒一樣松開那年輕人的嘴唇,然后離開,到處晃悠,和遇到的其他人親昵,再忘掉他們,直到疲憊后回到家,品味她源自決絕個(gè)性里的獨(dú)立、自由和率真,品味作為陌生人的那種寂寥空虛而又毫無羞愧的、怪異的愉悅——就像這次百無聊賴之下單純的外遇里,一個(gè)小小的面具和奇怪的裝扮讓她品味到的那樣。”
這種感慨的情緒積聚而成的是對于男性力量的解構(gòu),這種解構(gòu)無關(guān)所謂的叛逆或是覺醒,更多的是對于自我成長的救贖,是一個(gè)不依附于男人而存在的自我成長。在《關(guān)于南京的記憶》中,“我”是一個(gè)人到中年成熟回望的視角,小說不再具備感情上的取舍,同時(shí)也沒有任何不合乎倫理道德的因素,正相反,小說全篇都在對個(gè)人的內(nèi)心情感世界進(jìn)行深刻的書寫,這一角色具備女性的隱忍,同時(shí)也有著對于自身欲望的關(guān)注。
而很顯然,從小說的題目就可以看得出,以人到中年的回望來看,“我”的悵然若失實(shí)際上也是對“我”情感關(guān)系的懷戀和追溯,在移民過后,“我”的身份認(rèn)同是缺失的,無論是家庭生活還是在海外的生活經(jīng)歷,都使得“我”失去了生命力的涌動(dòng),也正是因此,“我”對于男人的懷念,也可以看作是對“南京”,也就是對那一段生活的懷念。小說利用了這種情緒上的復(fù)雜情感,來表現(xiàn)一個(gè)女性無聲的悲痛和掙扎。
在社會(huì)語境下,女性的欲望時(shí)常處于失語的狀態(tài),因此,女性在回望時(shí)刻的撕扯實(shí)際上也是對于“本我”的否定,對“超我”的追尋,小說中的“我”,無論自我生活如何平淡,始終都懷有對理想他者的渴望和籌謀,對于那一段從未發(fā)生過的“心血來潮”,多年的生活已然將這一小小的精神出軌加以篡改,也就構(gòu)成了對于超我理想的追尋。
很顯然,在社會(huì)處境下,女性的形象往往逃不脫妻子或是母親,在這種親子關(guān)系或者說情感關(guān)系下,女性的獨(dú)立意識(shí)是被隱匿的,也正是因此,張惠雯提出了她全新的思考。在她的小說中,我們能夠看到女性在自我情感關(guān)系上的找尋,看似背德的情感書寫所烘托的是鮮明而確切的女性力量,事實(shí)上,她們也通過情感關(guān)系的覺醒來塑造自我的獨(dú)立意識(shí)和身份認(rèn)同。
四、情欲符號(hào)中的具象隱喻
無論女性主義文學(xué)如何闡釋和變更,無論女性的社會(huì)身份認(rèn)同如何找尋,實(shí)際上,對于女性主義的話題書寫永遠(yuǎn)逃不開對于身體的控制權(quán)和支配權(quán)。由于天然的生理因素,女性在性生活中常常被強(qiáng)行冠以被支配的地位,男性對于女性的控制也就來源于此,再加上金錢與性關(guān)系的交換,更使得女性成為了從屬地位,不具備被平等對待的價(jià)值。
但今天的女性主義文學(xué)中,我們常常能夠看到對于女性特權(quán)的強(qiáng)調(diào),同時(shí),女性對自我的身體控制權(quán)也有了全新的認(rèn)知和理解,女性不再從屬于男性獲得性快感和性價(jià)值,正相反,女性成了主導(dǎo)地位,在反抗的隨意掌控中消解了情欲附屬,完成了對自我性別的認(rèn)同和書寫。
從小說《雙份兒》[7] 來談,和《關(guān)于南京的記憶》相似,小說同樣都是以中年人的視角回望年輕時(shí)所經(jīng)歷的一段情感,也同樣都對這一未發(fā)生的情愫抱有悵然若失。但男性視角和女性視角的不同也就從此顯現(xiàn)。
在小說《關(guān)于南京的記憶》中,“我”是平等地與“他”交流,有著一段“不同尋常的友情”,但也到此為止了,而也是因?yàn)檫@個(gè)人,“我”時(shí)至今日仍然對南京有著好感。但在小說《雙份兒》中,“我”作為男性的回憶卻是灰暗的、沉重的。對于“我”來說,那個(gè)女人的形象帶有更為復(fù)雜的情緒。
小說將這個(gè)女性設(shè)置成了一個(gè)“高級(jí)妓女”的形象,對于初入生意場上的“我”來說,能夠保持在淤泥之中不沾染泥土已然是需要很大力量,因此,對于妓女的解救所構(gòu)建的也是一個(gè)具象的身份象征。女人的身體所構(gòu)筑的是一個(gè)圣潔的、代表了強(qiáng)烈的權(quán)力空間。一方面,身體是這個(gè)女人所存在的本錢,也是她能夠獲得利益交換的來由;但另一方面,她也會(huì)利用自己的智慧,來賺取“雙份兒”錢。在“我”勸告她從良,希望她能夠擁有正常生活時(shí),她轉(zhuǎn)頭就向更高級(jí)告密。這種對于妓女的身體失控的隱喻,實(shí)際上也反映了“我”在情欲和利益之下的全面潰敗。
事實(shí)上,在小說的最后,“我”已然發(fā)現(xiàn),“我”早已成為了那個(gè)“我”曾經(jīng)所看不起或者說看不懂的女人:
“他有時(shí)會(huì)突然陷入那種陰沉的情緒之中,仿佛被濃霧籠罩……而他仍然得在那些日復(fù)一日的瑣碎、沒有意義的事務(wù)里消磨著余留的暗淡的有生之年……在他這個(gè)年齡,幾乎沒有什么東西值得他激動(dòng)地、匆忙地趕路,除了去捕捉、占有、體會(huì)那一點(diǎn)點(diǎn)快樂,但這快樂又轉(zhuǎn)瞬消散,之后就把他拋擲在漫長的蔭翳之中。他想,他也有他的“雙份兒”,他明知卑劣、罪孽卻始終舍棄不了的東西。”
正是由此,一個(gè)拯救者轉(zhuǎn)換為了捕捉者,小說不僅將女性身體卷入到政治中,更是借助了巨大的顛覆性力量,來對權(quán)力的結(jié)構(gòu)進(jìn)行反轉(zhuǎn)和諷喻。拿了“雙份兒”的女性看似是從屬地位,但卻具備了對于那時(shí)的“我”的支配權(quán),而后來在漫長的蔭翳中自我消解的“我”,也無法回歸到天真的狀態(tài),只能塑造一個(gè)虛幻的欲望形態(tài),自我沉淪到權(quán)力關(guān)系之中,來書寫永恒的話語霸權(quán),以及敘述者對于風(fēng)暴眼中心的某種批判和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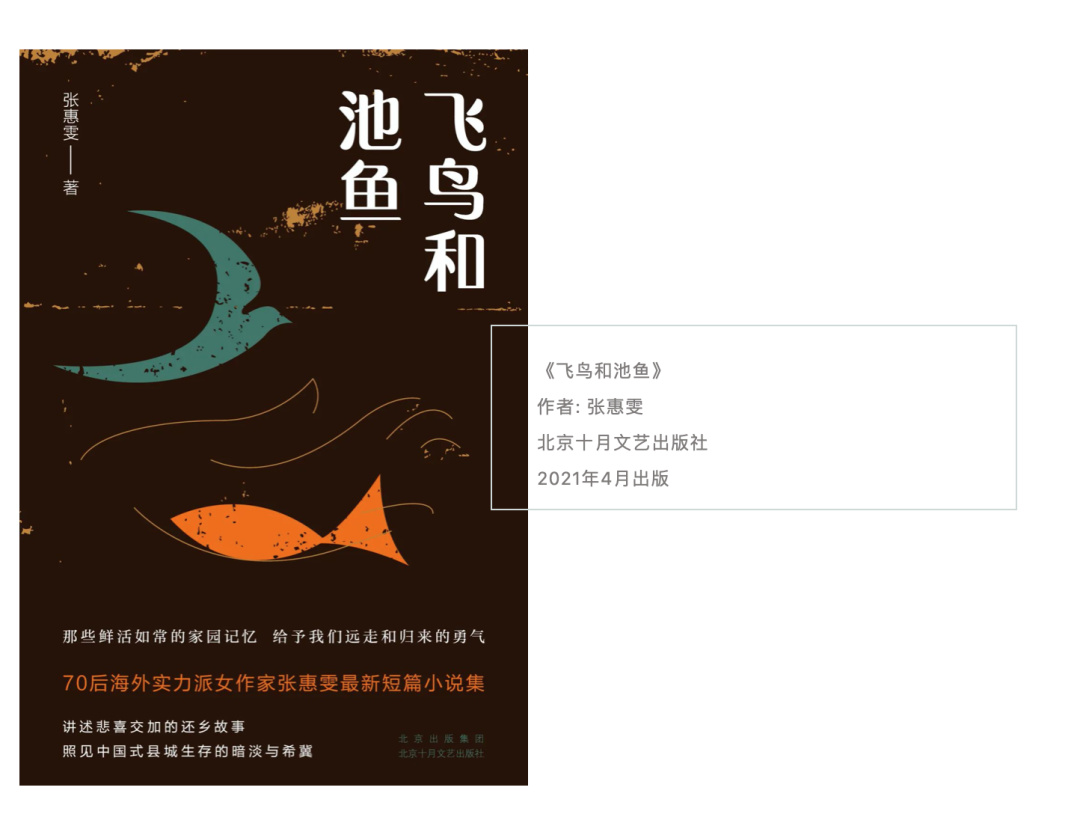
作為移民作家,張惠雯的作品往往能夠超越單一的國度,對東方視角下的西方場域進(jìn)行更加強(qiáng)烈的顯現(xiàn),而在小說所重置的情感困境之下,作家通過女性的自我價(jià)值找尋與家庭身份的割裂來完成對于精神捆縛困境的書寫,這種情感張力之下,小說具有了強(qiáng)烈的思想震撼力,同時(shí),也能夠穿透到現(xiàn)實(shí)世界之中,勾連出非常態(tài)空間之下的崩裂與坍塌。
[1] 張惠雯:《沉默的母親》,《江南》,2018年,第5期。
[2] 張惠雯:《二人世界》,《收獲》,2019年,第2期。
[3] 張惠雯:《玫瑰玫瑰》,《收獲》,2020年,第3期。
[4] 張惠雯:《雪從南方來》,《人民文學(xué)》,2019年,第4期。
[5] 張惠雯:《關(guān)于南京的記憶》,《花城》,2020年,第6期。
[6] [法] 西多妮-加布里埃爾·柯萊特(Sidonie-Gabrielle Colette):《面具后的女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
[7] 張惠雯:《雙份兒》,《上海文學(xué)》,2019年,第5期。
原文刊發(fā)于《粵海風(fēng)》2021年第4期
- 溫情與反思:2021年女性導(dǎo)演電影創(chuàng)作觀察[2022-02-24]
- 潘向黎:上海是能成全女性“做自己”的城市[2022-0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