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元珂:新文學名著的版本問題
編者按:學者張元珂視新文學作品版本研究與文學作品批評為他學術研究之兩翼,后者觀點散見于他關于韓東、劉慶邦、夏立君等作家作品的評論,以及多年來獨具個性的年度文學榜單中,而前者則集中展現在日前出版的《中國新文學版本研究》一書。在書中,張元珂基于豐富的史料和科學的方法,對國內外關于中國新文學作品版本研究的學術史和研究動態進行了回顧、梳理,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有所創新,對新文學版本的相關概念進行了辨析,對現當代文學的一些經典作品、名家作品的版本進行了考察,論及文學文本修改的相關問題,并呈現了一批新發掘的手稿、書信。經作者授權,中國作家網特遴選該書第一章“新文學名著的版本問題”發布,以饗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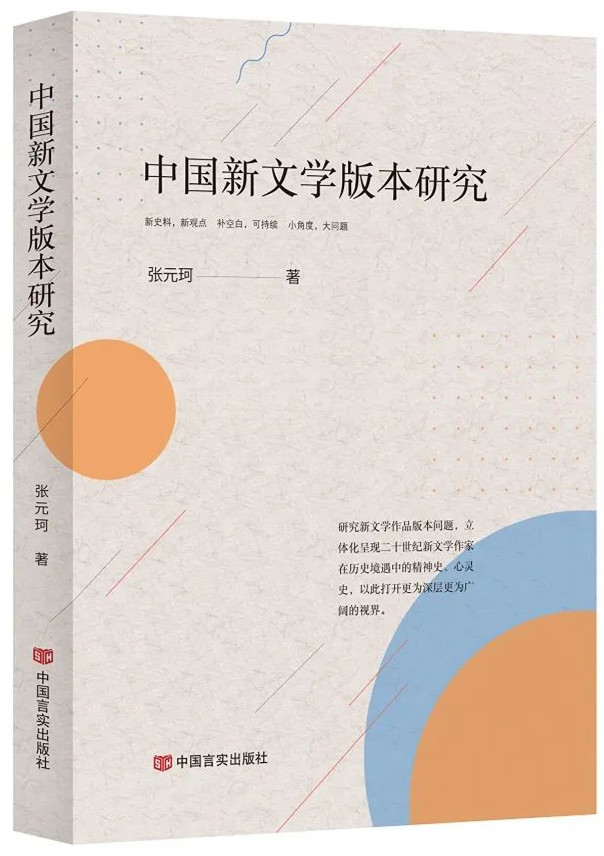
《中國新文學版本研究》,張元珂 著,中國言實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
一、版本、版本學與新文學版本學
何謂“版本”?原稱板本,它本是在雕版上印刷成的本子。所謂“雕版”,即用木板雕刻。雕版的制作過程大致如下:首先,用梨木、棗木等硬質木材做成板片。板片“要放在水里裹浸,津上個把月。如果急用等不及,也可以改用煮。浸或煮后再把它刨光,陰干,不能在陽光下曬,以免曬裂。干后擦上豆油,刮平,磨光,然后才能貼上‘寫樣’。 ”其次,經過這樣的特殊處理后,然后貼上“寫樣”,也即“上板”:“就是要把寫樣貼到版片上,要反貼,即把字的一面貼上去,這樣刻出來的才是反字,印出來的才是正字。貼的方法據《書林別話》是用熟飯泡水,在版片上壓融成糊,刮平,將寫樣反貼上去,用棕毛刷刷上好幾遍,等干后再磨光,以待刊刻。”再次,進行刊刻,即“把無字劃處刻掉挖掉,有字劃處留下來,使字劃凸出,才好印刷。 ”最后一道工序:鋸邊。雕版制作完成后,即可刷印。雕版印刷到宋代取得了壓倒性優勢。版本也就有了更為寬泛的指稱,后泛指各種形式的書本。或者說,所謂“古籍版本”,實際上是以刻本為主,同時也包括活字本、抄本、拓本、批校本、插圖本、稿本等在內的不同本子的統稱。
圍繞版本源流的考證、版本形態的描述、版本真偽的鑒定、版本優劣和價值的評定等活動而形成了一門專門學問:版本學。但我們所說的“版本學”,也即“中國古籍版本學 ”,后考慮到概念的簡單明了,一般稱之為“古籍版本學”。在中國古代,雖早在漢代就有學者注意到了版本差異問題,至明清版本收藏與考據更是繁盛空前,但作為一門學問,似乎只停留于特殊行業與特殊技術范疇,其知識譜系并不系統,學科屬性也不清晰。至于在系統與清晰方面的自覺追求與實踐,則是近代以來少數學者才有意識努力的方向。
古籍版本學是一門應用性很強的學科,也有其特定的研究方法、研究對象和時間上下限:“我國用漢文書寫的古籍,即從春秋末戰國初我國漢文書籍的正式出現開始,大體到清末為止的古籍,但并不管它的內容,而只管它的版本;而這版本又不包括過去的竹木簡書、帛書和卷子本,只包括雕版印刷通行以來的刻本、活字本、抄本、批校本。說得簡單點,古籍版本學的研究對象是我國漢文古籍通行雕版印刷以來的版本。 ”作為一門學問,古籍版本學可謂古老而常新。具體到文學領域,任何一部流傳至今的經典作品都有完整而復雜的版本譜系,故對作品版本的校勘,就必然成為文學研究的基礎工作。數百年來,眾多學者在這一領域辛勤耕耘,留下了眾多影響深遠的版本學著作 。版本概念流傳到今天,其外延與內涵更是大大超出了原初界定。
新文學版本,即伴隨新文學的發生與演變而生成的各類本子,它既可是某部著作,也可指單篇文章、某篇日記、某封書信,甚至某一份文獻。以“新文學版本”為研究對象,便形成了一門嶄新的學問,即“新文學版本學”。關于“新文學版本學”這一命名最早出自姜德明的一篇文章中:“新文學版本學完全可以沿用古籍版本學中的目錄學、校勘學等方法,對新文學的版本進行考證、辨析、輯軼、增補等一系列的復雜工程,工作起來也許很枯燥,但卻非常必要。” 與之類似的還有“現代文學版本學”之命名 。相比于古籍版本學的系統與成熟,新文學版本學尚處于起步階段,不僅發展歷史短暫,所取得的成績也相對有限。雖然如此,作為一門朝陽學科,其未來可期。
版本整理、發掘與闡釋是新文學作品版本研究首要任務。在新文學史上,很多重要作品都存在版本認定上的盲區或錯判,這不是小問題,而是事關作品和文學史研究的大問題,因而亟需澄清。比如:胡適的《嘗試集》到底有沒有第三版?如果有,它對我們研究《嘗試集》從初版、再版到第四版提供了怎樣的角度和新內容?徐志摩的線裝本《志摩的詩》到底初版于哪一年?它和1928年新月書店的初版本是同一個版本嗎?郁達夫的《她是一個弱女子》與《饒了她》、郭沫若的《劃時代的改變》與《反正前后》、巴金的《萌芽》與《雪》是同一個版本嗎?《子夜》在1930年代有哪幾種富有影響力的盜版本?這些盜版本的內容、體例、形態,與所謂“正版本”相比,有哪些不同?它們對我們認識《子夜》在1930年代的傳播與接受提供了怎樣的新穎內容?孫犁的《荷花淀》的初版本到底是1946年的華北書店本,還是1946年的東北書店本?這兩個版本有何不同?沈從文的《從文自傳》的日本東京版(“生活社刊行”)與中國大陸上海版(“第一出版社”)是同一個版本嗎?李廣田《引力》版權頁上所印的出版時間為1947年6月,這個時間準確嗎?梁斌的《紅旗譜》為什么存在1957年和1956年兩個年份認定上的分歧?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1948年光華書店初版)與《桑干河上》(1948年8月光華書店初版)都是初版本,那么,兩者有何區別?等等。版本校勘是貫穿文學、文學史研究始終的基礎性內容,在百年新文學史上,類似問題還有很多,很多,真是任重而道遠!
確定版本屬性,梳理異文變動,分析修改動因,闡釋文學價值,是從事版本研究最關鍵、最核心的環節。一,要格外重視手稿研究。手稿是作品生成的第一現場,圍繞手稿形成一門學問,即手稿學,在西方又叫“文本發生學”。作為特殊的版本,其在作品版本譜系中的重要性與研究價值自不待言。新文學作品的手稿本向來稀少,且作家們在二十世紀也普遍不重視對手稿的保護,故能留存于今的名家名作的手稿已不多。一般情況下,手稿本是唯一的,但也不盡然,一個作品的手稿有若干版本的現象也較為常見,且發生于手稿內部的文本修改也不一定全為作者所為,出版社編輯的意見會對作者的文本修改產生潛在影響,特殊時期特殊情況下,編輯甚至會直接參與“創作”,這些現象都需仔細甄別。另外,務必分清稿本與手稿的區別,切勿把抄稿、清稿、待印稿當成原稿。因為很多所謂“手稿”都是眾多稿本的結合,比如,兩千多頁的《紅旗譜》手稿就是由原稿、抄稿、清稿構成。六百多頁的《許茂和他的兒女們》手稿除原稿外,也有幾個章節是抄稿。二,要科學認定初版本價值與地位。初版本保留了一部作品的初始封貌,保存了作家初始的心路歷程、審美姿態和藝術風貌,是從事作品版本研究的起點和第一手材料,其在版本研究中的重要性無需贅言,但不加甄別與分析地視初版本皆為上品的意識與做法,實際上也是有問題的。也就是說,初版本并不一定是善本。那些改正初版本中文字錯誤、文本發生正向修改或承載特殊歷史內涵的后續版本,往往都優于初版本。在初版本善不善問題上,我們應保持一個科學態度。三,要客觀分析定本價值。定本認定與價值評估也是一個異常復雜的問題。作家都有定本情結,按照正常邏輯,定本一旦確定,便是對作家主體意志與作品藝術水準的最高顯現,但事實似乎并非如此。在具體實踐中,定本的確立也不是一次就完成的,而往往要經過時間沉淀、不斷篩選或修改后方能完成,且定本不一定全由作者定奪;有時候,作家對同一部作品定本的認定會出現反復,甚至同時認定兩個定本;一般情況下,作者對初版本情有獨鐘,因而,將初版本為定本的做法較為常見,但初版本并不一定是善本;定本與善本也不是同一個概念,有些定本非但不是善本,也有可能是劣本,因此,在作品版本譜系中,到底哪一個版本為善本,尤須認真比對和研究。四,要全面認定非初版本與定本的價值。從初版本到定本往往會出現若干過度形態的本子,常標有“重排本”、“重印本”或“修改本”字樣,以示與初版本有別。這些不同形態的本子并非單純版次上的形式變遷,其文本內部的異文變動往往與社會意識形態、作者藝術觀變動息息相關。故其價值實在不可有半點忽略或輕視。總之,從手稿、初版本、定本,到其他各類版本,都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每一個版本都有其不可取代的內涵與價值。
不斷探索新文學版本研究的方式、方法,嘗試建立學科體系與理論基礎,也是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在新文學史上,阿英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寫有《版本小言》 ,較早關注新文學作品的版本問題,認為新文學版本與古籍版本一樣具有同等重要的研究價值;唐弢著有《晦庵書話》,較早開拓了新文學版本研究的先河,并對版本理論問題有所提及,但他有關版本特質的認識論基礎基本局限于古籍版本學范疇 ;朱金順在他的《新文學資料引論》一書中專列“版本”一章,綜論新文學的版本屬性、版本構成、新善本的標準以及題跋等諸多帶有一定理論色彩的命題 ,從而為新時期文學版本研究趨向學科方向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姜德明在《書頁叢話——姜德明書話集》 第一輯《論新文學版本》中有對新文學初版本價值與書面裝幀藝術的相關闡釋,后又在《新文學版本》中又談了新文學版本的上限問題 ,也都是很具建設性的帶有一定學術性的探討。此后,陳子善、龔明德、劉增杰 、張澤賢、吳良忠等學者在該方面都有所涉及。但在此方面用力最勤、更趨于學科理論建設且成果最卓越的當屬金宏宇。無論他對版本譜系模式的歸納 ,提出的“三原則說 ”,對新文學副文本研究方法與理論基礎的初探 ,還是對現代文學考證學方法與理論的建構 ,都在新文學版本研究領域產生很大影響。他在繼承前人知識成果基礎上,充分借鑒西方文論資源與方法,構建了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研究中國新文學版本的理論體系和實踐方法,將作為學科分支或研究方向之一的新文學版本研提高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其貢獻與影響有目共睹。
從事新文學版本研究,其意義至為深遠。第一,密切服務于文學史寫作。版本就是貨真價實的史料,版本研究的追根溯源、去偽存真,不但為經典作家、作品的研究打開全新的視角,而且也為“重寫文學史”提供第一手的資料。第二,深入揭示知識分子精神世界。透過不同版本的比對、研究,不但能夠立體地呈現作家的精神世界、藝術品的生成過程,還能夠透過歷史的間隙,揭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心靈史)及命運抉擇。第三,立體呈現歷史(文學史)發展的復雜性。版本變遷就是一部濃縮的歷史。它的多元與復雜,皆在此映現。第四,開拓現代文學研究的新領地。版本問題與現代文學研究是一個展新的課題,其發展前景令人期待。第五,是從事文學批評的基本前提。對最新作品予以及時追蹤、評介,是文學批評最基礎、最重要的學科任務。而在活動開展之前,對包括手稿本、初刊本、初版本、再版本(修訂本)在內的眾本進行科學比對、篩選,繼而確定哪一個為善本,顯然是決定文學批評活動得以展開并得出可靠觀點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證。或者說,由于一部優秀作品版本差異,因而具體以哪一個版本為闡釋對象,最后得出的結論往往有別甚至相差甚遠。因此,在當代文學批評普遍不重視甚至完全忽視版本問題的大背景下,強調作品版本選擇在文學批評活動中的第一性地位,其價值和意義自不待言。
二、版本形態、構成與譜系
新文學作品存在時間雖然不長,最長的也不過百年左右,但每一部經典作品往往有好幾個版本,則是顯而易見的基本事實。《子夜》、《山雨》、《駱駝祥子》等名著版本尤甚,其譜系的復雜程度并不亞于古籍版本。若按常見類屬,作品版本除常見的手稿本、初刊本、初版本、修訂本、定本外,還有重排本、訂正本、重印本、叢書本、文庫本、農村版/征求農村讀者意見本、征求意見本/內部本、送審本、刪節本/節本、全集本/文集本等類屬。若按照版本形態來分,有毛邊本、線裝本、匯校本 、袖珍本、紀念典藏本、布面精裝本、平裝本、插圖本、眉批本、注釋本等類屬。若按照生產方式來分,有鉛印本、影印本、盜印本、翻印本(重排翻印、原版翻印)、手抄本等類屬。若按版式與紙張材質分,又有16開、24開、32開、34開、48開、64開以及橫排西式本、直排中式本、道林紙本、宣紙本、草紙本等名目繁多的眾多版本。某部著作或某一篇文章亦然。比如,上世紀20年代,發表于《東方雜志》上政論文章有北方版和南方版。1941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同時初版的《龍?虎?狗》(巴金)就有滬版和渝版兩種版本,兩者在版式、內容、紙張等方面都有所不同。由上可見,新文學作品版本既有特定的專名,也有各類別稱,這些專名與別稱首先顯示了新文學版本學自身在研究對象上的獨特性。收齊上述眾本是對一部作品展開全面、系統研究的基本前提。不要漠視新文學作品在版式上的這些變化,其對研究作品傳播與接受,都提供了嶄新的視角與內容。
新文學的“版本”一般是一個出版學的概念。一個完整的新文學著作版本,其構成有正文、封面、書名頁、題辭或引言頁、序跋、插圖、附錄、廣告頁、版權頁。后面九項又因其在版本中的相對獨立性而被歸入副文本范疇。其中,版權頁主要有著者、出版方、發行方、印刷方、出版時間、版次、印張與開本、印數、書號、版權印花等信息。實際上,絕大部分作品版本并非完整保有上述九個要素,缺其中幾項乃常態。但不管怎樣,這些要素都是新文學版本學的研究對象。有關正文中異文情況的比對與闡釋,一直是版本研究中最為核心的內容,但其它八項每一項都需逐一梳理、考證與研究。這些要素在新文學創生與發展過程中的表現形式、作用及文學史意義,也都有其獨有的價值。
在副文本諸要素中,以下幾方面尤須重點觀照:1、文學圖像(封面畫、插圖):封面裝幀的發展階段;每一階段的顯著特征;設計理念與文學思潮的互動;設計大家(比如,陶元慶、錢君淘)對新文學的貢獻及意義。2、序跋:新文學作品中的序跋是一個獨立的藝術門類;序跋的概念及形態;序跋的種類及特征;序跋的功能(審美功能、廣告功能、評判功能、話語權功能、文化功能,等等)。3、文學廣告。文學廣告的發生及形式特點;文學廣告與新文學的關系;文學廣告的功能。近年來,有關上述三方面的研究,已有相當一批成果出現 。此外,副文本中的一些看似非關要旨的要素現在看來亦應引起重視,比如:印刷用紙的變遷及意義;裝訂風格的變化及意義;環襯及扉頁的種類、風格、價值;版權頁上的內容及意義;即使像圖書的版次、印數、價格也應納入考察視野。
對副文本九要素的研究,其價值與意義不可小覷,這些研究將有助于開拓文學史研究的新模式、新局面。比如,對書籍裝幀與插圖的研究,誠如楊義所言:“既然把書刊裝幀插圖看作既是客觀的,又是主觀的,是主客觀融合滲透的產物,就可以從一個特殊的視角,透過裝幀插圖,看取作家或隱或顯的心靈世界,看取他們個人的修養和趣味,看取民族命運和中西文化沖突在他們心靈中的投射和引起的騷動。” 他甚至認為該項研究“煥發了我們追求文學史新模式的熱情和靈感,內心的爽朗,仿佛發現了文學史世界一片有待開發的肥沃的新大陸。” 楊義將對作為副文本要素之一的“文學圖像”(封面、插圖)的研究上升到看取作家心靈世界和文學史研究的高度,此評不虛,乃真知灼見。再比如,對圖書版次和印數的考察,其意義常被研究者弱化或忽略。其實,印數與版次可以為考察新文學作品的傳播與接受提供直接的數據標準。民國時期新文學初版本以首印2000冊印量最為常見,基本在1000—3000冊之間波動。如果出現再版或三版,也大都在這個空間浮動。當然,極為暢銷的圖書除外,比如1930年代丁玲的《母親》一連再版4次,總量達到一萬多冊。郁達夫的《迷羊》在一年零三個月內連版四次,總量達1.7萬冊。我們可以以2000冊為基準,來衡量新文學初版本的接受情況。
一部作品一旦誕生,就會脫離作者而成為一個獨立的文本。大部分新文學作品自創生至今,其文本演變史也不足百年,但每一部優秀作品尤其名著大都存在較為復雜的版本譜系。常見的譜系模式主要有單線遞進式、折返式、衍生式、合成式、雜糅式等幾種。不同的模式有著不同的形式特征,揭示了不同類型作家的不同思想。因此,既要關注其個性,又歸納其共性,對從事新文學作品版本研究,都是大有裨益的。
單線遞進式,即初刊→初版→修改本→定本。這是最為常見模式,也是新文學作品演進的主流模式。該模式的特點是后文本對前文本的修動一直處于增量過程中,即每一次修改都是一個臨時的定本,最后一次修改也即確立為最終的定本。該模式的實踐者對文本進化論思想篤信不疑。他們要么信奉藝術進化論,即每一次文本修改,都會引發藝術質變;要么信奉思想進化論,即每一次文本修改,都會在某種思想或意識上發生質變。巴金的《家》、郭沫若的《高漸離》、錢鐘書的《圍城》、楊絳的《稱心如意》屬于前一種;楊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紅旗譜》屬于后一種。當然,所謂“進化論”也不過是作者一廂情愿式的自信,在此意識指導與實踐下所生成的所謂“定本”,有些名副其實(比如巴金的《家》、錢鐘書的《圍城》),有些則是名不副實(比如楊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紅旗譜》)。但不論定本,還是偽定本,對作家本人而言,其定本意識與指認一般不會出現反復。如出現反復,則正可表明作家思想與審美發生了重大改變。
折返式,即發生一次以上版本遞進式演變后,又重新回到前文本中的某一版本。其中以回到初版本較為常見。比如,吳祖光的《風雪夜歸人》從初刊本到初版本(開明書店1944年出版),再到文集本(1955年收入《風雪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單行本(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都經由對前文本修改后生成新文本,截至1957年,其版本演變近似單線遞進式,但到1981年,吳祖光將又把初版本選為定本(收入《吳祖光劇作選》,中國戲劇出版社)。王林的《腹地》從手稿本(1943年完稿)、初版本(1949年由新華書店初版)、再版本(1950年由新華書店再版)、修改本(1985年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1949年版”(2007年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到文集本(2009年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也構成了一個較為清晰的版本流變譜系。其中,第四個版本又重新折返回初版本,自此以后,也以初版本為定本。這種模式主要是由作者在思想或藝術上的變動不居造成的。
衍生式,包括同源衍生與異源衍生兩種。同源衍生式,即由某一作品初版本所衍生出來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并列存在的文本。比如,穆旦《春》先后發表于《貴州日報?革命軍詩刊》(1942年5月26日)、《大公報?星期文藝》(天津版)(1947年3月12日)、 作者自費刊印詩集(1947年5月)。這三個刊物上的《春》各各不同,文本之間的修改不存在遞進關系。再比如,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1948年9月初版)和《桑干河上》(1948年8月初版)即是經由同一手稿本衍生而成。異源衍生式,即由同一部作品的不同版本為源頭所衍生出來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文本。比如:“文革”時期,張揚的《第二次握手》、靳凡的《公開的情書》等被稱為“地下文學”的作品在秘密流傳中生成了很多形態和內容都不一樣的手抄本。衍生式是在特殊語境下才發生的版本演變模式。
合成式,即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版本合成一個新版本。這種模式多發生于戲劇版本流變過程中。劇作者一般會將原始劇本和演出本——一般情況下,導演、演員參與創作——合成新版本,即初版本+修改本,或者初版本+演出本。前者較為常見,如“八個樣板戲”,后者如老舍的《龍須溝》,而陳白塵的《歲寒圖》(1956年選集本)是在初稿本(1944年修改)與群益本(1945年2月由群益出版社出版)基礎上修訂而成。相較于戲劇,在長篇小說版本流變過程中,該模式也較為常見。比如:蕭紅的《呼蘭河傳》有七個版本:初刊本(《星島日報》副刊《星座》從1940年9月1日——12月27日)、初版本(1940年桂林上海雜志公司)、“河山版”(1943年6月桂林河山出版社出版)、“寰星版”(1947年6月,上海寰星書店出版)、“新文藝版”(1954年5月,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版)、“黑人版”(1979年12月,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哈爾濱版”(1998年10月,哈爾濱出版社出版)。其中,“寰星版”是在初版本和“河山版”基礎上修訂而成。再比如,在當代作家中,韓東的長篇小說《扎根》就是由發表過的若干部中短篇擴充而成。
雜糅式,即作品版本在演變過程中屢屢兼容上述一種或一種以上模式,從而生成新文本。這種演變模式最為復雜,充分顯示了作者在思想與藝術上的矛盾性。某種歷史意識的強勢侵入,精神獨立性的喪失,藝術感知力的退化,都可導致雜糅式演變模式的生成。特別是經過“十七年”時期的大修大改后,絕大部分作為“定本”的新文學名著大都難脫“雜糅”之勢。比如,曹禺的《雷雨》、《日出》,郭沫若的《棠棣之花》。版本互串是其最大特點,甚至到最后連作者本人也無法確認哪一個為定本,或者說哪一個版本里的思想或藝術表現力更讓自己滿意。
版本演變模式并不只這五種,上述歸納與闡釋也并不一定完全合乎實際,每一部作品的版本演變史到底如何,需要具體分析。但對版本模式的研究側重點不在其外在形式特征,而在形式背后所反映的歷史內涵和作家精神演變史。因此,有必要為每一部文學經典名著建立版本譜系檔案,此乃中國新文學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所必須。
三、新文學名著的善本問題
“善本”二字始出宋代文獻,原指校勘精湛的書籍,故若以此衡定,并非所有宋刻本皆為善本,比如校勘不精的福建建陽的麻沙本書。善本也有時間上的限定,比如,在宋人看來,當時流行的監本書就非善本。宋以后,宋本因日漸稀少逐漸成為眾人搜求與珍藏的對象,自明以來特別是到清代,此種風尚愈演愈烈,似乎只要是宋元舊刻本皆被認定為善本,至于校勘精準與否則不在考慮范圍之內。明中葉后,凡舊必善理念已深入人心,至此,善本初始義已被徹底更改。事實上,善本并無確切含義,而總是隨著歷史進展有所變。在今天,精加校讎的版本、稀見舊刻、名家抄本、前代名人手稿,等等,都是善本。宋刻本、遼金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自不必說,民國時期的部分刻本,以及活字本、套印本、插圖本、抄本、稿本、批校本、影印本等名目眾多的本子,也都可稱為善本。
談及善本理念,清代張之洞與藏書家丁丙的觀點常被提起。張認為“善本非紙白板新之謂。謂其為前輩通人,用古刻數本,精校細勘,付槧不譌不闕之本也。” ,并以“足、精、舊”為善本“三義”:“ 一曰足本,無闕卷,未刪削; 二曰精本,精校、 精注; 三曰舊本,舊刻、 舊抄。” 丁則把善本歸納為舊刻、精本、舊抄、舊校四類(《善本書室藏書志》)。張之“三義”是從校勘精審與否(前兩條)以及文物價值(第三條)來說的。前兩條乃善本原義,后者則整合了時人觀念,即凡舊必新,不再把校勘精審與否列入篩選標準;丁也把宋元舊刻、洪武至嘉靖時的刻本視為“善本”,顯然也是從文物性角度考量的,但他在論及“精本”時又強調本子的校勘問題,這樣實際上又復歸善本的初始義。張、丁有關善本理念的闡釋有諸多重合處,但認定標準又時有矛盾,若按此篩選,很多被歸入善本的本子實際上并不善。這也表明,若給善本下一個完整、確切的定義,不僅難度很大,而且即使有,也往往與實踐相沖突。
后人陸續修訂已有善本理念,也陸續把前一代稀有文獻認定為善本。善本之義在今天更為寬泛,但不論怎么變,凡舊必善的理念又得到進一步強化。不過,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今人倒不再在善本外延與內涵上求取一統,而干脆在前人認知經驗基礎上,將善本之義做了折中處理。比如,李致忠提出善本“三性說”,即歷史文物性、學術資料性、藝術代表性 ,但后兩條標準受到同行質疑,認為后兩性很難成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委會借鑒李致忠“三性說”,提出“三性九條說 ”:“三性”為總則,“九條”為總則的具體化,也即只要符合其中任何一條即為善本。但這個以集體名義做出的善本定義和標準經不起推敲之處甚多,其現實操作意義遠大于理念意義,即為發動全國性的珍貴文獻發掘與整理提供一個最為寬泛的、可操作的依據。黃永年主張把“善本”分為兩種:一種是繼承宋以來的涵義,把凡是校勘精審接近古籍原貌的本子,歸入“校勘性善本”;一種是承認清以來藏書家、版本學家的講法,把凡已成為文物的古籍歸入善本范疇,稱為“文物性的善本” 。在諸多觀念中,我覺得黃永年的界定和區分最為科學,可行性較高。
通過以上論述,大可得出以下幾個結論:版本收藏家向來重視善本收藏,版本學家向來重視善本研究,但有關何謂善本的認知與實踐一直以來就難有統一標準;同代生成的經典文本一般不被認定為善本,也就是說,某個文本被認定為善本,須拉開一定的時間;文物性價值是任何時代所有善本應有之義,但除此以外的認定標準總會隨著歷史變遷而有所變化,有時其概念義會發生混雜甚至錯亂;在學術界,每次有關善本理念與標準的推出,都充分融合此前已有知識與經驗,且合乎當世善本發掘、整理與研究的需要。那么,在新文學領域,其善本理念與實踐又是怎樣的呢?可以確定的是,有關新文學善本有無問題的探討已無需再議,如今需要討論的是該如何建立新文學的善本理念和篩選標準,并確定哪些書是善本,以及如何推進善本整理、保護、研究與應用的問題。
在新文學版本研究領域,雖然在新時期以前陸續有學者注意到版本優劣問題,但終歸局限于感性的認知領域,或者說,還沒有上升到一種規律性的、可總結的學術高度。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陸續有朱金順、姜德明、金宏宇等版本研究專家談到了該命題。朱金順將新文學的原本、孤本、手稿本、解放后新印的善本定為善本 。他較多地繼承了古籍版本學領域中善本理念與標準,但他又格外看中善本的文獻、學術價值,即主要以文獻價值高低認定善與非善,而對文物價值較少討論。姜德明認為“不能簡單地把孤本認定為珍本或善本” ,而且光是這四條也不能涵蓋所有新文學善本。在他看來,至于哪些是善本書,需具體對象具體分析。有作家題跋的簽名本、親筆校訂本,各根據地和解放區出版的土紙本新文學書刊,國統區出版的各個時期的革命烈士的作品,封面裝幀藝術上乘者,某些珍貴的私人印書,等等,都是善本書。同時,他認為對善本概念外延的界定不宜過寬:“有人說凡是已經絕版多年的新文學版本,都可作為善本看待,這又過于寬泛了,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就好像說凡是民國版的文藝書都可作為新文學善本一樣。贊成這種說法的人,恐怕是盼望民國版的圖書能不斷升值。有的書盡管內容重要,然而不顧其他條件就定為善本也不妥……” 對善本標準的界定也不宜過死:“界定新文學版本中善本的標準,其實很難規定幾條便可作數。” 善本的生成是一個歷史過程:“新善本的形成,也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歷史環境的變遷才逐步被人們承認的。” 相對于朱金順在善本認定范圍上的狹隘性,姜德明主張進一步擴大了善本篩選范圍,指出了一些認知與實踐誤區,提出了一些合乎實際的觀點,這對于推進新文學善本理念的更新和相關研究是一個有益的補充。在新文學善本理念更新和理論建設方面貢獻最大的當屬金宏宇。他旗幟鮮明地指出舊的善本標準不適宜用來作為新文學寫作的原則,應該建立新的善本原則與標準,即“敘眾本原則或版本兼容原則”:“‘新善本’應該是指文本內容最具有歷史真實性和美學價值的版本。即在一部新文學名著中的眾多版本中,新善本不只是善版本,更應是善文本;不僅版本內容好,更要文本內容好。……‘新善本’概念中的‘本’同時也包含了‘版本’和‘文本’的新義 ……”那么,該如何確立新善本呢?他認為“對于那些作過思想跟進和藝術除魅式修改的作品,我們最好是回到它的初版本。對于那些出于藝術完善動機的修改并確有藝術進步的作品,則應重視其定本。有些作品的‘新善本’可能既不是初版本也不是定本,而是其中的某個修改本。” 金宏宇的新善本原則跳出了古典版本學范疇,對善本的概念義做出較為嚴格的界定,無論在理論還是在方法上,對推進新文學版本研究,都是一個不小的貢獻。至此,新文學的善本原則走出了古典范疇,開始有了自身的理論體系。但這個界定也有一定的問題,即因其所滿足條件較為苛刻,故若按此標準,能夠得上善本的版本并不多,也自然把朱金順、姜德明等學者所認為的許多善本書排除在外。看來,新文學的善本原則也難有統一標準。
而在版本研究諸環節中,善本問題——善本理念或理論、善本篩選與認定——是其中最為核心的、最棘手的、也是必須解決的重大課題。為什么非如此不可呢?這既是推進新文學研究精準化、上檔次、上水平的學科發展需要,也是推動新文學經典化和文化傳承的迫切需要。當前,文學批評與文學史研究普遍不注意作品的善本問題,由于對作品善本問題的忽視或研究薄弱,致使當代文學批評與文學史寫作中屢屢出現一些“硬傷”。比如:郭沫若早在1921年前后就是忠實的馬列信徒 ;《青春之歌》表達了“懺悔主題” ;昌耀五六十年代詩作表現出了疏離時代的寫作傾向 ;師駝的小說早在四十年代就展現出了高超、前衛的敘述藝術 ;胡風的《時間開始了》主要謳歌對象是“新中國”,其次才是毛澤東 ;沙汀的《困獸記》中的章桐最后決定奔赴延安,是因為章對八路軍及其活動區域懷有一份真摯的情感 ,等等,在今天看來這些結論都是不合實際的。表面上看,它們看似是文學批評、文學史問題或作家思想問題,若追根溯源,其實就是個版本(善本)問題。如果研究者稍稍辨析一下所用版本,相關研究就不會出現上述明顯的偏差。新文學善本認定與研究的重要性已無需贅言,既然“新善本原則能將某些作品向文學經典的方向前推進一步,或者說它是拯救文學名著的一種原則。” 那么,新文學的善本問題就不再單純是版本學內部的小議題,而是事關新文學批評、新文學經典化和文學史寫作的大問題。然而,新文學版本研究界并沒有建立起一套符合本學科體系和特點的善本理念以及實踐機制。近些年來,盡管也有學者在探討這一問題,但彼此爭議較大。那么,在新文學領域,其善本理念與實踐又是怎樣的呢?可以確定的是,有關新文學善本有無問題的探討已無需再議,如今需要討論的是該如何建立新文學的善本理念和篩選標準,并確定哪些書是善本,以及如何推進善本整理、保護、研究與應用的問題。
首先,要向古代“尋根”,即要借鑒古善本理念和篩選標準。
新文學善本理念與古籍善本理念,一方面,兩者都歸屬于版本學知識范疇,前者是對后者的繼承與超越,后者的已有成果為前者新理念的生成提供了堅實的方法論基礎。比如前述將古籍善本分為“文物性善本”與“校勘性善本”的分類,就同樣適用于新文學善本整理與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兩者既同又異,“同”顯示了版本學知識譜系中普適性、穩定性的一面,“異”顯示了版本學未知的、發展性的一面,“同”的一面固然重要,但對新文學善本特質而言,“異”的一面才是新文學版本研究的重點。
其次,要立于學科實際,從前人研究成果中吸取有益經驗。新文學作品版本作為史料之一種,或者作為一種正在形成中的學問,常被看作是中國現當代文學文獻學的一個子門類而被予以研究,尤其伴隨近些年來中國新文學研究趨向史料轉向背景下,這一趨向變得愈發明顯。包括唐弢、陳子善、金宏宇在內一大批以研究新文學版本而著稱的專家學者,都在該領域內做出了建設性貢獻。比如,無論是唐弢和陳子善對新文學作品版本的發掘和系統整理,還是金宏宇對新文學名著文本演變史的考梳、研究,以及對新文學版本理論的建構,都是后人在從事這項研究時所必須繼承或參照的學科基點。因此,對善本的認定、篩選、釋讀,也必須從學科傳統中汲取理論和方法上的支撐。新文學作品善本理論與實踐從無到有、從點到面的逐漸展開,正是與唐弢、姜德明、朱金順、金宏宇這種功勛學者的倡導、探索、建構息息相關。他們每一次在善本發掘、整理上的貢獻,或在理論、方法上的開拓,都會對新文學的善本研究打開新局面。可以說,正是這些“新局面”的次第累加,才奠定了今天善本問題在中國現當代文獻學中的學術地位。從目前實踐情況來看,新文學的善本理論雖不成體系,其內涵與外延也尚未定型,但其在不同時期陸陸續續出現的建設性觀點,不斷為后續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學科基礎。這就決定了新文學的善本認定和理論建設也必須繼承這種學科歷史,多多總結前人研究成果。
再次,在善本認定中,也應秉承實事求是原則。
善本不等同于定本原則。作家一般都有修改自有作品的習慣,也有極強的定本意識。比如,巴金一直對《家》進行頻繁修改,直到八十年代才完成。他始終堅信作品會越改越好,事實也卻如其所愿。然而,也有很多作家雖也抱定如巴金一樣的愿景,但結果往往事與愿違。因此,由作家本人認可的定本有些是善本,有些則不是。一般來說,那些趨于正向修改,以旨在提高文本藝術水平而做出修改,并因此而確定的定本大都可當作善本來認定。即使因時間太近而不便認定為善本,但在未來成為善本的可能性極大。比如,巴金和錢鐘書在八十年代分別對《家》、《圍城》經由最后一次修改后所形成的定本。有些定本不是善本,那些趨于負向修改,旨在迎合政治或主流意識形態的定本大都不是善本。比如,周立波、梁斌、楊沫、王林、曹禺將最后修改過的《山鄉巨變》《紅旗譜》《青春之歌》《腹地》《雷雨》立為定本,顯然是不能當做善本來看待的。因為這些經由修改過的版本相比于初版本在藝術上都大大退化。單單這一點就可以將之排除在外。
善本不等同于初版本原則。在版本收藏與研究界,對初版本的膜拜由來已久,很多初版本由于印刷精良、裝幀好、思想獨特、藝術性高或帶有特定文學史意義而成為善本。比如,魯迅與周作人合譯的《域外小說集》、魯迅的《吶喊》、郭沫若的《女神》、聞一多的《死水》、柳青的《創業史》等等。應該說,以“魯、郭、茅、巴、老、曹”為代表作的現代文學經作家在民國時期出版的絕大部分初版本著作都可歸入善本范疇。但也有特殊情況,需具體對待:一,有些初版本由于校對排印錯誤、甚至粗制濫造、錯愕較多反而淪為劣本乃至“惡本”。比如冰心的《關于女人》(1943年9月天地出版社初版)就錯字太多,“錯得使人啼笑皆非”,以致讓作者覺得“實在無法送人” 。這類初版本不應被認為為善本。二,在特殊情況下產生的初版本,即在二三十年代因國民黨查禁而出現的諸多刪節本、盜印本中,除了極少數初版本被認定為善本——比如,茅盾的《子夜》和王統照的《山雨》的初版本雖都是刪節本,但不妨礙被認定為善本——外,其他絕大部分當排除在外,比如,《雀鼠集》(魯彥)的國風書店版就是盜版本,原“文生版”中的《槍》被抽掉。《月牙兒》(老舍)的奉天振興排印局版有大量內容被刪節。顯然,這類初版本由于文本思想的不成熟或藝術體系的不完美,與此后陸續出現的修訂本、定本相比,并無優勢可言。故在善本認定時,也當一概將之排除在外。
善本生成的可能性原則。善本不一定是初版本、定本,也可能是介于初版本與定本之間的其它版本,但至于到底哪一個被認定為善本,存在認定難度。比如,魯迅的《吶喊》有1923年新潮社版、北新書局版 。其中,北新書局第四版的署名與題名為隸書風格,第十三版又抽掉《不周山》,后該版本就固定下來了。這樣看,北新初版、第四版、第十三版都具備善本特質,但到底哪一個更佳,實際上并不容易判斷。比如,茅盾的《見聞雜記》雖有1943年桂林文光書局版、1958年人文社文集本(第九卷),但就文獻價值而言一般認為1984年花城出版社版為善本。因為該本為全本,此前被刪、被遺漏的作品悉數收入,恢復了原文本風貌,而且紙質與封面裝幀亦佳。但是這種完善過程并非一次性的,存在多版次可能。如果僅從中認定一個版本為“善”或佳本,似也不容易決斷。再比如,謝冰瑩的《從軍日記》有1929年3月上海春潮書局初版本,但于同年再版時,作者又加入《再版的幾句話》、《一封給三哥的信》、《給女同學》和《革命化的戀愛》,故再版本在內容與篇目上較初版本更完備。因此,從初版到再版,同樣會帶來認定上的困難。總之,一部作品有好幾個版本,到底哪個為最佳善本,并非一時所能徹底決斷得了的。這既需要經驗、學識,也需要時間。或者說,到底那個為最佳,在未來認定中,都存在某種可能。
除上述“三原則”外,新文學善本的特殊性還在于:一方面,生成時間不夠長,不便認定。在傳統善本理念中,凡善本必經較長時間的檢驗,故一定的時間區隔是善本認定中一個約定俗成的基本前提。新文學版本生成周期最長也不過百年多,更可況大部分文本的文獻價值和藝術價值還有待檢驗,故存在不便認定的問題也就是必然的了。至于新時期以來生成的文本,由于較為常見,珍稀度不達標,即使文獻價值足夠高,故一般也不會被認定為善本。雖然不便認定或有待認定,但其中很多文本已具備善本標準,可稱為“準善本”。比如,自八十年代以來出現的《女神》、《邊城》、《駱駝祥子》等匯校本,雖因生成時間挨得過近而不能認定為善本,但它們完全合乎校勘性善本的標準。在未來,它們被認定為善本的可能性較大。另一方面,生成時間雖短,但文本生成過程也錯綜復雜,所以,一部新文學作品的善本可能并非唯一,不能排除有兩個甚至兩個以上的情況。比如,田漢的《關漢卿》就有悲、喜兩種不同的本子,作者都認可,研究界也難分伯仲。那么,也就存在兩個善本的可能。再比如,徐志摩的《翡冷翠的一夜》有1927年9月初版,分甲種和乙種本,正文共140頁,收詩52首。封面左側題有“翡冷翠的一夜 徐志摩著”,右側為江小鶼畫作,內容為翡冷翠維基烏大橋風景。1928年5月新月書店出再版本。“翡冷翠的一夜 徐志摩著”豎排,看上去,比初版本更緊湊。此版本的裝幀、紙張、篇目、內容、封面大小與初版乙種本基本一致,但封面畫有別于初版本。再版本封面繪有一位美女。她濃眉、大眼、長臉,披著頭巾,表情豐富。她坐于花樹叢中,獨自低首凝思。《翡冷翠的一夜》的封面裝幀、環襯設計、封面題字、作者手跡、正文內容都堪稱一流,故初版本和再版本都是新文學版本中的珍品。也都可認定為善本。或者說,像這種情況,若非要分出哪一個最佳,目前很難區分,只好留待時間驗證了。這也就為什么筆者特別強調新文學善本尚在生成中不便或難以認定的重要原因了。
綜上,相比于古籍版本學,新文學版本學是一門新學問,但尚處于起步階段。雖然在版本考證、集成與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無論理論還是方法都還沒形成符合本學科實際的成熟體系。而新文學的善本問題尤其難以界定,善本認定的標準更加難以統一。如果以同時具備文物(文獻)價值、藝術價值,且校勘精審為善本認定的充分條件,那么在新文學版本中能認定為善本的也就所剩無幾了;如果區分“文物性善本”和“校勘性善本”,那么在新文學版本中能夠得上此標準的倒也數量可觀,但其生成周期又不夠長,或數量偏多,故頂多認定為“準善本”;如果單以“文物性善本”論,它又是一個開放性的概念,就新文學善本內涵與外延而言,其生成與發展的可能性就更是無限敞開著,故可以肯定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新文學善本會在數量上呈現一個明顯的遞增態勢。總之,相比于古籍善本理念與認定的相對有章可循,新文學善本原則與理念除了繼承古籍版本學的某些遺產外,更多的還在形成中,若求取一套統一標準,其實踐的難度要遠甚于前者。鑒于此,筆者認為,有關善本原則及認定,應分在廣義和狹義之間尋求一個合乎實際需要的“折中”,即在文獻價值(稀缺性)、學術價值為其固有的標準外,還要充分考慮到其具體性和開放性的特點。
(因版式原因,注釋從簡,請以原書原文詳注為準。)
- 閻晶明:紙張壽于金石——《魯迅全集》出版史述略[2022-03-01]
- 版本譜系:作為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研究的方法[2022-02-25]
- 探索書籍裝幀的“新”形式[2021-1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