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作藩:基礎(chǔ)寬厚一點(diǎn),總是比較好的
編者按:2020年,在北京大學(xué)中國語言文學(xué)系建系110周年之際,北大中文系策劃了中文學(xué)人系列主題專訪,參與專訪的38位學(xué)人,既有白發(fā)滿鬢仍心系學(xué)科的老先生,也有忙碌在講臺與書桌之間的中青年教師。他們講述著人生道路上的岔路與選擇,詮釋著個人與世界之間具體而微的密切關(guān)聯(lián);他們梳理著治學(xué)過程中的難關(guān)與靈感,傳遞著樸素堅韌的中文傳統(tǒng)。這是中文學(xué)人的一次回顧、總結(jié)和反思之旅,沿著先生們學(xué)術(shù)與理想的歷史軌跡,我們得以觸摸“活的歷史”,感受“真的精神”。
2022年1月,這份匯聚北大中文幾代學(xué)人身姿與風(fēng)采的訪談實(shí)錄由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結(jié)集出版為《四海文心:我與北大中文系》。中國作家網(wǎng)經(jīng)出版方授權(quán),特遴選其中部分章節(jié),以饗讀者。唐作藩先生是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教授、著名音韻學(xué)家,在這則對話中他回顧了自身的學(xué)術(shù)與人生路徑,并向后輩敦敦教導(dǎo),“基礎(chǔ)寬厚一點(diǎn),總是比較好的,不要把自己局限在一些小框框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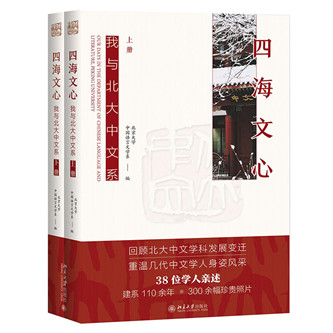
《四海文心:我與北大中文系(上下冊)》,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編著,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
受訪人:唐作藩,1927年生。1954年調(diào)至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工作。《語言學(xué)論叢》《中國語言學(xué)報》編委,《中國語言學(xué)》學(xué)術(shù)委員。曾任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副主任、中國音韻學(xué)研究會會長。著有《漢語音韻學(xué)常識》《上古音手冊》《音韻學(xué)教程》《漢語史學(xué)習(xí)與研究》《漢語語音史教程》等多種著作,發(fā)表論文一百多篇。
采訪人:向筱路,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漢語史專業(yè)在讀博士生。
采訪時間:2020年9月18日

唐作藩先生
向筱路:唐先生您好!您是我國著名的語言學(xué)家,在漢語音韻學(xué)、漢語語音史領(lǐng)域有深厚的造詣。從1954年中山大學(xué)語言學(xué)系合并到北大中文系算起,您已經(jīng)在北大中文系工作和生活了六十多年。今年適逢中文系110周年系慶,所以我們想借這個機(jī)會對您做一次訪談,主要想請您談?wù)勁c北大中文系的故事,以及您對漢語音韻學(xué)這門學(xué)科發(fā)展的回顧和展望。您是在中山大學(xué)語言學(xué)系接受的大學(xué)教育,從此走上了學(xué)術(shù)研究的道路。您當(dāng)時為什么會選擇語言學(xué)作為自己的專業(yè)呢?那一段經(jīng)歷對您之后的學(xué)術(shù)研究工作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
唐作藩:好的,我回顧一下。我覺得我是文人命啊!我的運(yùn)氣好吧。我出生在湖南湘西的邵陽地區(qū),當(dāng)時叫武岡縣。現(xiàn)在從武岡分出一個洞口縣,洞口縣下面有一個小鎮(zhèn),叫黃橋鎮(zhèn)—江蘇不是有一個黃橋么,我們那邊也有一個黃橋鎮(zhèn)—我就出生在那個小鎮(zhèn)上。那時根本沒有想到會有今天。
我出生的時候家里很窮,住在一個租來的小房子里面。我母親是個不識字的農(nóng)村婦女,父親在商店里當(dāng)了兩年學(xué)徒,剛剛出師吧,自己做一點(diǎn)小買賣。十一二歲的時候,母親老是帶著我到外婆家去,所以我從小是在外婆家里長大的。我外婆又善良,又能管家。外公我從來沒見過,很早就去世了。另外外婆家里還有兩個舅舅和一個大姨媽。后來家里條件慢慢好起來,自己還有地種了。本來我父親要我跟他一樣,去當(dāng)個學(xué)徒,做點(diǎn)小買賣。但我的一位二叔改變了我的命運(yùn)。我父親有三兄弟,他們都是做買賣的,我的二叔長年跑外,先是在家鄉(xiāng)的小鎮(zhèn),然后到寶慶府,即今邵陽市。我們那里近代出了兩個人,一文一武,文的是魏源,武的就是蔡鍔,所以別看這么個小地方,還是出了不少名人。因此我二叔的眼光比較長遠(yuǎn),他對我父親說還是讀書好。
這句話可以說決定了我的一生。于是我父親就送我去讀書了,即先去上黃橋中心小學(xué)。我本來念了兩年私塾,那時候已經(jīng)十二三歲了。去報名的時候,校長曾育賢老師說你這么大了,不能從一年級學(xué)起,念五年級吧。我一輩子都記得,念五年級的第一個學(xué)期,我的數(shù)學(xué)期末考試得了37分,不過到畢業(yè)的時候我已經(jīng)是全班的第二名了。讀完小學(xué)后接著去讀中學(xué),考上了洞庭中學(xué)。抗戰(zhàn)時期國民黨有一個軍校,叫作軍二分校,校長叫李明灝,是國民黨的一個中將。因為當(dāng)時有好多教官的子弟要上學(xué),他就創(chuàng)辦了這所中學(xué),在湖南武岡縣縣城郊外,取名叫湖南私立洞庭中學(xué)。我記得我是在初10班,后來在高4班,在這個時候就認(rèn)識了我老伴。我念高中的時候,她念初中。她家里比較富裕,有三姐妹,父親是國民黨的上校,所以跟著去了后方。她當(dāng)時還在念初中,兩個姐姐讀高中。在學(xué)校的時候我們常常演話劇,我記得演過《萬世師表》,講聞一多帶著學(xué)生從北京到昆明的故事,我演老師,她演學(xué)生,她大姐就演我的老伴。所以在中學(xué)的時候,我們就相互認(rèn)識了。

唐作藩與夫人唐和華合影
本來我是想考北大的,我記得當(dāng)時北大和清華同時招生,要么報清華,要么報北大,我就報了北大,結(jié)果沒考上,考上了中山大學(xué)。那時候在湖南還不能參加北大、清華的招生考試,得到上海去。湖南不是出銻嘛,有很多錫礦山,實(shí)際上是出銻,出的銻常常要運(yùn)到上海去。一個工程師的兒子跟我們是同學(xué),所以我們就坐運(yùn)銻的船去上海,參加考試。

1982 年春唐作藩與王力先生(左)合影
因為我們在中學(xué)演過話劇,我當(dāng)時不知道,以為語言學(xué)系是演話劇的,就這樣報考了中山大學(xué)語言學(xué)系。本來中山大學(xué)沒有語言學(xué)系,是王力先生創(chuàng)辦的。王力先生是清華的教授,系主任是朱自清,原本他是準(zhǔn)備回清華的。在他回北京之前,先回了廣西老家,然后經(jīng)由廣州回北京。結(jié)果在廣州的時候,中山大學(xué)的校長就挽留他,請他在廣州待幾年,然后再回北京。于是王力先生給朱自清寫信,說有朋友要他留在中山大學(xué)。朱自清說也好,同意他待在廣州。王力先生給中山大學(xué)提了一個要求,就是要創(chuàng)辦語言學(xué)系,校長答應(yīng)了他。我記得那時候除了王力先生,還有岑麒祥先生、高華年先生、嚴(yán)學(xué)宭先生等。高先生是教少數(shù)民族語言學(xué)的。另外還有黃伯榮先生,當(dāng)時是助教,后來我畢業(yè)的時候他是講師。
向筱路:20世紀(jì)50年代院系調(diào)整,中山大學(xué)語言學(xué)系合并到北大中文系,您也隨之北上,此后一直在這里工作和生活。您能為我們介紹一下當(dāng)時的情況嗎?
唐作藩: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宣部副部長胡喬木同志提出一個建議(他是王力先生在清華時候的學(xué)生)他想把全國搞語言學(xué)的老師集中到北大來,從北大中文系的語言文學(xué)專業(yè)中分出一個語言專業(yè),這樣就在1954年把中山大學(xué)語言學(xué)系的全部老師和學(xué)生調(diào)來了。我1953年從中山大學(xué)畢業(yè),那一年中山大學(xué)語言學(xué)系招了三十名學(xué)生,是歷年最多的,以前總是只有五六個人。我們那一級也只有六七個人,現(xiàn)在有些還有聯(lián)系,你可能聽說過。如暨南大學(xué)的詹伯慧,后來在中央民族大學(xué)工作的歐陽覺亞,現(xiàn)在在美國的饒秉才,還有麥梅翹,畢業(yè)以后留在了社科院語言所—麥梅翹比我們都大,現(xiàn)在已經(jīng)去世了。
我剛才說胡喬木要整合北大、清華、燕京大學(xué)的師資力量。當(dāng)時的燕京大學(xué)也合并過來了,像高名凱先生和林燾先生都是燕京大學(xué)的,魏建功先生是老北大的教師,還有周祖謨先生,他們都是很有學(xué)問的,都集中到北大來了。那時候北大沒有語言學(xué)系,所以王力先生建議創(chuàng)辦一個語言專業(yè)。后來成立了兩個教研室,一個漢語教研室,一個語言學(xué)理論教研室。語言學(xué)理論教研室是高名凱先生做主任,漢語教研室是王力先生做主任,后來漢語教研室又分為現(xiàn)代的、古代的兩個,那是60年代以后的事了。
我1954年來到北大,本來那時候中文系不光有漢語言、語言學(xué)專業(yè),還有一個新聞專業(yè),后來新聞專業(yè)合并到中國人民大學(xué)去了。
向筱路:到了北大中文系以后,有哪些先生對您的影響特別大呢?
唐作藩:主要是王力先生,還有岑麒祥先生。本來在中山大學(xué),留下我是做岑麒祥先生的助教的,跟著岑先生學(xué)語言學(xué)理論。到了北大以后,王力先生對我說語言學(xué)理論教研室已經(jīng)有兩個助教了,就是石安石跟殷德厚;我們剛成立的漢語教研室還沒有助教,那你就跟著我學(xué)漢語史吧。這樣我就轉(zhuǎn)換了研究方向,從此就一直跟隨王先生。我記得那時候住在現(xiàn)在咱們中文系所在的原朗潤園教師住宅區(qū)。朗潤園還是有四合院的房子,還沒有蓋咱們現(xiàn)在這個人文學(xué)苑,旁邊住的是聞一多的弟弟聞家駟。住在未名湖邊的,我記得還有季羨林先生。我在那里就這樣度過了好些年。

1955 年秋北大漢語教研室教師在頤和園聽鸝館前合影(左起:潘兆明、梁東漢、周祖謨、唐作藩、 魏建功、楊伯峻、姚殿芳、黃伯榮、林燾、王力、吉常宏)

1974 年《古漢語常用字字典》編寫組合影(前排左起依次為:戴澧、王力、岑麒祥、林燾,后排 左起依次為:蔣紹愚、張萬起、唐作藩、徐敏霞)
剛才提到,到北大之后,王力先生要我就跟著他學(xué)。這時候正好呂叔湘先生提出要普及語言學(xué)的知識,他就跟王力先生說,您來寫一個音韻學(xué)的普及讀物吧。王先生住的那個四合院,實(shí)際上只有東屋、北屋和西屋,王先生住在北屋和東屋,我就帶著我老伴和一個三歲的小孩,住在西屋,雖然只有一間房,但有衛(wèi)生間。王先生把我叫過去,對面就是他的書房,他說剛才開會回來,呂先生要求我寫一本音韻學(xué)普及讀物。他就要我寫,我說我還沒學(xué),他說邊學(xué)邊寫、邊寫邊學(xué)。這樣我就寫了第一本書——《漢語音韻學(xué)常識》。沒想到那本書后來在我國香港(1972)也出版了,在日本還出了兩種正式翻譯本(1962,1979)和一種自印翻譯本。所以這樣我就一直到現(xiàn)在,從事音韻學(xué)的教學(xué)與研究。
向筱路:關(guān)于“漢語音韻學(xué)”和“漢語史(上)”這兩門課程,您后來都出了教材,就是《音韻學(xué)教程》和《漢語語音史教程》,影響很大。這兩本教材的編寫過程,您在后記里都做了一些說明。我想請您講講當(dāng)時是出于什么考慮決定自己來編寫教材?它們和同類的著作相比有什么突出特點(diǎn)?比如王力先生的《中國音韻學(xué)》在1936年就出版了,后來改名《漢語音韻學(xué)》,他在50年代出版的《漢語史稿》(上冊)也是語音史的內(nèi)容。

唐作藩編著的第一本書《漢語音韻學(xué)常識》書影

1980 年中國音韻學(xué)研究會成立大會暨首屆研討會后北大校友留影(前排左起:徐復(fù)、黃綺、劉又 辛、殷煥先、嚴(yán)學(xué)宭、郭良夫、王均、李格非、唐作藩;后排左起:楊耐思、王宗孟、趙振鐸、陳 振寰、楊春霖、許紹早、李思敬、許夢麟、但國干、魯國堯)
唐作藩:另外還有羅常培先生的《中國音韻學(xué)導(dǎo)論》,是吧?王力唐作藩先生的《中國音韻學(xué)》,他每節(jié)后列為參考資料的內(nèi)容比正文多得多,所以一般的學(xué)生都看不懂。包括羅常培先生的《導(dǎo)論》,雖然是普及性的,但介紹給同學(xué)還是看不懂。所以我就根據(jù)自己學(xué)習(xí)的體會,編了《音韻學(xué)教程》。原來是跟著王先生寫《漢語音韻學(xué)常識》,然后就是《音韻學(xué)教程》,是這樣的。后來再編寫《漢語語音史教程》,也是考慮到學(xué)生們反映看王先生的那些書,不容易看懂。所以我的主要目的是想寫得更通俗一些,讓學(xué)生除了在課堂聽課,也能夠自學(xué)。
向筱路:主要是為了讓同學(xué)們能夠更早地、更方便地入門。
唐作藩:對。那時候同學(xué)住在禮堂前面,咱們的百周年紀(jì)念講堂原來是大飯廳,我記得外面行人路上還有一個橋。那時候很少有汽車,有輛自行車就不錯了。在那后面還有一個食堂,郵局也是在旁邊,就在三角地,還有好些小商店。那時候同學(xué)們就住在前面的樓里,現(xiàn)在是多少號樓我都記不得了,在禮堂的南邊,他們常邀我到學(xué)生宿舍里面去輔導(dǎo),尤其是57級、58級、59級的那幾個班。
向筱路:漢語音韻學(xué)可以分為今音學(xué)、古音學(xué)、北音學(xué)和等韻學(xué),它們各自都有相對獨(dú)立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您對每個門類基本上都做了研究。現(xiàn)在學(xué)科門類劃分得越來越細(xì),很多學(xué)者和青年學(xué)生限于時間和精力,往往只能就其中一個方面進(jìn)行探索,難以做到全面貫通的研究。音韻學(xué)研究也有這個趨勢,您怎么看待這個現(xiàn)象?
唐作藩:這種做法太窄了,我覺得不太合適。你學(xué)音韻學(xué)不光是音韻學(xué)本身,還要有漢語方言的基礎(chǔ),因為很多古音都保存在方言里面,特別是在南方的一些方言里,廣州話、客家話、福建的閩方言,都保存了比較多的古音。所以50年代袁家驊先生開方言學(xué)課,我就從頭到尾一直跟著他學(xué)了,學(xué)了以后還記錄了我湖南家鄉(xiāng)的方言,記錄以后請他看,后來發(fā)表在《語言學(xué)論叢》第四輯上。所以我覺得音韻學(xué)跟方言是分不開的,學(xué)音韻學(xué)一定要學(xué)好方言學(xué)。當(dāng)然還有一個前提,就是要把語音學(xué)學(xué)好,沒有語音學(xué)的基礎(chǔ),你就不會記音了,是不是?

唐作藩給中文學(xué)子題詞:“學(xué),然后知不足!”[徐梓嵐 攝]
向筱路:很多人把音韻學(xué)稱為絕學(xué),不管是對于學(xué)生還是研究人員都有比較高的門檻。據(jù)我所知,現(xiàn)在國內(nèi)還有一些高校的中文系或者文學(xué)院沒有開出“漢語音韻學(xué)”等課程,北大有非常好的研究漢語語音的傳統(tǒng)。您覺得北大中文系有哪些好的經(jīng)驗值得借鑒?
唐作藩:我覺得一方面系里面在安排課程的時候,不要忘了安排這門課,雖然有時候選課的人少,但是還是應(yīng)該開。另外就是要招收音韻學(xué)方向的研究生,因為你要想進(jìn)一步學(xué)好音韻學(xué),還是要通過研究生階段的訓(xùn)練。另外,我覺得不光是我們學(xué)語言學(xué)的需要音韻學(xué)的基礎(chǔ),學(xué)文學(xué)的有一點(diǎn)音韻學(xué)基礎(chǔ)也是好的。我的好朋友袁行霈先生,他就聽了王力先生的漢語史課,到現(xiàn)在我們還經(jīng)常有聯(lián)系。
向筱路:您覺得就漢語音韻學(xué)、漢語語音史的研究來說,我們北大中文系目前有沒有什么需要加強(qiáng)的?
唐作藩:據(jù)我了解,我覺得我們中文系還是不錯的,因為有好幾個教音韻學(xué)的教師。除了孫玉文老師,還有現(xiàn)在已經(jīng)退休的耿振生老師,還有張渭毅和趙彤,趙彤本來是北大畢業(yè)的,后來去了人大,現(xiàn)在調(diào)回來了。
向筱路:您在北大指導(dǎo)了不少研究生和訪問學(xué)者,您在指導(dǎo)過程中,最注重哪些方面的培養(yǎng),具體是怎樣體現(xiàn)的?
唐作藩:跟我學(xué)的日本的學(xué)生比較多一點(diǎn),最早是花登正宏、古屋昭弘,還有平山久雄的一個學(xué)生,叫什么我一下忘了。另外我在馬來西亞教了一個學(xué)期的課,除了教音韻學(xué),另外還開一門《詩經(jīng)》研讀課,所以有些那時候的馬來西亞學(xué)生到中國來旅游了,總是要來看看我。我覺得咱們還是要堅持開這些課吧,是不是?本科就開音韻學(xué),研究生就開上古音,中古音,《切韻》,還有《中原音韻》,對不對?過去咱們的校友楊耐思先生是研究《中原音韻》最好的學(xué)者,可惜已經(jīng)去世了。
我們在做研究的時候,最好既要做到專深,也要做到廣博。比如說你要是重點(diǎn)學(xué)中古音,近代音、上古音也得掌握,另外我也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方言學(xué)對學(xué)習(xí)音韻學(xué)、漢語史的重要性。
向筱路:您在中文系已經(jīng)工作和生活了六十多年,您覺得有什么特質(zhì)是北大中文人最應(yīng)該堅守的?
唐作藩:我覺得一般來說,北大的師生關(guān)系還是比較好的。另外像袁行霈先生他就強(qiáng)調(diào),學(xué)文學(xué)也得學(xué)點(diǎn)語言學(xué),我覺得他這個意見很對。那么我們學(xué)語言學(xué)的人也不要忘了文學(xué),也得學(xué)點(diǎn)文學(xué),這樣比較全面一點(diǎn)。基礎(chǔ)寬厚一點(diǎn),總是比較好的。不要把自己局限在一些小框框里面,盡量去了解一下別的學(xué)科,這樣對提高自己本身的研究也會有幫助。
向筱路:最后我想請您談一談對北大中文系未來的發(fā)展有什么樣的期待?
唐作藩:當(dāng)然是希望能越辦越好了。除了留我們自己學(xué)校畢業(yè)的,外校如果有好的青年人才也可以交流,條件成熟的話把他們引進(jìn)。因為要辦好一個學(xué)校,辦好一個系,主要還是教師吧,教師好,開的課才好,才能更好地培養(yǎng)學(xué)生,是不是?我們在中山大學(xué)的時候就是各個方面的教師都有,除了中大的,我記得還有從武漢大學(xué)、廣西大學(xué)、廈門大學(xué)等學(xué)校調(diào)來的。當(dāng)然,他們應(yīng)該都是有專長的。
- 吳寶三:恩師費(fèi)振剛先生[2022-01-14]
- 蔡元培執(zhí)掌北大的兩種假設(shè)[2022-01-12]
- 第十九屆北京大學(xué)王力語言學(xué)獎揭曉[2022-01-08]
- 清廷同文館的背后推手[2022-01-07]
- 學(xué)習(xí)貫徹習(xí)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lián)十一大、中國作協(xié)十大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精神學(xué)術(shù)研討會在北京大學(xué)舉行[2021-12-31]
- 胡適為北大學(xué)生證婚記[2021-11-18]
- 嚴(yán)家炎:“文學(xué)是癡情者的事業(yè)”[2021-11-05]
- 回憶茅盾與北大五四文學(xué)社[2021-1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