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你們都對我好點(diǎn)啊,我以后可是要進(jìn)文學(xué)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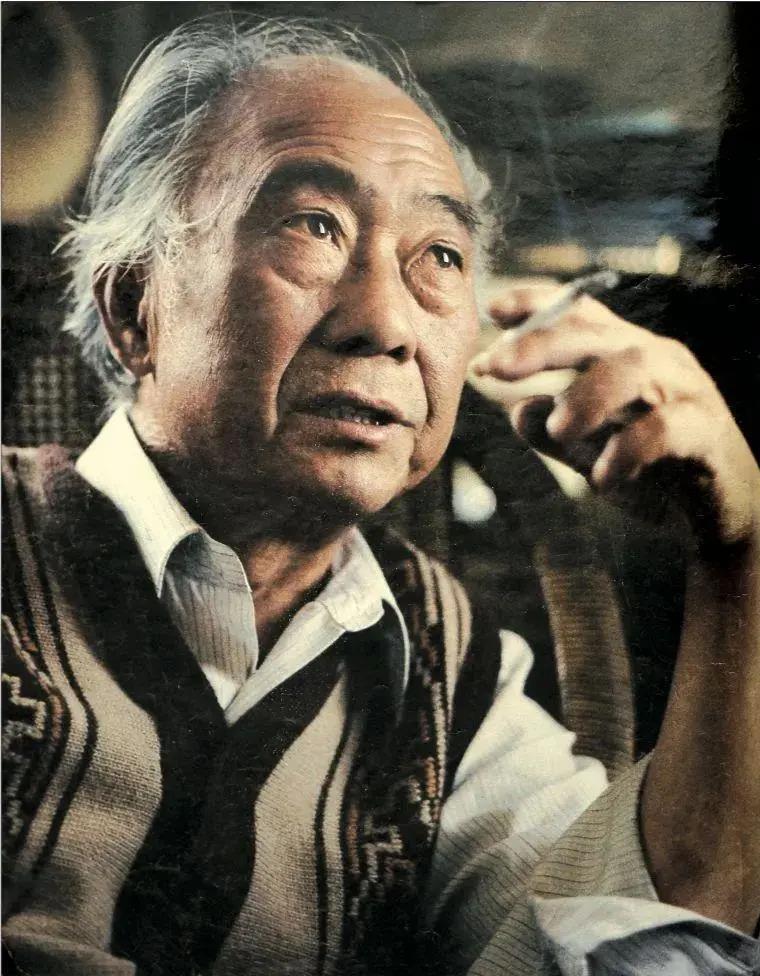
父親會武術(shù),汪曾祺卻體育成績差
張英:汪曾祺先生出身書香門第,似乎他的祖父便多才多藝?
汪朗:他寫過一些關(guān)于父親的東西,很少提到祖父,只說他是一個(gè)科舉時(shí)代最后的貢生,有個(gè)小功名,屬于秀才中的優(yōu)秀分子,但沒有到舉人那一級,他沒參加舉人考試。不過,他畢竟參加過科舉,古文、書法都還可以,暑假時(shí),祖父教汪曾祺學(xué)古文,讓他臨帖,這個(gè)汪曾祺在文章里寫過。至于別的,書畫這些,好像沒聽他說過。而且他祖父在的時(shí)候,他也比較小,才上小學(xué),后來他剛上大學(xué)時(shí)祖父就去世了。他也沒跟我們講很多。
張英:拔貢是正式的官位嗎?
汪朗:不是官位,是功名,就是考完秀才后,從中選拔一部分到北京來學(xué)習(xí),進(jìn)國子監(jiān),實(shí)際上進(jìn)不了那么多。但他只是在秀才這一級,沒參加再高的舉人考試。
張英:還是父親對汪曾祺的影響更大一些?
汪朗:是的,他們相處時(shí)間比較長,我們家老頭兒(北京人稱父親為老頭兒,母親為老太太,是一種親昵的稱呼,但多在背后使用)大概3歲,親媽就沒了,當(dāng)然,后媽也很照顧他。但他可能跟父親相處時(shí)間比較長,對父親的印象還是挺深的,他不是寫過《多年父子成兄弟》嘛。
他爹——也就是我們的爺爺,我們一般都不叫爺爺,因?yàn)闆]見過,有時(shí)我們也開玩笑:“老頭兒,你爹是怎么回事?”
總之,爺爺跟我們關(guān)系不是很深。但他對我父親的方方面面影響還是挺大的,我爺爺會畫畫,會拉胡琴,會體操,會體育,還會武術(shù)……后邊這幾個(gè)方面汪曾祺沒怎么學(xué)的,老頭兒的體育是很差的。大學(xué)兩年都不上體育課,后來畢不了業(yè),讓他補(bǔ)兩年的體育。
汪曾祺畫畫,最早是受他父親影響。他說他父親是舊式高中畢業(yè),那應(yīng)該不是在高郵上的,因?yàn)橹钡嚼项^兒上學(xué)時(shí),高郵都還沒有高中。他父親好像是在南京,還是在別的什么地方上的高中,他也沒有寫得很明確。
兒子唱戲,老爹拉胡琴
張英:老爺子喜歡戲曲,也是從父親那兒來的吧?
汪朗:他從中學(xué)時(shí)開始喜歡戲曲,開始聽唱片,也沒人教,聽完唱片,他跟著唱。開始唱青衣,后來唱老生,宗的余(叔巖)派。他去學(xué)校演出,他父親還給他拉胡琴,我們也就知道這些。
后來上了大學(xué),他主要就是唱昆曲了。經(jīng)常舉辦曲會,大學(xué)老師和學(xué)生湊在一塊兒,有吹有唱的。他說那時(shí)沒事,就半夜吹笛子,弄得整個(gè)宿舍都罵他——貓叫,不讓睡覺了?
他那時(shí)候比較隨意。
當(dāng)時(shí)拍曲,唱昆曲叫拍曲,好多人就是通過這個(gè)熟悉起來了。包括他的最好朋友朱德熙(著名語言學(xué)家、教育家)當(dāng)時(shí)也一起唱昆曲。還有后來搞植物學(xué)研究的,得過全國科技獎(jiǎng)最高獎(jiǎng)的吳征鎰,也在一塊兒唱。
張英:您妹妹也沒見過爺爺嗎?
汪朗:沒見過。因?yàn)槲覀儚男【驮诒本诶霞遥赡?960年就不在了,我直到1981年才回老家看了一下,我妹妹就更晚了,她是老頭兒去世后才回過老家。
張英:您爺爺那輩人,能這么教兒子,真讓人羨慕,估計(jì)與他去南京接受過新式教育有關(guān)系。
汪朗:應(yīng)該有關(guān)系,一點(diǎn)也沒有威權(quán)主義,給汪曾祺的成長創(chuàng)造了比較好的條件。汪曾祺后來的平等待人意識,可能是從他父親那邊繼承下來的,或者受他影響形成的,所以他對我們也都是那樣的。
張英:這就是家教吧。但是很少,一般像他那個(gè)年代的人,能夠和十幾歲的人一起抽煙、喝酒,像哥兒倆一樣,這種交情,我真沒見過。
汪朗:所以他對這個(gè)挺有感觸的,專門寫過文章。
張英:您父親后來對你們的家教,可能也延續(xù)了您爺爺?shù)姆绞剑?/span>
汪朗:對,我覺得可能我們更有點(diǎn)蹬鼻子上臉。我父親沒敢對他父親說什么。可老頭兒在我們家,尤其我那倆妹妹,經(jīng)常都是“老頭你懂什么你,別在那瞎扯了”,這話都有。當(dāng)然在文學(xué)上,肯定不能那么說了,但他有時(shí)在政治上或其他方面上,有點(diǎn)幼稚。人不可能什么都很強(qiáng)。
張英:老爺子的親生母親,那邊的家庭是什么樣的?
汪朗:我也弄不清楚,反正是高郵的一個(gè)大戶,比汪家影響大,功名也高,他們家出過進(jìn)士。
汪曾祺后來有兩個(gè)繼母,第一個(gè)繼母對他也不錯(cuò),但時(shí)間不長便不在了。后來這個(gè)繼母相處時(shí)間比較長,一直活到九十多歲,汪曾祺后來回老家時(shí),繼母還在。他還給她磕頭,畢竟長他一輩。
那時(shí)老師的國學(xué)底子好,汪曾祺是趕上了
張英:父親上學(xué)剛好在一個(gè)坎上,從幼稚園,到縣立第五小學(xué)、高郵初中、高中,剛好在一個(gè)新的教育體系里面出來。
汪朗:對。他們的幼稚園第一期招生,他正好趕上了。新式教育剛在老家興起,他就接觸到了。這也證明他爹比較開明,因?yàn)樗线^高中,在那時(shí)也算新式教育。所以比較開通,早早就給汪曾祺送到幼稚園了。
張英:老爺子一直接受新派教育,舊學(xué)功底從哪來的?
汪朗:他的祖父教過他,那時(shí)盡管開始新式教育了,但傳統(tǒng)的東西比現(xiàn)在要多得多,那時(shí)也沒政治學(xué)習(xí)這些東西,英語課什么的都有。再晚一點(diǎn),國民黨的那種黨義教育之類才進(jìn)了學(xué)校,最開始,就是純粹的文化教育。
汪曾祺幸運(yùn)的是,從小學(xué)開始,語文老師正兒八經(jīng)的國文底子、國學(xué)底子都比較好,正在新舊交替的時(shí)候,這些人雖然有教書資格,但受的教育都是舊學(xué)的,所以底子很扎實(shí)。一些優(yōu)秀人才來教他,他的悟性又比較好,所以從小學(xué)開始,作文經(jīng)常就是范文。就是他趕著了。你要現(xiàn)在,這些老師本身的底子就不行。
張英:汪曾祺上高二時(shí),日本人打過來,他高三換了三所學(xué)校才讀完,算正式畢業(yè)嗎?
汪朗:不知道,沒聽他說過,反正就是四處跑。雖然都在那一片,但離得有點(diǎn)距離。
張英:汪曾祺和祖父、父親在村莊小庵里頭避亂那段,他和您說過嗎?
汪朗:沒說過。高郵那時(shí)候確實(shí)有這么一個(gè)莊,后來文學(xué)研究者還找到小英子還是大英子的原型,當(dāng)時(shí)大英子還活著,大英子后人今天也還在。
張英:汪曾祺打腹稿的功夫是舊學(xué)念過來的嗎?今天人不太相信舊學(xué)功夫,但汪曾祺寫文章時(shí)打腹稿,一揮而就,不再改稿子,真的是硬功夫。他是怎么練會的這個(gè)本事的?
汪朗:那就不知道了。你可以看他的紙稿,都是很干凈的。勾勾畫畫有,但很少。我們看他寫東西時(shí),都很順暢。就這個(gè)話題,他曾寫過文章,說他有時(shí)一開頭要重寫幾遍,撕幾頁稿紙,但寫下來,就很順了。
一直用毛筆寫小說,怎么可能?
張英:他一直用毛筆寫作嗎?
汪朗:沒有。二十世紀(jì)八十年代以后的寫作,全都是鋼筆寫的。他早期拿毛筆寫得比較多,包括給家里寫信,寫文章用毛筆都很少。真是寫那種稿紙格子,用毛筆也太費(fèi)勁了。我們小時(shí)候,他下到張家口勞動(dòng)改造,他經(jīng)常讓我們?nèi)ソo他寄毛筆,他那會兒拿毛筆寫小楷。
我記得很清楚,他要的是雞狼毫,雞毛和黃鼠狼毛合在一塊。當(dāng)時(shí)“三年困難時(shí)期”,供應(yīng)都特別緊張。我們家那時(shí)住得離西單不遠(yuǎn),每次上西單,把口有一個(gè)叫文華文具店的,現(xiàn)在早就拆了。每次路過,都要去問問有沒有雞狼毫筆,如果有,就給他買幾支放那兒,什么時(shí)候給他一塊兒寄。所以我印象特別深。
張英:后來他在張家口畫的馬鈴薯圖譜,手稿找到了嗎?
汪朗:沒有。那個(gè)屬于他的工作任務(wù),完了以后,他就上交了。人家當(dāng)回事不當(dāng)回事的,那就是所里的事,而且時(shí)間又那么長了,所里可能早就不知道了。
張英:當(dāng)時(shí)不是要出書嗎?
汪朗:可能也沒出成。因?yàn)槟菚r(shí)紙張?zhí)貏e緊張,你看他當(dāng)時(shí)寫檢查的那個(gè)紙,那個(gè)黑、破,又黑又糙,方方面面供應(yīng)都不行。所以想出書,我覺得未必很容易。
張英:在西南聯(lián)大時(shí),除了沈從文先生之外,還有誰對他影響比較大?
汪朗:聞一多。聞一多比較欣賞汪曾祺的才氣,因?yàn)槁勔欢嘁灿胁拧M粼骱吐勔欢嗵幍帽容^隨意,他曾經(jīng)給低他一年級的同學(xué)寫了一篇讀書報(bào)告,聞一多看后大加贊賞,說你這個(gè)寫得好,比汪曾祺還好。
那個(gè)低他一年級的人,后來也是他們北京京劇團(tuán)的編劇,叫楊毓珉,這事是楊毓珉跟我們說的。但寫了什么東西,汪曾祺自己已經(jīng)記不太清楚了。好在楊毓珉幾十年一直把稿子留著,是楊毓珉自己的謄抄稿,但一看文風(fēng),就是老頭兒的風(fēng)格。
張英:1949年4月,他出了第一本小說集《邂逅集》。
汪朗:稿子早就給了,正好趕上那個(gè)時(shí)候出的。在巴金當(dāng)主編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應(yīng)該是1947年,那個(gè)時(shí)候汪曾祺在上海跟巴金走得比較近了,經(jīng)常去巴金他家。稿子是什么時(shí)候交的,我看應(yīng)該是差不多那個(gè)時(shí)期,他來北京之前,應(yīng)該就交稿了。因?yàn)槎际菍懤ッ鞯模瑳]有上海生活。
巴金的夫人是汪曾祺西南聯(lián)大的同學(xué),所以他在上海時(shí)候經(jīng)常去巴金那兒。可能是在巴金那兒,認(rèn)識了黃裳,一塊兒喝茶聊天。黃裳搞版本學(xué),喜歡買舊書。
斃稿斃出了大麻煩
張英:1950年,汪曾祺去了《北京文學(xué)》當(dāng)編輯,幾年后就去民間文藝研究會了,為什么?
汪朗:他為什么要調(diào)民間文藝研究會呢?《北京文藝》的一個(gè)領(lǐng)導(dǎo),好像是王亞平,調(diào)到民間文藝研究會去了,就拉他過去。說你到這兒,雖然還是編刊物,但可以經(jīng)常下去采風(fēng)、接觸生活,你不是想當(dāng)作家嗎,這個(gè)條件可能也要好一點(diǎn)。
汪曾祺覺得也好不到哪兒去。
民間文藝研究會答應(yīng),你過來,我給你漲一級工資。汪曾祺說漲一級也無所謂,因?yàn)槲以谶@兒馬上就要評工資了,我肯定也能漲一級。那邊說,那我給你漲兩級,汪曾祺說這還可以考慮。
當(dāng)時(shí)文藝級工資的級差挺大的,兩級工資就好幾十塊錢呢,當(dāng)時(shí)很值錢。
這些都是我聽他閑聊的。
張英:他在民間文藝研究會開心嗎?
汪朗:開始還可以,他也挺投入的。雖然里面也有一些矛盾,但他這人比較簡單,所以開始覺得還可以。但搞民間文藝,主要是兩大派:
一批是原來的那些教授,純粹從學(xué)術(shù)角度來研究民間文藝,鐘敬文、顧頡剛他們那一批,早就有了。中國民俗和民間文藝的研究,大概“五四”時(shí)就開始了,他們是從學(xué)術(shù)的角度,吸收一些西方思想,比較講究。
另一批是解放區(qū)去的,土一點(diǎn)。他們覺得,另一派都是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那套東西,他們看不上。
我聽我媽說,不管誰的稿子,汪曾祺只看質(zhì)量,無形中就把好多解放區(qū)派的稿子給斃了。這些人又掌實(shí)權(quán),當(dāng)然不舒服。汪曾祺被打成右派,很大原因在這里。
想回北京,原單位卻不肯接收
張英:難怪兩年后,上面給他摘帽,讓他回來,民間文藝研究會卻不收。
汪朗:因?yàn)槟切┤苏茩?quán),特別是掌了人事權(quán)。汪曾祺對這種人事干部很看不上,什么都不懂,就會拿政治標(biāo)準(zhǔn)打棍子、整人。
當(dāng)時(shí)要提意見時(shí),汪曾祺就提了一些這方面的意見,結(jié)果被打成右派,但深層次原因還是在用稿上。他那時(shí)候名義上算編委,實(shí)際上是執(zhí)行主編,定稿權(quán)基本是他說了算。
張英:那就難怪了,我曾經(jīng)很納悶,都摘帽兩年了,可以回來了,可原單位不收,那就沒辦法了。后來去北京京劇團(tuán),是找關(guān)系去的嗎?
汪朗:必須要找關(guān)系,首先得有一個(gè)接收單位,才能解決戶口的問題。
究竟找的什么關(guān)系,我就說不太清楚了。他的同學(xué)楊毓珉說,當(dāng)時(shí)北京市人事局的一位副局長姓孫,也喜歡寫戲,也知道老頭兒,他們就去找他,他說同意把戶口弄過來,但前提是,有單位接收他。
我印象里,當(dāng)時(shí)汪曾祺想回北京,民間文藝研究會是回不去了,除了北京京劇團(tuán),還有實(shí)驗(yàn)話劇院也在找話劇編劇。汪曾祺接觸過話劇,演過,還給人化過妝,但沒寫過劇本。但那是中央單位,解決戶口可能還不如北京京劇團(tuán)方便,所以最后就到了北京京劇團(tuán)。
當(dāng)上了反動(dòng)學(xué)術(shù)權(quán)威
張英:“文革”時(shí),汪曾祺又被打成反動(dòng)學(xué)術(shù)權(quán)威,這是什么緣故呢?是因?yàn)榧依锏刂魃矸輪幔?/span>
汪朗:地主出身倒不是主要問題,當(dāng)時(shí)主要打擊對象,一個(gè)是黨內(nèi)走資派,一個(gè)是反動(dòng)學(xué)術(shù)權(quán)威,還有一個(gè)可能是地富反壞右。
反動(dòng)學(xué)術(shù)權(quán)威主要是知識分子,不算走資派,因?yàn)闆]有行政職務(wù)。
汪曾祺的主要罪名是幫他們當(dāng)時(shí)的黨委書記寫了一個(gè)聊齋戲。這位黨委書記也是從延安過來的,還挺喜歡搞創(chuàng)作。他開始弄了一個(gè)聊齋戲《小翠》,然后就拉老頭兒一塊寫唱詞、構(gòu)思。戲最早是書記想的,后來書記被打成走資派,汪曾祺幫走資派,就變成反動(dòng)權(quán)威了,把他給捎上了。
這位黨委書記本名叫薛恩厚,后來改成薛今厚,后來又改回去了。改名,因?yàn)檎f“恩厚”顯得太封建了,改成薛今厚,就是厚今薄古了。反正都挺可樂。
這個(gè)戲成了一個(gè)大毒草。怎么是大毒草呢?戲中有一個(gè)傻公子,救了一只狐貍,可他不認(rèn)識狐貍,非說是貓。別人就勸他說,這不是貓,長一條大尾巴,貓哪有大尾巴的?他說這是大尾巴貓。人家又說,你看這狐貍是尖嘴,貓可不是尖嘴啊?
沒想到,這段竟被說成是惡毒攻擊。為什么?說這是惡毒攻擊偉大領(lǐng)袖,大尾巴貓就是大尾巴毛。
這是真事。當(dāng)時(shí)“文化大革命”就是這么給你找罪名的。虧得他們想出來。
張英:后來您父親在北京京劇團(tuán)退休的嗎?
汪朗:是的。他干了好多年,將近70才退。那時(shí)沒那么嚴(yán)格的限制,尤其像他們這樣有高級職稱的。
向吳階平請教腐刑切什么
張英:您父親大學(xué)時(shí)有寫長篇小說《漢武帝》的計(jì)劃,實(shí)現(xiàn)了嗎?
汪朗:沒有。他不是大學(xué)時(shí)有這個(gè)計(jì)劃的,而是挨整時(shí),“四人幫”倒臺后那段時(shí)間,沒事他就翻點(diǎn)東西,覺得漢武帝的性格挺怪異,想從心理分析的角度把他重新認(rèn)識一下。但就這么一說,當(dāng)時(shí)在不同場合,他都說過,好像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還挺當(dāng)回事的,專門幫他弄了一套《史記》《漢書》過來,后來就沒下文了。
張英:要寫的話,這是您爸第一部長篇小說。
汪朗:我覺得他很難寫出這個(gè)長篇小說,因?yàn)樗X得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了,不能胡來,包括當(dāng)時(shí)的典章制度、生活習(xí)俗,包括服裝,包括歷史細(xì)節(jié)等東西太多了,還包括對一些記載怎么看,包括司馬遷的腐刑是怎么回事,這玩意都弄不清楚,你怎么寫?他還找到吳階平去請教,說這腐刑是怎么割,割了什么,這都不清楚。
張英:他還真考究,去做工作準(zhǔn)備。
汪朗:對呀,你不能稀里糊涂地就過去了,要非常具體,他覺得想弄明白太難了,所以只有一些設(shè)想的東西。
汪曾祺在家從沒能把尾巴翹起來
張英:在四種文體中,小說、劇本、散文和評論,他自己最喜歡哪種?
汪朗:我覺得他還是更看重小說。寫劇本屬于職務(wù)行為,他說過,我在京劇團(tuán)端人家飯碗,不能不干這事,所以得寫一兩個(gè)。后來京劇也不景氣,演得不理想,所以興趣不大。
還有一些劇本,比如他寫過一個(gè)電影劇本,寫過一個(gè)歌舞劇,都是人家找上門來約的,他自己主動(dòng)寫的劇本不多,也不能說沒有。除了早期《范進(jìn)中舉》外,其他都和他的工作有關(guān),或者人家約的。而小說全是自己主動(dòng)要寫的,散文就是寫著玩。
張英:在您眼里,您父親他對寫作看重嗎?
汪朗:看重。他是很當(dāng)回事的,一個(gè)是他覺得他這方面還是有兩把刷子的。另外,他很看重發(fā)表以后的影響力和名聲,他說我寫東西不為了錢,但是揚(yáng)名還是想揚(yáng)的。他這方面還是挺當(dāng)回事的。
張英:很多人的文章寫到,汪曾祺對日常生活的熱愛比文學(xué)多,喜歡燒飯做菜,寫作反而沒有那么重要。在文學(xué)上他沒有太多的功利心。
汪朗:這要看怎么說。他確實(shí)不特別在意名利——不能說沒有,但不是一定要怎樣,或者為了這個(gè),我不計(jì)代價(jià)、不擇手段地去鉆營,去爭取,這些都沒有。
因?yàn)槲覀兗覛v來習(xí)慣,就是做飯是他的事,即便他創(chuàng)作欲望最旺盛的時(shí)候,他也從來沒有說,我現(xiàn)在要集中精力寫東西,這事都不干了。沒有,該干的,原來他認(rèn)為是他義務(wù)的事,照干不誤,而且一定要做得好好的。一到周末什么的,早早就琢磨咱們弄點(diǎn)什么吃的,然后一早就出去買菜。他周末不寫東西了。
張英:平時(shí)他也很少像個(gè)職業(yè)作家,說一天八個(gè)小時(shí)寫東西。
汪朗:絕對沒有。所以我們覺得他好像不是太把寫作當(dāng)回事,但他效率很高。他想好了東西,鋪開就寫,寫到該吃飯了就停了,該做飯了就停了。
張英:“文革”剛結(jié)束,好多作家解凍,可以再寫了,大家都覺得要把光陰奪過來,他們的家人說嫁作家很辛苦,基本上不能打擾他,輕聲輕氣供著,他好像跟日常生活沒有關(guān)系。
汪朗:我們家沒有。我們家人,該干什么還得干好,而且,從沒讓他能夠把尾巴翹起來。
晚年總算有了自己的書房
張英:我看過幾篇印象記,汪曾祺寫作,有時(shí)候在飯桌上寫?當(dāng)時(shí)的新聞報(bào)道,后來全家一直住您母親在新華社那邊分的房子,是吧?
汪朗:前期住的都是汪曾祺單位的房子,直到民間文藝研究會時(shí),后來他被打成“右派”了,那邊沒說收房子,但我媽就覺得跟這些人在一塊,或住這個(gè)單位的房子,心里接受不了,就把房子退了。
退完后,找新華社安排房子。那時(shí)新華社的房子挺緊張的,而且你是半道插進(jìn)來要房,所以剛開始,住的是那種中西結(jié)合的四合院門房。門房能有多大?一個(gè)五斗柜,一張雙人床,就滿了。
那時(shí)老頭兒不在家,倆妹妹上幼兒園,我上小學(xué)一年級,如果都回來,就在床外邊搭兩塊木板,大家擠在一張床上。“文革”前,分了一套兩居室的樓房,最多四十平方米。
張英:后來搬到蒲黃榆住,是哪一年的事?
汪朗:我們搬到蒲黃榆時(shí),有他一間書房兼臥室,七八平方米。一張單人床,兩張小沙發(fā),一張寫字臺,一個(gè)小書柜,就滿了,他也挺高興的。
但北京一個(gè)作家,原來在魯迅博物館工作,和我父親挺熟的,來了后覺得我們家太擠了,太寒酸了,國外客人來了都轉(zhuǎn)不開身。其實(shí),也不能說是轉(zhuǎn)不開身,應(yīng)該說也還能湊合。這位作家去找作協(xié)說,能不能幫解決一下?
作協(xié)說方莊好像有他們的房子,給汪曾祺補(bǔ)一套兩居吧。這事?lián)f被他們當(dāng)成一個(gè)政績,跟丁關(guān)根匯報(bào)。丁關(guān)根說,汪曾祺的夫人是新華社的,新華社剛蓋了房子,我跟新華社說說,讓新華社解決吧。可新華社不理他這茬兒。
這是我聽說的。新華社說,按我媽的級別,分的房子已達(dá)標(biāo)了,再要,只能去魯谷,那是他們的小區(qū)。我們還過去看了看魯谷的房子。老頭兒說不去,太遠(yuǎn)了,另外魯谷那離八寶山太近,所以這事就不了了之了。
張英:也就是說,汪曾祺從沒像他同時(shí)期的作家,有那種大書房?
汪朗:后來我們單位分房時(shí),我跟單位說了一下,因?yàn)槲矣蟹址抠Y格,但我愛人單位分的房實(shí)在交不出去。當(dāng)時(shí)分房,先得把舊房交出去,才能給你改善。
我說能不能把我父母住的舊房交給報(bào)社?單位同意了。報(bào)社分的房子大一點(diǎn)。這樣,老頭兒終于有了一間獨(dú)立的書房。
作協(xié)挺過意不去的,說房子沒給你,就弄張大寫字臺,讓他畫畫吧。送的寫字臺。不知道是哪個(gè)頭兒定的,剛定完他就離開了。
張英:如果您父親不離開北京市文聯(lián),住得一定很好。
汪朗:北京市文聯(lián)的房子都還可以,可問題是他關(guān)系在京劇團(tuán),京劇團(tuán)沒錢蓋房子。有一次,文化局分房,要給他解決一下,定在紫竹橋邊兒上,他也不想去,說太亂了,房子也沒有太大。
如果不在京劇團(tuán),按他的級別,房子能好一點(diǎn),退休時(shí)給他定了個(gè)局級待遇。只有退休了,他才知道自己是局級待遇。
張英:這個(gè)局級并沒拿到什么好處。
汪朗:沒有好處。
子女都是自己管好自己
張英:你們后來上大學(xué)到就業(yè),乃至職業(yè)選擇等,老頭有沒有設(shè)計(jì)?
汪朗:從來不管。我們家也怪,覺得你沒本事就干力氣活,也挺好,沒添什么麻煩,也沒搗什么亂。我媽對我插隊(duì)時(shí)的中學(xué)同學(xué),比對我還好。
1972—1973年,中國剛重返聯(lián)合國時(shí),喬冠華帶隊(duì)去美國開會,然后就說,國內(nèi)和國外的英語教學(xué)差距太大,就引進(jìn)了一些當(dāng)代美國的英語教材,其中一本是《英語900句》,都是日常生活用語,學(xué)會了,跟人家說兩句還可以。因?yàn)樵嬉M(jìn),市面上不多。我媽媽是新華社搞外文的,就給我們好幾個(gè)同學(xué),都是準(zhǔn)備上大學(xué)的,都給買了,送給他們,卻沒我的事。
我說我的呢?她就說:我再給你找吧。我不說,她居然想不起。
后來我拿這個(gè)聽美國之音,那時(shí)算是敵臺。但我想,學(xué)外語沒錯(cuò),別的我不聽就完了。
張英:您媽媽是新華社的特稿高級記者,她是寫什么方面的?
汪朗:新華社分得比較細(xì),國內(nèi)部報(bào)道國內(nèi)的事,國際部報(bào)道國外的事。她在對外部,把中國的事向國外傳播。對外部每天都要對外發(fā)時(shí)政之類的稿件,叫大廣播。還有一些專稿,叫特稿,每篇稿都是針對國外相關(guān)的報(bào)刊,給他們投稿。
張英:就是用英文寫稿?
汪朗:對,寫中國的事,但用外文,主要是英文。
張英:您媽媽是西南聯(lián)大外語系畢業(yè)的,在北大當(dāng)過英語老師,很厲害啊。
汪朗:后來老頭去美國,幾次演講稿,都是我媽給他譯成英文。到了那邊,再找人一念就行。他們說是很好的英文,看不出是中國人寫的。
張英:您的職業(yè)是做什么?
汪朗:我是記者。
張英:那你們都受媽媽影響啊。
汪朗:我是誤打誤撞。當(dāng)時(shí)恢復(fù)高考,第一年各地自己出題,當(dāng)時(shí)我在山西當(dāng)工人,初選有了,但最后沒上。第二年全國統(tǒng)一高考,當(dāng)時(shí)瞎報(bào),報(bào)的是北大中文系,結(jié)果給我分到人大新聞系了。這個(gè)系是“文革”中解散后,并入北大中文系,我們那年剛分出來,并不是說我想上新聞系。我媽還說,新聞沒得學(xué),但沒辦法,學(xué)這個(gè)就得干這個(gè)。所以一直在經(jīng)濟(jì)日報(bào)干到退休,小三十年。
張英:你們兄妹都自管自,爹媽也沒幫上什么忙,完全是放養(yǎng)。
汪朗:就看你自己。
后20年他寫作夠勤奮的了
張英:您父親在“文革”后二十年,從1979年到1997年去世,作品很多,但一直沒有寫長篇小說。
汪朗:已經(jīng)很不容易了。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出版他的《全集》大概是四百萬字,我估算了一下,起碼有三百萬字是后二十年寫的,而且基本上是他六十歲以后寫的,按這個(gè)時(shí)間段來說,產(chǎn)量不低了,而且質(zhì)量不低。他還有別的好多事呢,除了給我們做飯,還要寫字、畫畫,還要四處轉(zhuǎn)悠。
張英:還要經(jīng)常接待各地文學(xué)青年。
汪朗:來訪的也多,還出去參加筆會,他也愿意出去,一是有人捧他,另外他轉(zhuǎn)悠轉(zhuǎn)悠,能找點(diǎn)寫作題材。這么一算,老頭兒還是很勤奮的一個(gè)人,原來我們認(rèn)為他松松垮垮的,看不出來他繃得很緊,但實(shí)際上,他寫東西真是不少。看他的全集,小說當(dāng)然時(shí)間就相隔得比較長,散文有時(shí)幾天一篇。
張英:很多人不滿足,覺得汪老為什么不專攻小說呢?
汪朗:可寫的小說題材,他覺得不多。對于現(xiàn)在的東西,他覺得沒有太多把握。寫比較近的人,好多人還活著呢,不太好下筆。他在劇團(tuán)里工作二十多年,接觸不少人,但他寫劇團(tuán)題材的小說很少。
他寫過一個(gè)關(guān)系挺不錯(cuò)的同事,看著挺正面,被寫的那個(gè)人還挺高興,說自己成了小說人物。結(jié)果他閨女看完了,說:“爸,這汪叔叔罵你呢。”老頭兒在骨子里有他自己的看法,也不一味給人家唱贊歌。
他總共只寫過三個(gè)劇團(tuán)的人物,有的開始沒在內(nèi)地發(fā),拿到香港發(fā)了。一寫,都是典型事例,人家一下就知道你寫的是誰,就要對號入座,他覺得壓力太大。
張英:汪先生還是典型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
汪朗:對。他第一次回家,寫了一個(gè)小說,有點(diǎn)真實(shí)事例的基礎(chǔ),里面涉及的領(lǐng)導(dǎo)做派是他自己碰到過的。沒想到,當(dāng)?shù)馗刹烤筒桓闪恕F渲袑懙揭粋€(gè)房管所所長,是一個(gè)造反派,別人就對號入座。實(shí)際上,小說不可能都是真事,可這么一弄,他顧慮就比較大了。
張英:難怪,沒這種插曲,小說估計(jì)產(chǎn)量會大一些。
汪朗:肯定有一些題材可寫的,他自己說過。
不關(guān)注重大事件,只看細(xì)節(jié)性的東西
張英:從兒子的角度看,您父親是一個(gè)什么樣性格的人呢?
汪朗:每個(gè)人的性格都有多個(gè)方面,每個(gè)人看到的只是一個(gè)方面的東西。汪曾祺也是比較多面的一個(gè)人,不太好概括。曠達(dá),好像也到不了那個(gè)程度,也許就是他自己說的,是隨遇而安吧,可能更準(zhǔn)確一點(diǎn)。
他對周邊的人,包括年輕的文學(xué)愛好者和作者,都平等相待,或是以平視的角度去交往。所以好多年輕人跟他的關(guān)系都挺好。
張英:還有當(dāng)時(shí)的很多年輕文學(xué)編輯,比如龍冬他們。
汪朗:他對年輕人都很喜歡,同時(shí)他在骨子里又是很傲的一個(gè)人,特別是對文學(xué)上的事,絕不放棄原則,給你吹喇叭、抬轎子。好就是好,不好我可以不說,但絕不能說好。有些人間世故他還知道,我可以不說,但絕不能無緣無故地吹捧。關(guān)系再好,他在文學(xué)上的標(biāo)準(zhǔn)始終是不放松的。
張英:把鋒芒藏起來。
汪朗:是藏起來的。他當(dāng)然不是用文學(xué)標(biāo)準(zhǔn)來作為交友的標(biāo)準(zhǔn),那就找不著能交往的人了。
張英:他的文學(xué)觀完全來自沈從文嗎?一定要現(xiàn)實(shí)主義,要有原型,言之有物,每個(gè)句子都代表一種藝術(shù)的標(biāo)準(zhǔn)?
汪朗:這主要是自己悟的吧,沈先生給他們講,可能沒這么細(xì)。
張英:比如汪曾祺所有小說都是以小見大,反對宏大話語。
汪朗:我覺得他平常生活關(guān)注的就是這些,他不太關(guān)注重大事件。他感興趣的,就是從小角度去觀察,就是日常的一些細(xì)節(jié)性的東西。這可能跟他從水鄉(xiāng)走出來的經(jīng)歷有關(guān)系。
只承認(rèn)是京派,其他高帽都不收
張英:功成名就后,人們給了汪曾祺很多高帽子,比方說他是時(shí)代的曹雪芹。
汪朗:還有曹雪芹?這還沒聽說過。
他對把他列入京派,他還是能接受的。他原來對京派不太了解,北大編過兩本京派小說選,他一看林徽因、沈從文、廢名都是這派的,就覺得還可以。這些人都是他看重的作家,他原來對京派的來源、發(fā)展不是很了解。
把他列入鄉(xiāng)土派,他不接受。他認(rèn)為打出鄉(xiāng)土派這面旗幟,本身就根源于封閉性,用所謂的鄉(xiāng)土來拒絕外來的現(xiàn)代思想的進(jìn)入,而他不是這樣的人。他從大學(xué)起就接觸西方的現(xiàn)代文學(xué),他當(dāng)時(shí)寫的東西是很歐化的,雖然后來回到現(xiàn)實(shí)主義,回到民族傳統(tǒng),但他的前提是要有一種開放的心態(tài),能接納一切外來的優(yōu)秀因素。在這種前提下,回到現(xiàn)實(shí)主義,而不是排斥和拒絕現(xiàn)代主義的東西。同樣,回到民族傳統(tǒng)的前提,也是要能吸收一切外來的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
張英:那些高帽扔給他,不知道他怎么看?
汪朗:好像沒什么積極評價(jià)。
張英:后來專門有評論汪曾祺的文集,以及博士論文,他說你們不要把我切成幾塊,在那研究我。
汪朗:對,他說我是一條整的活魚,不要把我切零了。切零了也都能說得通,但都不夠全面。他自己也說不太清楚自己,什么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什么是個(gè)儒家。他對自己沒有一個(gè)很清晰的分析和很清晰的定位,他也不愿意做這種事。他覺得有點(diǎn)無聊,我的東西,你喜歡,看就是了,不要把我歸成哪一類人。他自己說他是個(gè)名家,不是大家。
張英:老先生再驕傲,在外面還是很平和的。
汪朗:也對,他確實(shí)不是大家,所謂大家,你要寫出氣勢磅礴的作品,能夠流傳后代,而且深刻尖銳。
張英:不知道他怎么看,后來很多派都把他往自己的派里拉。
汪朗:他也不是很嚴(yán)格,你們說你的,是不是,我心里有數(shù),我也不跟你爭論什么,一定是什么。好像他沒有什么很嚴(yán)格的自我評判的標(biāo)準(zhǔn)。而且那個(gè)時(shí)候,帽子還沒這么多。
張英:這幾年,對汪先生評價(jià)越來越高,基本上就是大師旗手了,要不就是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的曹雪芹了。
汪朗:那就是有點(diǎn)過,好像有點(diǎn)過,我也不敢說。現(xiàn)在也有點(diǎn)“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勁頭吧,找點(diǎn)別人沒說過的話來。要不然你說的都是別人的話,你不就顯示不出來你的水平嗎?是不是準(zhǔn)確,那就不好說了。
汪曾祺的檔案無處尋
張英:汪先生寫的檢查和交代材料,加起來也有二三十萬字了,為什么沒收入全集呢?
汪朗:那個(gè)東西拿到不容易。
張英:你們都看不到嗎?
汪朗:這事說出來,都是個(gè)笑話。小二十年前,陳國華,就是陳徒手,《人有病天知否》那本書的作者,他跟我們說,老頭兒的檔案里有大量的檢查,你們可以看一看。他抄了好多。他是《北京青年報(bào)》的記者,到北京京劇團(tuán)借老頭兒的檔案,就借出來了。現(xiàn)在《北京青年報(bào)》不行了,當(dāng)年人家覺得《北京青年報(bào)》來,還挺榮幸的。后來我們就去了,又查了一下。
張英:沒復(fù)印嗎?
汪朗:人家都拿出來了,突然問,你們跟汪曾祺是什么關(guān)系?我說是他的子女。人家說那不行,檔案別人可以看,子女不能看。我說這里頭有些東西應(yīng)該退還給我們。他說那也不行。已經(jīng)拿出來了,還是被拿走了。人家還專門說了句對不起。后來檔案又送到文化局,我們再去找,也沒找著。現(xiàn)在要查檔案,首先得開證明。
按說二十年以后,檔案應(yīng)該解密,誰都能看,還應(yīng)該把那些檢查都退還給親屬,或者銷毀。當(dāng)然,銷毀了就可惜了。
張英:為什么巴金那時(shí)的所有認(rèn)罪書都交還了?
汪朗:當(dāng)時(shí)有規(guī)定,對檔案進(jìn)行清理,把運(yùn)動(dòng)中的檢查交代都退還給本人,或者銷毀。當(dāng)時(shí)沒人給汪曾祺做這事。現(xiàn)在再找,連規(guī)定都找不著了。
張英:太可惜了,從中很容易看到一個(gè)人的風(fēng)骨。我看陳徒手在書中也提到,汪曾祺從沒咬過別人。
汪朗:他就如實(shí)說這事如何,我也不多說,也沒上綱上線。只說自己的事,只是客觀描述。
張英:他小說也是這個(gè)風(fēng)格,有點(diǎn)像海明威說的零度寫作,只描述,不評價(jià)。
汪朗:有人說,老頭兒的小說風(fēng)格和散文風(fēng)格實(shí)際上還是有區(qū)別的,但也有人說沒區(qū)別。在寫作手法上,可能確有區(qū)別,在小說中,確實(shí)就像你所說的,他從來只是陳述,沒有發(fā)表過任何的觀點(diǎn)性的東西。但是在散文中,他往往直接陳述自己的意見。
他說“八大山人無此霸悍”
張英:您父親后來畫文人畫,是哪個(gè)時(shí)期的事?
汪朗:他小時(shí)候就受到影響,似乎在小學(xué)還是中學(xué),他的畫就已經(jīng)被展覽了。小時(shí)候,他們家還有畫畫的東西,他還刻過圖章,但不是特別專,總之都干過。
上高中、大學(xué)時(shí),他就沒怎么干過了。以后就是下放勞動(dòng)時(shí),畫那個(gè)馬鈴薯圖,那時(shí)他練的那個(gè)水平應(yīng)該還可以。記得我小時(shí)候有一個(gè)裝東西的包裝盒,做得比較細(xì),里頭不知道裝著什么。他在包裝盒上畫菊花,一筆一筆地畫,特別細(xì),能看出來,確實(shí)有點(diǎn)功夫,而且是有觀察的。
再以后,就是“四人幫”倒臺后,清查他的時(shí)候,他天天在單位寫檢查、寫交代,覺得挺郁悶。那時(shí)還有一個(gè)好處,就是回家后就沒人管你了,你還可以罵罵娘、喝點(diǎn)酒,然后就買點(diǎn)紙,還不是宣紙,是黃的,寫字的那種很次的元書紙。也沒有國畫顏料,就拿那個(gè)寫字的毛筆,胡亂涂抹。
老頭兒畫畫是有范本的。畫完后,喝酒喝多了,就寫一個(gè)“八大山人無此霸悍”。我記得特別清楚,然后壓到桌子上面的玻璃板底下。都是那種扭著脖子的鳥,睜著大眼的魚,抒發(fā)他心中的悶氣。
張英:聽說您父親發(fā)明了個(gè)詞——人走茶涼,是這樣嗎?
汪朗:“人一走茶就涼”是他寫的唱詞,這不是什么諺語俗語,而是他創(chuàng)造出來的。情況慢慢好了以后,他高興了,就畫一畫。
后來生活條件也好了,地方也寬敞了一點(diǎn),我們有時(shí)候給他買點(diǎn)最便宜的顏料,他還舍不得用。那時(shí)候畫畫,用墨比較多。
他對繪畫一直有興趣,此前不怎么畫畫時(shí),還拉著我們上故宮看古畫展,我陪他去過,我妹也陪他去過,他看得挺仔細(xì)。他對這個(gè)有興趣。畢加索什么的,也能說幾句。
- 在汪曾祺看來,太次的茶葉只能煮茶葉蛋[2022-02-10]
- 汪曾祺小說的反諷藝術(shù)[2022-02-07]
- 汪曾祺:“人間送小溫”[2022-01-27]
- 汪曾祺的懊悔[2022-01-12]
- 王彬彬:魯迅與現(xiàn)代漢語文學(xué)表達(dá)[2022-01-05]
- 汪曾祺筆下的“食相”與“吃相”[2022-01-04]
- 水流云在——汪曾祺的昆明情結(jié)[2021-12-24]
- 汪曾祺給魯迅作注[2021-1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