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舒劼:“黑暗森林”還是“自由人聯合體”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科幻小說的命運共同體想象
摘 要 科技之于人類共同體的影響既是當前的重要現實,也是中國當代科幻想象的重要主題。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科幻小說中,共同體時常是不動聲色的主角,體現出個體與共同體的辯證關系。這批科幻小說對文明共同體間的關系,主要表現為惡意和善意兩種矛盾的想象模式;而文明間惡意關系的認知又與既有的共同體理論產生了矛盾,即“黑暗森林”與“自由人聯合體”的矛盾。在善與惡兩個端點之間,90年代以來的中國科幻小說還對科技介入人類共同體之后的復雜狀態鋪開多角度的想象。這些小說敘事在呈現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未來走向的關注和憂慮之時,也期盼著更有生命力的批判性想象。
“從根本上看,科幻小說是一種發達的矛盾修飾法,一種現實性的非現實性”,“是根植于這個世界的‘另外的世界’”[1]。科幻小說的想象之花無論如何芬芳馥郁,終究植根于現實的土壤。詹姆遜用以考察科幻小說的“未來考古學”,其方法論核心就是“將我們自己的當下變成某種即將到來的東西的決定性的過去”[2],歷史和未來以當下為中軸折疊起來。未來是擁有無限可能的星辰大海,還是必將趨于某種特定的狀態,科幻小說對此一直保持著高度的熱情和不懈的探尋。科學技術的發展如此深刻地改變了傳統的社會形態,大眾對“現代性”“地球村”“全球化”等名詞早已耳熟能詳,人類在事實上已經成為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2020年初開始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就是個生動的注腳。科技將把作為共同體的人類社會帶往何方?處于全球化發展與變化進程中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科幻小說,其想象已經在追問:如何理解人類作為共同體的存在?如何想象走出地球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狀態?科技是導向馬克思所說的“自由人聯合體”[3]的理想社會建設,還是最終激化人類之間或人類與其他文明間不可調和的沖突?交流合作或不可共存是否構成人類共同體未來前景的兩極?科幻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想象和現實之間構成了怎樣的對話關系?如何保持科幻小說想象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生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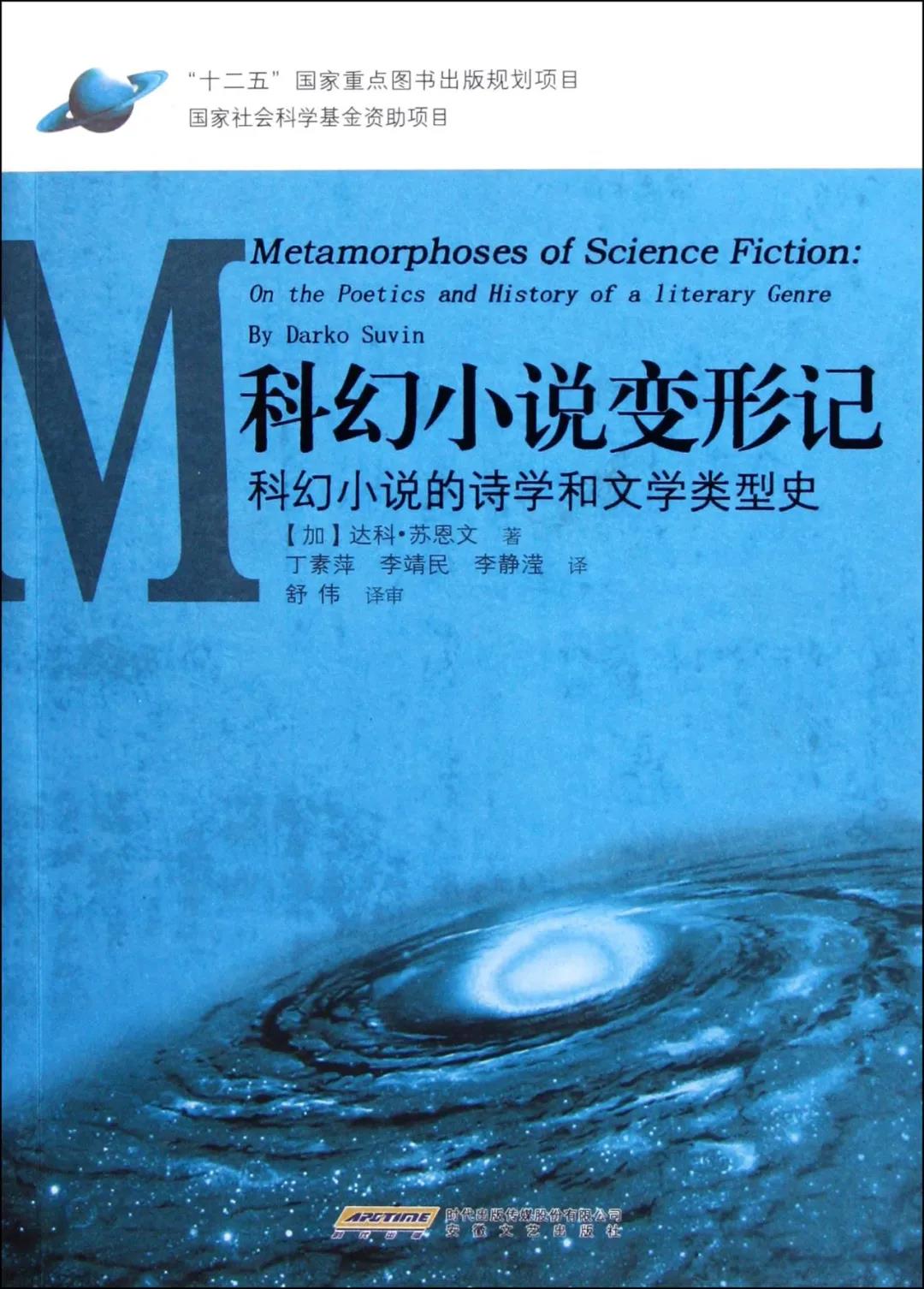
達科·蘇恩文:《科幻小說變形記:科幻小說的詩學和文學類型史》,安徽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
一
問題總是從歷史溯源開始。命運共同體意識并非20世紀90年代的產物,中國科幻小說在晚清萌芽之時,已經擁有強烈且富有時代氣息的家國命運共同體意識。晚清之際,家國有累卵之危,仁人志士憂心如焚,小說正是時代的鏡像。吳趼人的《新石頭記》使復活的賈寶玉親眼目睹清政府的腐敗和侵略者的蠻橫,碧荷館主人的《新紀元》讓“潛水雷”“綠氣炮”“氣球隊”等新式武器幫助中國大敗西方列強,陸士諤的《新野叟曝言》則令中國人征服歐洲、占領月球和木星。這批晚清科幻小說毫不掩飾地展示中西、新舊間的沖突和復興中國的渴望,無暇構想人類聯合為共同體的場景。家國危機是此刻的主角,病毒、地震和外星屠夫還在等候出場。1939年顧均正的《和平之夢》,將對峙雙方置換為美國和影射日本的“極東國”;1942年許地山的《鐵魚底鰓》描寫年已古稀的兵器科學家雷先生在戰火中研制新型潛艇,卻報國無門、為救潛艇資料而落水身亡。新中國成立前的科幻小說,其共同體意識不是想象人類作為共同體存在的可能、方式或危機,而是希冀國人團結救亡。在今天,“共同體”已成為包含地理區域、地域性社會組織、共同情感和互動關系等特征的復雜概念,它通常被描述為兩種類型:一是地域性類型,以村莊、鄰里、社區、城市等地域性社會組織為代表;二是關系性類型,如種族、宗教團體、社團等社會關系與共同情感[4]。從《新石頭記》到《鐵魚底鰓》,這批科幻小說敘事的重心,顯然不在描繪社會學意義上的地域性或關系性共同體的生成。它們所體現出的對共同體的理解,更多是凸顯小說敘事的愛國情懷和民族認同,努力建立作者與讀者間的情感聯盟,實現身份認同和價值認同的共鳴。有研究者指出:“共同目標、身份認同和歸屬感是共同體的基本特征,也是共同體賴以生成的基本要素。”[5]鮑曼則將判斷共同體的標準壓縮到了共識的形成上,共同體“首先是一種精神統合體。要沒有這種特性,根本就不算共同體。共同體的全體成員都會假定,首要的支撐就是共識,至少是達成共識的意愿和潛力”[6]。就此意義而言,這批小說在中國科幻文學史上留下了沾著憤懣和屈辱寫就的“我們”。
新中國的成立,將中國科幻小說帶進了新紀元。借用胡風著名的長詩的標題來形容,“時間開始了”[7]。科幻小說中那個努力將作者和讀者融成一個“我們”的敘事立場還在,但主色調已非屈辱和憂慮。1949—1966年,科幻作品“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輕快而富有發展前景的技術發明,這些發明涵蓋航天、生物技術、交通、氣象操控、電腦、農業、海洋科學、低溫人體科學、醫學等多個科學領域”[8]。普及科學技術、實現美好生活、建設獨立富強的國家,新的科幻小說敘事基調在形成,而批判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是新基調的另一條主線。童恩正在1960年出版的《古峽迷霧》中通過小說人物之口宣告,“我們”永遠不能忘記帝國主義的欺凌。1963年王國忠的《黑龍號失蹤》描繪了深海中日本軍國主義的蠢蠢欲動。憧憬未來的美好生活和警惕敵對勢力的破壞,在1978年后科幻小說的短暫復興中仍攜手同行。葉永烈于1978年出版的《小靈通漫游未來》洋溢著奮發昂揚、自信積極的樂觀主義精神,小說中的“未來市”就是“未來世”。與此同時,童恩正《珊瑚島上的死光》(1978)、王曉達《波》(1979)、劉興詩《美洲來的哥倫布》(1980),延續的則是《古峽迷霧》和《黑龍號失蹤》的主題。這批小說保持著鮮明的政治認同,“我們”是欣欣向榮的新生政權的主人翁、人民政權的保衛者或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解放者,從而加入了與時代政治氛圍相契合的共同體意識生產。
20世紀90年代的科幻小說進入了新的文化語境。隨著蘇聯解體、東歐劇變、鄧小平南方談話發表,中國逐步進入世界市場的競爭,文化交流和知識生產的國際化趨勢越來越明顯,互聯網技術日益深入社會生活,市場經濟開始重構文學場域。歷史的轉折必然投射到文學領域:“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科幻小說最重要的變化是擺脫了科普論、社會現實論,企圖尋求科幻文學本身的獨立存在價值,向科幻本體回歸。”[9]科幻小說的共同體觀念不再天然地依附時代思潮,而共同體已從滕尼斯、涂爾干、韋伯、雷德菲爾德、鮑曼等人的描述中繼續發展,成為包含權力組織、社會網絡、社會資本等多種新元素,具有多種功能的功能性共同體,沒有一個能夠確切涵蓋它各方面特征的統一界定[10]。進入21世紀后,全球化的發展進程日趨復雜,出現了反全球化、去全球化、逆全球化甚至是全球碎片化等種種不同的理解,但人類成為命運共同體的現實境況也愈加明晰。共同體何以可能、如何形成、如何運作,這些問題在加入科學技術的變量后更加令人著迷,充滿問題感的共同體想象正徐徐展開。
二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科幻小說共同體想象發生的新變,根源于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一方面,科學技術使人類大規模交往成為可能,吉登斯用“脫域”一詞說明,社會關系能從地方場景中跳出并實現跨時空重組[11],這使得“形成共識”意義上的共同體生產變得極為活躍。另一方面,科學技術帶來社會生活便捷的同時,可能進一步造成環境風險、恐怖主義、宗教沖突、經濟危機、階級矛盾等問題的加劇。科技發展本身帶來的負面效果,正被現實所證明,這不是哪個超級國家或超級英雄所能單方面解決的。想象人類文明危機及其克服方式,是90年代以來中國科幻小說命運共同體敘事重要的起錨點。
黑暗時刻總是出其不意地降臨,這是科幻想象的特權和特長。外星智慧隨時可以進攻地球并消滅人類,人工智能可能在某個時刻悄無聲息地跨過意識自主的奇點,高致死性傳染病或許毫無征兆地大規模擴散。于是,政府官員、銀行高管、技術專家、超市銷售、市井閑雜的身份差異不再重要,烈性病毒、眼放綠光的機器人和獰笑的外星人不考慮哪個地球人的銀行卡里數額更大。大多數危機的爆發不以人類意愿為準繩,在災難面前,形成有效的共同體無疑是人類增強抵抗能力的最佳途徑。劉慈欣《三體》三部曲在人類將被地外文明徹底消滅的背景中展開敘事,面對技術實力遠超自己的外星文明,人類在漫長的自衛戰中組成了不同形態的共同體,小說實際上可以看作針對外星入侵的一種社會形態反應。人工智能突變的隱患也是科幻想象的常見主題,從機械地接受指令到形成自主意識,人工智能不斷挑戰人之所以為人的屬性,王晉康的《生命之歌》、阿缺的《與機器人同居》、江波的《哪吒》、鮑浩然的《孤島》等都涉及人與人工智能形成命運共同體的可能。烈性傳染病打散后的社會運行在王晉康的《十字》、畢淑敏的《花冠病毒》、燕壘生的《瘟疫》中都得到模擬,這些小說多依靠人物個體的活動描述社會性的“戰疫”,但人物身上又往往集中了個性選擇與群體傾向的辯證關系,此時“不深究個人,就沒有共同體的深度”[12]。更進一步說,共同體是許多科幻小說中不動聲色的主角。

王晉康《生命之歌》
若以《三體》為例,多數讀者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羅輯、葉文潔、章北海、程心、云天明以及維德等人物,或是“黑暗森林”“猜疑鏈”“宇宙社會學”等理論想象,而不會對小說中的ETO(地球三體組織)、PDC(行星防御理事會)、艦隊聯席會議、地球國際、艦隊國際、PIA(行星防御理事會戰略情報局)、未來史學派等各式人類共同體組織留下太深印象。《三體》的忠實擁躉所制作的網絡動漫短篇《我的三體》系列的前三部,可視為《葉文潔傳》《羅輯傳》和《章北海傳》[13],但沒有也不大可能出現《ETO傳》《PDC傳》或《PIA傳》。羅輯、章北海、葉文潔等人物比PDC等共同體組織擁有更為廣闊的情感和性格表現空間,但根本上,主人公們的光彩奪目卻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各種人類共同體組織的塑形。在人類社會滅亡的陰影下,這些官方或非官方的共同體以成員內心的價值共識為基礎,依靠團體的凝聚力,從各方面影響并完成了人物。是誰將羅輯從玩世不恭、把專業等同于混飯吃的平庸學者塑造成了挽救人類命運的英雄?如果英雄的成長離不開自身的愛心與責任感,那么又是誰激發或喚醒了真正的羅輯?是PDC,主導面壁計劃、滿足羅輯所有的現實愿望、讓莊顏去末日等待以徹底激發羅輯潛力的PDC。PDC是什么?一群面目模糊但目標一致的人組成的共同體組織。相同的邏輯也體現在章北海身上。章北海以其堅定卻深藏的人類必敗信念,提出并參加首批“增援未來計劃”、鎖定逃離地球的實施方案、暗殺可能阻礙其目標實現的重要專家、劫持“自然選擇”號星艦逃離太陽系、成立星艦地球以保存人類文明的火種,這一系列行為使章北海成為星艦地球共同體的精神領袖,但這并不能作為共同體塑造章北海的反例。章北海所有的行為,都是“未來史學派”理念的實踐。他的自述很清晰:“我不需要思想鋼印,我是自己信念的主人。這種信念之所以堅定,是因為它不是來自我一個人的智慧。早在三體危機出現之初,父親和我就開始認真思考這場戰爭最基本的問題。漸漸地,父親身邊聚集了一批有著深刻思想的學者,他們包括科學家、政治家和軍事戰略家,他們稱自己為未來史學派……他們所預言的今天的強盛時代,幾乎與現實別無二致,最后,他們也預言了末日之戰中人類的徹底失敗和滅絕。”[14]章北海就是“未來史學派”這個思想共同體集中意志的體現。第三個例子是葉文潔。這位ETO的精神領袖,同樣受制于ETO內部的分化和矛盾。即便是作為ETO的最高統帥,她始終要保持與這個共同體的對話而非簡單地發號施令。而葉文潔之所以成為ETO的領導,又來源于她按下向太空發射地球信息的舉動——一次長期遭受迫害后的爆發,因此真正將地球拋入危險境地的,是那群在特殊年代中習慣將他人置于死地的人,一個隱性、松散卻又能量巨大的觀念共同體。如果還需要第四個例子的話,那就是在PIA計劃下被縮成一個大腦的另一位人類英雄云天明。涉及共同體因素的科幻想象,自然涉及個人與共同體的關系。包括《三體》在內的90年代以來的共同體科幻想象,都遵循這條鐵律:“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5]“人格個體”是“真正的共同體”的主體,“人格個體”只有在“真正的共同體”中才能實現[16],二者形成辯證統一。
三
共同體是時常隱匿于主人公身影中的主角,這較容易為讀者忽略。文明共同體之間如何相處,則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科幻小說命運共同體想象的焦點。包含《三體》在內的眾多文本參與了這一主題的想象。尤其是在地球文明走向宇宙的未來前景中,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升級版”,或者說另一種表現形式的宇宙命運共同體是否有可能實現?王晉康《與吾同在》、韓松《醫院》三部曲、劉慈欣《吞食者》、寶樹《人人都愛查爾斯》《黑暗的終結》《我的高考》和《安琪的行星》、何夕《浮生》、江波《星落》、張冉《大饑之年》和《太陽墜落之時》、分形橙子《贊神的宮殿》、謝云寧《太陽知道答案》、王侃瑜《云霧》、索何夫《出巴別記》、超俠《利維坦之殤》等各有自己的理解。盡管這份名單還可以繼續延長,但這批小說對人類/宇宙命運共同體的想象,集中表現為對文明間關系或惡意或善意的認知模式。在這種簡化關系的想象中,可以看出小說敘事者對人類命運共同體前景的不同理解。

王晉康《與吾同在》
零和!廣袤的宇宙是最好的戰場,從小說到電影再到游戲,星際戰爭的主題早已對受眾的接受心理形成飽和轟炸。在90年代以來中國科幻小說的人類/宇宙命運共同體想象里,將宇宙間文明的惡意沖突推到極致的,首選《三體》。“黑暗森林”,這個建立在小說“宇宙社會學”理論想象之上的概念,以比喻的方式勾勒出未來人類所面對的險惡的宇宙文明環境:宇宙就像暗無天日的森林,任何先暴露自己的文明都將遭到不知來源的、干凈徹底的毀滅性打擊,歌者文明以二向箔隨手抹去整個太陽系就是如此。“黑暗森林”邏輯貫穿了整部小說的想象,人類和其他宇宙文明不可能有和平共處的可能,所有文明在意識到自己身處宇宙文明圈后,最重要的就是小心翼翼地隱藏自己。人類文明開始了戰戰兢兢的時代,“黑暗森林理論對人類文明的影響是極其深刻的:那個篝火余燼旁的孩子,由外向樂觀變得孤僻自閉了”[17]。只有光墓——徹底將自己封鎖起來的技術,或許能向其他文明表明自己絕無外侵的雄心。
《三體》的“黑暗森林”模型擁有許多同行擁躉。索何夫的《出巴別記》將零和狀態歸因于本能:“作為一種天生的掠食者,人類的基因中攜帶著與生俱來的無法抑制的競爭本能……這個種族與另一個文明——無論這個文明與他們有多么的不同——和平共處的概率近乎為零……人類在這個宇宙中最為懼怕的不是天災,不是疾病,甚至也不是他們的同類,而是那些身為‘非我族類’卻像他們一樣能夠思考的存在。”[18]“非我族類”更像是“黑暗森林”理論的簡略版。相比之下,寶樹《安琪的行星》就迂回得多。小說有件動人的愛情敘事的外衣:大勇為安琪在宇宙中購買了一顆行星“ΣX-6470-2”,并將其命名為“安琪之星”,以虛擬技術再造的“安琪之星”景觀打動了被他人拋棄的安琪。到他們的24代后裔勇哲憑借空間擬合技術登上這個行星時,勇哲為向長尾巴的外星姑娘夏麗示愛,不顧“安琪之星”上存在與地球高度相似的文明,而要按照先祖的美好想象來重塑“安琪之星”。“安琪之星”人將為此承受的滅頂之災在勇哲眼里不值一提:“這些徒勞的生物,他們全然不知,自己和整顆行星的命運已經走到了盡頭……至于上面的原生態系統……那只是一些順帶被清除的雜質而已。”[19]《安琪的行星》的特別之處是呈現了一種以愛為名的殺戮,宇宙間高階生命對低階生命的傲慢和冷漠,被“美”和“愛”這種炫目的辭藻所包裹,猶如鉆石的璀璨可能遮掩了礦工的血汗。作為文明共同體間零和關系的補充,寶樹的《時間之墟》還設計了一個每隔20小時左右就重啟一次的時空場,人類間因此爆發無休止的相互殘殺,直至再也無法想象出新的摧殘生命的方式為止。人與人難以結成共識基礎上的共同體,恰如文明間遵循零和邏輯一般。張冉的《大饑之年》似乎想給零和關系一次重新選擇的機會,致命真菌孢子的釋放者安德魯·拉爾森曾給自我立約:從下飛機的一刻起,若第一個對話的人懷有善意就停止釋放真菌。個體對共同體是否能達成的信念,直接影響到共同體的生成。結果這場帶有偶然因素的試驗又必然地失敗了,小說同時暗示,人類和其他生命體之間的關系也可能是零和的。
是否存在非零和的可能?另一批小說傾向于樂觀地看待文明共同體間的關系。宇宙如此浩瀚,生命又總有時限,沒有必要整日你死我活。分形橙子的《贊神的宮殿》正面否定“黑暗森林”,勾勒出類似人類文明導師的外星智慧形象。小說里的拉瑪文明,雖然染有阿瑟·克拉克《與羅摩相會》中羅摩形象的印記,但比冷酷的羅摩文明熱情多了。它們至少將火星改造成第二個地球,賜給人類自救的機會。原因何在?“至少就‘拉瑪’的所作所為來看,宇宙的真實圖景并不是黑暗森林那么簡單……文明最大的敵人不是其他文明,而是險惡的宇宙環境,嚴酷的低溫、真空、星體撞擊、一個超新星的爆發就足以摧毀一個文明,還有我們尚不了解的其他宇宙災變……宇宙本身就是生命和文明最大的敵人。只有建立更廣泛的合作,才能幫助文明更好地生存下去……合作很可能是唯一對抗宇宙的模式。”[20]江波《星落》中的布丁人更是受惠文明眼里善良的神,不僅無意控制或消滅弱小文明,還提供無智慧的星球以保存文明。“文明聚散,是星星間的常事,你無須為此擔心。”[21]布丁文明施惠于人而不求回報,這份灑脫令人神往。善舉多與愛心相隨,謝云寧《太陽知道答案》希望在“愛”的基礎上構建“云網絡”形態的宇宙文明共同體,“不同生命體之間真實的情感交流,亙古以來都是宇宙間微妙而永恒的主題……對于所有發現云網絡的智慧文明,云網絡都歡迎其加入”。小說承認攻擊和爭斗總會出現,“一些心懷鬼胎的種族在成功駁入云網后暴露出貪婪的本性,不斷侵擾別的種族,瘋狂掠奪別族的計算資源,讓云網充斥著艱險與爭斗”,然而“云網中所有文明都必須重新審視自己的提升之路,生命不應只是趨利避害的計算程序”,“云網絡”有干涉文明間沖突的能力,但“是否懂得‘愛’仍是我們評判一個文明高低的首要標準”[22]。如果文明要自我提升,就不可能總甘于蜷縮在“黑暗森林”之中。
四
矛盾如巨鯨般浮出海面,它不僅存在于科幻小說的想象之中,還存在于文本想象和理論闡釋之間。文明間的爾虞我詐、你死我活,的確比充滿善意的互助能演繹出更繁復的波折,然而文學上的精彩沒有資格宣告想象的正確,恰如真善美可能有交集但無法彼此替代。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科幻小說就人類/宇宙命運共同體的可能給出了兩種不可共存的想象,需要注意的是,這種共同體文學想象又與共同體理論推演產生了矛盾。馬克思的“自由人聯合體”、習近平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指向的是與“黑暗森林”迥異的、充滿生機與光明的人類未來。
馬克思將共同體理解為人類進行社會交往的方式,共同體是人類的基本生存方式,也將伴隨著人類發展而變化。只要人的社會屬性不變,人類就總會體現為某種共同體狀態。馬克思在人的狀態由“未異化的局部發展的依賴關系”到“異化的普遍發展的依賴關系”,再到“剝去異化且全面社會化了的依賴關系”的三階段上,對應性地將共同體的歷史形態歸結為“本源共同體”“虛幻共同體”“自由人聯合體”三階段[23]。“自由人聯合體”意味著克服資本主義抽象而虛幻的共同體,意味著將人和人的關系從市場競爭的你死我活狀態中解救出來。《共產黨宣言》強調:“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24]人終將在自由發展的基礎上形成共同體,而不是陷入猜疑、爭斗、殺戮的循環,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性的揭示。站在人類發展新的歷史起點上,習近平提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以求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25],實現人類的共同利益、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馬克思主義及其在21世紀的新發展,提供了有別于從滕尼斯到鮑曼等人的共同體理解。“黑暗森林”式場景在“自由人聯合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的觀照下,逐漸暴露出自身想象的裂縫。
“黑暗森林打擊都有兩個相同的特點:一、隨意的;二、經濟的。”[26]在《三體》的“茶道談話”中,掌握宇宙智慧文明許多秘密的智子,曾如此總結高階文明的攻擊方式。可這兩個特點有明顯的矛盾:徹底的“隨意”是不考慮“經濟”的。智子強調“所謂經濟的,是指只進行最低成本的打擊,用微小低廉的發射物誘發目標星系中的毀滅能量”[27],在本質上,“黑暗森林”打擊是“經濟”限定下的“隨意”。經濟意味著什么?一般意義上,經濟被理解為滿足人類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動,包含對物質和精神的生產、流通、分配、消費諸環節。馬克思指出,經濟范疇“是生產的社會關系的理論表現,即其抽象”[28],“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和消費形式”[29]。沒有脫離人際交互活動的經濟,交流即是選擇。萊昂內爾·羅賓斯曾對經濟學做出一個著名的限定:“經濟科學研究的是人類行為在配置稀缺手段時所表現的形式。”[30]“黑暗森林”打擊的存在本身、尤其是它對“只進行最低成本的打擊”的本質性強調,已經確證了這種打擊必然要遵循特定的經濟規律,從而是某種生產關系基礎上的價值選擇。這與人類的戰爭經驗并無二致。“人類戰爭的發端都是經濟原因,打仗的根本目的都是要爭奪人口、財產和土地資源的控制。不論軍事斗爭的手段怎樣千變萬化,這個根本原因卻是從古至今始終如一。”[31]宇宙間的文明共同體,在根本上仍要遵循人類間構建命運共同體的規律。距離的超遠可以隨著技術能力的提升得到克服,《三體》已經表明,現有科學認為不可變更的自然規律也可能被文明所改造。另外,宇宙雖大但物質總量仍有限度,這與地球資源整體上的有限性也是一致的。將“黑暗森林”打擊推演到底的后果就是宇宙不斷降維,無可挽回地滑向文明的同歸于盡,更何況“低維的資源對高維沒有用”[32]。那么,頻繁發起打擊,對與低階文明同處一個宇宙的高階智慧而言,究竟有什么益處呢?
文明發起的攻擊,總會受到文明之所以成為文明的那些因素的限制。交流、協商、合作,比猜疑、爭斗、毀滅更贏得人心,這是人類文明演化所昭示的道理。馬克思關于世界歷史形成的論斷眾所皆知:“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33]沿著這條路徑,賴特在《非零年代》中提出,人類歷史發展總體朝向“非零和”規則上的日趨復雜的變化:“新科技產生,引發或容許新的、較豐富的非零和互動,接著(基于人性中顯而易見的原因),社會結構跟著演進,實踐這項豐富的新潛能,將非零和互動轉化為正面的綜合,最后使社會的復雜性更為寬廣,也更為深邃……人類的生活終于深植于互相依存的更大更豐富的網絡中。”“從頭到尾,人類的命運就是讓彼此的命運越來越密不可分。”[34]《贊神的宮殿》等“黑暗森林”模式的反對者,就將未來的想象建筑在這種理論的推演上:“人類最開始是通過簡單的血脈組成的家族進行個體合作,眾多的血脈家族組成了更大的部落,部落組成了更大的部落聯盟,文化認同又讓我們組成了國家,國家與國家的合作組成了聯合國,現在我們正走在更緊密的合作這條道路上。而現在,我們知道了還有更大的合作可能,從不同的星球上發展出的不同的文明可以進行更廣泛的合作,共同對抗嚴酷的宇宙。”[35]而鑒于“黑暗森林”打擊最終玉石俱焚的結局,名為“歸零者”的高階文明終于在《三體》的尾聲階段登場,號召各文明將為躲避零和打擊而構建獨立小宇宙的質量還回大宇宙,以避免大坍縮的宇宙末日降臨。“歸零者”試圖重啟宇宙、回到宇宙田園時代的愿望和努力,更像是通過“否定之否定”實現宇宙共同體的實踐。“每個文明的歷程都是這樣:從一個狹小的搖籃世界中覺醒,蹣跚地走出去,飛起來,越飛越快,越飛越遠,最后與宇宙的命運融為一體。”[36]當然,在朝向人類命運共同體或宇宙智慧共同體的航線上,仍是波詭云譎。
五
科技擁有的塑造未來命運共同體的巨大能量無人能忽視,無論對此前景持樂觀或悲觀態度,科技都參與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技術“像法律一樣統治著我們。它不僅塑造著我們的物理世界,也塑造著我們居住和行動的倫理、法律和社會環境”[37]。善意或惡意的文明共同體關系,只是位于想象兩個端點上的極致狀態,善意和惡意之間巨大的空白,留給科技介入社會文明后可能產生的復雜變化。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科幻小說已經注意到,科技介入后的技術統治、智力區隔、人機結合,都影響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生成狀態。相比于未來命運共同體可能與否的整體想象,這些想象的維度更多地關注了人類共同體某種具體的狀態及其隱藏的問題,同時也是對未來共同體建設面臨挑戰的思考。
張冉的《太陽墜落之時》討論了將技術本身作為人類未來社會基礎的可能性。如果徹底地依靠技術來運行社會,就會“創造出一種新的社會結構”,在這個社會里,技術“成為城邦文明之間的等價交換物”,“經濟行為依托于技術發展”,“人人都是城邦技術集合體的組成部分”[38]。懷揣著這個共同體理想的“特里尼蒂”組織最終沒能實現他們的技術烏托邦理想,但毫無疑問,將未來人類發展的重任都放在科技的肩上是一類流行的想象。技術如何成為等價交換物,什么樣的技術能成為等價交換物,此類細節的缺失讓未來共同體的想象黯淡許多。與此同時,技術成為“惡托邦”源泉、形成專制型共同體的擔憂也始終在場。張冉的《以太》中的“手指聊天聚會”組織,以觸覺接觸的方式反抗“以太”技術監控下的共同體社會;超俠的《利維坦之殤》在霍布斯的“利維坦”理念上塑造了一個外御強敵、內控人民的無所不能的巨型機器城市,生活在這個安樂共同體中的代價是自由意志的喪失。技術可否被替代?寶樹的《我的高考》就試圖將智力作為未來共同體的運轉軸心。“新制度是嚴格按照智力區分的等級制度,不同智力階層之間不相互侵害,但是卻擁有不同的政治權限。原來的人類和低階的智力提升者無權進行統治,而必須絕對服從高階者的命令,如同兒童要服從大人。”[39]然而,以智力區隔出階層并施行統治的制度,同樣無法擺脫技術的身影。如果僅僅依靠技術或智力的單方面力量來解決人類命運共同體問題,就必然要簡化共同體建構的復雜性。
將人與機器融為一體的賽博格,正是體現共同體建構復雜性的一片疆場。唐娜·哈拉維指出:“賽博格是一種控制生物體,一種機器和生物體的混合,一種社會現實的生物,也是一種科幻小說的人物。”[40]賽博格攪亂了建立在身體之上的人類感覺經驗和知識系統,“我是誰”及其引發的問題愈加撲朔迷離。順著唐娜·哈拉維的視線,賽博格挑戰穩定的身份認同、突破清晰的邊界意識、引起認識的混亂與沖突。“賽博格神話是有關邊界的逾越、有力的融合和危險的可能性”,“我們幾乎不能期望得到關于反抗和再結合的更有力的神話”[41]。更艱難的境況、更尖銳的追問,才能更真實地面對人類共同體的未來。陳楸帆的《荒潮》,正是包含了賽博格等多種因素在內的未來共同體模擬。小說敘述處處引人生疑:硅嶼的各方人士,根本不在意擺在面前的改善命運的機會;快到21世紀中葉的硅嶼社會,仍保留著宗族制度;數碼科技和虛擬技術極為發達,而巫術和非自然現象同樣大行其道,有批評興趣的讀者在閱讀時可以發現許多文學社會學的介入視角。硅嶼固化成鎮區和村區兩個對抗的空間和階層,叢林社會是硅嶼各方默認的行為準則,外骨骼機器人成為鬼神存在的標志,小米由垃圾人變為賽博格并分裂出“小米0”和“小米1”兩種意識,義體增強軀體的快感生產又重組身份認同,歷史作為敘事的記憶在數據服務的介入下走向消亡,這一切幾乎都在摧毀既有的共識。硅嶼的土地上好像無法眺望真正的“自由人聯合體”的曙光。
歷史總是在克服矛盾中前進,因為未來共同體建構中可能存在的困難而放棄構建共同體的努力,既是理論的怯弱也是想象的偷懶。在一些未來的想象中,文明個體間僅剩下意識或能量的交流,這多少回避了共同體建構的復雜性。何夕的《浮生》認為人的軀體終將消失,生命間的交流僅以能量的形式存在,“合作早已失去意義”[42]。與此類似的是,未經矛盾的克服而直接宣告共同體在未來的實現。如寶樹的《黑暗的終結》描繪八百萬個智慧種族達成了一致、完成了從形體到政權的統一,從而“永遠終結了各種族、文明、智慧體系之間的沖突,再也沒有對資源的爭奪,再也沒有敵意和仇殺,再也沒有陷阱和詭計。宇宙成為了我/們,我/們也成為了宇宙本身”[43]。濃郁的烏托邦更多地反映出愿景,而非對問題的深度認知。歸根結底,該怎樣激發想象未來命運共同體的生命力?
六
必須回到現實的重大問題中來。習近平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旨在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創造人類的美好未來。作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所指向的,正是弊端累累的資本主義全球治理術。“全球資本主義正面臨著一場深層次危機,這場危機既涉及棘手的結構層面,即積累過剩的危機,又涉及政治層面,即合法性或霸權的危機,這場深層次危機幾乎正在成為資本主義統治的普遍危機。”[44]資本邏輯是世間苦難的根源,同樣滲透到未來。寶樹在《人人都愛查爾斯》中突出強調了資本無遠弗屆的力量,依靠腦波傳遞技術吸引了數量龐大的觀眾的查爾斯,其飛行技術、運動裝備都受控于資本的利潤生產。一旦查爾斯想要回歸個人生活,資本的代理人立即發出警告:“這些公司和機構是一個龐大的利益共同體……如果說有一個幕后大老板,那既不是美國政府也不是羅斯柴爾德家族,而是資本本身。你是整個體系中最重要的環節之一,但絕不是獨立的。”[45]查爾斯希望掙脫資本掌控下的虛擬共同體、重回真實生活,只能付出生命的代價。無論是聰明的大腦還是先進的技術,資本都能收編;無論是狂熱的擁戴還是忠誠的癡迷,都可能受制于資本的驅使。資本主導的包括技術與智力在內的諸多因素走向唯利的共謀,給人類未來命運蒙上巨大的陰影。尤為重要的是,“盡管遇到了嚴重的挑戰和存在普遍的玩世不恭,但沒有其他任何世界觀達到接近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意識形態力量或實際成就的程度”[46]。資本主義早已擬就一套自我神話的劇本,如塞壬的歌聲般迷魅而危險。
科幻小說的未來共同體想象,必須能跟得上資本主義編寫神話的想象力,更應當警惕極具變革性能量的科技被資本所收編后,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產生的異化以及這種異化過程中同步生產的意識形態幻象。《荒潮》警告說:“那個標榜自由、民主、平等的社會,排異與歧視以更加隱蔽虛偽的方式進行。”[47]這種警惕不主張退回到自然時代,而要關注科技發展對人類社會的影響,重拾批判的武器,追問“觀念從何而來,又為誰服務”,無論它是有意識或是無意識[48]。進入21世紀以來,科技已經充分展示了其改變世界的能力,以大數據、互聯網、物聯網、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新一輪信息技術不斷突破,人類的思維和行為都處于變化的進程中,共同體建構的變數也在驟然增多。是在發展中迎接更多的構建新共同體的挑戰,還是安于既有的穩定的小共同體生活?劉維佳在《高塔下的小鎮》中就設置了這樣一組共同體發展時所面臨的矛盾:在自動電磁大炮保護下過了三百年衣食無憂的生活,卻與外界隔絕的小鎮居民,是選擇危機重重的前行之途,還是安于現狀?女主人公水晶在目睹了黑鷹部落為發展而進攻小鎮卻被電磁大炮屠殺殆盡后,仍然跨出電磁大炮的保護圈,是因為她堅信只有超越和進化才孕育著希望。“現代共同體構建肩負著一項重大使命:實現對于傳統的‘共同體’和‘社會’概念的批判超越——即通過非自然手段建立包容性聯系,實現大范圍的個體有機整合。只有通過這種超越,一個取代舊有聯系網絡、融合整個人類社會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出現才成為可能。”[49]馬克思主義的復興,也是批判精神的復興。“只要資本主義制度還存在一天,馬克思主義就不會消亡。”[50]馬克思主義描繪的共產主義前景,并不是對人類未來的細筆精描。“共產主義存在于人們抵制資本主義、爭取自主空間的每一處……存在于對可替代選擇的希冀中,體現在人們與資源、所有權、財富、知識、食物、住房、社會保障、自主決定、平等、參與、表達、健康、準入權等各種貧困類型的斗爭之中。”[51]在種族、階層、性別等維度上,需要跨過的共同體溝壑還有很多。為共同體建構而斗爭,恰是科幻小說想象未來命運共同體的生命力所在,也為科幻敘事從“實然”描繪到“應然”想象提供了最好的武器。
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在真正的共同體的條件下,各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并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己的自由。”[52]自由與和諧的統一將在未來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實現,而科幻敘事必然卷入這漫長而又復雜的過程之中,宛如人類邁向星辰大海。那就讓批判性的想象從當下再次出發吧,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這里是羅陀斯,就在這里跳躍吧!這里有玫瑰花,就在這里跳舞吧!”[53]
注釋
[1] 達科·蘇恩文:《科幻小說變形記:科幻小說的詩學和文學類型史》“英文原版序”,丁素萍等譯,安徽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頁。
[2] 弗里德里克·詹姆遜:《未來考古學:烏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說》,吳靜譯,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379頁。
[3] “自由人聯合體”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重要概念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了“自由人聯合體”的概念(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頁)。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又形容這是一種“更高級的、以每一個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馬克思:《資本論》,《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83頁)。
[4][10] 李慧鳳、蔡旭昶:《 “共同體”概念的演變、應用與公民社會》,《學術月刊》2010年第6期。
[5] 張志旻、趙世奎等:《共同體的界定、內涵及其生成——共同體研究綜述》,《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10年第10期。
[6] 齊格蒙特·鮑曼:《社會學之思》,李康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44頁。
[7] 《胡風的詩——〈時間開始了! 〉及〈獄中詩草〉》,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頁。
[8] 吳巖:《十七年科幻小說創作綜述(1950—1966)》,姚義賢、王衛英主編:《百年中國科幻小說精品賞析》第1冊,科學普及出版社2017年版,第184頁。
[9] 楊鵬:《科幻類型學》,福建少年兒童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頁。
[11] 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田禾譯,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頁。
[12] 殷企平:《華茲華斯筆下的深度共同體》,《杭州師范大學學報》2015年第4期。
[13] 張七:《從〈三體〉到〈章北海傳〉》,《北京晚報》2020年3月25日。
[14] 劉慈欣:《三體II·黑暗森林》,重慶出版社2008年版,第353—354頁。
[15] 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1頁。
[16] 侯才:《馬克思的“個體”和“共同體”概念》,《哲學研究》2012年第1期。
[17][26][27][32][36] 劉慈欣:《三體III·死神永生》,重慶出版社2010年版,第79頁,第221頁,第221頁,第205頁,第509頁。
[18] 索何夫:《出巴別記》,全球華語科幻星云獎組委會編:《金陵十二區》,萬卷出版公司2019年版,第166—167頁。
[19] 寶樹:《安琪的行星》,《時間外史》,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249—252頁。
[20][35] 分形橙子:《贊神的宮殿》,程婧波等:《冷湖II·宿主》,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472—473頁,第473頁。
[21] 江波:《星落》,全球華語科幻星云獎組委會編:《再見哆啦A夢》,萬卷出版公司2019年版,第150頁。
[22] 謝云寧:《太陽知道答案》,全球華語科幻星云獎組委會編:《成都往事》,萬卷出版公司2019年版,第268、265、269、279、269頁。
[23] 徐斌、鞏永丹:《馬克思共同體理論的歷史邏輯及其當代表現》,《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9年第2期。
[24]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3頁。
[25] 習近平:《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的演講》,《人民日報》2017年1月20日。
[28]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2頁。
[29] 馬克思:《馬克思致帕維爾·瓦西里耶維奇·安年科夫》,《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2—43頁。
[30] 萊昂內爾·羅賓斯:《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朱泱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19頁。
[31] 徐焰:《戰爭與經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頁。
[33][52]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0—541頁,第571頁。
[34] 羅伯特·賴特:《非零年代:人類命運的邏輯》“前言”,李淑珺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255頁。
[37] 希拉·賈薩諾夫:《發明的倫理:技術與人類未來》,尚智叢、田喜騰、田甲樂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7頁。
[38] 張冉:《太陽墜落之時》,全球華語科幻星云獎組委會編:《太陽墜落之時》,萬卷出版公司2019年版,第71頁。
[39] 寶樹:《我的高考》,《太陽墜落之時》,第254—255頁。
[40][41] 唐娜·哈拉維:《類人猿、賽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陳靜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14頁,第325、327頁。
[42] 何夕:《浮生》,《再見哆啦A夢》,第212頁。
[43] 寶樹:《黑暗的終結》,《時間外史》,第62頁。
[44] 威廉·I. 羅賓遜:《全球資本主義危機與21世紀法西斯主義:超越特朗普的炒作》,趙慶杰譯,《國外理論動態》2019年第11期。
[45] 寶樹:《人人都愛查爾斯》,《金陵十二區》,第252頁。
[46] 斯克萊爾:《資本主義全球化及其替代方案》,梁光嚴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382頁。
[47] 陳楸帆:《荒潮》,上海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234頁。
[48] 戴維·麥克萊倫:《馬克思以后的馬克思主義》,李智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72頁。
[49] 劉偉、王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視閾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管理世界》2019年第3期。
[50] 特里·伊格爾頓:《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李楊、任文科、鄭義譯,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7頁。
[51]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文森特·莫斯可:《導論:馬克思歸來》,張韻譯,福克斯、莫斯可主編:《馬克思歸來》上卷,傳播驛站工作坊譯、校,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5頁。
[53]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74頁。
作者單位:福建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 杜學文:劉慈欣科幻小說的思想資源[2022-02-15]
- 《三體》英文版續約再創新紀錄 以近800萬續約美出版社 [2022-01-10]
- 人工智能科幻敘事的三種時間想象[2021-12-22]
- 《三體》之外,中國科幻文學找到生存法則了嗎[2021-12-14]
- “難產”的《三體》“復活”了 [2021-12-13]
- 宋剛:日本社會與華人科幻文學[2021-12-03]
- 等了又等之后,我們期待什么樣的中國科幻“名片” [2021-11-26]
- 等了又等之后,我們期待什么樣的中國科幻“名片”[2021-1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