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文君:科學與人文張力之下的敘事 ——以劉慈欣《三體》系列為中心
一
2007年,《三體》出版后,劉慈欣與江曉原有過一次廣為人知的對話。劉慈欣聲稱自己是個“瘋狂的技術主義者”,他堅信“技術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江曉原據此認為劉慈欣“是科學主義者”,但江曉原認為科學并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譬如“人生的目的”。劉慈欣的回答是:“科學可以讓我不去找人生的目的,譬如說,利用科學的手段把大腦中尋找終極目的這個欲望消除。”(1)
劉慈欣在這次對話中提到了正在創作的小說內容,“假如造出這樣一臺機器來,但是不直接控制你的思想,你想得到什么思想,就自己來拿”。后來我們知道,他指的就是《三體》第二部中面壁人比爾·希恩斯的“思想鋼印”。劉慈欣在現場和江曉原做了“為了人類文明存續下去是否吃人”的思想實驗,在《黑暗森林》中,他將此安排成了“青銅時代”號艦隊成員在“黑暗戰役”之后的真實選擇。江曉原向劉慈欣發問:“在中國的科幻作家中,你可以說是另類的,因為其他人大多數都去表現反科學主義的東西,你卻堅信科學帶來的好處和光明,然而你又被認為是最成功的,這是什么原因?”劉慈欣回答:“正因為我表現出一種冷酷的但又是冷靜的理性。而這種理性是合理的。你選擇的是人性,而我選擇的是生存,讀者認同了我的這種選擇。套用康德的一句話:‘敬畏頭頂的星空,但對心中的道德不以為然’。”(2)
引用作家的傳記資料用以闡釋作品是需要謹慎的,即便是夫子自道,其權威性和準確性也需要辨析和界定。2018年,劉慈欣在另一場對話中,說自己“不算是科學主義者。因為我覺得作為一個寫科幻小說的人,應該讓自己的世界觀處于一種飄忽不定的狀態。如果有太明確、太堅定的世界觀的話,寫出一個作品來是不好看的。因為科幻小說它本來就是表現一種人面對宇宙的迷茫”。(3)
作為類型文學的一種,科幻小說有其文體自身的規定性,“天然”要展現“科技”的力量。但劉慈欣在《三體》系列作品中,整體性地思考人類文明命運的敘事企圖清晰可辨,因此動用的思想資源必然非常復雜。必須看到,他在敘事中,一邊凸顯科學技術成為決定文明生死存亡的力量,一邊也始終讓人文的力量在場生效。第二部《黑暗森林》中,羅輯的內在動機是對妻女的愛,他的愛人莊顏是其小說創作時擬想的“夢中人”化身,兩人定情的地點是盧浮宮,在那幅文藝復興的象征物《蒙娜麗莎》前面。第三部《死神永生》中,那位被眾多讀者詬病的程心,卻被小說家一直保護著存活到“宇宙的盡頭”,留下了敘事文本《時間之外的往事》作為人類文明存在過的記錄……
與其去逼問“大劉本意”,不如認真觀察小說提供的紛繁多姿的“思想景觀”。誕生在21世紀初的這三部作品,在世界范圍內引發了廣泛的興趣,獲得巨大肯定,因為它構成映射當下人類文明困境的“鏡域”。進入21世紀20年代,人類處在人文與科技的張力拉扯之中,這是最為重要的現實之一。我們的人文學者開始研究人如何逐步“喪失了主體性”,如何從“機器”帶來的“理性荒誕中突圍”,厘定“人學是文學”。(4)但我們能夠看到直接呈現這一張力的敘事文本并不多,《三體》系列小說,應該是個罕見的例外。劉慈欣讓科學與人文兩種向度的力量在他的“敘事實驗室”中,形成了具有巨大不確定性的耦合力場,間接指向了一個重大且頗具現實性的問題:當人——個人乃至人類——作為意義生成的來源開始變得可疑之后,敘事該怎么辦?

小說《三體》書影
二
人成為意義之源,是人文主義得以確立之后發生的。在此之前,無論東方還是西方,在各自的文化體系中,人的意義是由某種超越力量賦予的。無論是作為神的選民,還是天地之間的“一才”,人在不同的“宇宙故事”中占據一個位置,且因為承擔了那個位置賦予自己的使命,因而獲得了意義。無論這個使命是讓“神的道行在地上猶如行在天上”,是篤行教義進入天國,還是“奉天承運”統一六合,是“致君堯舜上”,抑或只是春種秋收傳宗接代。
進入現代社會之后,無論意識形態和文化形態有著怎樣的不同,人文主義思想已經成為人類通約的文明共識:人擁有自由意志,人是道德主體,人同時也是藝術、市場、政治的主體,人是一切的出發點和目的。自然,人也成為現代敘事的意義生成的根源。雖然人文主義思想在發展過程中產生了各種分化,這個“人”,可能是指第一人稱單數的“我”,也即個人;也可能是指第一人稱復數的“我們”,作為歷史主體的“人民”。現代敘事分別在“我”和“我們”的身上生成意義。
人文主義思想的這一勝利,與現代科學與理性的興起是同時的。某種意義上,科學進步與理性崛起有力支持了人獲得“大自然的主人與所有者”的地位,也為以“人”作為價值標準的人文主義思想掃清了道路。我們曾經以為:科學處理的是與“物”相關的問題,生成描述事實的各種知識;人文處理的是與“我”相關的問題,生成關于人與人以及人與世界的各種關系及意義。我們可以讓科學的歸科學,人文的歸人文,這顯然是一種誤解。
科學塑造了人的認知觀念,帶來了海量的知識,尤其到了20世紀,知識與知識之間的學科壁壘越來越高,人們因此變得更加“盲目”,既“無法看清世界的整體,又無法看清自身”,掉進了海德格爾所謂的“對存在的遺忘”那樣的狀態。胡塞爾在1935年發表演講,認為歐洲科學造成了“歐洲人性危機”,這個“危機”可以一直追責到伽利略、笛卡爾那里。
米蘭·昆德拉談及胡塞爾的這次演講時說:“將這一如此嚴峻地看待現代的觀點看作是一種簡單的控訴會很幼稚,我倒認為兩位偉大的哲學家(指胡塞爾與海德格爾)指出了這一時代的雙重性:既墮落,又進步。”(5)昆德拉是小說家,他認為“現代的奠基人不光是笛卡爾,還有塞萬提斯”,“現代小說從現代的初期開始,小說就一直忠誠地陪伴著人類。它也受到‘認知激情’(被胡塞爾看作是歐洲精神之精髓)的驅使,去探索人的具體生活,保護這一具體生活逃過‘對存在的遺忘’,讓小說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6)
自現代以來,敘事從各個層面充當著人性的呵護者和捍衛者,這里的敘事不僅指昆德拉談及的以展現存在復雜性和人的可能性為使命的作為藝術的小說,即我們通常所謂的嚴肅文學,而且也包括各種大眾文化敘事,如各種類型小說,影視敘事等。但隨著時代的發展,我們發現在人文主義大框架內完成意義生成,變得越來越困難,也越來越無力。機械復制時代,越來越“貧乏”的經驗使得人這個意義之源呈現出“枯竭”的態勢,世界和人都被科學和技術實質性地改變了,尤其是信息技術和生物科學的發展,把“人何以為人”這樣的根本性問題,推到了敘事者的面前。
但人文主義原則依然頗為有力地約束著我們的敘事。科幻敘事是可以完成某種“越界”實驗的理想場域,但事實上我們收獲的卻是大量“反科學主義”的作品,有對人性的批判,但更多的是對技術“越界”的恐懼,敘事給出的可以依賴的對抗性力量,還是人類自身。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電影敘事中“人與非人”的“戰爭”想象,如《黑客帝國》三部曲、《逃出克隆島》《AI》等,最終都是一曲人的頌歌:因為人有愛、忠誠、勇敢、尊嚴、主體性、自由意志……
科學雖然沒有替代人文成為意義的基礎,但科學思維卻對人文思想構成了制約和限制,開始動搖這一基礎。以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經典偵探小說《東方列車謀殺案》的三次電影改編為例:1974年版的設定與原著基本一致,據說是克里斯蒂生前看過最為認可的電影改編,波羅的憤怒在于自己遭受了愚弄,12人陪審團的“形式”改變了血親復仇的性質,謀殺成為審判,最后道德和智力握手言和,波羅給出了一絲釋然的微笑;2010年版劇集中,波羅天人交戰,在“不可殺人”的宗教戒律、“法律的信念一旦崩塌,文明社會將無棲身之所”的堅持和“正義復仇”之間無法抉擇,最后面色冷峻的波羅在沉默中緊緊攥著自己的念珠,而殺人者則有充分的自省與道德邊界——不能因為要掩蓋秘密而再次殺人;2017年版電影中,波羅在揭秘之后,毫不困難地做出了選擇,因為他看到的不是陪審團,也不是“復仇者”,而是“病人”,他們需要的“不是懲罰,而是治療”。(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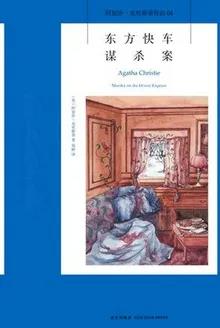
小說《東方快車謀殺案》書影
從這個例子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技術理性對于人文精神的入侵。敘事從完全信任“人”的情感和道德判斷,到認知到人的有限性而陷入自我掙扎,最后我們發現,原來科學真的可以“讓問題消失”:PTSD(創傷后應激障礙)構成了對戕害行為的動力闡釋,這使得敘事毫無意義,如同“抑郁癥”會消解敘事中一切悲傷的思想價值與審美價值。
80多年前胡塞爾敏銳地發現科學把世界變成了一個簡單的、科技與數學探索的對象,引發了“歐洲人性危機”;40多年前昆德拉還認為可以信賴“偉大的歐洲小說的傳統”,杰出的敘事里有著對抗“簡化”的力量;到了21世紀,面對徹底被科技“祛魅”的世界,就連人文學科本身,都開始略帶不安卻難掩興奮地擁抱數字技術了:“算法”出版詩集,介入文學批評,“數字人文”作為一種新的研究方法對傳統人文研究發起了全方位挑戰。(8)
本該最具思想生產力的嚴肅文學,似乎還陷在碎片化的個人經驗泥潭里,拽著文化沖突的藤葛探出頭來,呼吸一下后現代虛無的悲涼之霧,看著萬馬奔騰的現實,一籌莫展。這種朝向自我和微小化的趨勢,也出現在科幻小說這樣的類型文學創作中,那些宏大的“太空歌劇”,誕生也都幾十年了。嚴鋒說劉慈欣“竟以太空史詩的方式重返歷史的現場”,“在當今這個微小化、朋克化和奇幻化的世界科幻文壇,相當不與時俱進”。(9)
劉慈欣的異質性不只表現在將自己的科幻敘事嵌入了真實的歷史時空,同時又延展到了宇宙盡頭,建立了恒星際的“社會學”,更具價值的是他放棄了很多敘事者都有意無意遵循的“政治正確”,以一個“零道德”的宇宙作為實驗空間,整體性地審視現代以來的人文思想,重新討論人的位置和價值生成。
三
第一部《三體》的敘事設定中,小說時間與真實歷史時間是同構的: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21世紀初。小說的整體架構是偵探小說,中文版全書分為36個章節,以警察史強所代表的地球官方力量偵破物理學家自殺之謎案進入故事,以“科學邊界”成員物理學家汪淼介入“三體”游戲進而加入ETO(地球三體組織)從而破獲這一組織謎案作為主線索,葉文潔和伊文思的往事是以回憶的形式進行插敘,輔以紅岸基地揭秘密檔案這樣的拼貼文本補充信息。《三體》英文版在結構上做了一些調整,分為三部分:“寂靜的春天”“三體”與“人類的落日”。(10)除了將插敘部分內容前置作為序曲性質的第一部分,其余內容一致,并未改變偵探小說所規定的信息釋放原則。
無論在中文版中作為插敘,還是英文版中作為序曲的第一部分,《三體》對“文革”的描寫,營造的都是圖景式的“歷史感”而非真正的歷史書寫。我們當然不能苛求劉慈欣在科幻小說中進行深入的中國當代史書寫,“文革”在《三體》中呈現為降臨在個體身上的社會性災難,這恰好對應了我們通用描寫“文革”的語匯“十年浩劫”。這一無法追責、無人懺悔的災難,成為葉文潔對人類絕望的直接原因。隨后,經濟發展帶來的生態災難與“冷戰”格局因核武器帶來的“末日”威脅,使得“人的本質”被葉文潔定義為“丑惡與瘋狂”。
對人類本質的思考,使葉文潔陷入了深重的精神危機。她首先面臨的,是一種奉獻目標的缺失,她曾是個理想主義者,需要將自己的才華奉獻給一個偉大的目標,現在卻發現,自己以前做的一切都全無意義,以后也不能有什么有意義的追求。這種心態發展下去,她漸漸覺得這個世界是那樣的陌生,她不屬于這里,這種精神上的流浪感,殘酷地折磨著她……(11)
創傷性經歷與意義感缺失,是類型敘事中“大反派”誕生的經典原因。無論敘事者賦予此類角色怎樣的性格特征和行為呈現,可能是囂張瘋狂也可能冷峻隱忍,但對其精神世界的定性都是扭曲、病態的,由此滋生的邪惡驅使其犯下“反社會”甚至“反人類”的罪行,最后通過設定懺悔或懲罰性情節來完成意義生成。劉慈欣的敘事拋開了這個人文主義框架,給了葉文潔這個“科學女性”完全不同的設定:“拒絕忘卻”,“用理性的目光直視那些傷害了她的瘋狂與偏執”。不僅如此,劉慈欣還讓她把自己的思考放在了古今中外的哲學和歷史的經典著作里去進行衡量和判斷,從而完成了自覺且理性的選擇。(12)
當“人”不能成為意義之源,葉文潔回到了“神”,向想象的“他者”和超越性力量求助。來自四光年外的一絲信號,使她再度擁有了理想——將宇宙中更高文明引入人類社會。她判斷文明高低的標準簡單粗糙:技術水平等于文明程度。葉文潔做出的“超級背叛”,是當代敘事中少有的對人文立場的徹底背離。但離開人文立場之后,葉文潔的立足之地卻是混合著基督教末日救贖、紅衛兵造反、納粹軍國主義和恐怖主義氣息的ETO(地球三體組織)。劉慈欣顯然并不認為這些“思想資源”是有價值的選擇,但作為敘事者,他對葉文潔的處理非常特別,他小心地維護著葉文潔的“體面”,這是一種懷著特殊的尊重和理解的“懸置”。這一點對比那位ETO的實際創立者和操控者伊文思的情節設定可以看得更為清晰。這位“物種共產主義”者,不只反對人類中心主義,而是直接把人類看成了地球上需要消滅的“害蟲”,劉慈欣毫不留情地讓他在“古箏行動”中被切成三截,死無全尸了。
否定顯然是更容易的選擇。但劉慈欣始終沒讓葉文潔說出一句帶著懺悔甚至自我否定的話,葉文潔被捕后,坦白了曾經殺人的罪行及所了解的三體方面的信息,更是平靜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擁有跨越星際的技術能力、科學昌明的三體世界,必然擁有更高級的文明和道德水準。審訊者問她:“你認為這個結論,本身科學嗎?”葉文潔沒有回答。此處劉慈欣讓審訊者“冒昧地揣測”了一下葉文潔的思想來源,其父親深受祖父科學救國思想的影響,而她又深受父親的影響。葉文潔不為人察覺地嘆息了一聲,回答:“我不知道。”(13)在獲悉了“三體世界”的真相之后,葉文潔更加沉默。
這份沉默里有著敘事者有意為之且內蘊復雜的“懸置”。正如埃科所說,偵探小說在所有的敘事模式中最具“形而上”意義,“哲學(精神分析也一樣)的基礎問題和偵探小說是同一個,誰之錯?”(14)
偵探小說的結尾,人物固然可以“死不認錯”,作者卻不可以不給出判斷。但劉慈欣沒有讓這個判斷輕易落下來。他甚至在“尾聲”中安排了雷達峰、紅岸遺址、夕陽如血云海浸染這樣優美、壯麗的背景,讓暮年的葉文潔遠眺云層下面的齊家屯——人性的美好與溫暖在這個小村莊里曾把她冰原般的心融化出了一汪水,讓她意味深長地完成了一次宣告:“這是人類的落日……”
這樣的敘事設計很難在人文主義的框架內生成確定的意義,反而在立場騰挪的縫隙間造成錯綜的張力,構成了一個敞開的思考空間,懸置給出的不是陳腐的答案,而是一系列嶄新的問題:人類文明的基礎原則,是否該變一變?如何變?我們能信賴的力量和改變的目的是什么?
四
第一部《三體》中拋出的問題,在第二部《黑暗森林》和第三部《死神永生》中,劉慈欣以“毀天滅地”為代價,進行了徹底而全面的實驗。
《黑暗森林》從敘事的角度來看,采用的是我們最為熟悉的個人英雄成長史的模式。小說的設定進入了未來時間,以“應激”狀態的人類社會為大背景,男主人公羅輯,一個虛無的個人主義者,有著小布爾喬亞的多愁善感與玩世不恭相混雜的氣質,隨著敘事展開,在外界壓力和內在情感的合力驅動下,他靠著對“黑暗森林法則”的參悟,以個人生命為骰子,把兩個星系文明中的所有生命,放在了“宇宙的賭桌”上,最終建立起了威懾平衡,從而暫時拯救了“三體”危機之下的人類,成為救世英雄,并且迎來了與妻子女兒的團聚。
在《黑暗森林》中,劉慈欣用兩類誕生于這段未來時間的“新人類”繼續著第一部中的叩問。第一種新人類是“二次文藝復興”之后的人類主體。“三體”危機爆發之后,人類經歷了在戰備高壓之下經濟萎縮民生艱難的“大低谷”,人口銳減至公元時代的一半,人類領悟到應該“給歲月以文明,而不是給文明以歲月”,“活在當下”帶來了技術的進步和文化的繁榮。“末日之戰”來臨之前,劉慈欣描摹了“新人類”沉浸在夜郎自大的進步幻覺和文化優越感中,還戲謔地通過來自公元世紀的冬眠者之口,把準備接納三體人進入人類社會的“陽光計劃”推行者叫作“東郭族”。一位“東郭族”議員躲避著反對者投來的西紅柿,一邊堅持演講:
我請大家注意,這是第二次文藝復興后的人文主義的時代,這個時代對各個種族的生命和文明給予最大的尊重,你們就沐浴在這個時代的陽光中!……這個原則不僅在憲法和法律上得到確認,更重要的是得到了所有人發自內心的一致認同……陽光計劃不是慈善事業,是文明人類對自身價值的一次確認和體現!(15)
接下去,劉慈欣便在小說中用“強互作用力”技術鑄造的“水滴”,將這個脆弱的“人文主義時代”擊得粉碎,“陽光”新人類陷入了導致社會失序的精神崩潰與末日癲狂之中。
另一種新人類則與之相反,這些少數的“例外”,是由于章北海驅艦“叛逃”、丁儀的先見之明而從“水滴”屠殺下幸存,后來組成“星艦地球”的艦隊成員,他們在爭奪生存資源中互相殘殺,勝出者成為太空“黑暗懷抱中哺育出”的“黑暗的新人類”,但“黑暗是生命和文明之母”。(16)也正是這部分“星艦地球”上的“黑暗新人類”,將人類文明延續到了宇宙的盡頭。
劉慈欣無情嘲諷了信奉人文主義的“陽光新人類”在精神上的“幼態持續”,但也沒將他的英雄羅輯放進生存至上的“黑暗新人類”行列中。羅輯手握葉文潔轉交的“人類勝利的鑰匙”,在與妻女別離后的孤寂里獨自“面壁”,飽受誤解、詆毀和傷害,最終成長為“偉大戰士”,既有宇宙公理賦予的“霹靂手段”,又懷著人文主義的“菩薩心腸”,只手扶起了孩子般挨打后只會倒地大哭的“陽光”新人類社會。《黑暗森林》的結尾,一家團圓的羅輯與最初向葉文潔發出警告的三體人對話,表示愿意為“愛”冒險,“我有一個夢,也許有一天,燦爛的陽光可以照進黑暗森林”。(17)
前兩部構成了敘事上的完整性,劉慈欣通過羅輯這個人物,某種意義上回答了第一部通過葉文潔拋出的問題。但這個回答顯然抒情性大于思想性,如同羅輯建立的“威懾平衡”一樣,“愛的力量”生效,完全依賴個體英雄的人格特質。于是在后來得以完成的第三部中,劉慈欣進行了更進一步的思想實驗。
第三部《死神永生》有著“史詩”敘事的架構,將近50萬字的規模,分為六部分,扉頁是紀年對照表,幾個主要角色程心、云天明、維德所占篇幅都相對有限,劉慈欣把敘事重點放在了宇宙圖景的描繪和更多帶著明顯思想實驗性質的極端情境的設計上。羅輯兼而有之的“霹靂手段”與“菩薩心腸”,在第三部里被分別賦予了維德和程心,前者的有效性遭到了后者一次又一次地破壞。
在劉慈欣的敘事設定中,人類社會始終處在一種夸張的幼稚狀態,膚淺、脆弱,自以為是且無比自戀。三體世界在向人類輸出技術的同時,也輸出了模仿人類文化藝術的作品,人類將此現象稱為“文化反射”。三體世界的反射文化甚至“取代了在頹廢中失去活力的地球本土文化,在學者中成為新的文化思想資源和美學理念的源泉”,(18)對著“鏡子”顧影自憐的人類顯然忘記了,這短暫而虛假的美好,不過是“威懾平衡”庇護下的“幻影”;也忘記了,被迫轉向后的三體第一艦隊,正在必死的絕境中堅忍地等著求生的機會。
張維迎在分析人類非理性“陷阱”時指出:決策需要信息,但大部分決策信息是不完備的,存在著缺失。特別是,越是重大的、一次性的決策,信息缺失越嚴重。這就是哈耶克講的“無知”(Ignorance)……無知使得決策變得非常不容易,而更大的麻煩是,許多人不僅不知道自己的無知,甚至認為自己無所不知,而結果就出現了哈耶克所講的“致命的自負”(Fatal conceit)。致命的自負常常導致災難性的決策。(19)
人類這次導致“地球失落”的更換執劍人的決策,并非三體人“欺騙”的計謀得逞,更本質上是人類有意無意“自欺”的結果。在《三體》三部曲中,也有少數的清醒智者,譬如苦心孤詣的“獨立面壁者”章北海駕駛“自然選擇”號“叛逃”,物理學家丁儀讓“量子”號與“青銅時代”號提前進入“深海”狀態,他們之所以在關鍵時刻做出了正確的決定,不是因為他們比別人擁有更多的信息,而是因為他們對自己的“無知”有著足夠的警惕與明智的判斷。
在劉慈欣設計的“零道德”宇宙中,人的各種有限性被一再放大,人文主義精神被折射為“愛的童話”成為生存的最大障礙。然而被人類選擇或者裹挾的“愛的化身”的程心,雖然“一錯再錯”,但被敘事者保護到了宇宙盡頭,愛人且被人愛,洞悉宇宙無比黑暗的真相之后,依然愿意為新宇宙誕生而犧牲自己可以安享的“小宇宙”。這顯然是一個更具思想廣度的回應。雖然不是答案,卻指出了方向,人類文明只有在更為寬廣的思想框架下,才有可能完成更新和發展。
五
劉慈欣在為《三體》英文版寫的后記里回憶了自己少時在故鄉河南農村的經歷,他坦言并不是要通過自己的小說批評現實,而更想把科學講述的關于宇宙和萬物的瑰麗詩篇用敘事“翻譯”給大眾,不過他接著又說:
但是,我無法逃避現實,就好像我不能離開自己的影子一樣。現實在我們每個人身上烙上了難以磨滅的印記。生活在任何時代,人們身上總會套上那個時代隱形的桎梏,而我只能戴著自己的鐐銬跳舞。在科幻小說中,人類經常作為一種整體來被描寫。而在這本書中,一個名為“人類”的人遭遇了一場災難。面對存在和湮滅,他表露的一切毫無疑問都可以在我經歷過的現實中找到根源。科幻小說的奧妙在于,在假想的世界設定中,它可以將那些在我們現實中邪惡和黑暗的事物變得正當和光明,而反之亦然。這部書以及兩部續集旨在于此。但是,不管現實如何被想象扭曲,歸根結底它還在那里。(20)
成功的敘事作品一定具有廣闊的闡釋空間,但我認為劉慈欣最值得敬佩的一點是,作為罕見的例外,直面了今天最大的現實:科學與人文的張力使得人類文明的基礎框架正在扭曲開裂。科學技術并不是人文精神的“敵人”,它只是把一個沒有目的的宇宙放在了人文面前,強迫它講述一個新的“宇宙故事”,生產出新的對于人類有效且有力量的“意義”。
通過上文對于《三體》系列作品的敘事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到劉慈欣雖然挪動了“人”作為唯一意義之源的位置,通過設置力量相反的敘事“暗物質”,凸顯、放大了人的種種有限性,如果對客觀世界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缺乏深刻的洞見,人文主義很可能是具有“腐蝕性”的,但他并沒有放棄人文精神,始終把它當作人類珍貴的文明成就,期待著它能與新的思想資源的產生耦合,完成更新、超越和重生。
相比之下,沉浸在個人話語營造的“主體性幻覺”中的嚴肅文學,顯然與今天最大的現實產生了距離。科學與人文對于人類來講,都是無比重要也無比珍貴的成就,每一點進步都來之不易。原本人類左手執黑,右手執白,在下兩盤棋,但棋至中盤,不斷延展的兩個棋局混在了一起。我們習慣依賴的思想資源正在失去闡釋能力和對人的影響力,這是今天整個人類社會——無論生活在哪個文化場域中——的敘事者,都不得不面對的現實難題。人類文明走到了需要自我更新的歷史節點,直面這一現實的敘事,必須更具想象力、創造性和思想生產能力。
注釋:
(1)(2)劉慈欣、江曉原:《人類為什么還值得拯救》,《新發現》2007年第11期。
(3)劉慈欣、潘石屹:《人類正活在技術的安樂窩里》,引自https://finance.sina.com.cn/china/2018-10-12/doc-ihmhafir1878673.shtml。
(4)黃平:《人學是文學:人工智能寫作與算法治理》,《小說評論》2010年第5期。
(5)〔捷克〕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第5頁,董強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
(6)〔捷克〕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第6頁,董強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
(7)這三部根據克里斯蒂原著改編的影視劇分別是:1974年英國G.W.Films 2.EMI Films Ltd出品的電影《東方列車謀殺案》;2010年英國ITV出品的系列劇集《大偵探波羅》中的同名劇集;2017年,二十世紀福克斯公司出品的同名電影。
(8)邵燕君等:《數字與文學的對話——“數字人文規范對傳統文學研究方法的挑戰”研討會紀要》,《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年第5期。
(9)嚴鋒:《心事浩渺連廣宇:〈死神永生〉序言》,劉慈欣:《死神永生》,第3頁,重慶,重慶出版社,2010。
(10)Cixin Liu,The Three-Body Problem,Translated by Ken Liu,NewYork,Tom Doherty Associates,LLC,2014,p.8.文中引文為筆者翻譯。
(11)(12)劉慈欣:《三體》,第201、200頁,重慶,重慶出版社,2008。
(13)劉慈欣:《三體》,第261頁,重慶,重慶出版社,2008。
(14)〔意〕翁貝托·埃科:《玫瑰的名字》,第55頁,沈萼梅、劉錫榮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
(15)(16)(17)劉慈欣:《黑暗森林》,第358、423、470頁,重慶,重慶出版社,2008。
(18)劉慈欣:《死神永生》,第104頁,重慶,重慶出版社,2010。
(19)張維迎:《不可高估理性的力量》,《讀書》2020年第10期。
(20)Cixin Liu,The Three-Body Problem,Translated by Ken Liu,NewYork,Tom Doherty Associates,LLC,2014,p.668。文中引文為筆者翻譯。
- 杜學文:劉慈欣科幻小說的思想資源[2022-02-15]
- 《三體》英文版續約再創新紀錄 以近800萬續約美出版社 [2022-01-10]
- 人工智能科幻敘事的三種時間想象[2021-12-22]
- 《三體》之外,中國科幻文學找到生存法則了嗎[2021-12-14]
- “難產”的《三體》“復活”了 [2021-12-13]
- 宋剛:日本社會與華人科幻文學[2021-12-03]
- 等了又等之后,我們期待什么樣的中國科幻“名片” [2021-11-26]
- 等了又等之后,我們期待什么樣的中國科幻“名片”[2021-1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