閆作雷:《三體》中的“樸素主義社會(huì)”與“最初的人”

閆作雷,北京大學(xué)文學(xué)博士,現(xiàn)任教于中央民族大學(xué)文學(xué)院,主要從事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發(fā)表論文多篇。
《三體》中的人類未來(lái)社會(huì),其實(shí)是當(dāng)下某些人宣稱的終結(jié)了歷史的社會(huì)的延伸,然而在宇宙文明之戰(zhàn)中,這個(gè)“美麗新世界”的文明法則成為人類生存 延續(xù)的障礙。《三體》通過(guò)設(shè)置地球與三體世界的生死戰(zhàn),直達(dá)人類“最后的社會(huì)”。在自然狀態(tài)的宇宙中,“最后的社會(huì)”中的“最后的人”如何應(yīng)對(duì)這場(chǎng)生存危機(jī)?基于此,《三體》從宇宙視角審視人類文明,揭示現(xiàn)代性弊病的同時(shí),試圖超克“最后的社會(huì)”“最后的人”。
“地球往事”三部曲設(shè)想的“最后的社會(huì)”,具有宮崎市定所謂的“文明主義社會(huì)”的特征,它導(dǎo)致了一種爛熟的文明病。在與三體世界的對(duì)比中,在對(duì)人類“最后之覺(jué)悟”的描繪中,《三體》勾勒了一個(gè)“樸素主義社會(huì)”的輪廓,以及“睜眼看宇宙”、具有強(qiáng)烈斗爭(zhēng)意志的“最初的人”的形象。引入“樸素主義”,不是使其與“文明主義”截然對(duì)立,而是帶來(lái)反思“現(xiàn)代社會(huì)”的契機(jī)。
一、科技與道德
《三體》要上演這出社會(huì)實(shí)驗(yàn)的戲劇,必須跳出人類文明自身的經(jīng)驗(yàn)。只有將人類的“文明主義社會(huì)”置于自然狀態(tài)的宇宙中,才能在危機(jī)時(shí)刻暴露人類文明的弱點(diǎn),讓“最后的社會(huì)”“最后的人”的局限一覽無(wú)余。而要做到這一切,必須先破除普遍主義的宇宙道德觀,因?yàn)橐粋€(gè)可以結(jié)束自然狀態(tài)的人道主義宇宙,仍不過(guò)是人類文明自我想象的延伸。
《三體》是從葉文潔的故事開始的,但若僅從她的遭遇來(lái)看,類似故事在新時(shí)期初期的科幻中已有不少。比如《三體》后記中提到的《月光島》。讀過(guò)《月光島》會(huì)發(fā)現(xiàn),兩部小說(shuō)女主人公的經(jīng)歷幾乎完全一樣。《月光島》的故事同樣發(fā)生在1960年代末。主人公孟薇是一位大學(xué)教授的女兒,父親被誣為間諜隔離審查,母親因此心臟病發(fā)作去世,她本人也被考上的大學(xué)拒收,無(wú)奈之下跳海輕生;后被梅生救活并與之相戀,但卻因家庭背景連累了梅生。小說(shuō)最后,絕望的女主人公跟著月光島上的外星人,“自由的天狼星人”,離開地球飛往天狼星。與葉文潔一樣,與外星人的接觸使孟薇獲得了從地球之外審視人類、人性的視角,她深深同意天狼星人對(duì)地球人的評(píng)價(jià):“在我們看來(lái),地球人還未最終脫離動(dòng)物的狀態(tài),野蠻!自私!褊狹!虛偽!怯懦!殘暴!粗野!”在離別之際,孟薇已認(rèn)同天狼星人的道德和價(jià)值觀,并在精神上將自己作為天狼星的一員,在給梅生的永別信中寫道:我將永遠(yuǎn)“離開你們的地球,到那個(gè)遙遠(yuǎn)的星球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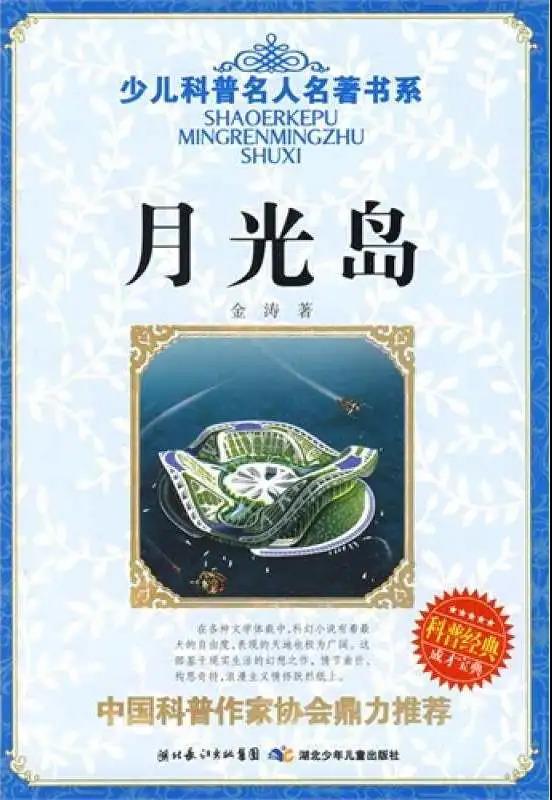
《月光島》
發(fā)表于1980年的《月光島》[1]提供的通過(guò)對(duì)外星人的想象和向往來(lái)擺脫人類危機(jī)、治愈同類人施予的傷痛的嘗試,在當(dāng)時(shí)其他科幻中也能找到。比如一篇小說(shuō)寫地球不再適宜居住,人類的太空飛船在茫茫宇宙中找到一顆存在智慧文明的瑪雅星,這顆星球科技發(fā)達(dá),沒(méi)有壓迫、剝削和不幸,“到處是繁榮昌盛的景象”。當(dāng)?shù)厍蚴拐呦颥斞磐醣磉_(dá)移民的想法時(shí),得到的回答居然是:“沒(méi)問(wèn)題,沒(méi)問(wèn)題!這事包在我身上!”[2]另一篇小說(shuō)寫遙遠(yuǎn)的SZ1350星球人極富同情心,專門派UFO來(lái)地球搭救那些陷入絕境之人。SZ1350星球人仿佛救世主、正義之神[3]。確實(shí),如劉慈欣所說(shuō),新時(shí)期初期的科幻小說(shuō),“外星人都以慈眉善目的形象出現(xiàn),以天父般的仁慈和寬容,指引著人類這群迷途的羔羊。金濤的《月光島》中,外星人撫慰著人類受傷的心靈” [4]。
今天已很容易發(fā)現(xiàn)這些科幻中的文化政治寓言。外星人通常以金發(fā)碧眼的西方人形象出現(xiàn),“飛離地球”無(wú)不是離開中國(guó)、移民到更“先進(jìn)”文明的隱喻。在冷戰(zhàn)松動(dòng)的背景下,新時(shí)期初期的人道主義思潮、人性論從地球擴(kuò)展到了全宇宙。而當(dāng)充斥叢林法則的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到來(lái)時(shí),這一美好想象只能土崩瓦解,1980年代言情小說(shuō)中的“白蓮花”紛紛讓位給新世紀(jì)之后的“黑蓮花” [5]。《三體》中的黑暗森林法則也正是這個(gè)新時(shí)代現(xiàn)實(shí)的折射。
葉文潔的故事在《月光島》中已初露端倪,孟薇再向前走一步就是葉文潔。然而,劉慈欣并不是要重復(fù)書寫“傷痕科幻”的故事,相反,正是要與《月光島》等科幻小說(shuō)對(duì)話。《三體》通過(guò)反思葉文潔的思想和選擇,打破宇宙人道主義的幻想,發(fā)出“劉慈欣之問(wèn)”:“如果存在外星文明,那么宇宙中有共同的道德準(zhǔn)則嗎?往小處說(shuō),這是科幻迷很感興趣的一個(gè)問(wèn)題;往大處說(shuō),它可能關(guān)乎人類文明的生死存亡。” [6] 進(jìn)而重審科技與道德的關(guān)系。事實(shí)上,支撐新時(shí)期宇宙共同道德觀念的另一個(gè)重要想法,是一個(gè)文明的道德水平與其科技發(fā)展程度成正比。
劉慈欣打碎普遍主義宇宙道德觀的起點(diǎn),即是展現(xiàn)葉文潔思想行為的可怕后果。葉文潔對(duì)人類徹底絕望的原因是“文革”傷痛、黑暗人性及生態(tài)災(zāi)難。值得注意的是,葉文潔回復(fù)三體人并邀請(qǐng)其占領(lǐng)地球的時(shí)間是1979年,此時(shí)葉哲泰已獲平反,她本人也即將回清華大學(xué)教書,但她“拒絕忘卻”,繼續(xù)用“理性的目光”審視“那些傷害了她的瘋狂和偏執(zhí)”[7](1,200),她要三個(gè)已淪落到社會(huì)底層的前紅衛(wèi)兵懺悔道歉,不接受她們借用的電影《楓》的解釋。恰恰在這個(gè)“人性復(fù)歸”時(shí)刻,她精心策劃謀殺了“紅岸”政委雷志成,而且不惜讓她無(wú)辜的丈夫一起陪葬,這與她母親背叛葉哲泰沒(méi)多大區(qū)別;她關(guān)于人類文明需外力介入的執(zhí)念,與她妹妹葉文雪對(duì)理想主義的堅(jiān)守也大同小異。說(shuō)到底,葉文潔仍是一個(gè)理想主義者[8],她的精神結(jié)構(gòu)是那個(gè)時(shí)代形塑的,“需要將自己的才華貢獻(xiàn)給一個(gè)偉大的目標(biāo)”(1,201)。意志頑強(qiáng)、科技發(fā)達(dá)的三體世界的出現(xiàn),對(duì)于她,仿佛意義失落的“潘曉”一下子找到了替代性的價(jià)值目標(biāo)。“冷靜、毫不動(dòng)感情地做了(指殺害雷志成與楊衛(wèi)寧)。我找到了能夠?yàn)橹I(xiàn)身的事業(yè),付出的代價(jià),不管是自己的還是別人的,都不在乎。”(1,216)那些“別人”中也包括讓她感受到溫暖的人們,如她生楊冬時(shí)照料她的齊家屯的樸實(shí)百姓。這同樣也是一種“瘋狂和偏執(zhí)”。受到失去“人性”傷害的葉文潔,變本加厲地照搬了曾傷害過(guò)她的那些行為方式。葉文潔對(duì)三體人幻想的自然延伸即是人權(quán)高于主權(quán)。“三體”游戲玩家聚會(huì),討論的重要話題就是人類社會(huì)的主權(quán)與人權(quán)問(wèn)題,如果贊同西班牙殖民者介入“黑暗的”阿茲特克帝國(guó),就會(huì)被地球三體組織(ETO)接納為同志。這是ETO成員的基本共識(shí)。但反諷的是,作為精神領(lǐng)袖的葉文潔根本無(wú)法管控組織的分裂,拯救派和降臨派復(fù)制了“文革”時(shí)期紅衛(wèi)兵組織的發(fā)展邏輯,出現(xiàn)了嚴(yán)重的分歧和斗爭(zhēng)。降臨派對(duì)拯救派一些成員進(jìn)行肉體消滅,為了迎接三體人主持的最后審判,其下設(shè)的“環(huán)境分支”專門制造“環(huán)境災(zāi)難”,“生物和醫(yī)療分支”專門制造“濫用抗菌素災(zāi)難”(1,184~185),至此已完全背離環(huán)保主義和“物種共產(chǎn)主義”的初衷。即使溫和一些的葉文潔,也同樣相信宇宙正義和普遍的宇宙道德,相信三體世界的人道主義光輝將照亮地球的黑暗,拯救人類于水火。在她那里,科學(xué)意味著德行,科技并非中立的“事實(shí)”,而是一套價(jià)值觀念:
審問(wèn)者:你為什么對(duì)其(三體人)抱有那樣的期望,認(rèn)為它們能夠改造和完善人類社會(huì)呢?
葉文潔:如果他們能夠跨越星際來(lái)到我們的世界,說(shuō)明他們的科學(xué)已經(jīng)發(fā)展到相當(dāng)?shù)母叨龋粋€(gè)科學(xué)如此昌明的社會(huì),必然擁有更高的文明和道德水準(zhǔn)。
審問(wèn)者:你認(rèn)為這個(gè)結(jié)論本身科學(xué)嗎? 葉文潔:......(1,260~261)
作為“事實(shí)”的科學(xué)同時(shí)也是“價(jià)值”之源,這個(gè)觀念并不新鮮,它在近代科學(xué)誕生時(shí)期的思想家和現(xiàn)代落后國(guó)家的人們那里非常常見。培根(1561—1626)設(shè)想的科學(xué)烏托邦“本色列”的終極目的是在全世界收集、傳播科學(xué)之“光”,其科學(xué)廟“所羅門之宮”的規(guī)章儀式類似于宗教,在這里,發(fā)明家享有圣徒的榮譽(yù),科學(xué)促進(jìn)繁榮,也是德行之基[9]。圣西門(1760—1825)主張未來(lái)社會(huì)應(yīng)建立以萬(wàn)有引力為基礎(chǔ)的科學(xué)宗教[10],以牛頓代替耶穌行使上帝的精神權(quán)力,讓牛頓“教導(dǎo)和命令一切行星上的居民”,同時(shí)以“牛頓協(xié)會(huì)”代替羅馬教廷[11]。1920年代發(fā)生在中國(guó)的“科玄之爭(zhēng)”中的科學(xué)派,比如吳稚暉、唐鉞等,皆認(rèn)為科學(xué)可提升人類公德[12],產(chǎn)生“大我”,導(dǎo)向“人類大公”[13],這些看法都或隱或顯將科學(xué)昌明程度與 社會(huì)道德水平相聯(lián)系。
與繼承了上述觀念的新時(shí)期科幻相比,“地球往事”三部曲展現(xiàn)了一個(gè)零道德的宇宙,科技與文明體的道德不存在正比例關(guān)系。葉文潔最終對(duì)宇宙中科技與道德的關(guān)系有了全新領(lǐng)悟,并在女兒墓前把宇宙社會(huì)學(xué)公理告訴了羅輯。葉文潔的很多觀念來(lái)自新時(shí)期,但在最后一刻,葉文潔超越了孟薇,超越了自我,甚至超越了1980年代。另外,《三體》對(duì)ETO成員的年齡有過(guò)一次說(shuō)明,ETO成員主要是中老年社會(huì)精英,年輕人非常少(1,168)。或許,在叢林社會(huì)中野蠻生長(zhǎng)起來(lái)的年輕人,有著拒斥童話般宇宙人道主義的潛意識(shí)[14]。出生于1980年前后的羅輯,這個(gè)公元世紀(jì)的年輕人,一個(gè)學(xué)術(shù)混混,即將開啟其“明心見性”(吳飛的用語(yǔ))的未來(lái)之旅。
二、樸素與文明
三體世界對(duì)地球的入侵,終結(jié)了普遍主義的宇宙道德觀。地球被置于宇宙的黑暗森林中,一個(gè)不可能擺脫自然狀態(tài)的叢林。人類“最后的社會(huì)”中的“最后的人”被迫迎接末日之戰(zhàn),與三體世界對(duì)決。
面對(duì)整個(gè)文明的生死存亡,人類應(yīng)該采取什么樣的社會(huì)形態(tài)以整體應(yīng)對(duì)危機(jī),個(gè)人應(yīng)葆有怎樣的精神狀態(tài),以及怎樣處理個(gè)人與集體、民主與集中的關(guān)系,應(yīng)該是首要議題,畢竟地球處于緊急狀態(tài)。《三體》第一、二部也曾涉及對(duì)人類未來(lái)社會(huì)形態(tài)的想象。比如ET0成員潘寒基于環(huán)保理念和“溫和技術(shù)”,設(shè)想并付諸實(shí)踐的“新農(nóng)業(yè)社會(huì)”——“中華田園”。但隨著ETO被剿滅,該社團(tuán)不復(fù)存在。再如雷迪亞茲為對(duì)抗資本主義,并吸取社會(huì)主義社會(huì)的教訓(xùn),在委內(nèi)瑞拉建立的“二十一世紀(jì)社會(huì)主義”,“南美洲各個(gè)國(guó)家紛紛仿效,一時(shí)間,社會(huì)主義在南美已呈燎原之勢(shì)”(2,84)。“二十一世紀(jì)社會(huì)主義”,從《三體》對(duì)未來(lái)社會(huì)的設(shè)定看,應(yīng)消失于“大低谷”之后。同時(shí),小說(shuō)懸置了中國(guó)的社會(huì)形態(tài)在未來(lái)幾百年中的潛在可能。而危機(jī)初期的“技術(shù)公有化運(yùn)動(dòng)”慘遭失敗,“它使人們認(rèn)識(shí)到,即使在毀滅性的三體危機(jī)面前,人類大同仍是一個(gè)遙遠(yuǎn)的夢(mèng)想”(2,31)。“戰(zhàn)時(shí)經(jīng)濟(jì)大轉(zhuǎn)型”產(chǎn)生了帶有軍事色彩的社會(huì),導(dǎo)致了“大低谷”。這樣,劉慈欣便堵死了人類未來(lái)社會(huì)形態(tài)多元化的可能,只保留了唯一一種社會(huì)形態(tài)。此社會(huì)形態(tài)即“高度民主文明的高福利社會(huì)”(3,217)。自“大低谷”結(jié)束到掩體紀(jì)元300多年,人類生活在這樣一個(gè)“文明主義社會(huì)”中,文藝復(fù)興、啟蒙運(yùn)動(dòng)提倡的人文主義原則得到徹底實(shí)行。這個(gè)歷史終結(jié)處的人類社會(huì),崛起于危機(jī)紀(jì)元后期,鼎盛于威懾紀(jì)元,衰落于掩體紀(jì)元。危機(jī)紀(jì)元后期的信條是“給歲月以文明,而不是給文明以歲月”(2,309)。這個(gè)基于私有制的“美麗新世界”曾一度讓羅輯“淚流滿面”,但在末日戰(zhàn)役中證明不過(guò)是不堪一擊的花瓶。“威懾紀(jì)元彌漫著自由和懶散的享樂(lè)主義”(3,238),“文明主義社會(huì)” 發(fā)展到極致,“愛(ài)”是這個(gè)社會(huì)最可貴品質(zhì)。文藝的美學(xué)風(fēng)格是“一種從未有過(guò)的溫馨的寧?kù)o和樂(lè)觀”,批判性、革命性藝術(shù)消失得無(wú)影無(wú)蹤(3,102~103)。《三體》以公元男人的視角,稱其為沒(méi)有“男人”的女性化時(shí)代。
作為人類社會(huì)的對(duì)比,小說(shuō)也寫到與地球文明接觸后,三體世界發(fā)生的變化。總體來(lái)說(shuō),三體世界更具歷史連續(xù)性。以地球時(shí)間算,三體世界從收到地球信息的1975年到被光子摧毀的2275年(廣播紀(jì)元5年),300年間經(jīng)歷了兩個(gè)階段:威懾紀(jì)元之前的“高科技+專制社會(huì)+本土文化”階段,之后的因與地球和平交往而產(chǎn)生的“高科技+不明社會(huì)形態(tài)+混合文化”階段。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思想透明的三體人學(xué)會(huì)了地球人的欺騙和計(jì)謀。人類社會(huì)面對(duì)危機(jī)制訂了令人眼花繚亂的各種計(jì)劃,而學(xué)會(huì)了地球人謀略的三體人的計(jì)劃,小說(shuō)并未正面描寫。《三體》的基本設(shè)定是:地球人懼怕三體世界的高科技,三體人則懼怕人類文化。人類一直有一種文化優(yōu)越感,三體世界對(duì)地球“人文主義”這個(gè)最可怕的武器,一直是防范的。三體人認(rèn)識(shí)到,“文明主義”可以瓦解三體,但同樣可以摧毀人類自身,依據(jù)這個(gè)認(rèn)識(shí),三體世界實(shí)際上也制訂了針對(duì)地球“文明主義社會(huì)”的計(jì)劃。于是,“樸素主義”與“文明主義”的競(jìng)爭(zhēng)在兩大文明間展開。
最明顯的莫過(guò)于三體世界的“反射文化”計(jì)劃。1379號(hào)監(jiān)聽員對(duì)地球文明的向往,讓三體的“宣傳執(zhí)政官”意識(shí)到,“地球文明在三體世界是很有殺傷力的,對(duì)我們的人民來(lái)說(shuō),那是來(lái)自天堂的圣樂(lè)。地球人的人文思想會(huì)使很多三體人走上精神歧途”(1,282),所以三體元首制定了嚴(yán)格限制地球信息流入的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地球文明對(duì)于三體高層和曾經(jīng)的三體人來(lái)說(shuō)并無(wú)新意,因?yàn)樽杂擅裰鞯奈拿髦髁x社會(huì)在三體世界也曾存在過(guò):“你向往的那種文明在三體世界也存在過(guò),它們有過(guò)民主自由的社會(huì),也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chǎn),你能看到的只是極小一部分,大部分都被封存禁閱了。”(1,268)因這種文明在宇宙中的脆弱性,三體世界摒棄了這一社會(huì)形態(tài)。所以對(duì)三體人來(lái)說(shuō),如果想要這種社會(huì),無(wú)須自外輸入,只需將自身封存的遺產(chǎn)敞開就可以了。
因此可以肯定,威懾紀(jì)元時(shí)代,三體世界接受地球文化有一定的欺騙性;反向輸入到地球的“反射文化”(三體人依據(jù)人文主義原則創(chuàng)作的文藝作品)正是三體宣傳部門的計(jì)謀,目的是麻痹地球人,而他們自己對(duì)這種文化一直是有保留的。三體世界確實(shí)接納了部分人類價(jià)值觀,思想自由促進(jìn)了科學(xué)進(jìn)步。這或許是真的,但至于說(shuō)三體世界向地球通報(bào),三體社會(huì)形態(tài)發(fā)生了巨變,半個(gè)世紀(jì)中爆發(fā)了多次革命,其政治體制和社會(huì)結(jié)構(gòu)與地球越來(lái)越相似,基本可以判定是為了迷惑人類。
首先,如果三體也變成了地球上那個(gè)喪失戰(zhàn)爭(zhēng)意志、沒(méi)有“男人”、彌漫著“愛(ài)”和人道主義的文明主義社會(huì),就決不會(huì)在程心接任執(zhí)劍人時(shí)突然攻擊地球,如果兩個(gè)社會(huì)已經(jīng)高度相似,執(zhí)劍人也沒(méi)必要存在,和平就會(huì)降臨(程心就是這樣認(rèn)為的),但事實(shí)證明,六個(gè)水滴一直隨時(shí)待命,攻擊—占領(lǐng)—滅絕三部曲,是三體人蓄謀已久的計(jì)劃。其次,如果三體已高度民主,是否攻擊地球,應(yīng)該由三體人集體投票決定,但顯然在那關(guān)鍵時(shí)刻,攻擊命令是三體元首直接下達(dá)的。三體世界有過(guò)因“文明主義社會(huì)”毀滅的教訓(xùn),不會(huì)毫無(wú)反思地接受地球文化。最后,真實(shí)的三體文化究竟什么樣子,人類其實(shí)不得而知,“三體世界本身仍然籠罩在神秘的面紗中,幾乎沒(méi)有任何關(guān)于那個(gè)世界的細(xì)節(jié)被傳送過(guò)來(lái)。三體人認(rèn)為,自己粗陋的本土文化現(xiàn)在還不值得展示給人類”(3,104),而“粗陋的本土文化”對(duì)三體人來(lái)說(shuō)才是重要的,才是需要隱藏的,他們清楚,輸入地球的“反射文化”是致命的麻醉劑,它將會(huì)在人類“最后的社會(huì)”中塑造一個(gè)又一 個(gè)“末人”。
三體世界并沒(méi)有完全人文化,而是保留了“樸素主義”傳統(tǒng),盡管這是一種冷酷的“樸素”,卻是歷經(jīng)無(wú)數(shù)次毀滅和重生的三體世界的主動(dòng)選擇。在恐怖的威懾平衡中,三體在“樸素”基礎(chǔ)上引入“人文”,在集中基礎(chǔ)上引入民主,以便在威懾紀(jì)元形成對(duì)地球的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這一變化讓三體世界更有彈性。至此,三體世界有了“菊”與“刀”兩副面孔。而地球人則只有一副姣好但也柔弱的文明主義面孔。相對(duì)于地球世界總是搖擺于兩個(gè)極端(要么民主,要專制;要么人性,要么獸性;要么精英,要么庸眾......),三體世界開始注意文明與延續(xù)、樸素與人文、民主與集中的辯證平衡。三體世界“菊”與“刀”的兩面,由三體世界的大使智子完美體現(xiàn)出來(lái)。
智子是一日本少女形象,劉慈欣的這一設(shè)定(包括對(duì)三體世界“恥感文化”的描寫),意味深長(zhǎng)[15]。兩個(gè)文明和平交往時(shí)的智子,身穿素雅和服,頭插小白花,癡迷茶道,沉醉于“和敬清寂”之境界。這位少女大使可愛(ài)又禮貌,無(wú)害而美好。“這時(shí),程心已經(jīng)忘記眼前是一個(gè)外星侵略者,忘記在四光年外控制著她的那個(gè)強(qiáng)大的異世界,眼前只是一個(gè)美麗柔順的女人。”(3,105)但這只是一面。當(dāng)水滴疾速向地球飛來(lái),程心扔掉引力波發(fā)射器之際,智子已與之前判若兩人,“她身穿沙漠迷彩”,圍著“忍者的黑巾”,“背后插著一把長(zhǎng)長(zhǎng)的武士刀”,“英姿颯爽”中透著“美艷的殺氣”(3,144)。為了恢復(fù)保留地澳大利亞的社會(huì)秩序,智子直接訴諸暴力,用滴血的武士刀教訓(xùn)人類:“人類自由墮落的時(shí)代結(jié)束了,要想在這里活下去,就要重新學(xué)會(huì)集體主義,重新拾起人的尊嚴(yán)。”(3,158)三體人并不敬畏地球的“文明主義社會(huì)”, 相反,是深深地鄙視。

智子形象示意圖
所謂“樸素”并不等同于專制(專制并不意味著樸素),也不是不要文明,而是要避免一種爛熟的文明病。正如宮崎市定對(duì)“東洋的樸素主義民族與文明主義社會(huì)”的觀察:
文明社會(huì)的先進(jìn)文化影響著周圍的野蠻民族,同化著周圍的野蠻民族。然而,野蠻民族在文明化的進(jìn)程中并不是沒(méi)有任何犧牲的,他們失去的往往是本民族最為寶貴的東西。我將這種最為寶貴的東西叫作“樸素性”。文明社會(huì)表面上繁花似錦,香氣四溢,但其內(nèi)部卻不乏光怪陸離,詭計(jì)多端。文明社會(huì)的種種弊端,生活在其中的人們是很難察覺(jué)到的,而尚未受到文明的毒害、尚具純真性的野蠻民族從外部卻能看得非常真切。[16]
宮崎市定對(duì)元朝蒙古人接受喇嘛教和中原文化后“野性的樸素”的消失非常遺憾,認(rèn)為那些東西“傷害了政治”[17] 。相比于清王朝貪圖安逸喪失了樸素性,相比于歐洲社會(huì)“也在不知不覺(jué)中向純粹的文明主義社會(huì)變質(zhì)”,其弊端已在毒害社會(huì),宮崎市定驕傲于日本的“樸素主義精神”尚未泯滅:“我國(guó)的國(guó)民成功地將科學(xué)移植到了日本,以至于最終掌握了如何使文明生活和樸素主義相互協(xié)調(diào)的關(guān)鍵。”在他看來(lái),明治維新的成功正是做到了樸素與文明的平衡,而“建立一個(gè)近乎完整的樸素主義社會(huì)”,正是“東方社會(huì)對(duì)我們的希望”[18]。宮崎市定的觀點(diǎn)雖然可被用來(lái)論證日本入侵東亞文明主義社會(huì)的所謂正當(dāng)性,但不妨礙文明與樸素辯證法的啟示意義。
《三體》第三部寫威懾大廳中的羅輯,目光威嚴(yán),“穿的整潔的黑色中山裝格外醒目”(3,131)。當(dāng)羅輯決定穿“黑色中山裝”踐行使命,他一定悟出了樸素與文明的辯證法,這是真正“明心見性”的時(shí)刻。他或許從這件已消失了兩百多年的衣服中,感受到一股剛健質(zhì)樸的力量。穿“黑色中山裝”的羅輯,“我將無(wú)我”,凜然不可侵犯,以劍客的目光逼視著三體世界,“這目光帶著地獄的寒氣和巨石的沉重,帶著犧牲一切的決絕,令敵人心悸,使他們打消一切輕率的舉動(dòng)”(3,132)。在沉默中堅(jiān)守了半個(gè)世紀(jì)的羅輯,終成不可戰(zhàn)勝的圣斗士,“他的勝利無(wú)人能及”(3,134)。“黑色中山裝”并非圣物,沒(méi)必要夸大,它僅在象征意義上聯(lián)系著一個(gè)遙遠(yuǎn)的樸素主義時(shí)代,但卻也展示著與病態(tài)文明主義 及極端個(gè)人主義決裂的姿態(tài),三體世界一定能深得其味。
“地球往事”三部曲讓地球處于緊急狀態(tài),然后順著“人性”向前推,投其所好,給出最好的因,結(jié)出最壞的果,以宇宙視角觀察著小小地球的“最后的社會(huì)”:看它起高樓,看它宴賓客,看它樓塌了。這也是從當(dāng)下推演未來(lái),反思“現(xiàn)代社會(huì)”,在歷史的終結(jié)處,想象一種容納“樸素主義社會(huì)”的可能,在“樸素主義”與“人文主義”的辯證中開出新路徑。逃向太空的“藍(lán)色空間”號(hào)應(yīng)實(shí)行什么樣的社會(huì)制度,章北海的決定是:既非三體世界的專制社會(huì),也非地球的“文明主義社會(huì)”,而是嘗試建立一個(gè)能平衡個(gè)人與集體、民主與集中關(guān)系的社會(huì),“需要經(jīng)歷一個(gè)漫長(zhǎng)的實(shí)踐和探索的過(guò)程才能為星艦地球找到合適的社會(huì)模式”(2,405)。如此,歷史并不必然非此即彼,就沒(méi)有終結(jié)。
三、“初人”與“末人”
福山意義上的歷史終結(jié)后的社會(huì),就是一個(gè)“文明主義社會(huì)”。宮崎市定在與“樸素人”的對(duì)比中歸納“文明人”的特征:“文明人有文明人的教養(yǎng),樸素人有樸素人的訓(xùn)練;文明人善于思考,樸素人敏于行動(dòng);文明人是理智的,樸素人是意氣的;文明人情意纏綿,樸素人直截了當(dāng);文明人具有女性的陰柔,樸素人具有男性的剛強(qiáng)。更進(jìn)一步說(shuō),文明人崇尚個(gè)人自由主義,樸素人囿于集體統(tǒng)制主義,總之,在幾乎所有的方面,兩者都表現(xiàn)出了相互對(duì)立的特征。”[19]而盧梭所謂科學(xué)與藝術(shù)腐蝕尚武精神、敗壞風(fēng)俗,也是在說(shuō)“文明主義”的負(fù)面作用,背后也聯(lián)系著兩種社會(huì)兩種人[20]。如果說(shuō)宮崎市定、盧梭的分析稍顯粗陋,那么福山則試圖從哲學(xué)、心理學(xué)層面對(duì)“最后的社會(huì)”中“最后的人”進(jìn)行思考。
歷史終結(jié)之后,“自由社會(huì)最典型的產(chǎn)物”是一種“布爾喬亞的新型個(gè)體”[21]。這些“最后的人”專注于身體安全與物質(zhì)滿足,缺乏共同體意識(shí),自私自利。這是福山贊美歷史終結(jié)的最大障礙。“最后的人”,馬克思已從“左”的方面揭露其虛偽,但福山認(rèn)為最難以回避也最難反駁的是尼采從右的方面的無(wú)情批判。尼采認(rèn)為“現(xiàn)代社會(huì)”的造物是一群發(fā)明了“幸福”的“末人”,他們的道德、教養(yǎng)和平等意識(shí)顯示的是奴隸本性:
他們有某種可以自豪的東西。那種使他們自豪的,他們把它叫做什么?他們稱之為教養(yǎng),這使他們顯得比牧羊者優(yōu)越。
因此他們不愛(ài)聽對(duì)他們“輕蔑”的話。因而我要就他們的自豪來(lái)談?wù)劇N乙獙?duì)他們講述最該輕蔑的人:末等人。[22]
沒(méi)有牧人的一群羊!人人都要平等,人人都平等:沒(méi)有同感的人,自動(dòng)進(jìn)瘋?cè)嗽骸23]
“末人”固守他們發(fā)現(xiàn)的道德價(jià)值,失去了創(chuàng)造新價(jià)值新道德的超越性。即使在福山那里,“最后的人”也不過(guò)是“喪失了激情的自由人”。一切都得到滿足的“后歷史動(dòng)物”,突然置身于自然狀態(tài)下的宇宙文明之戰(zhàn)中,置身于人類文明可能毀滅的歷史進(jìn)程中,他們會(huì)如何應(yīng)對(duì)?《三體》正是基于這樣的問(wèn)題意識(shí)展開社會(huì)實(shí)驗(yàn)。《三體》中,“高度民主文明的高福利社會(huì)”中生活的“最后的人”,奉行“人文原則第一,文明延續(xù)第二”(2,335),沒(méi)有斗爭(zhēng)意志,以自我保存、物質(zhì)生活與道德原則為全部滿足,而一旦面臨滅頂之災(zāi),又只會(huì)祈求于救世主和宗教,冷漠理性中潛藏的卻是最大的非理性。抽象“愛(ài)”的背后又是牢不可破的個(gè)人主義。這些觀念與自三體世界輸入的“反射文化”一起,織成一張布爾喬亞意識(shí)形態(tài)的天羅地網(wǎng)。這就是為什么劉慈欣認(rèn)為《1984》中的社會(huì)要好于《美麗新世界》中的社會(huì)的原因,因?yàn)榍罢咄ㄟ^(guò)改變還有恢復(fù)人性的可能,而后者則以滿足人性的名義失去了人性[24] 。
三體世界在威懾紀(jì)元的另一個(gè)計(jì)劃可稱為“末人計(jì)劃”,準(zhǔn)確地說(shuō),是要在“末人”中尋找代理人,通過(guò)干預(yù)執(zhí)劍人選舉確保“末人”當(dāng)選。因?yàn)椤白詈蟮娜恕笔チ诵袆?dòng)力,更不愿承擔(dān)責(zé)任,所以第二任執(zhí)劍人在七個(gè)“公元人”之間展開,六個(gè)維德那樣不擇手段的惡徒,一個(gè)善良有愛(ài)的天使。在這一時(shí)刻,智子出來(lái)鼓動(dòng)程心競(jìng)選:“我們女人在一起,世界就很美好,可是我們的世界也很脆弱,我們女人可要愛(ài)護(hù)這一切啊。”(3,106)。而六大惡人卻勸程心不要參選:“在公眾眼中,最理想的執(zhí)劍人是這樣的:他們讓三體世界害怕,同時(shí)卻要讓人類,也就是現(xiàn)在這些娘兒們和假娘兒們不害怕。這樣的人當(dāng)然不存在,所以他們就傾向于讓自己不害怕的。你讓他們不害怕,因?yàn)槟闶桥耍驗(yàn)槟闶且?個(gè)在她們眼中形象美好的女人。這些娘娘腔比我們那時(shí)的孩子還天真,看事情只會(huì)看表面......現(xiàn)在她們都認(rèn)為事情在朝好的方向發(fā)展,宇宙大同就要到來(lái)了,所以威懾越來(lái)越不重要,執(zhí)劍的手應(yīng)該穩(wěn)當(dāng)一些。”“難道不是嗎?”程心問(wèn)。(3,108)這里,劉慈欣并非要觸犯女性主義的政治正確,而是以極端方式揭示“末人”的幼稚病。然而讓人感到壓抑的公元男人,反而激發(fā)了程心參選的決心。當(dāng)然,程心當(dāng)選,威懾失敗。而這一切都在三體世界的預(yù)料之中:“你做出了我們預(yù)測(cè)的選擇”(3,144)。“宇宙不是童話”(3,145)。最終,人類在計(jì)謀和欺騙上也輸給了三體人。
在自然狀態(tài)的宇宙中,放棄尋求承認(rèn)的斗爭(zhēng),就是甘居奴隸地位,然而更可怕的是,宇宙文明博弈是零和博弈,奴隸本身會(huì)被肉體消滅,這意味著宇宙文明間不存在黑格爾闡發(fā)的那種在主奴辯證法中生成歷史的機(jī)會(huì)。《三體》設(shè)置了這個(gè)生存死局,堵死了奴隸“返回自身”成為“自為存在”的可能[25]。宇宙的自然狀態(tài),就是你死我活、做奴隸而不得的狀態(tài),它無(wú)法像人類那樣,在地球自然狀態(tài)中經(jīng)歷“一切人反對(duì)一切人”的悲劇后,達(dá)成社會(huì)契約,進(jìn)而創(chuàng)建一個(gè)保護(hù)他們的利維坦[26]。宇宙智慧文明的差異首先是物種的差異,人類的“文明主義社會(huì)”在宇宙中可能不過(guò)是一個(gè)特殊存在。
這里順便提及一個(gè)問(wèn)題,就是對(duì)《三體》中“高科技+專制社會(huì)”這一社會(huì)形態(tài)的質(zhì)疑,認(rèn)為高科技不會(huì)與三體世界這樣的專制社會(huì)并存,“長(zhǎng)老的二向箔”顯示了劉慈欣未來(lái)烏托邦想象的貧乏[27]。這個(gè)話題很有意思。但對(duì)它的分析不能僅局限于人類經(jīng)驗(yàn)。要考慮到,物種的生理差異是科技發(fā)展程度的變量。《鄉(xiāng)村教師》中的碳基聯(lián)邦人,他們科技的發(fā)達(dá)與其信息傳播和接收方式、記憶可遺傳等有巨大關(guān)系,這意味著他們更智能,在他們眼中,人類的生理構(gòu)造非常原始,即使建立了文明型社會(huì),科技也不可能走太遠(yuǎn)。同樣,三體人的信息交流方式也有其優(yōu)越性,而且記憶可部分遺傳。歌者所在的大神級(jí)文明,“長(zhǎng)老+二向箔”,但歌者有自我意識(shí),只不過(guò)他的生理結(jié)構(gòu)使其可以刪掉危害生存的思想,他們的文明詞典中可能根本沒(méi)有“專制”、“民主”這樣的詞匯,但這不妨礙他們科技發(fā)達(dá)。置身于自然狀態(tài)的宇宙,人類自身經(jīng)驗(yàn)是需要超越的,這應(yīng)該是“地球往事”三部曲的主題之一。即使在人類文明中,辨析此問(wèn)題也需要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視野。“中東石油帝國(guó)”那樣的社會(huì)才是專制,還是說(shuō)一切與歐美社會(huì)形態(tài)不同的社會(huì)都是專制?按照這個(gè)邏輯,印度的科技水平應(yīng)該遠(yuǎn)遠(yuǎn)高于中國(guó)才是。劉慈欣對(duì)這個(gè)問(wèn)題的認(rèn)識(shí)確實(shí)混亂不堪。思想自由可以促進(jìn)科技進(jìn)步,但思想自由必須輔以利益訴求,在近代世界,是無(wú)“思想”的“奴隸”發(fā)明了技術(shù),再經(jīng)科學(xué)的資本化,這才促進(jìn)了科技進(jìn)步[28]。市場(chǎng)社會(huì)欲望驅(qū)動(dòng)的競(jìng)爭(zhēng)機(jī)制確實(shí)可以刺激滿足人性的創(chuàng)新,尤其在民用領(lǐng)域,但當(dāng)今時(shí)代重大科技突破越來(lái)越取決于資金投入及其背后的科研機(jī)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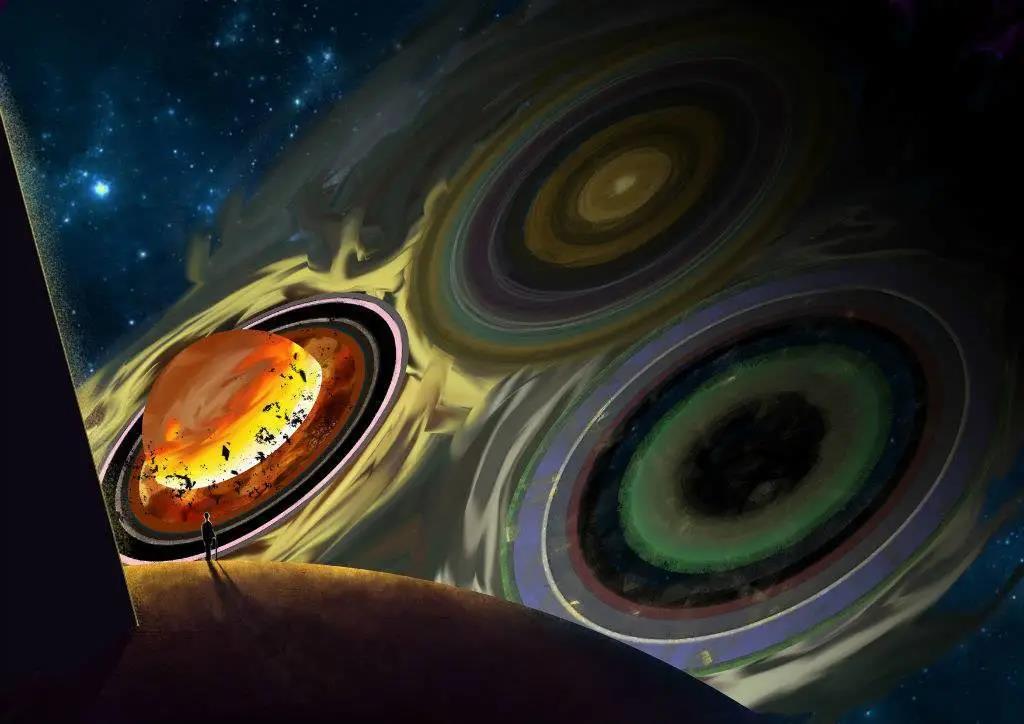
二向箔示意
那么,如何超克“最后的人”?對(duì)于這些幸福的“末人”,尼采大呼“我教你們做超人”,“創(chuàng)造新事物和一種新的道德”[29],“人是應(yīng)該被超越的某種東西”,“一切生物都創(chuàng)造過(guò)超越自身的某種東西:難道你們要做大潮的退潮,情愿倒退為動(dòng)物而不愿超越人本身嗎”[30]?但這種瘋狂的權(quán)力意志與現(xiàn)代社會(huì)的平等訴求背道而馳。福山為了拯救“最后的人”,將尼采的超人轉(zhuǎn)化為類似貴族精英的“優(yōu)越意識(shí)”,以平衡布爾喬亞的“平等意識(shí)”,但其所謂的“優(yōu)越意識(shí)”不過(guò)集中于藝術(shù)、體育競(jìng)技等去政治化方面。為了提升“最后的人”的共同體意識(shí),福山又訴諸黑格爾的“最初的人”。
“最初的人”為尋求他人承認(rèn)而斗爭(zhēng),斗爭(zhēng)結(jié)果是主奴關(guān)系的確立。在黑格爾那里,主人是獨(dú)立的自為存在,而奴隸則為對(duì)方而存在[31],主人為捍衛(wèi)名譽(yù)冒死而戰(zhàn),奴隸則屈服示弱,因而主人更有自我意識(shí)更有人性,奴隸則未擺脫動(dòng)物狀態(tài),所以導(dǎo)致這個(gè)承認(rèn)也是不完滿的:主人獲得的不過(guò)是奴隸的承認(rèn),而奴隸則處于不平等狀態(tài)。但其后,奴隸通過(guò)勞動(dòng)“返回自身”,有了平等訴求和自由意識(shí),通過(guò)斗爭(zhēng)建立的自由國(guó)家,主人和奴隸都得到了承認(rèn),所以自由國(guó)家保留了主人的高貴和奴隸的勞動(dòng)。歷史因此終結(jié)。而歷史終結(jié)處,正是馬克思、尼采批判的起點(diǎn)。福山對(duì)黑格爾的這番科耶夫解釋,是為了借助“最初的人”喚起布爾喬亞喪失了的斗爭(zhēng)激情,一種“戰(zhàn)爭(zhēng)喚起的德性和雄心”[32],因?yàn)椤白畛醯娜恕背絼?dòng)物本能,超越自私自利,可以讓布爾喬亞具有共同體意識(shí)。但“最初的人”的斗爭(zhēng)也可能帶來(lái)破壞性,所以福山小心翼翼將之控制在一定范圍內(nèi)。
《三體》中的“最初的人”不同于黑格爾的“最初的人”,因?yàn)樗粚で笾髋P(guān)系;也不同于宮崎市定的“樸素人”,因?yàn)樗灿小拔拿魅恕钡囊幻?更不等同于尼采的“超人”,因?yàn)樗幻镆暣蟊姟V皇窃谧畹拖薅壬希c他們共享著某些相似的精神品格。《三體》中“最初的人”,是在自然狀態(tài)的宇宙中,在危機(jī)時(shí)刻為挽救地球文明,以非道德的方式開創(chuàng)一條生路,在星辰大海中延續(xù)人類文明的人;是“睜眼看宇宙”,超越人類文明經(jīng)驗(yàn),認(rèn)識(shí)到宇宙殘酷真相,為尋求其他文明的承認(rèn)而斗爭(zhēng)并不惜付出生命的人;是具有頑強(qiáng)意志,在文明沖突的緊急狀態(tài)下觸犯布爾喬亞的道德信條,創(chuàng)造新道德新價(jià)值的人。“最初的人”的斗爭(zhēng)意志與超越意識(shí)不是指向同類,而是針對(duì)外星入侵者,與其說(shuō)他是救世主,毋寧說(shuō)是面對(duì)宇宙神秘黑色方碑的好奇古猿。“最初的人”是英雄與惡魔的混合體,野蠻兇猛,瘋狂有力。
執(zhí)劍人交接時(shí)刻,羅輯如“孤獨(dú)的鐵錨”般,端坐于“像墳?zāi)挂粯雍?jiǎn)潔”的威懾大廳。十分鐘后,程心走進(jìn)大廳。程心看到時(shí)間仿佛在這“死寂”的大廳中停滯,她決定首先要讓這個(gè)“墳?zāi)埂薄盎謴?fù)生活的氣息”,這里將是她的全部世界,“她不想像羅輯那樣,她不是戰(zhàn)士和決斗者,她是女人”(3,134)。在這樣的對(duì)比中,作者將兩人斗爭(zhēng)意志的差異不動(dòng)聲色地刻畫了出來(lái)。簡(jiǎn)潔樸素的大廳,帶著地獄寒氣的決斗者的目光,以及它們的對(duì)立面,構(gòu)成了一幅“最初的人”與“最后的人”辯論的畫面。
在《三體》中,劉慈欣將“最初的人”具象化為一群公元人。維德的出場(chǎng)是從冒犯“文明人”的道德倫理開始的。他問(wèn)新入職的程心:“你會(huì)把你媽賣給妓院?jiǎn)?”(3,42)這個(gè)不擇手段前進(jìn)的人,“就像一塊核燃料,即使靜靜地封閉在鉛容器中,都能讓人感覺(jué)到力量和威脅”(3,343~344),他的威懾度爆表,但他參選執(zhí)劍人并不是要當(dāng)獨(dú)裁者,不是為了滿足一己的權(quán)力欲望,而是出于隨時(shí)犧牲一切與三體世界一決雌雄的決斗意志;在掩體紀(jì)元研發(fā)光速飛船并試圖讓星環(huán)集團(tuán)獨(dú)立,也是為了他所說(shuō)的“事業(yè)”,這個(gè)事業(yè)就是為自由而戰(zhàn),“為成為宇宙中的自由人而戰(zhàn)”(3,381)。苦心經(jīng)營(yíng)逃亡,在太空中創(chuàng)建星艦地球的章北海亦復(fù)如是。羅輯于危機(jī)紀(jì)元的最后時(shí)刻終于肩負(fù)起應(yīng)有的責(zé)任,并在半個(gè)世紀(jì)的執(zhí)劍生涯中道成肉身。公元世紀(jì)還是學(xué)術(shù)混混的羅輯最終“明心見性”,體會(huì)到“人可以被毀滅,但不能被打敗”的斗爭(zhēng)意志,用“最初的人”的威嚴(yán)目光警告三體世界:“地球可以被毀滅,但不能被打敗。”
說(shuō)到底,開創(chuàng)歷史的“最初的人”,是終結(jié)歷史的“最后的人”的鏡像。
結(jié) 語(yǔ)
確實(shí),想象未來(lái)的社會(huì)形態(tài)是最難的,一個(gè)超克了歷史終結(jié)的總體性社會(huì)[33],一個(gè)令人期待的烏托邦,超出了劉慈欣的想象能力[34]。但順勢(shì)而為,在歷史終結(jié)處演出一場(chǎng)人類生存危機(jī)的戲劇,給“現(xiàn)代社會(huì)”以警示和痛擊,仍有其現(xiàn)實(shí)意義。《三體》顯示,那個(gè)假定的“文明主義社會(huì)”,仍然存在政治不平等和經(jīng)濟(jì)鴻溝,且充滿了布爾喬亞的虛假意識(shí)。未來(lái)的社會(huì)形態(tài)不就是在對(duì)宣稱“最后的社會(huì)”“最后的人”的反思批判中創(chuàng)生的嗎?
“地球往事”三部曲為了讓人類意識(shí)到黑暗是生存和文明之母,首先破除了普遍主義的宇宙道德觀,然后在宇宙自然狀態(tài)下布下零和博弈的戰(zhàn)場(chǎng)。“睜眼看宇宙”,面對(duì)宇宙文明之戰(zhàn),人類文明也是自身的敵人。在此危急時(shí)刻,《三體》展開了對(duì)“樸素主義社會(huì)”與“文明主義社會(huì)”、“最初的人”與“最后的人”的辯證思考,一種在“文明主義社會(huì)”中容納“樸素主義”,將“最后的人”轉(zhuǎn)化為“最初的人”的努力。
星辰大海中,開創(chuàng)歷史可能性的斗爭(zhēng),生生不息。
本文原刊于《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叢刊》2020年第6期
注 釋
[1]金濤:《月光島》,《科學(xué)時(shí)代》1980年第1~2期。
[2]吳狄:《飛向瑪雅星》,《科學(xué)文藝》1982年第2期。
[3] 潘洪君、張會(huì)群:《歸來(lái)兮》,《科學(xué)時(shí)代》1981年第3期。
[4][6] 劉慈欣:《后記》,《三體》,重慶出版社2008年版,第300、300頁(yè)。
[5] 王玉玊:《從〈渴望〉到〈甄嬛傳〉:走出“白蓮花”時(shí)代》,《南方文壇》2015年 第5期。
[7]劉慈欣:《三體》,重慶出版社2008年版,第200頁(yè)。第二部、第三部采用的版本為: 《三體2·黑暗森林》,重慶出版社2008年版;《三體3·死神永生》,重慶出版社 2010年版。以下引文,頁(yè)碼在括號(hào)中注明,不再一一標(biāo)注。
[8]吳飛:《生命的深度:〈三體〉的哲學(xué)解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9年 版,第40頁(yè)。
[9] [英]弗·培根:《新大西島》,商務(wù)印書館1959年版,第35~37頁(yè)。
[10] [法]圣西門:《論萬(wàn)有引力》,《圣西門選集》上卷,商務(wù)印書館1962年版。
[11] [法]圣西門:《一個(gè)日內(nèi)瓦居民給當(dāng)代人的信》,《圣西門選集》上卷,商務(wù)印書
館1962年版。
[12] 吳稚暉:《一個(gè)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張君勱、丁文江等:《科學(xué)與人生
觀》,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3] 唐鉞:《科學(xué)與德行》,《科學(xué)》1917年第3卷第4期。
[14] 陳頎注意到汪淼、葉文潔對(duì)待科學(xué)與文明關(guān)系的不同態(tài)度,與他們所處時(shí)代有關(guān)。作
為年青一代的科學(xué)家,汪淼沒(méi)有“文革”傷痛,沒(méi)有“河殤”情結(jié),會(huì)不自覺(jué)認(rèn)同、 捍衛(wèi)自己的時(shí)代和文明。參見陳頎《文明沖突與文化自覺(jué)——〈三體〉的科幻與現(xiàn) 實(shí)》,《文藝?yán)碚撗芯俊?016年第1期。
[15] [美]露絲·本尼迪克特:《菊與刀》,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
[16] [17] [18] [19] [日]宮崎市定:《東洋的樸素主義民族與文明主義社會(huì)》,《宮崎市定亞洲史論考》(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26、120、127~129、26頁(yè)。
[20] [法]盧梭:《論科學(xué)與藝術(shù)的復(fù)興是否有助于使風(fēng)俗日趨純樸》,商務(wù)印書館2011年版。
[21] [32] [美]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jié)與最后的人》,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4年版,
第176、336頁(yè)。
[22] [23] [29] [30] [德]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shuō)》,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4年版,第12、13、43、7頁(yè)。
[24]劉慈欣:《我的科幻之路上的幾本書》,《我是劉慈欣》,北岳文藝出版社2016年 版,第32頁(yè)。
[25] 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法,參見黑格爾《精神現(xiàn)象學(xué)》(上),商務(wù)印書館2010年版。
[26] [英]霍布斯:《利維坦》,商務(wù)印書館2010年版。
[27] [34] 陳舒劼:《“長(zhǎng)老的二向箔”與馬克思的“幽靈”——新世紀(jì)以來(lái)中國(guó)科幻小說(shuō)的 社會(huì)形態(tài)想象》,《文藝研究》2019年第10期。
[28] 閆作雷:《技術(shù)發(fā)明主體之爭(zhēng)與1970年代的科學(xué)問(wèn)題》,《文藝?yán)碚撆c批評(píng)》2018年 第1期。
[31] [法]黑格爾:《精神現(xiàn)象學(xué)》(上),商務(wù)印書館2010年版,第144頁(yè)。
[32] 李靜:《制造“未來(lái)”:論歷史轉(zhuǎn)折中的〈小靈通漫游未來(lái)〉》,《文藝?yán)碚撆c批 評(píng)》2018年第6期。
- 杜學(xué)文:劉慈欣科幻小說(shuō)的思想資源[2022-02-15]
- 《三體》英文版續(xù)約再創(chuàng)新紀(jì)錄 以近800萬(wàn)續(xù)約美出版社 [2022-01-10]
- 人工智能科幻敘事的三種時(shí)間想象[2021-12-22]
- 《三體》之外,中國(guó)科幻文學(xué)找到生存法則了嗎[2021-12-14]
- “難產(chǎn)”的《三體》“復(fù)活”了 [2021-12-13]
- 宋剛:日本社會(huì)與華人科幻文學(xué)[2021-12-03]
- 等了又等之后,我們期待什么樣的中國(guó)科幻“名片” [2021-11-26]
- 等了又等之后,我們期待什么樣的中國(guó)科幻“名片”[2021-1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