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向北》:揭示工業(yè)社會(huì)的生態(tài)文明走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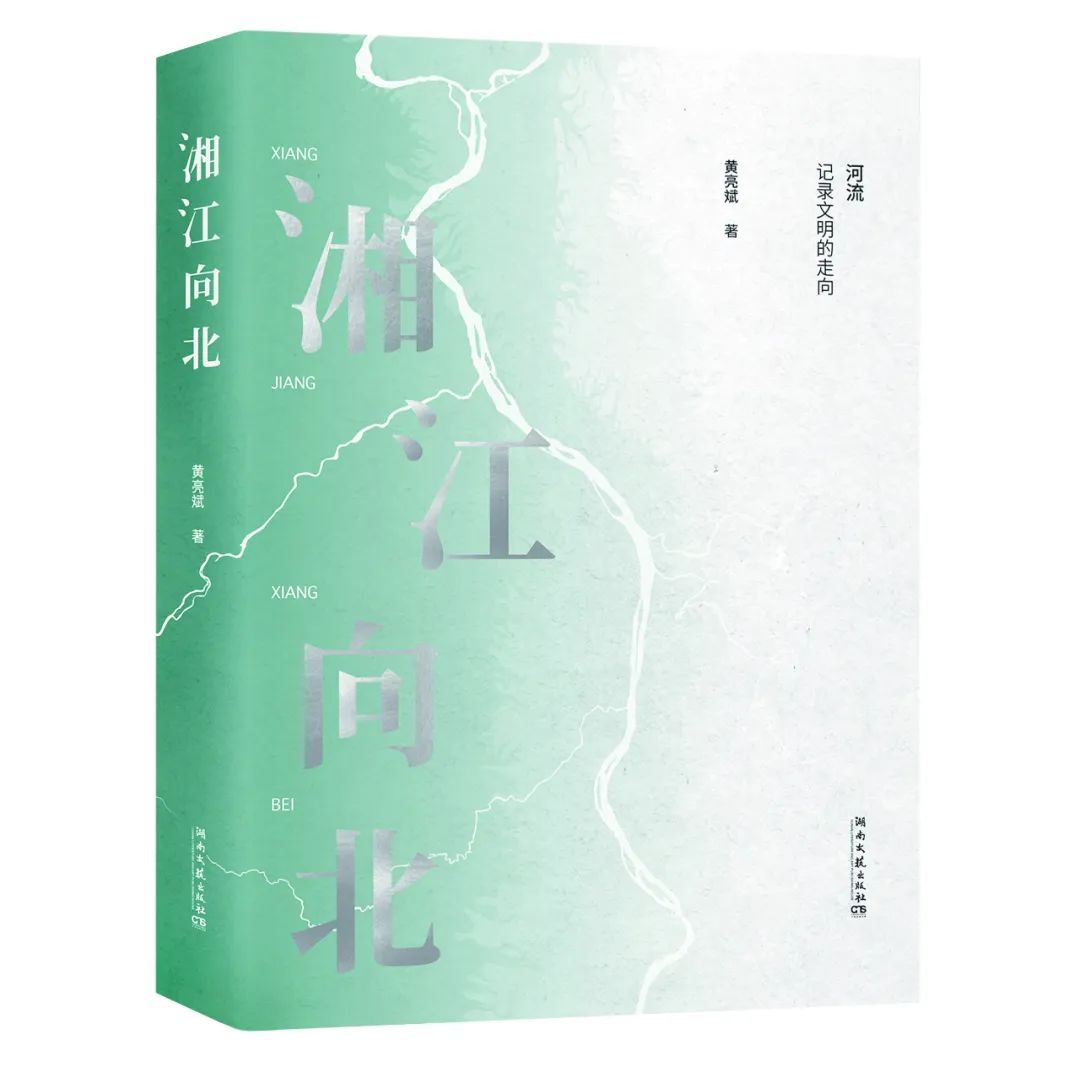
《湘江向北》是資深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工作者黃亮斌最新出版的一部長(zhǎng)篇報(bào)告文學(xué)作品,講述了湖南母親河湘江的百年歷史,被評(píng)為“青山碧水新湖南”優(yōu)秀長(zhǎng)篇征文作品。
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題材作品的一種樣貌
李景平:我關(guān)注環(huán)境文學(xué)到生態(tài)環(huán)境文學(xué)再到生態(tài)文學(xué)的發(fā)展已久,在世界環(huán)境日50周年之際,高興地看到亮斌兄的長(zhǎng)篇報(bào)告文學(xué)《湘江向北》面世。這大概是國(guó)內(nèi)第一部系統(tǒng)地寫一條河流污染治理的長(zhǎng)篇作品,是“污染防治攻堅(jiān)戰(zhàn)”這一題材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一次嘗試。《湘江向北》敘述了什么樣的主體故事?
黃亮斌:《湘江向北》是一部長(zhǎng)篇報(bào)告文學(xué)作品,講述了湖南母親河湘江的百年歷史。由于近現(xiàn)代的工業(yè)革命,湘江近百年的變化超過了歷史時(shí)期的總和,經(jīng)過了一段從“漫江碧透”到嚴(yán)重污染,再回歸“一江碧水”的曲折過程。要全面講述這樣一段漫長(zhǎng)復(fù)雜的歷史,單純從自然生態(tài)的角度是不夠的,也是根本完成不了的,因此我同時(shí)講述了百年湘江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歷史,尤其是百年湘江流域的工業(yè)發(fā)展歷史,這就涉及了湘江流域采礦行業(yè)和工業(yè)企業(yè)的歷史流變。湖南是著名的有色金屬和非金屬之鄉(xiāng),這些礦產(chǎn)和冶煉企業(yè)就主要集中在湘江流域。應(yīng)該說,由于我的職業(yè)優(yōu)勢(shì),這部作品的資料是較為翔實(shí)的。
生態(tài)環(huán)境部華南督察局相關(guān)負(fù)責(zé)人寫的書評(píng)是:“《湘江向北》的出版,說明終于有人記錄下了這個(gè)如巨浪拍岸又倏忽而逝的過程。工業(yè)化發(fā)展過程中人與自然關(guān)系的演變和重塑,這個(gè)過程如同歷史齒輪的滑牙,充滿劇烈的沖突和深切的鈍痛。身逢其時(shí),從‘螳臂擋車’到‘滾石上山’再到‘眾人拾柴’,是我們這代環(huán)保人的幸事,見證記錄下來,為史書添一筆,足可謂有心人。”
李景平:在你的筆下,作品的基本事實(shí)應(yīng)該是湘江的水流由黑到清,岸畔的生態(tài)由灰到綠。那么,湘江曾經(jīng)污染到什么程度,現(xiàn)在又改變到什么程度?你能給出一個(gè)形象生動(dòng)的解說嗎?
黃亮斌:湖南在晚清時(shí)曾引領(lǐng)了中國(guó)思想與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的變革,1895年湖南“新政”后,錫礦山、水口山興建了中國(guó)最早的一批礦山企業(yè),并在之后成為“世界銻都”和“世界鉛都”,湘江也因此成為全國(guó)最早一批被污染的河流。1986年我投身環(huán)保工作時(shí),很多人片面理解“發(fā)展才是硬道理”,搞“有水快流”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湘江一度陷入越治理越污染的窘境。到1995年,湘江水質(zhì)陷入谷底,干流35個(gè)水質(zhì)斷面僅有7個(gè)達(dá)標(biāo)。2006年湖南遭遇兩次重金屬污染事件,隨后幾年,湘江曾被媒體描繪成“中國(guó)重金屬污染最嚴(yán)重的河流”。2011年,湘江被國(guó)家列為重金屬污染試點(diǎn)河流。2013年起,湖南將湘江流域與治理列為“省一號(hào)重點(diǎn)工程”,連續(xù)實(shí)施3個(gè)三年行動(dòng)計(jì)劃。現(xiàn)在,“漫江碧透”和“魚翔淺底”的美景回到了我們眼前。可以說,湘江治理是中國(guó)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和污染防治攻堅(jiān)戰(zhàn)的一個(gè)縮影。我寫湘江,某種意義上也是為中國(guó)的污染防治攻堅(jiān)戰(zhàn)“立此存照”。湘江是國(guó)家重金屬污染治理試點(diǎn)河流,我的寫作還有一點(diǎn)向國(guó)家“交賬”的意味。
李景平:在中國(guó)的生態(tài)文學(xué)作品里,過去,寫環(huán)境保護(hù)題材的居多;時(shí)下,寫自然生態(tài)題材的居多。即使過去寫環(huán)境保護(hù)的作品,也是做揭露批判的多,寫建設(shè)建樹的較少。當(dāng)然這是有客觀的歷史和現(xiàn)實(shí)原因的。那么,現(xiàn)在寫環(huán)境保護(hù),應(yīng)該不會(huì)僅僅局限于揭露和批判。中國(guó)50年的環(huán)境保護(hù)歷史,有足夠的理由大寫特寫建設(shè)、建樹。你以為如何?
黃亮斌:你我有著共同的工作經(jīng)歷,我相信我們書架上大致有著相同的文學(xué)作品,《伐木者,醒來》《淮河的警告》《江河并非萬(wàn)古流》《黃河追蹤》《長(zhǎng)江怒語(yǔ)》等。這大概是您所指的揭露與批判性作品,但我覺得也不能說這些作品中描寫的建設(shè)建樹較少。那個(gè)時(shí)候江河盡墨,需要這些作品喚起人們的重視,抽打我們麻木的神經(jīng),進(jìn)而采取行動(dòng)。我認(rèn)為,這些作品對(duì)推動(dòng)中國(guó)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起到了建設(shè)性的作用,這些作家一直是我敬重師法的榜樣。
中國(guó)環(huán)境保護(hù)經(jīng)歷半個(gè)多世紀(jì)的發(fā)展,山河得到了較好的治理,環(huán)境質(zhì)量在恢復(fù)和改善,我們應(yīng)該當(dāng)好這段歷史的記錄者,寫出時(shí)代的最新變化。在生態(tài)文明新時(shí)代,我們需要?jiǎng)?chuàng)造具有時(shí)代性的新型文學(xué)形象和新型文學(xué)成果,生態(tài)文學(xué)必須做出新的文學(xué)建設(shè)和形象建樹。不僅中國(guó)的生態(tài)文學(xué),而且整個(gè)中國(guó)文學(xué),在這樣一場(chǎng)偉大的歷史進(jìn)程中,都不應(yīng)該缺位和失位。
李景平:一條河流就是一部人類文明史。你在湘江百年歷史的講述里,不是僅僅揭露批判環(huán)境問題,也不是簡(jiǎn)單書寫治理成就,而是揭示超越地域的普遍規(guī)律:工業(yè)文明何以最終走向現(xiàn)代生態(tài)文明?我認(rèn)為這正是這部生態(tài)文學(xué)作品獨(dú)有的新意所在。一條河流確實(shí)蘊(yùn)藏著許多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密碼,你發(fā)掘呈現(xiàn)了什么樣的密碼?
黃亮斌:湖南文藝出版社將“河流,記錄著文明的走向”作為唯一提示語(yǔ)設(shè)計(jì)到封面,抓住了這部作品的靈魂。我們習(xí)慣將河流稱為“母親河”,這是因?yàn)楹恿髟杏肃l(xiāng)村和城市,孕育了人類與萬(wàn)物,人類的源頭在江河的源頭里,人類的文明無(wú)不起源和受惠于大江大河。我在講述湘江百年歷史時(shí),總是情不自禁地禮贊江河。這就決定了我寫作湘江的態(tài)度,也決定了我寫作湘江的目的與意義。我對(duì)江河的態(tài)度是感恩和禮贊,我寫湘江就是為了揭示河流對(duì)人類文明構(gòu)建的普遍意義。因此,我的這本書不會(huì)停留在對(duì)環(huán)境破壞的無(wú)情批判,盡管這種批判也是必需和必要的;也不會(huì)止步于河流治理的謳歌,盡管作為一名環(huán)保宣傳工作者,這至今仍是我的日常事務(wù)。但回到文藝,我認(rèn)為文學(xué)擔(dān)負(fù)著比日常新聞更持久、更加深沉的使命,就是揭示一種文明的規(guī)律和走向。
百年湘江自身的流變,本身就隱藏著人與自然關(guān)系的密碼。我只要把這一歷史時(shí)期的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和自然歷史忠實(shí)記錄下來,不用著意挖掘,就能自然詮釋出人類文明演替的規(guī)律。這個(gè)規(guī)律就是,從最初的原始文明,到后來的農(nóng)業(yè)文明,到近代的工業(yè)文明,再發(fā)展到現(xiàn)在的生態(tài)文明。現(xiàn)代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的發(fā)展,必須遵循和符合自然規(guī)律,悖逆不僅沒有未來,而且即便在當(dāng)下也無(wú)法解決和調(diào)和現(xiàn)實(shí)矛盾。正是百年湘江的歷史流變給了我這樣的啟示,使我能夠以更加平和、包容的心態(tài)看待河流的滄桑歲月,也以更加客觀真實(shí)的態(tài)度呈現(xiàn)河流的過往歷史。我的責(zé)任就是把河流本身演繹的這一重大意義說出來,讓人們少走彎路,不犯過去同樣的錯(cuò)誤。河流給人類的經(jīng)驗(yàn)在這里,教訓(xùn)也在這里。這也許就是隱藏在河流里的文明的密碼。
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題材作品怎樣書寫
李景平:說起來有個(gè)“想當(dāng)然”的細(xì)節(jié),我第一眼看到《湘江向北》這個(gè)書名的時(shí)候,竟看成了《湘江北去》。不知你是否考慮過這個(gè)選項(xiàng)?
黃亮斌:在中國(guó)無(wú)數(shù)條被稱為“母親河”的河流中,湘江之所以出名,跟毛澤東主席的詩(shī)詞《沁園春?長(zhǎng)沙》有著極大的關(guān)系。我之所以沒有借用“湘江北去” 這句名詩(shī),是因?yàn)楹铣霭媪艘槐就}的繪畫本圖書,我只好另謀出路,于是就有了《湘江向北》這個(gè)書名。
李景平:我們?cè)?jīng)就生態(tài)文學(xué)中環(huán)境保護(hù)題材作品的寫作做過簡(jiǎn)單交流,認(rèn)為環(huán)境保護(hù)題材的寫作有個(gè)門檻問題。外面的作家寫不進(jìn)環(huán)境保護(hù)里,里面的作家又寫不到文學(xué)意蘊(yùn)上。對(duì)你而言,30多年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經(jīng)歷,無(wú)疑是座素材富礦,會(huì)不會(huì)也是個(gè)題材藩籬?你是怎么突破環(huán)保領(lǐng)域的局限而實(shí)現(xiàn)拓展,突破環(huán)保和文學(xué)的隔膜而實(shí)現(xiàn)融合的?
黃亮斌:我熟悉的很多作家朋友都有過創(chuàng)作環(huán)保題材的計(jì)劃。2021 年湖南省委宣傳部牽頭組織“青山碧水新湖南”文學(xué)專修班,我們也是活動(dòng)組織方之一,當(dāng)時(shí)我們積極引導(dǎo)作家們書寫洞庭湖和湘江。但在最后報(bào)送的選題中,依然是以自然山水和局地污染治理的居多,我們最關(guān)注、最期待的湘江還是沒人報(bào)題。正當(dāng)大家有些失望時(shí),有人提議說我是寫作這一題材的適合人選。省委宣傳部主要領(lǐng)導(dǎo)甚至在辦公室單獨(dú)約見我,希望我在此次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展示新作為。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進(jìn)入了《湘江向北》的創(chuàng)作。
文學(xué)界的專業(yè)作家進(jìn)入環(huán)保寫作確實(shí)有個(gè)門檻問題,因?yàn)榄h(huán)保領(lǐng)域涉及的專業(yè)知識(shí)太多。至于環(huán)保系統(tǒng)的同人,習(xí)慣于“搖瓶子”,很難做到將專業(yè)的環(huán)保問題進(jìn)行文學(xué)表達(dá)。我從事環(huán)保工作30多年,參與了波瀾壯闊的中國(guó)環(huán)境治理。閉上眼睛,我都數(shù)得出湘江流域哪些企業(yè)關(guān)停了,哪些地方上了治污設(shè)施。我聽到過百姓的呻吟,也見到了群眾的笑容。當(dāng)我真正對(duì)這條河流爛熟于胸后,所謂的文學(xué)表達(dá),就只是技術(shù)問題了。從這個(gè)角度來看,我感覺我的工作不是創(chuàng)作的藩籬,而是文學(xué)表達(dá)的富礦,我很慶幸自己在環(huán)境保護(hù)崗位堅(jiān)守了30多年。
李景平:你在這部報(bào)告文學(xué)的寫作中,要調(diào)動(dòng)積累,要回溯歷史,要查閱資料,要實(shí)地察看,要走訪人物。相關(guān)內(nèi)容涉及決策者、實(shí)施者、執(zhí)法者,多是行政性的、概括性的、粗線條的。這類內(nèi)容與行政書寫、新聞書寫可能天然接近,而與文學(xué)書寫存在天然隔膜,你是怎么將其轉(zhuǎn)化成生動(dòng)的文學(xué)故事的?
黃亮斌:我自1986年從學(xué)校畢業(yè),就開始與環(huán)境新聞打交道,最早是寫作新聞稿,后來是組織報(bào)道,可能我也算是中國(guó)做環(huán)境新聞時(shí)間最長(zhǎng)的人了。新聞界的朋友們都樂于同我打交道,因?yàn)槲页浞肿鹬匦侣剛鞑ヒ?guī)律,一直盡力為記者提供公眾聽得懂的素材,而且我認(rèn)為好的新聞也需要文學(xué)表達(dá)。
當(dāng)然,我自己在文學(xué)上也是有些積累的。20世紀(jì)80年代,我讀過不少文學(xué)名著以及國(guó)內(nèi)主流文學(xué)刊物,現(xiàn)在還記得自己蹲在湖南省圖書館一角如饑似渴閱讀《平凡的世界》和《文化苦旅》的情景。我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學(xué)情有獨(dú)鐘,我寫過的《紅樓夢(mèng)》人物和植物系列文章至今還有人在“頭條”點(diǎn)贊,我還出版了《詩(shī)經(jīng)》名物學(xué)專著,我的散文集《圭塘河岸》多次再版。這些都增添了我創(chuàng)作長(zhǎng)篇紀(jì)實(shí)作品《湘江向北》的信心。
當(dāng)然,我們必須跳出習(xí)慣性的行政言語(yǔ)方式而以文學(xué)敘事方式來講述百年湘江的生態(tài)環(huán)保故事。譬如,寫“天湖爆炸案”,行政工作簡(jiǎn)報(bào)可能用一句“礦產(chǎn)資源爭(zhēng)奪,導(dǎo)致天湖爆炸案發(fā)生”來完成事實(shí)交代;新聞報(bào)道應(yīng)該會(huì)粗線條地交代案件的時(shí)間、地點(diǎn)、原因、涉及人群以及警方的處理結(jié)果;而作為紀(jì)實(shí)文學(xué),就要生動(dòng)地寫出案件的歷史背景、原因根由、人物糾葛、情結(jié)脈絡(luò)、細(xì)枝末節(jié)、事情結(jié)果、社會(huì)影響,要還原一個(gè)完整的故事。
李景平:重金屬污染問題歷來比較敏感,你在現(xiàn)實(shí)采訪寫作和重新發(fā)掘歷史的過程中,遇到過什么難題嗎?在整個(gè)過程中又是如何把握和處理的?書稿出版以后,這些問題成了什么新的問題嗎?
黃亮斌:湘江一度被媒體描述為“中國(guó)重金屬污染最嚴(yán)重的河流”,當(dāng)時(shí),有的重金屬污染是實(shí)實(shí)在在的,有的則是臆想出來的。2021年7月我重啟這一題材的創(chuàng)作時(shí),湘江干流已經(jīng)連續(xù)多年實(shí)現(xiàn)重金屬斷面全面達(dá)標(biāo),支流超標(biāo)斷面也只是零星存在。流域內(nèi)的地方政府和相關(guān)企業(yè),也不再把重金屬污染當(dāng)作敏感問題,所以沒有回避或者拒絕我的采訪。
何況我自己過去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處置本省涉重金屬污染的輿情,因此接受我采訪的同人都非常支持我,并且希望我寫作這樣一部記錄時(shí)代、記錄湘江歷史的書。我所在的單位給了我足夠多的采訪創(chuàng)作時(shí)間,參與湘江治理的同事還幫我認(rèn)真修改文稿,沒有人擔(dān)心我的寫作會(huì)釀成所謂的輿情。一位業(yè)內(nèi)讀者在書評(píng)中寫道:“大概是長(zhǎng)期環(huán)境保護(hù)宣教工作的培養(yǎng),這些故事在敘述上顯得十分克制。”
我很慶幸自己完成了這次寫作。從根本上說,人都是健忘的,再絢爛的煙花也會(huì)冷寂,再轟轟烈烈的大事都會(huì)成為過去,如果我不把這一段文明的歷史及時(shí)記錄下來,將是一件極為遺憾的事情。我在寫作和出版《湘江向北》后,很多業(yè)內(nèi)人士表達(dá)對(duì)我的感激,認(rèn)為我做了一件極其重要、極具意義的事情。我知道,這種感激是發(fā)自內(nèi)心的。
李景平:一條河流從污濁到清澈的過程,不啻是一場(chǎng)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持久戰(zhàn)。取締土法方式,淘汰落后生產(chǎn),治理污染企業(yè),修復(fù)自然生態(tài),矛盾、沖突、博弈、激戰(zhàn),很多甚至是生死交鋒。生態(tài)環(huán)保的博弈,其實(shí)也是政治經(jīng)濟(jì)的博弈和文化人性的博弈。你以怎樣的態(tài)度在廣博深邃的社會(huì)意義上書寫這樣的生態(tài)環(huán)保?
黃亮斌:我大體上是一個(gè)較為平和寬容的人,這種寬容與平和是河流教會(huì)我的。因此,我在《湘江向北》第一章就禮贊了河流的這種高貴的品性:湘江,這條湖南人的生命之江,盡管曾經(jīng)因?yàn)楸池?fù)有色金屬之鄉(xiāng)工業(yè)革命的重任,一度演化成“中國(guó)重金屬污染最嚴(yán)重的河流”,然而一旦我們選擇友好,她就會(huì)摒棄前嫌,以“逝者如斯夫”的從容與淡定,顯示出“上善若水”和“天至慈,陽(yáng)光雨露育萬(wàn)物;地至慈,山川河流養(yǎng)眾生”的博大胸懷,原諒我們?cè)?jīng)的過失和魯莽,并以巨大的自凈能力蕩滌身上的塵埃……
在母親河這種高貴品質(zhì)的感染下,我也以同樣的寬容來看待過去的魯莽與失誤,看待那些為了“政績(jī)”的盲目決策者,那些為了逐利的肆意排污者,那些“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江河守護(hù)人,因?yàn)椋赣H河已經(jīng)懲戒過了我們。在湘江過往的歷史中,我看到了政府的作為,也看到了企業(yè)的行動(dòng),更看到了志愿者的奮斗,我向河流兩岸的每一個(gè)迷途知返亡羊補(bǔ)牢的人致敬,我向每一個(gè)奔波在河流上的守護(hù)者致敬。
李景平:我想知道《湘江向北》是如何處理紀(jì)實(shí)與文學(xué)之間關(guān)系的。書里有許多事實(shí)是可以展開成為情節(jié)化的故事的,但你沒有在這上面用力;許多細(xì)節(jié)也是可以放在典型化的情景中處理的,你也沒有在這上面發(fā)揮。我想知道你在構(gòu)思和寫作的時(shí)候是怎么考慮的?
黃亮斌:在《湘江向北》的寫作過程中,我必須非常克制地使用我所接觸的素材,不然這本書的篇幅遠(yuǎn)不止是目前成書的30萬(wàn)字。
言之無(wú)文行而不遠(yuǎn)。這本書如果沒有很好的文學(xué)性,沒有富有哲理的、優(yōu)美的語(yǔ)言文字,只是埋頭于環(huán)保層面的敘述,不涉及工業(yè)層面乃至社會(huì)層面的展開,就會(huì)非常單薄和枯燥。因此,在作品謀篇布局的時(shí)候,我必須根據(jù)我構(gòu)思設(shè)計(jì)的每個(gè)單元所用素材題材的多少進(jìn)行處理。
在我筆下,湘江流域分為五大重點(diǎn)區(qū)域。處于上游的三十六灣,大型礦山和企業(yè)集群相對(duì)較少,而散亂小礦場(chǎng)較密。聚焦三十六灣,我就可以拿出更多筆墨來拓展人性與社會(huì)的寫作,這樣,就有了這一篇章下的《奪命》《村莊》的故事。這些篇目寫的是全民開礦背景下,三十六灣區(qū)域被撕裂的社會(huì)、被踐踏的傳統(tǒng)倫理、被扭曲的人性以及緊張的人際關(guān)系,這些都是湘江流域工業(yè)文明初起先天不足和成長(zhǎng)缺陷的縮影。我都集中到這一個(gè)章節(jié)來寫。對(duì)于這樣的處理,不同的讀者有不同的看法,三十六灣的有些讀者對(duì)此心有戚戚,而另外一些讀者則堅(jiān)持認(rèn)為,這一章節(jié)是全書文學(xué)色彩最重的部分,真實(shí)再現(xiàn)了工業(yè)文明在成長(zhǎng)和發(fā)展歷程中曾經(jīng)存在的種種弊端,凸顯了本書寫作的現(xiàn)實(shí)意義和社會(huì)價(jià)值。
然后,沿著湘江往下走,就到了水口山和清水塘,這里存在工業(yè)體量更為龐大、工業(yè)結(jié)構(gòu)更為復(fù)雜的經(jīng)濟(jì)體。雖然更為復(fù)雜的城市會(huì)有更為廣泛的社會(huì)撕裂,但我不得不凝神聚氣,把筆觸從社會(huì)層面收回,全部筆墨集中在密實(shí)的企業(yè)、密實(shí)的污染和密實(shí)的環(huán)境治理上。工業(yè)-污染-環(huán)保-工業(yè),我必須循著這條循環(huán)推升的敘事主線,借鑒司馬遷等先賢們樸素明晰的文風(fēng),小心翼翼地處理各種歷史資料和現(xiàn)實(shí)材料,盡量翔實(shí)地完成我對(duì)湘江百年歷史的講述。
我在這個(gè)漫長(zhǎng)復(fù)雜的講述中,放棄了對(duì)很多典型化的情節(jié)細(xì)節(jié)的處理,是因?yàn)樽鳛橐淮伟倌晗娼I(yè)發(fā)展和環(huán)境保護(hù)的龐大敘事,我需要保持克制以確保敘事在主干道上推進(jìn)。在社會(huì)發(fā)展背景上體現(xiàn)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的意義,在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主體上體現(xiàn)社會(huì)發(fā)展的規(guī)律,就是這部作品的典型意義。
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領(lǐng)域蘊(yùn)含文學(xué)的潛力
李景平:作為一個(gè)生態(tài)文學(xué)作家,生態(tài)環(huán)保職業(yè)成就你而使你擁有了素材富礦,文學(xué)藝術(shù)素養(yǎng)成就你而使你成為生態(tài)文學(xué)作家。對(duì)于中國(guó)生態(tài)文學(xué)創(chuàng)作和發(fā)展的歷史和現(xiàn)實(shí),你是怎么看待的?
黃亮斌:現(xiàn)在,很多人都去看手機(jī)和刷短視頻了,紙質(zhì)的文學(xué)閱讀已經(jīng)成為小眾行為,很多文學(xué)大師受到網(wǎng)絡(luò)大咖的嘲諷與消費(fèi)。在這種背景下,能夠有人堅(jiān)持進(jìn)行生態(tài)文學(xué)創(chuàng)作已經(jīng)很不錯(cuò)了,我對(duì)每一位堅(jiān)持坐“冷板凳”并熱情開展生態(tài)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作家表示敬意。中國(guó)關(guān)于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無(wú)論是過去的環(huán)境文學(xué)、生態(tài)環(huán)境文學(xué),還是當(dāng)下的生態(tài)文學(xué),都凝聚了每一位作家的心血,他們是建立人與自然和諧關(guān)系的文化推動(dòng)者。文學(xué)縱使寂寞,我依然認(rèn)為,它是一個(gè)民族最基礎(chǔ)、最深沉、最根本的力量。生態(tài)文學(xué)亦然。
李景平:在中國(guó)生態(tài)文學(xué)創(chuàng)作和發(fā)展中,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題材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可能更具現(xiàn)代生態(tài)文學(xué)意義和生態(tài)文明意義,蘊(yùn)含著巨大的文學(xué)潛力。作為置身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系統(tǒng)近40年的生態(tài)文學(xué)作家,你認(rèn)為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題材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和繁榮,對(duì)于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會(huì)發(fā)揮什么樣的作用?
黃亮斌:脫貧攻堅(jiān)和污染攻堅(jiān)是國(guó)家確定的兩大戰(zhàn)役,但生態(tài)文學(xué)創(chuàng)作明顯偏弱于脫貧攻堅(jiān),即使生態(tài)文學(xué)創(chuàng)作,涉及自然山水的寫作也多于環(huán)境保護(hù)題材的創(chuàng)作,不僅數(shù)量多而且質(zhì)量高。環(huán)境保護(hù)是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的主戰(zhàn)場(chǎng),需要生態(tài)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深度參與,也必將催生一批經(jīng)典的生態(tài)文學(xué)作品。
可以說,中國(guó)生態(tài)文學(xué)創(chuàng)作任重道遠(yuǎn),且潛力巨大。各級(jí)黨委、政府以及生態(tài)環(huán)境部門和文學(xué)藝術(shù)團(tuán)體,在生態(tài)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與培育上應(yīng)該發(fā)揮關(guān)鍵性的組織和支持作用。我在這里特別建言的是,涉及自然生態(tài)領(lǐng)域的科學(xué)家、生態(tài)環(huán)境學(xué)者以及像我這樣的多年浸潤(rùn)于生態(tài)環(huán)境領(lǐng)域的生態(tài)環(huán)保人,應(yīng)該將多年的知識(shí)和職業(yè)積累,轉(zhuǎn)化為生態(tài)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資源。
- 歐陽(yáng)黔森:用文學(xué)的力量塑造新時(shí)代的英雄[2022-10-03]
- 《大地文心——第四屆生態(tài)文學(xué)征文優(yōu)秀作品集》出版[2022-09-28]
- 呼喚生態(tài)道德,提升公民素質(zhì)[2022-09-26]
- 每個(gè)人心中都有一座昆侖[2022-09-22]
- 《詩(shī)意棲居柯柯牙》講述30年新疆如何創(chuàng)造荒漠變綠洲奇跡[2022-09-20]
- 何建明:新時(shí)代報(bào)告文學(xué)開拓者[2022-09-20]
- 感謝時(shí)代 感謝文學(xué)[2022-09-19]
- 歐陽(yáng)黔森報(bào)告文學(xué)研討會(huì)在銅仁學(xué)院舉行[2022-09-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