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漫談—— 側近政治與精神閹寺 ——漫談《宦官:側近政治的構造》
常人對中國古代史時期宦官現象的理解,通常受制于新時期以來的通俗文藝。僅從個人閱讀而言,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電視劇《康熙微服私訪記》中的三德子、《走向共和》中的李蓮英與小德張、《甄嬛傳》中一應角色,電影《霸王別姬》中的張公公,網絡小說《偷天》中的“嫪毐”、《慶余年》中的洪四庠、《大奉打更人》中的魏淵等一系列閹寺者形象影響著我對男性失格群體的感性印象。顯然,宮廷劇在大眾文化中的不斷復辟更新著今人對古典文學與文化的改寫策略,這在客觀上為日漸模糊的宮闈歷史塑造出了新的肉身,但同時也混淆了與之相關的文化記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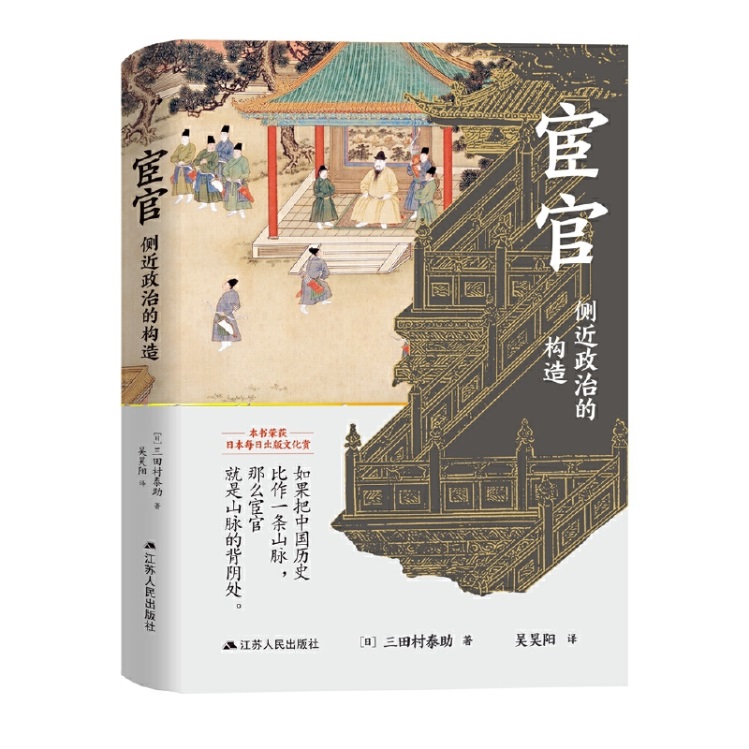
《宦官:側近政治的構造》,[日]三田村泰助 著,吳昊陽 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
新近出版的譯著《宦官》([日]三田村泰助 著,吳昊陽 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矯正并豐富我們對中國歷史上閹寺者的認識。作者三田村泰助師承近代日本思想史巨擘內藤湖南先生,長期從事明清史研究,有《清朝前史研究》《明帝國與倭寇》等著作出版。三田村泰助認為宦官制度與歷史中的深層結構關系密切,通過對漢、唐、明三個中國古代史上宦官最為活躍的歷史時期的觀察,他試圖以“側近政治”的觀念觀照中國君主政治的歷史命運。所謂“側近政治”,即對側近者與皇權實際控制人之間空間距離的描述,空間距離越近,側近者的權力則越大。換言之,空間距離的差距就是側近者權力的差距。三田村泰助在書中以有明一代以來閣臣奏事流程為例,解釋了側近政治觀念的必要性:
所謂的側近政治,就是離皇帝的空間距離越近,權力越大,空間距離的差距即是側近者權力的差距。分隔內外廷的墻壁中間有道云臺門,云臺門左右兩邊各有一道小門,東邊的叫后左門,西邊的叫后右門,三道門合稱為“平臺”。即使皇帝緊急召見,閣臣也只能去到平臺,在門外候旨,不得內進一步。走進后右門,西側有一道向東的門,名為隆宗門。后右門和隆宗門之間有協恭堂。協恭堂就是影子內閣的辦公地,首相級別的掌印太監及以下的宦官干部從早到晚都在自己的辦公室里工作。
內臣與外臣之間被明代厚重的宮墻分隔,在天聰口諭如何傳達、何時傳達的問題上,宦官的權力先朝臣一步。離君主空間上更近的宦官群體逐漸得勢,這種空間上得天獨厚的優勢使得王振、江彬、劉瑾、魏忠賢等權欲滔天的惡宦陸續出現。空間結構影響著權力結構,宦官制度與君主制度的互為表里,或成為晚近中國歷史變動的內在動因之一。按三田村泰助的話來說,“如果把中國歷史比作一條山脈,那么宦官就是山脈的背陰處。”
宦官的出現及宦官制度的形成遠非古代中國所獨有,南歐、北非、中亞以及東方的朝鮮半島上,閹寺者群體參與政治構造屢見不鮮。在早期社會中,閹寺者的失格體現為被征服的異族夸示力量的象征,“其實質是古代人特有的殘暴與神圣行為混合而成的產物”。古希臘史學家希羅多德很早就意識到,宦官的存在是因為君主對臣下的有效控制,同時宦官也需要扮演維護君主神秘性的角色。在土耳其宮廷中,白人宦官首領“卡普?阿卡西”和黑人宦官首領“基茲拉爾?阿卡西”分別為“宮門支配者”和“侍從長”,后者在正式場合更被稱為“達爾斯?色阿德特?阿嘎”,意為“祝福的房間之長”。據三田村泰助說,“達爾斯?色阿德特?阿嘎”是土耳其的最高官職,負責向蘇丹所建的清真寺收取租稅。雖說土耳其黑人宦官首領的具體歷史地位有待另考,但“宮門支配者”“侍從長”的稱謂也足以說明宦官在側近政治構造中的重要性是不分中西的。
但顯然,這種跨越地域的側近政治構造在古代中國最為著名,并真實地改變了中國歷史的發展。時至今日,“高力士脫靴”的典故仍保留在盛唐文學教學對李白的生平介紹中,更毋提蔡倫、石顯、李輔國、程元振、仇子良、梁師成、鄭和、劉瑾、魏忠賢、安德海、李蓮英等人那些赫赫有名的事跡或劣跡了。三田村泰助擅長以故事描述史實,并善于通過重要宦官與時人的親疏遠近關系勾連起一個時期的歷史狀況,高力士即為一例。唐玄宗李隆基與高力士之間的交往已經超越了普通的君臣之分,進入到相伴相助的更高境界:與太平公主的爭斗中,玄宗數次落於下風,得虧高力士追隨政變才功成開元盛世。高力士因功獲封三品右監門將軍——這已超越唐太宗定下的內侍品級不越宰相之制,后又提擢至一品驃騎大將軍。高力士裁斷姚重奏請,調解安祿山、哥舒翰爭寵,參與肅宗登基,無論行政事務還是內廷事務皆從他處經手,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大權在握。“太子以兄事之,各諸侯王稱其為翁。”側近政治的便捷與高效在高力士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榮寵長存與皇權穩固同構,一旦君主的光輝黯淡,宦臣的命運之輪也向下轉。玄宗退位后,與高力士等歌舞妓眾隱居于長慶樓內,李輔國曾假傳圣旨,妄將玄宗暗中轉移羈押,被高力士喝退。他此舉亦徹底開罪李輔國,終被后者施計流放云南邊陲。借側近之便逆刺君權的例子也不在少數,安祿山寵愛并重用宦官李豬兒,日常更衣行儀皆由他手,“安祿山愈發肥胖,足足有三百三十斤,溢出來的肚腩垂到了膝蓋,系腰帶都要三四個人幫忙,兩個人托住肚腩,李豬兒用頭把肚腩頂進去,最后一人趁此機會把腰帶系上。”正因此,晚年安祿山被李豬兒背叛剖腹之前,幾近無察覺。從漢末“十常侍”亂政到近世明代皇帝屢次被暗害,側近政治對皇權的窺伺也自成脈絡。
公正地說,三田村泰助的《宦官》并非是一部可堪細讀的學術著作,盡管他提出的“側近政治”觀念頗具啟發,但書中不少述史都相對隨意,缺乏史料列陳與定量分析,作者天然地將“閹寺者”與“宦官”并置于同一語境下不加區分,則在忽視了對閹寺者身體理解的同時導致了定性研究的混亂。從這一點看,三田村泰助不僅未能達到他所仰慕的日本學者桑原騭藏早年論文《中國的宦官》的寫作高度,其筆力猶在當代國內學人之下。若想真正深入對中國古代史中這一特殊且不可回避的群體細致探析,《中國宦官制度史》(余華青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身體的淪陷:帝國閹宦簡史》(馬陌上 著,敦煌文藝出版社,2006年)、《宦官史話》([日]寺尾善雄 著,王仲濤 譯,商務印書館,2011年)、《佞幸:中國宦官與中國政治》(杜婉言 著,東方出版社,2017年)、《明代宦官制度研究》(胡丹 著,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年)、《神策軍與中晚唐宦官政治》(黃樓 著,中華書局,2019年)等著作都已取得更長足的論述。不過,自《宦官》一書日本原本1963年出版以來,該書在日已經印行近百余次,并獲得日本“每日出版文化賞”,很難不稱其為暢銷書。若非如此,中國出版界也不會在作者逝世三十余年后將其作品引入國內。三田村泰助廣受讀者歡迎必不是因其嚴謹的學術旨歸,與之相反,可能因為書中不自覺的歷時性知識點厾與或有或無的現實能指之間碰撞出了更深層次的思考。
三田村泰助指出,宦官(閹寺者)的供給在有唐一代出現了重大變革。在唐以前,宦官(閹寺者)的構成多為被征服的異族或本族中罪民,以懲戒的方式促使他們工具性轉化,在唐代,“政府下令各個地方每年都要獻上一定數量的私白——在民間已經去勢完畢的人。……唐朝皇宮內的必需品均以貢品的名義向全國征收,宦官即屬于貢品的一種。”這般類稅收的征采方式引發了閹寺者販賣出海的浪潮。唐時嶺南地區的人口買賣本就猖獗,南方是中原地區的奴隸供給來源,開放征采之后,作為當時南海貿易中心地的廣州甚至成為了阿拉伯商人與南中國地方豪強交易不同膚色閹寺者的集散中心。“此時的私白稱為‘火者’,這個詞是印度語Khwaja的音訛,源于印度的穆斯林對私白的稱呼。‘火者’這個外來詞成為中文的一部分是外來宦官被大量運到廣東的明證。”罪惡的發展無疑會激發人性的暗面,唐末時,廣東甚至出現了南漢國——一個宦官王國。“對于賢能的大臣或科舉考試中名列前茅者等國家必需的人才,要先閹割后才能為官。一個南漢小國,竟然有足足兩萬名宦官。”等到宋代,情況發生了新的變化,男性自宮行為獲得官方許可:
愿意自宮的男性要先到兵部備案,記錄下姓名出身,然后選個良辰吉日閹割,并告知兵部閹割日期,兵部記錄后再向上報備,認定閹割已行,待傷愈后便可送該人進宮。自宮者正式任官后,把自宮之日當作是新的生日,自己的吉星也變成了當天的星辰,與過去的一切再無糾結,開始新的人生。
如何看待這種官方許可,三田村泰助有洞見。在他看來,從唐到宋,階級身份制度被大幅撤銷,個人自由的范圍也明顯擴大,“社會開始以財富多寡來決定身份高低,企業精神和注重現實的功利主義萌芽。知識分子可以通過國家考試打破身份牢籠,靠實力當上大臣甚至宰相。所以,那些不甘居于人下,但苦于身無長物又大字不識的底層百姓在察覺到時代的風向后,毅然決然地去當了宦官。”這多少有些令人愕然,但或許是一定程度上的殘酷真實。明初廢除了宰相制度,皇權在形式上得到了極大地增強。可并非所有帝王都具備明太祖朱元璋一般的才干精力,對朝臣的警惕必然滑向對宦官的重用,想要以此謀取權柄之人定當增加。明宣宗還開設了太監學校“內書堂”,以培養識文斷字的宦官輔佐皇權。據《明會典》記載,明代已經被迫開啟了自宮禁令,瓦解了來自北方少數民族的長期困擾后,久違的漢族政權以儒教精神實行社會控制,將自宮與“不孝”的倫理畫上等號,但凡有擅自自宮者被發現,不僅要處以極刑,還要家人鄰里遭受連坐。然而,這種把影子賣給魔鬼的私下交易在閹黨權大的明代已經到了難以斷絕的程度,“愚民競閹其子若孫,以圖富貴。有一村至數百人者,雖嚴禁亦不之止也。”三田村泰助書中引用此文時按語:“連盡力美化修飾過的政府官方記載都已經到了這種程度,實際情況如何可想而知。”此外,顧炎武的《日知錄》中亦有相關記錄:“景泰以來,乃有自宮以求進者,朝廷雖暫罪之,而終收以為用。故近畿之民畏避徭役,希凱富貴者,仿效成風,往往自戕其身及其子孫,日赴禮部投進。自是以后,日積月累,千百成群,其為國之蠢害甚矣。”當官方頒布的重法與實際形成悖論,只能說明主流話語的失效,看似是追求個人與家庭富貴的器官斷舍,其實是來自宦官勢力的暗中慫恿。試想,倘若自宮真的令行禁止,那閹黨如何進一步壯大自身?閹黨在朝勢大,已然再次扭曲了人性。
時至今日,宦官制度早已隨舊歷史走進故紙堆,但“類側近政治”的結構卻不斷延續下來。三田村泰助在附記中對現代社會的“類宦官”群體做出了大膽的假設,他發現宦官與“秘密”、“秘書”之間有著相似的西文詞源構成。“秘密讓權力更強大”,現代社會使得“秘書”成為一個擁有高度技術與能力的成熟行為,私下的人際關系愈發容易越界集體領域,也不斷為向權力者傳達準確信息增添了難度。三田村泰助對“類宦官”的當代指認富有現實意義,但他或許沒有意識到,“類宦官”的邊界遠大于“秘書”從業者,古代社會肉體上的非人化失格演變成現代社會組織行為的整齊管理——細想之下,高度的機械復制與揮刀閹割之間的確互為暗語,被閹寺者為男性還是女性,是否保留某種原生的生理形態或性別記號或表意符號,反而不重要了。
在明代,那些迫于生計無法抵擋飛黃騰達誘惑召喚的幼齡男童及其家庭恐怕尚無法認識到,當生殖裝置與快感裝置同時被消解,這種男權社會下的象征資本也就與其斷絕了聯系。當然,如果剛直正大的意蘊最高級被確認為皇權本身,那性別政治也就天然地成為社會制度的倒影,本不匹配的價值關系能夠再次掛鉤。魯迅先生曾有名言,“我們中國的最偉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藝術也就是男人扮女人。”這自然不是污蔑,只不過是關于民族性的警示。吊詭的是,對勞動力價值并不過分強調的古代文人同樣不易感受到生活快感的呼喚。犬儒主義總以躲閃潛藏的方式告別危險但有益的“革命訴求”,那就等于主動附和了意識形態在精神層面二度閹割的企圖。不幸的是,從很多古典藝術的蛛絲馬跡中都能發現主體性的流溢與抵達自我邊界方式的變化,比如傳統詩文繪畫常通過對“月”“花”“影”的寄托完成一種“次性別意識裝置”。也就是說,借用中藥理論打個比方,許多古代文人在“君臣佐使”的搭配中放棄了前者的主體訴求,說得更明白一點,就是在“妻妾成群”里選擇了后者的身份認同。這或許是一種彼此讓渡的良善動機,同時也是在舒緩中飲鴆止渴的潛在危機,背后的必然性實在太多,但此時也不愿用歷史決定論來尋求某種“合理性”解答。
如果說古代社會閹割的目的是權力對人性的馴服,是文明對肉欲的鐫刻,那么在現代,肉體的閹割在普遍意義上得到了禁止,精神上閹割正進入一個新場。這令人想起沈從文先生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八駿圖》中對人性缺欠的譏諷:初生的都市中所謂的知識者,不過是用種種文明枷鎖自我束縛,讓虛偽的道德將無辜的生命戕害。沈從文先生有意提醒我們,精神閹寺并沒有隨著古典的終結長久緘默,它的間歇性發覆要求人類對避免成為文明的齒輪保持警醒。近百年之后,其狀更甚。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里,大數據、人工智能已經顯示出強大的控制力,與這種無處不在、無處不滲透的公權力相比,前現代時期的帝王權術實在不值一提。對自由更加精微的控制,要求精神前所未有地馴服。涉及身體的所謂的標新立異——我們日益常見的肉體震驚術比如驚異發型、巨幅紋身以及對指甲、肚臍或相關性器的夸飾性變動,可被理解為精神馴服之后的個體反抗。然而,當亞文化的身體性已經完成了自身的世俗轉換后,又怎能不是對更宏闊意識形態的無意識服膺?而不可避免的消費行為伴隨,亦說明了身體行為所謂的優先權之虛妄。性與性別的政治性在時下被極大地增強了,也就意味著精神對肉體的轄制權被極大地削弱了。在這種史無前例的境況里,身體的器官同時具有了產品性,它在文化意味上發生出的半身體性緩解了對器官唯一性的焦慮(并替代性地滿足了各類古典筆記文學中閹寺者對斷肢重生的幻想),而這種身體感性亦成為平衡個體“肉體-精神”的結構要素,投射并參與到了構建集體記憶的歷史話語之中。
- 寒山:觸目皆在的痕跡[2022-02-24]
- 清代詩歌選本中的選家詩話[2022-02-24]
- 汴京氣象:宋代文學中東京的聲音景觀與身份認同[2022-02-23]
- 《論語》的前世今生[2022-02-23]
- 文士與勇士:陳子龍的詩與仕[2022-02-22]
- 戴燕談《洛神賦》[2022-02-22]
- 20世紀詞學十事[2022-02-21]
- 劉緒義:一闋冰雪詩 千秋家國心[2022-0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