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澤:在人間——關于陳彥長篇小說《裝臺》
http://www.tc13822.com 2015年11月10日08:02 來源:人民日報 李敬澤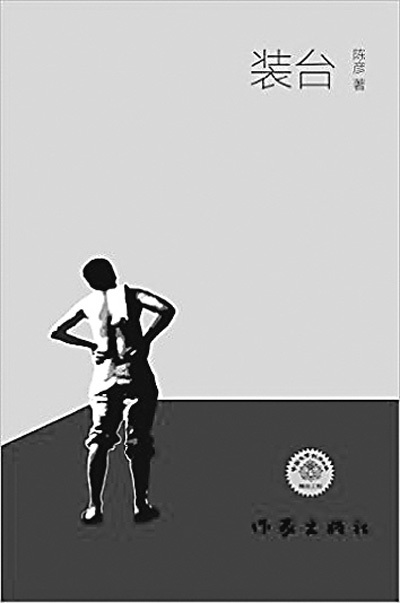 |
|
《裝臺》 :陳彥著;作家出版社出版 |
裝臺人,是藝術與娛樂這個龐大產業機器卑微的末端。陳彥寫了一部長篇小說,就叫《裝臺》。這些卑微如螻蟻的裝臺人在此 被照亮。很少有一本書會像《裝臺》這樣,我拿起來,竟心甘情愿地走下去了,在那喧鬧的生活里,在那些渾身汗臭的男人和女人身邊,和他們一起過著狼狽不堪的 日子,而我竟不想放下,不想離開。
那個刁順子,蹬著三輪車,帶著一班兄弟裝了無數臺,在這部小說里,他在舞臺中心,成了主角。但他真是 辜負了他的名字,他真是不順啊,他就是一個超級倒霉蛋,從一個失敗走向下一個失敗,把人生走出了一路坎坷。就是這個人,我有時覺得我就是他,他所經歷的我 感同身受,我的問題根本不是同情他、憐憫他,我的問題是,和他一起熬過去、挺過去,經受著這一天的勞累和為難和卑賤和喘息和快樂和愛和無奈,然后和他一 樣,栽倒便睡。也就是說,《裝臺》做到了一件事,至少對我來說是當下的小說很少能做到的事,它把在我的社會圖景上無限遙遠、幾近于無的一個人,變成了我的 一部分。不是外在于我,不是我觀看、憐憫、同情、思考的對象,他是我們心中被召喚出來的一個人,就那樣破舊而執拗地站在那里,讓我們不知所措,無從判斷。
我知道,《裝臺》很容易被裝到“底層敘事”“底層文學”的抽屜里。我也認為,這的確是一個有效的闡釋路徑。但是,這是做文章的路徑,卻未必是好的閱讀方法。“底層”盡管廣大,但這個概念卻裝不下任何一個活生生的人。所以,我寧愿像推敲自我一樣推敲順子——
是的,我承認,我一直以為這部小說將以悲劇結束,至少按照底層敘事的通行邏輯,某種險惡的世界意志總會出面了結一切,留下一具尸體作為寫作者關于世界本 質的論述的注腳。也就是說,底層敘事通常是有一個先在的“超級文本”,人的命運早已寫定,那個作者過去我們叫天意,現在可能叫歷史或社會。但是,這里有一 個人,他叫刁順子,這個人竟然不聽招呼不聽安排,他竟然在一次次理當被世界碾成紙片的時候,一次次晃晃悠悠又站了起來,他這不僅是挺住,簡直是要跟這世界 沒完沒了了。也許這是喜劇,是的,在泥濘中展開的滑稽喜劇。它的精髓就在于,人在一個機變百出的世界上的笨拙,他瘋狂地手忙腳亂地應付八方風雨,永遠是五 個杯子四個蓋子,但他執拗地認為杯子就應該有個蓋子。這樣一個人,我從前還真沒有在哪部中國小說里看到。刁順子這個人身上幾乎沒有光芒,他是低的、小的, 他是笨的、弱的、羞澀的、窩囊的,對這樣的人,你除了“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之外還能說什么?
但是,就是這個人,在他黑色的、滑稽的倒 霉史中,我們逐漸看出了一種碾不碎的癡愚,他總是覺得自己該對世界、對他人好一點,就如浪中行船而手中捧著件性命攸關的瓷器,他因此陷入持久的狼狽不堪。 他所有的卑微根本上都出于不舍,但這不舍不是對著別人的,而是對著自己的,不舍那心中的一點好,也因此成了這一點善好的囚徒。陳彥在小說中反復提起螞蟻大 軍,我猜測,他是以此隱喻裝臺人這樣的“蟻民”。而我恰恰不喜歡這些螞蟻,我也不認為以上帝視角去看螞蟻或者看人很有思想。陳彥很可能不自覺地受了當代文 學中關于庶民生活的“活著”邏輯的影響,覺得不提一下活著之堅韌境界就上不去。但是小說家陳彥遠走在了思想者陳彥前頭,這個刁順子,他豈止是堅韌地活著, 他要善好地活著,兀自在人間。這就又不是喜劇了,這是俗世中的艱難修行,在它的深處埋伏著一個圣徒,世界戲劇背面的英雄。
這個人,他也 在我們心中,我們常常會對他的存在感到不好意思,我們每天都在教導自己更強大、更堅硬、更肆無忌憚,我們愿意想象惡,想象惡無往而不利的成功,但是,對于 心中的這一點好,我們通常把它視為羞處,歸于無言。陳彥就是在這樣一個基本語境下寫作的,他要打開不可能性,他必須說服我們,讓我們相信刁順子原來是可能 的。陳彥似乎從來不擔心不焦慮的一件事,就是他作為小說家的說服力。是的,取信于人的說服力首先取決于語調。好的小說家必有他自己的語調。《裝臺》的語調 完全是講述的,引號里邊是活生生帶著氣息帶著唾沫星子帶著九曲回腸和刀光劍影的“這一個”的聲音。而敘述者很少越出人物自身的邊界,他設身處地、體貼入 微,他隨時放下自己,讓每個人宣敘自己的真理或歪理。
作為深浸于傳統戲曲和傳統文化的戲劇家,陳彥也許在這個問題上并未深思,而是提起 筆來,本能地就這么寫下去。這種傳統說書人的牢固本能,使得《裝臺》成為了一部罕見的誠摯和誠懇的小說——在藝術上,誠摯和誠懇不是態度問題也不是立場問 題,不是靠發狠和表白就能抵達,而是這個講述者對他講的一切真的相信,這種信是從確切的人類經驗中得來的。
就好比刁順子,這樣一個人物 其實最不易取信于人。但是現在,刁順子就站在這里,連他身上的氣味都那么確切,武松打虎三碗不過岡,王少堂的評話里,一碗又一碗竟是各個不同、波瀾壯闊, 而刁順子,他的每一次倒霉都是一碗別開天地的酒,人類經驗的復雜紋理被打開展開,細密結實,生動雄辯。甚至刁順子每一單買賣掙多少錢、怎么分,都各有一筆 一絲不茍的細賬,說起來似是瑣屑,但在小說中,正是這種瑣屑之處為人物提供了不容置疑的基礎。講述者給人的感覺是,對于刁順子他所知的比他講出來的還要多 得多,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他就是那條名叫刁順子的魚。
被照亮的不僅是裝臺人,也是一個人間。
像中國舊小說一樣,某 種程度上也像狄更斯一樣,《裝臺》有一種盛大的“人間”趣味:場景的變換、社會空間的延展和交錯、世情與禮俗……現代小說常常空曠,而《裝臺》所承接的傳 統人頭攢動、擁擠熱鬧。《裝臺》的人物,前前后后至少上百,各有眉目聲口,大致上是以刁順子為中心,分成兩邊。一邊是他在裝臺生涯中所打交道的五行八作, 另一邊是他的家庭生活,特別是通過他女兒菊花牽出的城中村的形形色色。兩邊加在一起,真稱得上是呈現了“廣闊的社會生活”。所有這一切構成了刁順子的世 界,這世界帶著如此具體充沛的重量,每時每刻都在向他證明他是多么渺小多么脆弱,又每時每刻向他提出嚴苛的要求。他小聲地、謙卑地與這個世界、與自己爭辯 著,因為同時他又總能在這個煙火人間找到活下去且值得活的理由。在根本上,《裝臺》或許是在廣博和深入的當下經驗中回應著古典小說傳統中的至高主題:色與 空——心與物、欲望與良知、強與弱、愛與為愛所役、成功和失敗、責任與義務、萬千牽絆與一意孤行……
網友評論
專 題


網上學術論壇


網上期刊社


博 客


網絡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