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wǎng)>> 新聞 >> 作協(xié)新聞 >> 正文
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五人談
http://www.tc13822.com 2015年08月19日08:26 來源:人民日報 |
|
標題書法:梁永琳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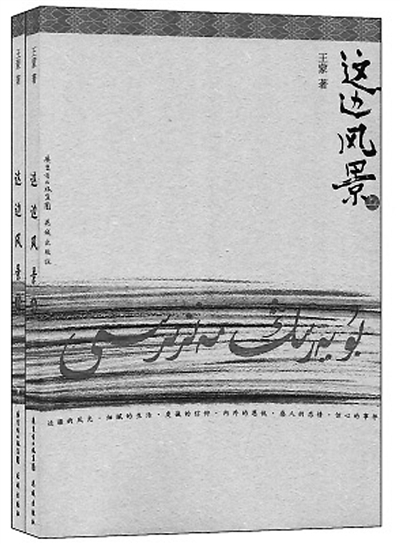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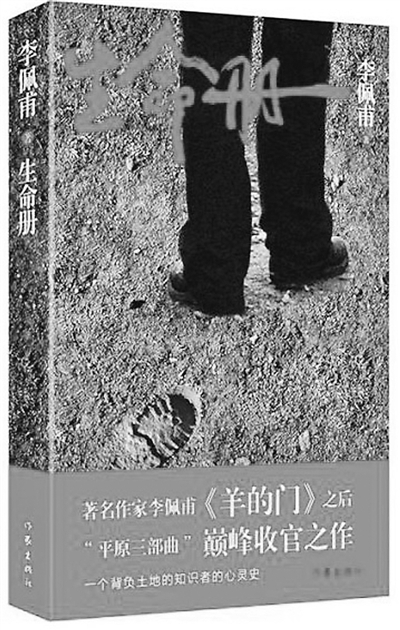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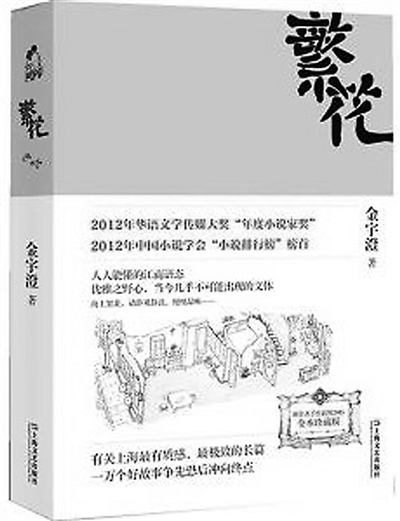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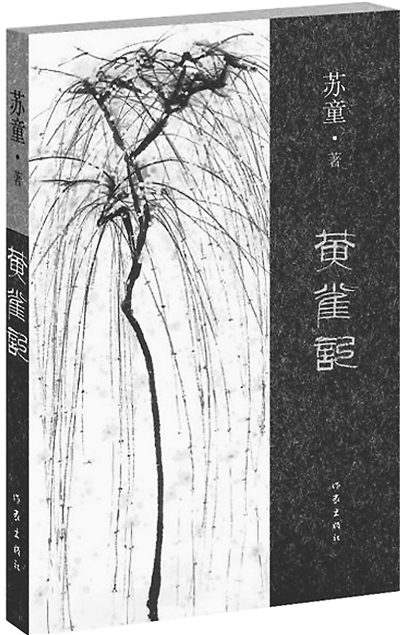 |
第九屆茅盾文學獎8月16日揭曉,格非《江南三部曲》、王蒙《這邊風景》、李佩甫《生命冊》、金宇澄《繁花》、蘇童《黃雀記》等5部長篇小說獲獎,我們特約請5位獲獎作家講述他們的創(chuàng)作歷程與創(chuàng)作理念,分享他們對文學變遷與時代脈動的觀察、思考。
——編者
格非:與歷史片段對話
寫長篇是一件曠日持久的事情。《人面桃花》《山河入夢》《春盡江南》這《江南三部曲》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構(gòu)思,在寫的過程中不斷有新的想法、 新的敘事“溢”出來,但又不能推倒重來,原來的構(gòu)想也舍不得放棄,所以一邊寫,一邊尋找平衡,既回應前面的很多線索,同時又把新的異質(zhì)性內(nèi)容放置進去,突 破和妥協(xié)都在其中。
而“溢”出來的內(nèi)容又成為我手頭正在寫的一個新長篇的“引子”,那就是《江南三部曲》未及展開的上世紀60年代我在鄉(xiāng)村的童年經(jīng)歷。告別鄉(xiāng)村已 經(jīng)很久了,經(jīng)過充分的記憶沉淀,現(xiàn)在再來講述反而更合適。曾經(jīng)的家鄉(xiāng)現(xiàn)在是工業(yè)化城市中常見的“新區(qū)”,少有人提及它從宋代起就存在于長江邊的歷史,再不 去寫,它可能真的就悄無聲息地湮滅了。
我寫長篇,偏愛這些有意味的歷史片段。《江南三部曲》構(gòu)思之初聚焦的就是辛亥革命前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新世紀之初這三個歷史片段。每個片段 都是完整的世界,承載著非常重要的歷史信息和歷史判斷,很多故事只有放入歷史中,和其他事件相比較,才能顯出它的意義和作用來。文學超越直接描摹的地方就 在于它有往前看和往后看的視角,往前是一種想象力,往后意味著一種冷靜的觀察力,試圖看清曾經(jīng)走過的路。對當下的中國社會來說,往后看尤為必要,因為歷史 不僅沒有終結(jié),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重要。
個人的“歷史片段”未嘗不是如此。回過頭來看,上世紀80年代的新奇、沖動、走極端甚至凌空蹈虛,給我的創(chuàng)作打上了特立獨行的印記,但也留下了 過于注重技術(shù)修辭的隱患;這30年來,對普通人與普通生活的“發(fā)現(xiàn)”讓我打破了通俗與精英二元對立的思維,這種觀念的變化無疑會反映到創(chuàng)作中來,成為我個 人文學觀念的一種重要調(diào)整。歷史感的獲得,讓我不斷反省作為一個作家,自己究竟是在用什么樣的眼光打量現(xiàn)實、描繪現(xiàn)實,批判意識也罷,抒情傳統(tǒng)也好,可能 都有自己生存體驗的影子。歸根結(jié)底,我們是用自己的眼睛在與時代、社會和記憶對話。
當下的文學從主題、結(jié)構(gòu)、語言到傳播方式,產(chǎn)生了諸多變化。對我來說,最根本的是讀寫關(guān)系的變化。讀者的性格、趣味、判斷力日漸強勢,讓作家的 “引導”變得困難,文學共識的獲得也越來越難。這些年我自己的文學變革不是形式化、風格化的推倒重來,而是在內(nèi)部悄悄地改變,為的是尊重不同層次的讀者, 不放棄讀者。我相信,這些微小的變革同樣有意義,因為好的作品會在不同層面上給予讀者不同的信息和養(yǎng)分,偉大的作品反而往往是簡單的。
王蒙:想念真正的文學
可以說我們現(xiàn)在的文學很繁榮。“文革”前17年,出版長篇小說200部,平均每年近12部。現(xiàn)在,紙質(zhì)書加網(wǎng)絡(luò)作品,一年數(shù)千部長篇,可多數(shù)是消費性的,解悶、八卦、爆料,還有刺激、胡謅、暴力之類。
我想念真正的文學,提供高端的精神果實,拷問平庸與自私,發(fā)展人的思維與感受能力,豐富與提升情感,回答人生的種種疑難,激起巨大的精神波瀾。 真正的文學,滿足靈魂的饑渴。真正的文學,讀以前與讀以后你的人生方向會有所區(qū)別。我相信真正的文學不必迎合,不必為印數(shù)操心,不必為誤解憂慮,不必為僥 幸的成功胡思亂想,更不必炒作與反炒作。
真正的文學有生命力,不怕時間的煎熬,不是與時俱逝,而是與時俱燃,火焰不熄。它經(jīng)得住考驗掂量,經(jīng)得住反復爭論,經(jīng)得住冷漠對待與評頭論足。不怕棍棒的揮舞,不怕起哄的浪濤。
真正的文學充滿生活,充滿愛情,充滿關(guān)切,充滿憂思與祝福。真正的文學充滿著要活得更好更光明更美麗的力量。
不要聽信文學式微的謠言,不要相信苛評派、謾罵派的詛咒,也不要希冀文學能夠撞上大運。作家需要盯著的是大地,是人民,是昭昭天日,是歷史傳統(tǒng),是學問與思考,是創(chuàng)造的想象力,是自己的海一樣遼闊與深邃的心。
我的處女作《青春萬歲》壓了23年,1956年定稿,1979年出版第一版,但是它至今仍然在不停地重印,仍然擺在青年人的案頭,仍然是閱讀對象,而不僅僅是研究者的文學檔案。
我的《這邊風景》,初次定稿于1978年,出版于2013年,塵封了35年。作者耄耋了,書稿卻比1978年時顯得更年輕而且新鮮,哪怕能找出它明顯的局限。
我的《活動變?nèi)诵巍烦醢嬗?986年,至今已經(jīng)出版了29年,仍然有新的重印。
我有時發(fā)問,文學作品是像小籠包一樣新出鍋時滋味好,還是像醇酒一樣經(jīng)年發(fā)酵效果好?或者二者都是?
文學是一種精神力量,是一種感動,是一種對精神包容空間的開拓,是一種犀利的解剖與挖掘,還有痛徹骨髓的鞭撻。從文學里可以看出人的惻隱之心、 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從文學里可以看出人的度量、智慧、靈動與莊嚴,從文學里可以看出人的美好或者偏狹,高尚純潔或者矯情做作。
文學并不能產(chǎn)生文學,是天與地、是人與人、是金木水火土、是愛怨情仇死別生離、是工農(nóng)兵學商黨政軍三百六十行產(chǎn)生文學。從中外文學史上看,寫作 者如果一輩子生活在文學圈子里,或者把自己封閉起來,就太可憐了,他們?nèi)菀资撸菀鬃詰伲菀装l(fā)狂,容易因空虛而酗酒、自殺,還容易互相嫉恨、窩里斗。
讓我們更多地接地氣,接天氣(精神的高峰),接人氣,也接仙氣(浪漫與超越),接純凈的空氣吧。眼界要再寬一點,心胸要再闊一點,知識要再多一點,身心要再強一些。我們絕對不能只滿足于精神的消費,更要追求精神的營養(yǎng)、積累、提升與強化。
李佩甫:找到自己的平原
“我是一粒種子。”這是《生命冊》的第一句話,我曾經(jīng)花了一年時間,廢掉幾萬字,就為了找到它。我要通過這“第一句話”來決定整部作品的語言基調(diào)和情緒走向,確立這部小說的寫作方向。
“平原三部曲”之間是遞進關(guān)系,我期望一次比一次更深入地向平原發(fā)問。繼《羊的門》《城的燈》之后,收官之作《生命冊》無論從寬闊度、復雜度、深刻度來說,都是最具代表性的。它反映了中原文化獨特的生存環(huán)境和生命狀態(tài),是一次關(guān)于“平原說”的總結(jié)。
平原已經(jīng)不僅僅是生我養(yǎng)我的地方,也是我的精神家園,我的寫作領(lǐng)地。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熟悉的環(huán)境和領(lǐng)域。我的寫作領(lǐng)地是平原。我說的平原以豫中 平原腹地為根基,這里一馬平川,人口密度大,無險可守,歷史上災難深重。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經(jīng)人工開掘過的,到處都是人的痕跡。找到了我的“平原”,就 有了一種“回家”的感覺。我作品中的每個人物,都是我的“親人”,當我寫他們的時候,我是有疼痛感的。因為,實實在在地說,我就是他們中的一個。
就《生命冊》而言,我寫的是一個“背著土地行走的人”,著力于寫他的“背景”、他的“土壤”。這里所說的“背景”,是指平原上一個名叫“無梁” 的村莊。這個村莊是虛擬的。作品中的“我”(吳志鵬)是從無梁走出來的知識分子,他從鄉(xiāng)村一路走來,身份也一直在變,從大學老師、北漂槍手到南方股票市場 上的操盤手,再到一家上市公司的藥廠負責人……可他不是一個人在行走,他是背著一個鄉(xiāng)村在走。他身上背負著“五千七百九十八畝土地,近六千只眼睛,還有近 三千個把不住門兒的嘴巴……”他身上的每一條血管都與無梁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這部長篇我采用第一人稱,以內(nèi)心獨白的方式切入,“以氣做骨”,在結(jié)構(gòu)方 式上,采用分叉式的樹狀結(jié)構(gòu),從一風一塵寫起,有枝有杈,盤旋往復。小說時間跨度很大,有50年之久,要寫的東西太多太多,我?guī)缀鮿佑昧艘簧膬洹?/p>
近年來,社會生活發(fā)生了高速螺旋式的變化,常常使人目不暇接,甚至目瞪口呆。在平原,農(nóng)民已逐漸演變?yōu)榱鲃又⑦w徙著的人,在大變革的潮流中被 裹挾著四處奔突,過著一人帶一家、一家?guī)б蛔濉⒁蛔鍘б淮澹绕春蠖ň拥膹椭剖健⒂∪臼降纳睢_@是連根拔起的一種生活,是疼痛與憧憬并存的一種生活。 當我們吃飽飯后,卻發(fā)現(xiàn)大地已經(jīng)滿目瘡痍,我們已經(jīng)喪失了詩意的“家園”,人類怎么與土地、與大自然和諧相處,不再是一個老話題,也成了一個迫切需要面對 的新命題。
金宇澄:愛以閑談消永晝
一部長篇從初稿到完成,到交付第一讀者——出版社編輯,聽取意見,再到出版,最后到獲得讀者的評論,這個過程一般要經(jīng)過幾年的時間。《繁花》走 的是另一條路,從初稿五百字起,就開始接收網(wǎng)上不間斷的讀后感,一直伴隨它到最后的完成。這是網(wǎng)絡(luò)現(xiàn)場的魅力——寫作是給讀者讀的,寫了之后可以立刻被閱 讀,寫完一段就能獲得讀后感,這對作者來說,是極為愉快的感受,一種始終被閱讀的奢侈。
直面讀者的方式,是西方的經(jīng)典傳統(tǒng),作者寫了一段,習慣是念給朋友聽,這也是現(xiàn)今我們很流行的“文學朗讀會”的前緣。后來一度改為狄更斯式的 “小說連載”,同樣隨寫隨發(fā),從寫出第一個字開始,直面讀者,整個過程都有讀者陪伴。民國初年我們不少小說正是這樣寫的,讀者同樣會給作者去信,講自己的 讀后感。不過,再之后寫小說,我們就變?yōu)槁袷子跁S的一種安靜沉默的方式了。
在網(wǎng)上寫小說不用真名,同樣來自連載的傳統(tǒng),這是一種非常打開的狀態(tài)。作者仿佛換了一個人,那么愉快又那么迫切地去回憶,這是平常很難有的機會 ——忽然之間,你所有的名目都消失了,你不再是你。但你又始終在讀者的關(guān)注下,每天寫一節(jié),每一節(jié)的結(jié)尾處理就會有一種現(xiàn)場感——作者非常緊張,又有高度 的表現(xiàn)欲,與讀者之間是吸引與被吸引的關(guān)系。雖然《繁花》初稿經(jīng)過數(shù)次改動,但成書后節(jié)與節(jié)的劃分仍然保持了原貌,現(xiàn)在書中的每一節(jié)都是當時每一天寫的, 這同書齋里獨自寫作時每一節(jié)的處理完全不同。
意識到每天的更新文字,始終暴露在讀者眼前,那種愉快的程度難以言表。或者說,讓你產(chǎn)生出一種超常的謹慎和警敏,調(diào)動全身心投入,逼出自己所有 的經(jīng)驗和力量,仿佛什么沉睡的記憶都醒過來,進入了一種更安靜也更喧鬧的狀態(tài)里,與你的人物故事一起緊密呼吸。最佳的階段,是你變得心事重重,茶飯不思, 寢食難安,不吐不快,除了趕回家寫字以外,沒有任何的興趣。我常開玩笑說,這大概類似懷孕的感受,整個人都不對了,不過是一種幸福。
此外就是閑談,就是中國傳統(tǒng)的“愛以閑談而消永晝”。我眼中的作者和讀者,確實需要這一類閑散的空間。我喜歡博爾赫斯的看法:“正如《一千零一 夜》一樣,旨在給人感動和消遣。”對讀者來說,感動和消遣是閱讀最重要的部分,是文學允許的一種方向。記錄生活的特殊性和平凡性,是文學永恒的方向。
蘇童:從沒離開這條街
“香椿樹街”是我作品中的一個重要的地理標簽,我從來沒離開過它,從這條街上我時常回頭看自己的影子,向自己索取故事。我期望這條街能夠延展, 能夠流動,因為流水不腐。有人擔心這條香椿樹街會顯得狹窄短促,我從未擔心過。我描繪勾勒的這條街,最終不是某個南方地域的版圖,而是生活的氣象,更是人 與世界的集體線條。我固守香椿樹街,因為我相信,只要努力,可以把整個世界整個人類搬到這條街上來,而我要做的,就是讓沒有喧嘩權(quán)利的語言,齊心協(xié)力順流 而下,把讀者送到這條街上來。
好多年前,我熟悉的一個特別靦腆的街坊男孩,令人意外地卷入了一起轟動街頭的青少年輪奸案,據(jù)說還是主犯。男孩的父母一直聲稱兒子無辜,為此跑 斷了腿,說破了嘴,試圖讓當事的女孩推翻口供,未有結(jié)果。那個靦腆男孩多年后從獄中出來,混得不錯,性格依然很靦腆,人到中年之后,我遇見過他,有機會刺 探當年的案底,追問他的罪與罰是否真實公平,卻始終沒有那份勇氣。
好在有小說。我把他寫進了《黃雀記》。
小說里有自由。自由給小說帶來萬能的勇氣,也帶來了最尖銳的目光,它可以幫助我們刺探各種人生最沉重的謎底。不過,讀者對文字始終是警惕的,充 滿拷問意識的,當你要模糊“所有格”的時候,他們也許恰好要厘清,那是誰的生活,誰的社會,誰的思想?讀者與作家面對一個共同的世界,他們有權(quán)利要求作家 眼光獨到深刻,看見這世界皮膚下面內(nèi)臟深處的問題,他們在沉默中等待作家的診斷書。而一個理性的作家心里總是很清楚,他不一定比普通人更高明,他只是掌握 了一種獨特的敘述技巧。
《黃雀記》里橫亙著香椿樹街式的倫理道德,人們生活于其中,有真切的溫暖與寬恕,有真實的自私與冷酷,有痛楚陪伴的麻木,有形形色色的遺忘與搜尋的方法。當然,隱喻與象征在小說里總是無處不在。《黃雀記》里的人物面對過去的姿態(tài),放大了看,也是幾億人面對過去的姿態(tài)。
展望未來是容易的,展望的結(jié)果大多化作浪漫的詩篇。而面對過去,最為艱難痛苦的,是自我清算,這無關(guān)仇恨與復仇,自我便是自我的敵人。不過,在 控告之后,至少還應該反省,至少還有懺悔。反省與懺悔的姿態(tài)很美好,那是我所能想到的最恰當?shù)拿鎸^去的姿態(tài)。這個姿態(tài),可以讓一個民族安靜地剖析自己的 靈魂。這個姿態(tài),還有可能帶來一個奇跡,讓我們最真切地眺望到未來,甚至與未來提前相遇。
版式設(shè)計:宋嵩
人物速寫:羅雪村
網(wǎng)友評論
專 題


網(wǎng)上學術(shù)論壇


網(wǎng)上期刊社


博 客


網(wǎng)絡(luò)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