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穿越千年的纖繩——賴特與白居易詩的英譯轉(zhuǎn)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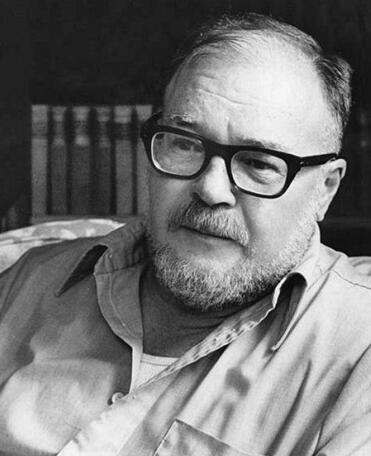
詹姆斯·賴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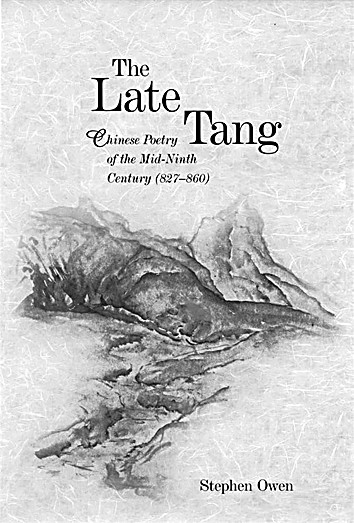
宇文所安《晚唐:九世紀中葉的中國詩歌》
美國漢學(xué)家華茲生在《哥倫比亞中國詩選》中介紹白居易的詩歌時寫道:“就如亞瑟·韋利幾十年前發(fā)現(xiàn)的那樣,在英語世界,白居易似乎比其他任何一位中國大詩人都要更加深入人心……”白居易歷來受翻譯家們的青睞,從十九世紀末翟理斯的《古今詩選》到二十世紀初韋利的《漢詩一百七十首》、洛威爾的《松花箋》、賓納的《群玉山頭》,再到二十世紀中葉雷克斯羅斯的《漢詩百首》、葛瑞漢的《晚唐詩選》,以及較為晚近的華茲生的《哥倫比亞中國詩選》、宇文所安的《晚唐:九世紀中葉的中國詩歌》,都選譯了白居易的詩,韋利還專門寫了《白居易的生活與時代》。
究其原因,白居易語言平實、易于轉(zhuǎn)譯是一重要因素。除此之外,白詩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其日常化、生活化、社會化的立場也促成了它的被接受。英國漢學(xué)家葛瑞漢在《晚唐詩》中言簡意賅地總結(jié)道:“杜甫是儒家圣人,李白是道家仙人,而白居易則是人間凡人。”也就是說,白居易寫的是日常與煙火。
與白居易唱和:忠州與明尼阿波利斯
廣泛的譯介增加了白居易在當代歐美詩壇的影響。艾倫·金斯堡、肯尼斯·雷克斯羅斯等眾多詩人都曾寫詩與白居易唱和,要么聚焦他的生平,要么由他的詩文催發(fā)詩思。其中最為學(xué)界所津津樂道的是美國詩人詹姆斯·阿靈頓·賴特(James Arlington Wright)的《冬末,跨過泥坑,想及古代中國的一位地方官》。在這首詩中,賴特以韋利所譯白居易《初入峽有感》的詩句“況吾時與命,蹇舛不足恃”為引言,直呼其名問道:
白居易,脫發(fā)謝頂?shù)睦险渭遥?/span>
何必這般徒勞呢?
我想到你
惶恐不安地駛?cè)腴L江三峽,
纖夫拉著船逆著湍急的水流,
送你到忠州城去,
做一個什么差事。
我猜,你到達時,
天已經(jīng)黑了。
而現(xiàn)在是1960年,春天將至,
明尼阿波利斯高聳的巖石,
構(gòu)筑了我自己的暮色,
也有纖繩與湍流
……
賴特隨后寫到了貶謫忠州的白居易與元稹之間的離別,問他是否“在山的那一邊找到了孤零人的城市”,是否“還在緊握著那條磨損了的纖繩的一端,一千年也沒有放手”。對于這首詩的探索,論者多將其視作一個特例,單獨摘出討論。顯然,賴特對白居易的征引與對話不是孤立與斷裂的,若將其置于詩人整個詩學(xué)脈絡(luò)與文化背景里看,便會發(fā)現(xiàn)背后錯綜復(fù)雜的關(guān)系。在賴特那里,白居易詩歌的諸多元素被拆解、變形,糅合在其創(chuàng)作之中。
在詩中,他將美國中西部地區(qū)的明尼阿波利斯及居民,與白居易詩里的忠州及“巴人”形成了一種平行對照的關(guān)系,表現(xiàn)為一種跨越千年的相挈。這首詩出自《枝不會斷》這部詩集,是全集的第一首,定下了整部詩集的基調(diào)。詩集第一版的版面設(shè)計也呼應(yīng)了它的主題——一根磨損但依然堅韌的繩索,貫穿了封面與封底。想必《初入峽有感》的孤寂感深深地打動了賴特,冬日的凋零蕭瑟、羈旅的孤苦無依成了統(tǒng)攝整部詩集的主導(dǎo)情緒。一旦確立了這一閱讀方向,便不難從詩集中抽繹出更多的線索,發(fā)現(xiàn)賴特這一時期的創(chuàng)作與白居易迂回曲折的關(guān)聯(lián)。整部詩集交織著與衰老、病痛、孤獨相關(guān)的主線——賴特在詩中寫道,自己描述的是“悲悼與雪的季節(jié)”。其中的敘事雖是基于美國中西部地區(qū)的所見所聞,但對白居易詩歌中的相關(guān)意象和主題進行了回應(yīng)與闡釋。
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一次演講中,賴特指出韋利為他打開了中國古詩的大門,并稱贊了白居易的詩歌,現(xiàn)場朗誦了《初入峽有感》以及《臼口阻風(fēng)十日》。在他看來,白居易詩中描述的羈旅漂泊之苦讓他想起在明尼蘇達州某個人煙稀少的車站時的心境。韋利的白居易譯詩及《白居易的生活與時代》構(gòu)成了賴特的參照系。在《枝不會斷》里,白居易的影子若隱若現(xiàn),暮年、感時、傷懷等白詩中的主題,在賴特的筆下被靈活地演繹。《明尼阿波利斯之詩》寫道:
我不知去年冬天又有多少老人
在密西西比海岸
饑餓與無名的恐懼中游蕩
被風(fēng)吹盲了眼睛
……
我愿我的弟兄們好運
有一個溫暖的墳?zāi)埂?/span>
詩歌表達了寒冬季節(jié)對于受苦者的悲憫以及對于溫暖的渴望。韋利譯白居易詩《新制綾襖成感而有詠》寫道:“那么多的窮人在遭受寒冷,我們能做些什么來預(yù)防呢?僅給一個人帶來溫暖是沒有多大用處的。我愿擁有一張一萬丈的毯子,可以把全城的每一寸土地都覆蓋上。”這便是:“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暖亦何情……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不管是在主題還是措辭上,賴特的詩句均回應(yīng)了這首詩,許多語句都是從這首譯詩中直取而來。白居易多次表達了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式的悲憫,例如《新制布裘》也寫道:“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wěn)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在這里,白居易的袍子經(jīng)由韋利的譯文變成了毯子,而在賴特的想象中,又轉(zhuǎn)化成了死亡的解脫。
對于底層民眾的同情深嵌在賴特的詩歌中。賴特將地點替換到美國中西部地區(qū),那里充滿了礦工、賭徒、流浪漢、拾荒者、印第安人等一系列被邊緣化的人物。就連其中的動物也是疲憊不堪的,例如喘息的老馬,拖曳著花粉的蜜蜂。他們對應(yīng)了韋利譯詩中的賣炭翁、侏儒以及“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的折臂翁等一系列的可憐人。不過,賴特的詩中,除了令人傷懷的蔭翳,時不時也會有積極的亮色。《北方的狗魚》一詩中,賴特連禱般重復(fù)“繼續(xù)活下去(go on living)”這個短語:
我希望我們讓
活著的繼續(xù)活下去。
一位我們篤信的老詩人
說了同樣的話,因而
我們在黑暗的香蒲叢中駐足祈禱
為了麝鼠,
為了它們尾巴劃過的漣漪
……
詩中的這位老詩人是不是白居易呢?韋利譯集所錄白居易《食后》中的“無憂無樂者,長短任生涯”,譯為“但那些心中沒有歡樂也沒有悲傷的人,不管生命的‘短’或‘長’,都要繼續(xù)活下去”。“繼續(xù)活下去”便是聯(lián)系兩者之間的蛛絲馬跡,面對生命的短暫與無常不言放棄的人生哲學(xué)出自此處。從白居易那里,賴特看到了“活下去”的樂觀與堅韌。白居易的詩歌滲透在《枝不會斷》的文字肌理中,韋利所選白居易詩歌的三個不同向度,不管是對于社會的批判,對于暮年的書寫,還是關(guān)于日常生活的省思,都折射在賴特的詩歌中。
詩的暮年:“我浪費了我的生命”
與白居易的日常美學(xué)如出一轍,不管是對于社會性還是個體性主題的呈現(xiàn),賴特的詩歌出發(fā)點也是寫實的。《枝不會斷》中收錄了他的名詩《躺在明尼蘇達州松島威廉·達菲農(nóng)場的吊床上》:
在我的頭頂上方,我看到一只青銅色的蝴蝶,
在黑色的樹干上入睡,
就像一片樹葉在綠色的陰影中飄動。
空房子后的峽谷里,
牛鈴聲聲作響
遁入午后的遠方。
在我的右邊,
兩棵松樹之間的一片陽光下,
去年的馬糞
閃耀如金色的石頭。
我往后倚靠,夜色降臨。
一只雛鷹飛過,尋找家園。
我浪費了我的生命。
這里表達的是時間的主題——在靜謐無聲的自然變化之中體味時光的流逝,也暗含了回望人生的失落與悵然。全詩經(jīng)過一系列景象的羅列,一步步推進,最后落腳在一句看似突兀的感慨之上。這首詩被視作賴特的代表作之一,常被作為單獨的詩篇收錄在各個詩選里,似乎與中國詩歌并無糾葛。不過,一旦將其與整部詩集的白居易基調(diào)聯(lián)系,便會發(fā)現(xiàn)諸多隱匿的關(guān)聯(lián)。
韋利所錄白居易《村居臥病三首》寫道:“夏木才結(jié)陰,秋蘭已含露。前日巢中卵,化作雛飛去。昨日穴中蟲,蛻為蟬上樹。四時未嘗歇,一物不暫住。”
與賴特詩相比較便會發(fā)現(xiàn),兩首詩有著相似的視角轉(zhuǎn)換過程,均包含草木、禽鳥與蝶蟲:在白居易的詩中,從草木至禽鳥再至蝶蟲,遵循的是由遠及近、從外及內(nèi)的編排次序;在賴特的詩中,則是從蝶蟲至草木至禽鳥,從上至下,從遠及近。兩首詩寫景狀物的語言均是冷靜的、客觀的、自省的,結(jié)論都是逝者如斯,感嘆世事變化。也就是說,賴特的動力機制與白居易詩同一機杼——他所描述的地理景觀、花草禽蟲是美國中西部的,但其認識方式以及修辭卻是唐詩的。在一首題為《在寒室中》的嘆惋年華老去的小詩中,賴特寫道:
我?guī)追昼娗八?/span>
而爐子已熄滅了數(shù)個小時
我正在變老(I am growing old)
一只鳥在光禿禿的接骨木上啼叫。
寒冷、昏睡、暮年與炭火燒盡的火爐,表達了悲涼衰微的氣息,但落腳的尾句,鳥兒的鳴啼似乎又暫時打破了昏昏欲睡的氛圍,點破了心中的困頓。這是從物象到心境的轉(zhuǎn)換過程,摘取日常生活的片段,以視覺、聽覺、想象等方式加以表現(xiàn)。這種細膩的描述是賴特營造詩境的關(guān)鍵元素,借用了火爐、寒冷等白居易晚年詩歌中常見的意象,又取法其文字的精簡與直白。韋利所錄白居易詩,包括了多首“火爐”詩,如“轉(zhuǎn)枕頻伸書帳下,披裘箕踞火爐前。老眠早覺常殘夜,病力先衰不待年。”他的《漢詩一百七十首》便以題名《最后一首》翻譯了白居易的《自詠老身示諸家屬》作為譯集的結(jié)尾,其中火爐也是重要的日用器物——“置榻素屏下,移爐青帳前”。韋利將這首詩視作白居易生前的最后詩作,更加凸顯了死亡的寓意。除此之外,細察韋利的白詩譯本,便會發(fā)現(xiàn)“我正在變老”這句話原封不動地摘自《臼口阻風(fēng)十日》一詩中“老大光陰能幾日,等閑臼口坐經(jīng)旬”的譯文。賴特對這句話表達的情緒極為認可,在另外一首詩中,又重復(fù)使用了一次。對于暮年的思考,最為突出地表現(xiàn)在《我懼怕死亡》這首詩中:
曾經(jīng),我懼怕死亡,在田野的枯草中。
但現(xiàn)在,
一整天我都走在潮濕的田野上,
努力保持安靜,傾聽
那些小心翼翼移動的昆蟲。
或許它們正在啜飲空蝸牛殼里
以及飄落地上的雀羽的藏身之所里
漸漸聚集的新鮮露珠。
詩歌描述了詩人從畏懼死亡到坦然接受死亡和欣賞生命的過程。整首詩既有對生命的敬畏之情,也用空蝸牛殼、雀羽的意象暗示了一種虛空的主旨。原野、秋露與秋蟲這些意象來自哪里?韋利的《白居易的生活與時代》收錄了《村夜》這首詩:“霜草蒼蒼蟲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絕。獨出前門望野田,月明蕎麥花如雪。”譯詩為:“田野上的草結(jié)滿了(streaked)霜(frost),蟲聲(insects)吱吱作響;/村子的南邊(south)和北邊無人(soul),一片寂靜(stirs)。/我獨自出門,站在門前,望著開闊的田野(fields);/在月光下,蕎麥花(flowers)像雪(snow)一樣潔白。”
這是一首聲色兼具的詩。在視覺上,它寫的是月下之景,從衰草的霜色到月光下的空無,再到盛開的蕎麥花,描畫了一個白色的世界。而聲音上則是入耳的秋蟲聲,在韋利的譯文中,最為突出的聲響效果來自一系列輕柔的咝擦音構(gòu)成的頭韻,如“s”有streaked(結(jié)滿)、insect(蟲)、 south(南)、soul(人)、stir(動)、snow(雪);“f”有frost(霜)、fields(田野)、flowers(花)等。這兩種聲音的穿插,形成了輕柔舒緩的音樂感。賴特的詩中,也同樣以田野、安靜、雀羽等詞的“f”與“s”音編排,制造了相似的聲響效果。全詩暗含了在音韻層面上對于白詩的借鑒。
賴特的詩中,靜寂蕭瑟引發(fā)了對于死亡的思考,然而它的壓抑被一處偶然捕捉的自然生機打破,平衡了衰微、寂寞與死亡的滯重。實際上,《枝不會斷》里,路的盡頭一只野雞突然振翅飛去,橡樹林中一只鷹隼的叫聲,原野上幾只蟋蟀的動靜,都會為風(fēng)景帶來擾動——似乎這些小小的發(fā)現(xiàn),可以抵抗生活的無常與壓抑。這正是他的一系列小詩常見的動能機制。對于受苦受難者的悲憫,對于自然生物帶來的微小卻深刻的感動的書寫,所有的詩筆都建立在精準的觀察、敏銳的感知與悲憫的情懷之上。
“枝不會斷”的樂天主義
賴特的詩中飄逸和沉重并舉。他既從白居易那里汲取了一種悲天憫人的寫實主義,還從他的詩歌里找到了內(nèi)心的安寧閑適,抵達了一個可供暮年詩人自處的世外桃源。從尋常事物至“靈光一現(xiàn)”式的生命體悟,是其常用的結(jié)構(gòu)。這構(gòu)成了一種轉(zhuǎn)折與變化,往往是非邏輯的、非線性的,超離了理性思維的慣式。《枝不會斷》中有一首被眾多詩選收錄的名詩,其中詩人描述了在明尼蘇達州的高速路旁偶遇兩匹小馬的情景,繼而寫到被它們深深打動,最后想到:“我突然意識到/如果我走出我的身體,我就會綻放/開花。”
這里表述了一種典型的轉(zhuǎn)折關(guān)系,在景物中發(fā)現(xiàn)靈光一現(xiàn)的洞見,從而擺脫環(huán)境的羈絆。這首詩的中心意象,和白居易詩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韋利所錄白居易《夢上山》中有關(guān)于形神之對比的討論:“既悟神返初,依然舊形質(zhì)。始知形神內(nèi),形病神無疾。形神兩是幻,夢寐俱非實。”詩人年老身衰,只能夢中登山,“夜夢上嵩山,獨攜藜杖出”,但也由此生發(fā)了擺脫形神對立的思想。這種形神之間的關(guān)系,在韋利譯文中轉(zhuǎn)化為肉身與靈魂,而它的關(guān)鍵詞“body”與“soul”,在賴特的詩中升華為“綻放/開花”的超脫。韋利所錄白居易《渭上偶釣》中寫道:“雖然我的身體坐等魚兒上鉤,我的心卻游到虛無之地。”即“誰知對魚坐,心在無何鄉(xiāng)”。這種身心的分離,經(jīng)由某種沉浸式、入神的體驗,超越肉身的束縛,正是賴特詩中描述的狀態(tài)。
無論是白居易的垂釣還是賴特的觀馬,均是使浪漫化、主觀化的想象讓位于精細的觀察。一切想象都錨定在寫實主義的穩(wěn)固性之上,詩人并不隨意施加某種意義,而是讓意義在意象的連綴中自動呈現(xiàn),達成平實通達的生命體悟。這種編排方式意味著一種中式的蘊藉之美。它打破了常規(guī)的語義鏈條上的邏輯關(guān)系,總會有一個突如其來的轉(zhuǎn)折,或靈光一現(xiàn)的時刻,從而構(gòu)成了對于現(xiàn)實境況的救贖,讓整個世界澄明起來。賴特在一首詩中寫道:
在一棵松樹上,
離我的窗臺幾碼遠的地方,
一只藍鳥上下跳躍,上下跳躍,
在一根樹枝上。
我笑了,因為我看到他全心投入,
完全的喜悅,因為他和我都知道
這根樹枝不會斷掉。
整個詩節(jié)構(gòu)成了一幅有趣的小品,由內(nèi)及外,由靜到動,由我及物,既比又興,自然生趣與內(nèi)心情緒相映照,“我”的心也隨之敞開、躍動。鳥兒臨窗歡鳴,雀躍于枝頭,讓人想起白居易詩:“晨光出照屋梁明,初打開門鼓一聲。犬上階眠知地濕,鳥臨窗語報天晴。”賴特的取景可以與白居易詩中的臨窗寫景相較,既有嵌入日常生活的趣味感,又重演了由內(nèi)及外的視角——窗如鏡框,提供了一種特有的體物方式。
這是中式的自然觀與宇宙觀,高揚生命的真性,表達活潑潑的快意,也是詩集中一系列體物詩的核心意旨。賴特詩集的題名《枝不會斷》便來自這里的詩句。詩的最后落腳在松枝之上,我們可以想象一只鳥兒在細枝上彈跳,樹枝大幅度地擺動,仿佛隨時會斷。這個形象制造了一種脆弱感與偶然性,詩人既憐愛小鳥的輕盈活潑,又在想象松枝可能的狀態(tài)。賴特強調(diào)松枝也別有用意。白居易愛松,韋利的譯集中,白居易有多首詩寫松,比如為松搬家——“移轉(zhuǎn)就松來”,自稱“松主”,又在《與元微之書》中寫布置草堂,“前有喬松十數(shù)株”。松為白氏園藝之必須,“未稱為松主,時時一愧懷”。賴特詩里的憐松之意因而也參照了白詩中松的意象。這種從日常的瑣碎中汲取意義的做法是白居易式的——賴特也會以一只松鼠的跳躍、一行螞蟻搬運花瓣的隊伍以及蟋蟀的叫聲來打破靜態(tài)的環(huán)境,抵達某種出離的體驗。在這樣的視角下,如賴特所言:“每一個時刻都像一座山。”
人類的悲歡是相通的,隔著千載,還會有一根磨損了的纖繩牽連了兩個詩人,連接在世界文學(xué)的賡續(xù)綿延中。中國的詩人如白居易對人生的甘苦體味極其深切,特別能從細微處洞察社會及個體的真相,記載人生在世的生命體驗,至今依然可以指引我們品咂其中的滋味。白居易的詩歌清淺而又豐贍,從意象、字詞、音韻的微觀環(huán)節(jié),到主旨、立意、結(jié)構(gòu)的宏觀層面,賴特均對其進行萃取,將其融到自己的審美旨趣中。這也恰是詩歌遺產(chǎn)的彈性:所謂“枝不會斷”,或許暗示了一種看似脆弱實則柔韌的精神價值——上下晃動的纖細的松枝,變成了一個關(guān)于詩意傳遞的余味悠長的隱喻。
(作者:孫紅衛(wèi),系南京大學(xué)外國語學(xué)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