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科技、幻想與人類相遇,未來意味著什么

復旦大學中文系“類型文學研究”系列活動圍繞科幻、偵探、懸疑、武俠等小說類型,及相關影視劇、游戲、綜藝等文學文化現象展開,包含講座、讀書會、工作坊等多種形式。此次“糖匪《后來的人類》讀書會”為系列活動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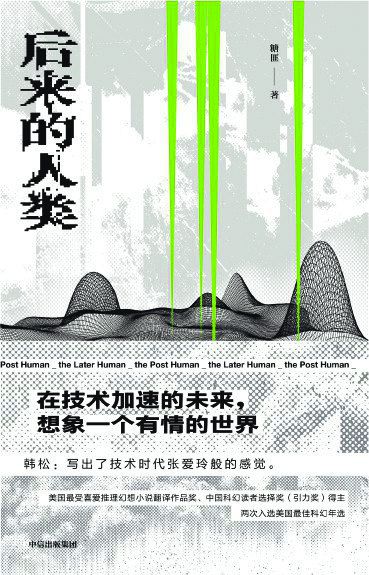
《后來的人類》,糖匪著,中信出版社,2023年4月
@謝詩豪:《后來的人類》中的“新”空間給我的印象很深,尤其是《看云寶地》中的“房間”——一個需要密鑰才能進入的云上空間,以及《快活天》里的“公寓”。克拉考爾在《偵探小說:哲學論文》中細析了教堂和酒店大堂的區別。在教堂中,個體的“匿名”是為了匯入祈禱的共同體,“站在上帝面前的人們彼此唯有足夠陌生才能互認為兄弟”,這讓他們確認了存在;而酒店大堂截然不同,其中的相聚是真的“不具意義”,“人們發現自己與‘無’面對面”。他的分析或能幫助我們理解《后來的人類》中的空間。比如《快活天》中的“公寓”。公寓中的主腦出廠名叫小壹,小說中也被稱作“家神”。“它擁有權威,照顧家中方方面面,事無巨細都在它的控制中。”實際上,如果將公寓理解為某種生活場景或方式,《快活天》里的公寓可能只是一個表象,“后來的”公寓代表的是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場景。這個場景真正的核心是“家神”。以小說中的四名女性為例,她們的生活被割裂,和朋友只偶爾在線上或線下聚會。但是在她們頭頂存在一張巨大的網絡:有“神”在看且“調度”著他們的生活,維持一種宏觀也貌似“客觀”的平衡。公寓是“神”實施力量的空間,在這里,“個體”走向無名,“后來的”世界里,“神”以服務的樣式重新出現。然而頗具意味的是,面對監控所有、無所不知的“家神”,欣敏好奇地想:家神能看到鬼魂嗎?這有對技術的反思,用鬼魂這一“過去的存在”反問“后來的”世界里的“神”,用“信仰”的存在提問技術的“神”。
@戰玉冰:我想進一步討論在“公寓”空間中所發生的日常行為實踐——家務勞動,《快活天》中對于家務勞動的書寫特別精彩。小說中,家庭主腦的普及表面上看似乎減輕了很多日常家務勞動的負擔,但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家庭中的結構性困境。家庭主腦的出現不僅沒有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女性,反而施加更多的束縛,并更清楚地暴露出日常生活中的不對等。比如想把烹飪模式改為燒烤模式這一簡單的生活需求,就需要調整房間安全參數;想要調整參數,就需要獲得相應的權限;而權限則只掌握在丈夫手中。又比如想在朋友家中試做一頓碳烤雞肉,連接炭烤箱卻需要征得全部住戶的同意。德·塞托曾將烹飪視為抵抗社會規訓、獲得個體自由的重要日常生活實踐方式之一,在他看來,烹飪過程中勞動者發揮其主觀能動性的自由時刻,就是主體性解放的瞬間。加斯東·巴什拉在《空間的詩學》中更是頗為浪漫地認為家務料理具有某種詩意,它“在一個對象與另一個對象之間編織起統一古老的過去和嶄新的日子的連線”,“家務使沉睡的家具蘇醒”。但家庭主腦的出現卻破壞了這種家務勞動中所可能包蘊的自由與詩意,一切家務勞動都有其固定的程序,必須被嚴格遵守,主體性在這種徹底的可計算性邏輯支配下遭受進一步壓抑。
小說中的雙重反抗在一開始便打下伏筆。面對失敗的料理、燒焦的雞肉與一場沒有火焰的大火,欣敏感受到并記住的卻是雞肉被炙烤后所釋放出的氣味——“真是香”。借用朗西埃的說法,欣敏的身體、感受與動作,在其作為家務勞動主體與技術規訓對象的過程中,不得不服從于其所處的社會空間與社會秩序,而嗅覺感知則意味著一種感官政治的重新分配,這是一種對于秩序規訓的逃逸和反抗、一種審美的斷裂、一個主體性解放的時刻。進一步來說,這種逃逸規訓與尋求解放的方式甚至構成了整部小說的基本結構:面對“便捷”“健康”的速成餐,她想要進行一次親手烹飪;面對時時被監控、計算的住宅與家庭,她精心策劃一場“意外”……小說中的反抗從家務勞動中的一次偶然“失控”,最終發展為一場“謀殺”。
@史建文:糖匪的寫作旨趣并非以令人目眩神迷的未來科技產物刺激讀者的感官神經,而是將關注的目光投向了時代中另一部分人群,考察“后來的人類”在不同維度空間的科技倫理下所受到的多重重壓。《看云寶地》中以新型科技構建的云上世界重新定義了人類的生存空間,滿足人們的日常需求,以至于云上的消失意味著社會意義上的“失蹤”。短短數十年間,因為云上空間的出現,現實世界的社交倫理及婚戀倫理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全新的倫理道德法則隨著新科技的誕生運用而漸趨穩定。《快活天》則將考察的視角聚焦于未來家庭,新型科技的投入使用反而加劇了人際關系中的固有矛盾。所謂為人類“孵化夢想”的集約化智能住宅本質上是為“雙系撫育”提供便利,而家庭主腦的一切運行法則即為最大化、最優化地維持家庭的正常秩序以撫育后代、繁衍族群。欣敏所在的密友圈正代表了女性的四種生存樣態,拒絕進入婚姻的阿璨最終因社會的“放逐”而走向死亡。與其將欣敏的行為定義為精心策劃的謀殺行動,毋寧稱之為捍衛生育權、生命權與個人主體性的殊死搏斗,是普通個體面對龐大的科技系統與其伴生的社會倫理法則的消極對抗。
@梁鉞皓:我關注是主體人物與客體裝置之間是否存在一種內在關聯。“科幻”對于糖匪仿佛一套陌生化裝置,與其說她的小說關乎未來,倒不如說在試圖逼近當下生活的真相。在書的后記中,她說自己更愿意在路邊就地坐下,然后看向世界。這個描述讓人想起小津安二郎的低機位,這是一種漠不關心地將目光投射至未來的視角,因為它必將被擁擠的人群和他們的日常生活所阻隔。所以,在這本小說集中我們看到的所有“后來的人類”幾乎都能在今天的世界里找到身影,小說中出現的種種未來科技裝置,也成為了這種現實隱喻的組成部分。
《快活天》中“家神”被制造出來的目的,就是在家庭內部全知全能一般地掌管一切裝置,完成一切家務勞動,并且監視整個家庭。這樣的職責讓人想起女性在家庭中古老的職責。這一點在欣敏父親的家庭變化中顯得尤為突出。一個中風癱瘓的老男人,頑固地排斥一切新科技,堅持由欣敏的母親來全權照料自己,但是當欣敏母親突然去世之后,他卻近乎基因突變般接受了軀體的賽博格改造,還有主腦的引入。這正說明了主腦是“母親”這個女性職責在家庭中的替身。由此,最詭異的一幕在家庭生活中出現了,當欣敏試圖修改參數來使用新鍋時,主腦告訴她只有她的丈夫,也就是這個家庭里唯一的男性擁有修改權。也就是說,這個全知全能的神事實上受限于那個漠不關心的男性。至此,“家神”這個稱呼幾乎變成了一種詛咒般的命名,在要求無所不能的同時也要求順從臣服。尤其是作者告訴我們,主腦的根本邏輯是維護這個家庭,它會選擇欺騙來保持家庭的穩定,就像是小說中母親的靈魂勸告欣敏不要離開丈夫。先進與古老于此交匯了。
主腦將家庭主婦從“母親”的幻覺中解放出來,欣敏和母親之間的關系,雖然矛盾重重,但并非對立,她們是共生的,如小說中一再強調的,其實沒有什么小零,那只是小壹的幻影。如同欣敏和主腦最后那場充滿了傷感的告別,就像在說,“我選擇不同,但我來自她們。”
@曹禹杰:雖然披著科幻的外衣,但是在琳瑯滿目的技術語詞背后,小說傳遞的依舊是對記憶、情感、性別等主題生生不息的觀照。值得追問的是,當科技、幻想與人類耦合的時候,人類或者人性到底意味著什么?糖匪提醒我們“后來的人類”可以從相互糾纏的兩個維度解讀,表面上,這是指向未來社會與后人類的時態語法,但它又可以指稱那些“被技術拋下落后于時代的人,那些不知不覺就從視野里消失的人”。糖匪把二者扭結在一起,在科幻語境中生成了令人膽戰心驚的反諷視角:那些看似一往無前,奔向未來的后人類,轉瞬之間就有可能成為被技術淘汰、被時代拋棄的“后”“人類”。
從后人類旋滅為“后”“人類”的成因撬動了我們對科幻文學中科技與人類關系的慣常思考,挑戰了我們對于“新人”的認識。小說最后,糖匪借助鶴來提出了另一種她所期許的“新人”形象:鶴來有著種種現實的欲望、顧慮與羈絆,他無法像成音那樣徹底舍棄過去,讓曾經熟悉的人事都“向他背轉身去”。盡管他可以帶著不變的記憶、無數過去的形象,假裝仍然活在現在,但是鶴來并不愿意成為這樣的“新人”,因為他對“關于生命的走向,時代的噪音,進化道路上一些被拋棄的和留下來的”還有眷戀與困惑。情感、記憶與現實生活的互通有無,最終促使鶴來以失蹤的方式退場,離開云上/云下這個截然對立的世界體系,雖然糖匪并沒有明確交代鶴來最終的結局,但是無論如何,他做出了真正屬于自己的選擇,創造了既定道路之外另一種可能性,“屋子里沒有人,卻有不少人生活過的細小痕跡,就像那種主人暫時出門的屋子……清丑頑拙的神秘空間。似乎在前一秒剛剛成新。開天辟地般的新。”失蹤的鶴來最終成為了一個似新實舊,似舊實新的“新人”。
趙園曾這樣定義她心目中的“新人”:“無論在生活還是文學中,準確意義上的‘新人’,應當指人群中的那一部分,即集中地體現著時代精神和時代前進的方向,對于‘使命’更為自覺,依歷史要求而行動的先覺者和實踐的改革者。”無論是在科幻文學的脈絡中,還是在19世紀中葉以俄羅斯作家和批評家爭鳴的“新人”譜系中,抑或是糖匪自身的創作流變中,《看云寶地》所提出的對于“新人”的思考都有難能可貴的意義。何為“依歷史要求而行動”?何為對“時代精神和時代前進的方向”的自覺?何為真正的“新”?借助科幻書寫,糖匪將這些在技術浪潮中逐漸被淡忘,但又值得我們時時反顧的命題重新問題化。正是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中,可以看到,糖匪在過往作品中反復觸及的命題,如代際關系、技術倫理在《后來的人類》中逐漸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對于人性、生活與現實的感受、探索與追問,這是真正的貼地飛翔。糖匪未來的創作值得期待,這并不是在翹首等待一個典型“新人”的出場,而是在瞬息萬變的現實與無遠弗屆的未來中,守望永遠自覺、先覺且永不定型的人性與人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