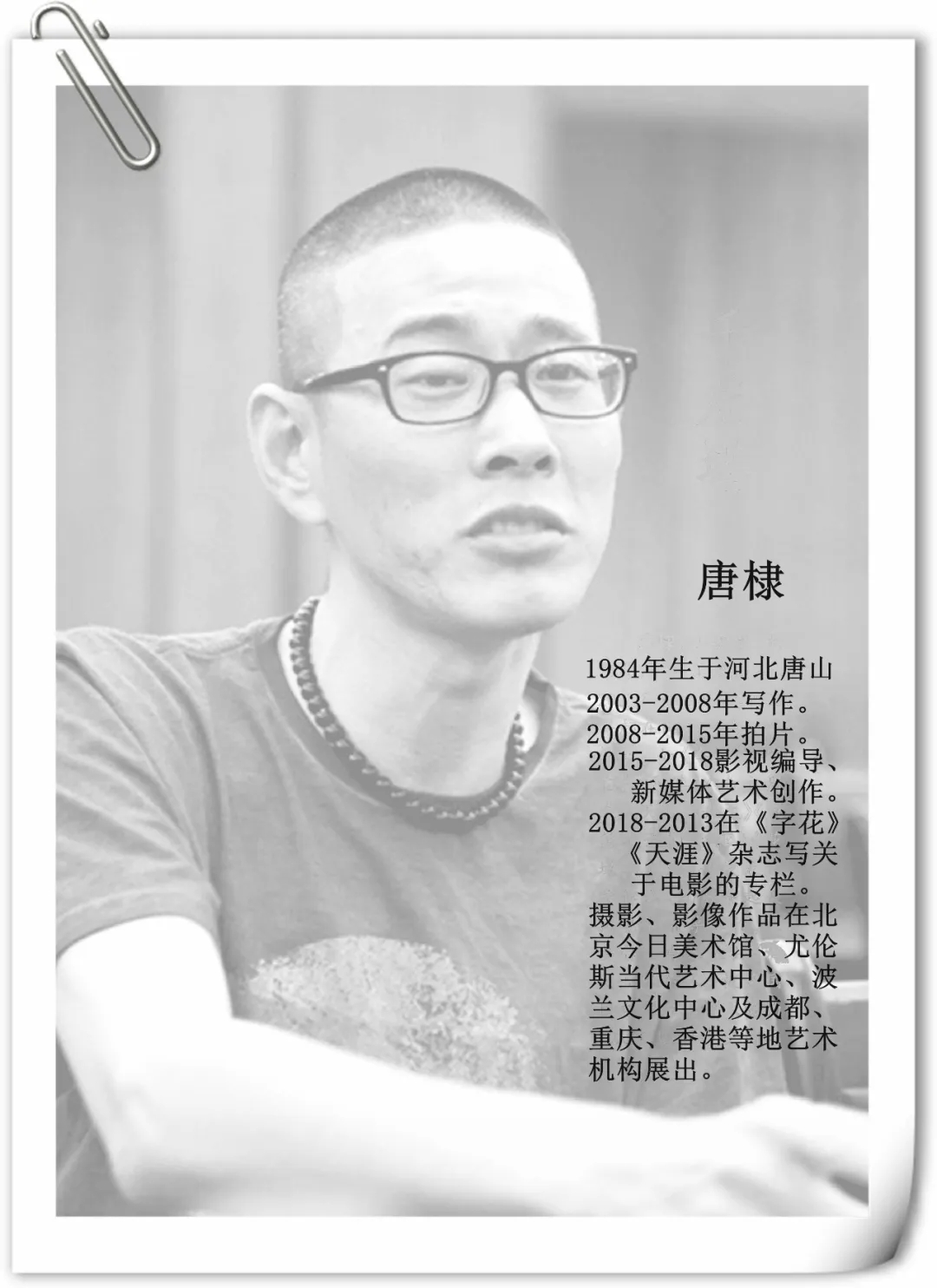《野草》2024年第3期|唐棣:相逢無名氏
一
“無名氏”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群體,甚至比群體更大。現實中和文學史上太多這樣的人了,為人有意思,做的事也有價值,我一時間也不知該怎么更好地形容他們。一直帶著這個想法等待,好多年就這么過去了,記來記去,我腦子里也只留下了幾個無名氏,畢竟應有的記錄不多,相逢的契機少了一點。
在我看來,瑞士作家羅伯特·瓦爾澤就是一個文學史上的“無名氏”。我一度把他和德國作家馬丁·瓦爾澤搞混。看書就是這樣,我又不打算做研究。混淆有混淆的好處,在當時羅伯特·瓦爾澤的書種類不多的情況下,反而有幸把兩個瓦爾澤的書都讀了一下。這幾年,一向自稱失敗者的羅伯特·瓦爾澤,在中國迎來了大量年輕讀者。中國這一代年輕人在失敗的意義上找到了共鳴。每個人成功的標準不同,沒有人知道瓦爾澤為何自稱“不成功的寫作者”。我這里說的“失敗”,更像是在形容一種生活受阻的感受。
瓦爾澤的生活,總是給人一種灰溜溜的感覺。十四歲時,他就被家人送去本地銀行做了學徒,熬到十七歲,獲得銀行正職后他忽然辭了職,從此以后在社會上頻繁更換工作。他做過舞臺演員、小店的服務員、辦公室職員等等,1905年隨家人搬到柏林。他很早開始寫作,但寫作始終沒有為他帶來任何現實回報。荷爾德林書中有一句話:“在我的職業里,人們獲得的結果在本質上都太隱秘了,讓人難以感受到它的力量。”也許,寫作這個事為瓦爾澤帶去過某種隱秘的力量吧,反正他經常失業,不斷停止一件事再改做另一件事,只有寫作沒有停止過,直到1913年回到瑞士故鄉。有人問他,為什么不去巴黎。當時,所有文藝人士都往巴黎跑。瓦爾澤連去那里的勇氣都沒有,“對我而言,在柏林受到重挫之后,退回到小小的故鄉,是唯一正確的選擇。”(《與瓦爾澤一起散步》)
瓦爾澤在寫作上已經很努力了,早期也充滿熱情。他第一部長篇小說《坦納兄妹》一開頭,寫的就是一個叫西蒙的年輕人熱情洋溢地到書店應聘店員。在西蒙的想象中,賣書“讓人著迷,奇妙又可愛”,所以他想自己一定能堅持“賣書”很多年。可是理想豐滿,應聘成功后的第八天,西蒙就不干了。這樣的事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家人擔心他,但他嘴上能說出的辭職理由都不是真正的理由。他也不明白,自己到底為什么不想工作了。
如阿城所說:“道德是一種規定,道變了,相應的德也就跟著變。”到了現代社會,不想工作的人越來越多,相應的看法越來越寬容,哪怕職業道德也面臨著變化。
這一代讀者和媒體把西蒙視為“反內耗”的職人代表。在這個為讀者帶來爽感的形象樹立起來的過程中,我有個小發現:工作也是一種身份限制、道德規定。干了這個,就不能干別的,打破規矩的事牽扯著你的工作前景。你的精力總有被耗光的時候。
那時候又該怎么辦呢?我不認為瓦爾澤是一個這方面的好榜樣。他晚年與朋友卡爾·澤利希的散步聊天中,回憶起這本“自反”色彩過重的小說時是有反思的——“人不應該否定社會。人必須生活在社會中,或為之斗爭或反對它。”(《與瓦爾澤一起散步》)
二
“藝術,尤其是文學,之所以非凡,之所以有別于生活,正在于它憎惡重復。”詩人布羅斯基這篇文章的題目很直接,就叫《文學憎惡重復,詩人依賴語言》。現代文學、藝術似乎也都是來自生活,始于“為之斗爭或反對它”這個意識的,而且最愛討論的不是想象的無限,而是生活中的種種限制——身份只是其中之一。
說起文學史上有意思的身份,不能不提卡夫卡《審判》的主人公K。這個人在冒充土地測量員以前,只是一個想在村子里安定下來的流浪漢。在村里一個客棧入住,睡得正香時,他忽然被一個年輕人叫醒。得知村子屬于城堡,想要在這里入住,必須得到城堡主人的允許,他就這樣被驅逐出村。在一次偶然情況下,他聽說城堡主人正在等一個土地測量員,于是立馬自設限了一下。
先別管K知不知土地測量員是干什么的,但他知道這個身份對自己有好處——自己演得越像土地測量員,越有機會接近城堡。只要走進城堡,就離見到城堡主人,得到允許就不遠了。
《城堡》的故事,只講到了K發燒、臥床不起,等待是否同意他進入城堡的消息。事實上,這個小說和卡夫卡其他幾個長篇《美國》《審判》一樣,戛然而止。
有人猜《城堡》的結局是K在彌留之際,城堡的通知來了,他可以留在村里,但不許進入城堡。
其實,還有一個更悲觀的結局:后來K病痊愈,城堡通知沒有來,他又被開頭驅趕他的年輕人,再次趕下了床。卡夫卡很可能會這樣寫。現代派小說家都喜歡這種結構,像加繆筆下的西西弗一樣,每天推著石頭上山,然后石頭滾下來,他繼續推。K的話,就是繼續扮演土地測量員,繼續等待城堡的通知。
我看一些人說《城堡》的主題是各階層之間的溝通障礙,尤其是底層和上層之間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不僅這篇小說的主題是這個,我覺得,卡夫卡所有小說主題幾乎都是這個。在這個意義上,卡夫卡寫下來的,的確是現代主義小說,與之相配的現代社會里的確出現了這個狀況。
詩人米沃什曾在一篇短文中思考過這個問題,并且自問自答。最后,他說:“溝通的價值有賴于承認自己的局限,而神秘的是,這些局限也是很多其他人共有的局限。”從過去發展到現在,直到未來,這些問題都存在的,不明白、迷失了,這都再正常不過。
也許,一般讀者都認為卡夫卡寫的東西過于抽象,過于藝術化,難懂,但他描述的冷漠、孤獨、沉默,每個現代人都不陌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解。
在不讀卡夫卡多年之后,我偶然翻開一本德國小說《一把雨傘給這天用》。小說主人公是個“鞋子測試員”。鞋子測試員的工作是,穿上半成品的高級皮鞋到處走路,直到“摸清鞋子的特性,并且能夠貼切地描述一雙鞋子的舒適程度,尤其是鞋子對腳跟與鞋頭可能產生擠壓的地方。”這個工作很像主人公本人境遇的隱喻:他是經過高級教育的人,社會上卻沒人認可他的才華,于是他只能每天在被小混混毀壞了長凳、沒人注意的河岸邊走來走去。“沒人注意”這點很重要,在邊緣地帶,除了他們自己,沒有別的人影——K是在“城堡”外圍打轉,也不希望有人看見自己。鞋子測試員則是在被人忽略的河岸默默干他的活兒。和K略有不同的是,鞋子是存在的、具體的,而城堡幾乎是一個不存在實體的“目標”。鞋子測試員的喜怒哀樂特別具體,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了,最后這個故事也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走向,就是這個鞋子測試員和女朋友結束約會,明天還要繼續工作,“我卷入令人厭惡的工作,或卷入了處理厭惡的工作,或卷入了真正的厭惡,我這時候無法明確分辨出這些差異。”真正悲哀的還是K,他幾乎陷入了死循環:目標越虛幻,他越沒辦法停下來。生活不停,他也不會停,朝著目標前進,變成了一種純粹的活著的動力。
在我看來他們不是失敗者,而是“能屈能伸”的小人物,因為他們信念是堅定的,“盡管有些荒謬存在,我至今尚未發瘋。害怕發瘋往往只是在害怕投降。”(《一把雨傘給這天用》)這些人是不對現狀投降的人。但在長期、機械性的生活中,必須找到一個有效的紓解方式,避免發瘋。
沉默就是這時候來的。不像我們過去認為的那樣,沉默只是一種表現。現代小說里的沉默,接近一種相對“積極”的應對方法,“克制是我擁有的唯一武器,也是地位卑微的我唯一能擁有的。”(《與瓦爾澤一起散步》)
德國作家威廉·格納齊諾的《一把雨傘給這天用》,寫出了現代人焦慮、沒安全感、窩窩囊囊的生活,最后把“出口”落在了沉默上,如主人公所說:“事實上,我越來越不想說話,這讓我有點害怕,因為我不知道我這輩子這么多沉默的時刻是否還算正常……我近來想到,該寄給我認識及認識我的人一份沉默時刻表。星期一和星期二會是一直沉默,星期三和星期四只有早上一直沉默,下午則是寬松性沉默,也就是可以短暫交談和短暫通電話。只有星期五和星期六,我會愿意說三道四,不過也要十一點以后。星期天則是絕對沉默。”
顯然只是這么一說,鞋子測試員還是要去和客戶、皮鞋制造商溝通——事實上,連土地測量員K都得和能幫助自己進入城堡的村長、村學校領導等人溝通。這種溝通可能是無效的。城堡在哪,這些人都不知道,所以他越努力溝通越無效,離目標越遠。
三
一八五三年,美國作家梅爾維爾創造出了“巴特比”這個文學形象。如今,這個形象已經被各個研究領域覆蓋了。寫《抄寫員巴特比》這篇小說時,梅爾維爾三十四歲,他預感到自己的寫作生涯將全然失敗,前途一片渺茫,于是有點自我投射性質地寫了一個在華爾街律師事務所上班的抄寫員的故事。
在沒有打印機的時代,抄寫員的工作不允許有自我,越準確越像原始材料越好。巴特比就是干這個的,可是有一天他不干了。不僅拒絕工作,還不肯離開辦公室,除了“我寧愿待著不動”“我更喜歡不”這兩句話之外。徹底沉默,直至一動不動地死在了監獄里。
過去我們可能沒注意到,在少數創造者與大多數大眾之間有這樣一個群體——他們從不創造,只是重復,但創作者名垂青史,又離不開他們。一切都不影響他們繼續無名下去。幾個現代社會精神代表性的形象:西西弗、K、巴特比,全部來自西方文學。前兩者是機械生活的執行者,巴特比算是半個覺醒者,他這一停,除了意味著失敗,也宣布了反抗。
抄寫這個工作也看成是一種對文字的測量和測試。大小、結構、布局等等都涉及尺寸(限制)概念。機械復制時代來臨前,這個工作對某些重要文件和藝術品的流傳起著重要的作用。我們古代也有這樣一種“搨書手”的工作,只是古籍、文獻上的記錄不多,但不等于他們不存在。
一次偶然的契機下,我讀到了一段德國人本雅明對“搨書手”這個工作的描述:“抄寫的文本,就這樣單獨指揮著抄寫者的靈魂,而純粹的讀者絕不會發現文本內部的新視角,絕不會發現文本怎樣穿過越來越稠密的內部原始叢林開辟出那條道路,因為純粹的讀者在他如夢般自由翱翔的領地依隨的是那搏動著的自我,而謄抄文本者卻任憑它發號施令。因此,中國謄抄書籍的實踐就這樣無與倫比地成了文字文化的保證……”
搨書手和巴特比干的工作內容差不多,從來沒人寫過他們中的任何人。搨書手兢兢業業地謄寫著,最后消失在歷史中,極少出現在歷史典籍上,更不會隨著模寫出的作品而被流傳。大部分人已經忘記他們的存在。
無名搨書手和一個字母的簡稱K,再加上連名字都沒有的鞋子測試員,似乎在提醒我們,抄寫員巴特比和書店店員西蒙這種人,忽然停下工作——為之斗爭或反對它的意義。順著這個思路我也在想,也許他們就是真實地反應了內心而已,沒有被生活挾持。
這一停,世界就可能會發生一些微小又劇烈的變化,這些變化累積到一個神秘峰值,說不定生活已慢慢變成另一番樣子。也許古老的問題并不會全消失,但歷史上的每一次小改變都至關重要。
那時,我們迎來的就不再是沉默,而是一個全力創造、留下痕跡的生活局面了——這是個人意義帶來的好處。但我們也得看到,巨大的壓力也會把現代人打趴,宋元文人畫的出現就是個例子——從無名作者簽名的一刻,社會責任就壓下來了。個人真的有那么大的抗壓力嗎?現代社會,個人意識崛起后,藝術家“被打趴”的表現就是發瘋,古往今來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以前集體藝術的背后是無名工匠的付出,在人數、壓力和技術上,文人畫無法和秦漢輝煌的藝術相比,原因大概就在這里。
四
1944年1月2日,在一次外出散步的路上,朋友忽然問瓦爾澤要不要去看荷爾德林紀念碑。當時他們離那里很近,瓦爾澤說:“荷爾德林的命運只是在這里上演的眾多人類命運之一。不應因為有名的人而忘記那些無名者。”我不記得,最終他們去了沒有,但記住了這句話。以現在的觀點看瓦爾澤,他已經非常有個性了,但在他那個年代的處境,和我們在這個時代一樣,我們可能比他更清晰地認清了一個事實:機械復制時代就是一個抹去個性的、充滿無名氏的時代。
我忽然想到輝煌的藝術史上,從無名氏到有名者的那些變化。文藝復興前,西方繪畫都是宮廷向繪畫作坊定制。作坊是合作制的,由分工明確的匠人組成。匠人們只需要掌握自己的技能即可,然后大家分工,按步驟完成繪畫。那時的匠人享受著“無名”的保護,他們不承擔壓力,通常干完自己的活兒就休息去了,第二天接著干。文藝復興來了,個人有機會獨立接單,署名意味著責任,你不僅要一筆一筆創作,還要為作品產生的社會效應負責。繪畫的定制方沒有變,都是特權階層,一旦發生問題,你就完了。
在我們的歷史上,中國畫發展到宋朝都不興簽名和題款,雖然都是自己畫,但按傳統都避諱彰顯自我。名畫《溪山行旅圖》上沒有作者信息,期初被認為符合歷史記載。后來有專家在畫的角落,偶然發現了作者范寬的小心思——他在茂盛樹木的縫隙處簽了名。
在長期由無名氏組成的藝術史上,這個事很大條。其實,藝術之外的歷史很缺乏類似的改寫。現代生活造成了無名氏越來越多,甚至多到無以數計,可以決定藝術家只能是少數派的地步。個性看似受到包容了,其實越來越稀少。
寫作圈子中有不少有個性的無名氏。這些人保持著和世界緊張的關系。我覺得,無名很可能保護了現代社會上的這種人——劍拔弩張的關系,隨時可能傷到自己,倒不如像沉默一樣,把脆弱的人包裹起來,至少可以默默寫下去吧。
“此時此刻,當我把這些話寫在紙上,無數其他人也在做同樣的事,而我們這些用色彩明亮的封套包著的書,將被加入那一大堆其姓名和書名淹沒和消失的書中。”詩人米沃什說的,是一種普遍的境遇。假如,現代人還覺得真實生活是重要的,那么我就可以引用哲學家馬丁·布伯在那本1923年出版的小書《我和你》里說過的那句話了:“所有的真實生活,都是相遇。”
在我的想象中,最重要的一場相逢是推石頭的西西弗、土地測量員K、鞋子測試員,以及搨書手,從書中走出來,站在一座橋下,抬頭仰望。視野盡頭是,離職店員西蒙和抄寫員巴特比,他們走向了一架由沉默搭起的窄橋(瓦爾澤原話:“我們在沉默搭起的窄橋上相會。”)
就在那個相逢的瞬間,兩個人重疊在一起,只剩下一個人的形象(他們本來就是不同時期精神敏感的人的代表)。既然生活已經很荒謬了,那為之斗爭或反對它,也許就是為這一幕發生,創造了一個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