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里新文學——浙江新荷作家群巡禮”系列訪談 池上:我更在意和享受寫作時的全身心投入
編者按:
“浙里新文學——浙江新荷作家群巡禮”是浙江文學院推介文學新人的重要舉措。中國作家網特邀入選該推介計劃的9位青年作家進行獨家專訪,傾聽他們的成長故事,聚焦當下青年寫作的來路與遠景。

池上,1985年生。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杭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先后在《收獲》《十月》《鐘山》《作家》《江南》《山花》《西湖》等刊物發表小說若干。獲首屆“山花小說雙年獎新人獎”、第六屆“西湖·中國新銳文學獎”。出版小說集《鏡中》《無麂島之夜》。
大學畢業后,池上進入一所小學教書,一開始她還擔心學校“簡單”的環境會讓她的經歷也變得“簡單”,但在學校的時間越長,她越來越意識到,經歷“豐富”并不一定指向創作“豐富”,經歷“簡單”也未必指向創作“簡單”,像威廉·福克納和艾米莉·勃朗特這樣沒有傳奇人生卻仍舊寫出不朽作品的作家亦不在少數。事實上,池上筆下一系列校園題材小說面向孩子,更面向成人;關注學校,更關注社會現實,呈現出更為復雜多向的面貌。2022年10 月,池上最新中短篇小說集《曼珠沙華》將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這是池上的第三本小說集,她雖然寫得慢,但這么多年以來,她一直在斷斷續續寫作,也并不在乎外界的眼光,正如她在受訪時所說,“我自身沒有標簽,也不怕標簽,因為標簽既然可以貼上,也可以撕下,那代表不了全部的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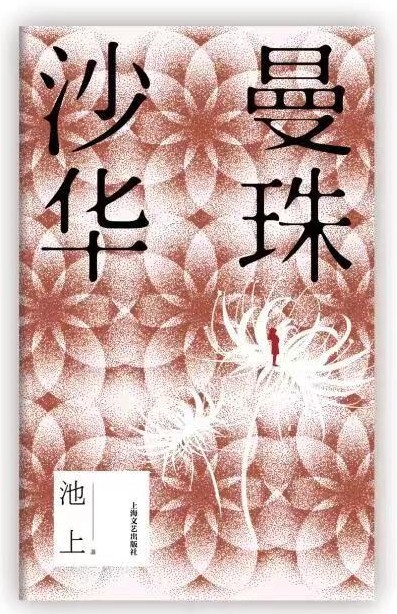
池上最新中短篇小說集《曼珠沙華》將由上海文藝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
中國作家網:能先說一下“池上”這個筆名嗎?背后有怎樣的故事?
池上:很多人第一眼看到這個名字都會想到白居易的那首同名詩,也有人會想到臺灣那個著名的產米之鄉。但事實上,它和這些無關,和它有關的其實是杜甫的一首詩《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里面有句“池上于今有鳳毛”。
中國作家網:你的創作經歷大概是怎樣的?除了寫作,還有哪些愛好?
池上:大四寫下第一篇短篇小說,之后寫寫停停,好在最后堅持了下來。生活中,我熱愛追劇、旅游、美妝護膚、服飾搭配,但最愛的還是宅家發呆。
中國作家網:能否談談創作和生活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如何從生活中提取創作素材?
池上:在奧威爾題為《一次絞刑》的隨筆里,犯人在走向絞刑架的途中,避開了一個小水塘。詹姆斯·伍德的《小說機杼》對此做了如下描述:“邏輯上說犯人確實沒有道理避開水塘。這純粹是一個舊習的條件反射。而生活中永遠難免有一些過剩,有一些無緣無故,生活給我們的永遠比我們所需的更多:更多東西,更多印象,更多記憶,更多習慣,更多言語,更多幸福,更多不幸。”我以為用詹姆斯·伍德的這段話來解釋創作和生活的關系再合適不過。作家首先得擁有一種剔除生活中過剩東西的能力,但僅僅如此顯然還不夠,一名優秀的作家理應關注到那些“無關”——就像犯人避開水塘的做法毫無意義(他的生命馬上就要被剝奪),但他還是選擇了避開,只因為不想弄臟鞋子——無關緊要卻又意義重大,多么絕妙!
中國作家網:你覺得,學校環境和教師身份給你的小說寫作帶來了什么樣的影響?
池上:大學畢業后,我一直在一所學校教書,以至于有一陣子我覺得自己的人生經歷未免太過簡單。我羨慕那些簡歷上寫有N種工作的人,也曾想過來一次說走就走的辭職,但如今年歲既增,我越來越覺得學校環境給了我一種特有的松弛感。這并不是說學校工作有多輕松,而是說學校的氛圍,特別是和學生之間的相處能讓我保持一種少年感。且每一屆學生和學生之間是不同的,每一個學生在成長過程中也有其細微的變化。這世上固然有許多書寫自己豐富人生經歷的作家,但像艾米莉·勃朗特這樣沒有傳奇人生卻仍舊寫出不朽作品的作家亦不在少數。
中國作家網:你會給學生講文學作品(包括您自己的)嗎?他們的接受度如何?在閱讀內容極為豐富多樣的網絡時代,他們的閱讀和寫作怎么樣?
池上:作為一名小學老師,我很難直接讓孩子閱讀我的作品,但這并不妨礙我和他們的文學交流。在寫作的起步階段,我更關注的是孩子們對寫作的興趣而非寫作的技巧等。回憶一下我們小時候,是不是一提到寫作文就頭疼?討厭一周一次的周記,還有每次春游回來后都要例行寫一篇游記。所以,我所帶的班級從來不布置周記或是春游后的游記;我也不讓他們看范文大全之類的書。因為很多范文本身并不具有靈氣,不過是一些陳詞濫調組合而成的大雜燴。有這個時間,不如多閱讀一些經典名著。事實證明,這樣的操作完全可行。我班里的孩子們并沒有因為寫作數量太少而質量下降,相反,他們總體的質量很高,且部分孩子很有靈氣。他們的閱讀量也相當大,至少比我小時候大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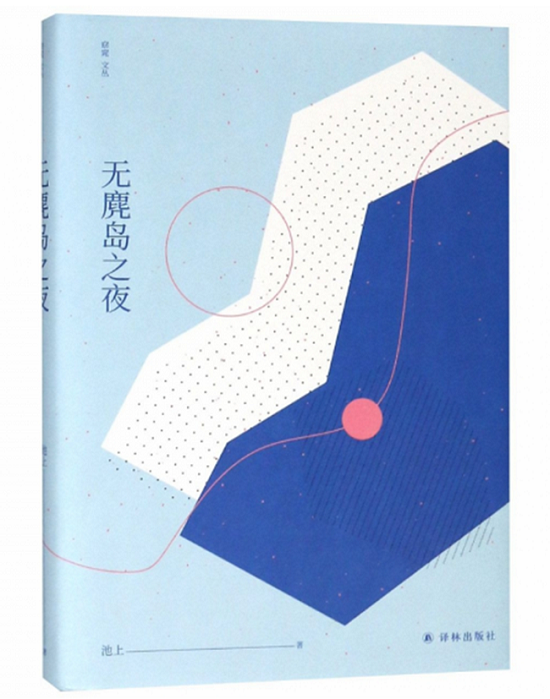
池上小說集《無麂島之夜》,譯林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
中國作家網:在你的小說中,“鎮”這個地理概念頻繁出現,比如,《靜川》中的白葦鎮,《在長樂鎮》中的長樂鎮。《在長樂鎮》中的唐小糖路過長樂鎮,就住了下來,而長樂鎮并非她的故鄉,也不是她的目的地;《靜川》中的少女靜川就想生活在白葦鎮,哪怕姐姐蕓溪勸她去遙遠的杭州她都不為所動。作為城市與鄉村的過渡點,“鎮”在你的筆下似乎被賦予了特殊的含義,而你在寫“鎮”時,似乎也更從容更平靜,也總會多寫一些鎮上的水和橋、云和風等自然風物的文字,“鎮”不僅僅是一個地理概念,似乎更是一個情感概念?
池上:有一種說法是許多作家終其一生都在文字中尋找童年,重返童年。我的童年是在浙江余杭長樂鎮附近的一個農場度過的,直到初三才回到杭州。和福克納筆下的約克納帕塔法不同,起初,我并沒有刻意去創造我的一個文學地域。“長樂鎮”也好,“白葦鎮”也罷,一切好像是自然而然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既是城市與鄉村的過渡點,同樣也承載了我從兒童期到青春期的轉變(我初一、初二去了鎮中,之前在農場念小學)。
長樂鎮當然不是我的故鄉(在我固有的概念里,我的故鄉在農場);它亦不是我后來的落腳地(那座人人向往的省會城市)。但如您所說,在我的作品里反而是它顯露出從容平靜來,既不似農場那般“暗流涌動”,又不若城市給以一種“壓迫逼仄”之感。想來,可能是恰當的距離反而讓我和它有了一種特別的情感。
2001年,長樂鎮和其他兩個鎮合并,合稱“徑山鎮”,從此,“長樂鎮”在地圖上消失了。有一天,我的一位朋友轉發來一段文字,說是她的朋友看到我的小說,說她熟悉的長樂鎮又回來了。我想這就是文學的力量吧。
中國作家網:從小說主題角度來說,你的很大一部分小說似乎都呈現出成長小說的某些特質,早期的《靜川》,近兩年的《創口貼》《藍山農場1997》《曼珠沙華》等都屬于此類,不過,如果說《靜川》還以家庭為中心通過描摹少女靜川青春的感傷與愛情的幻滅記錄成長歲月,那么,小說《創口貼》和《藍山農場1997》則移位學校,前者以細密的事件呈現程小雨與潘家和的暗中較量,后者在“我”、王東東、許樂文、趙安琪等人物之間圍繞一輛被盜的自行車牽扯出種種復雜糾葛,他們的成長顯然比靜川的成長“復雜”和“艱難”。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你如何看待?
池上:如果單看《創口貼》《曼珠沙華》里出現的學生、教師,確實很容易讓人想到成長小說,但“成長”這兩個字顯然不僅僅止步于青春期的成熟。《靜川》的寫作初衷是寫一段青春的感傷,因此天然就有一種懸置感;而《創口貼》《曼珠沙華》關注學校、社會等現實問題,《藍山農場1997》則涉及到知識青年下鄉的歷史。在寫這幾個小說的時候,我寫了成長中的孩子,也寫了成長、變化的成年人,他們交織在一起,使得他們的成長顯得更“復雜”和“艱難”。
中國作家網:你近期的一篇小說《情緒帝國》(發表于《青年作家》2022年5期)以控制情緒、切斷情感為切入點,在充滿“海葵”“藍星”等科幻元素的敘述中,意圖構建人類未來世界的烏托邦,結構方面也以章節形式展開,呈現出與你之前作品完全不一樣的面貌。怎么會想到要寫這樣一篇小說?凝聚了你的哪些思考?
池上:在回答這個問題前,我想先講一個故事。據說當年拜倫與雪萊在日內瓦徹夜暢談,興致所至時,拜倫提議在場所有人各寫一篇神怪小說以做紀念。孰料兩位詩人沒能完成約定, 瑪麗·雪萊卻寫出了一篇小說,這篇小說便是文學史上第一部科幻小說《弗蘭肯斯坦》。之所以講這個,是想表明作家的創作動機各式各樣,而創作這篇小說的契機源于對于人類文明飛速發展的另一種思考:發展的催熟一旦產生,整個變化的進程很有可能失控,而其中最極端的例子恐怕便是斯坦利·庫布里克的電影《奇愛博士》。

池上小說集《鏡中》,浙江文藝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
中國作家網:有沒有這樣的時刻,讀者看不出來,但是對你個人而言具有分水嶺意義的寫作時刻?
池上:作品是有其文運的。每個作品一經發表就不只屬于作者本人,而它能不能受到讀者的認可,產生更大的影響則和很多因素有關。我把這些看作是寫作所帶來的附屬品,更在意和享受的是寫作時全身心投入的每一刻。每一次的寫作都是一次新的挑戰,一次新的出發,至于我個人的分水嶺自己清楚就行。
中國作家網:你會關注同代人寫作嗎?如何看待自身標簽以及當下的青年寫作?
池上:會,但關注不多。我覺得我們就像置身在一個喧囂的菜市場,和各種自媒體公號、短視頻的“吶喊”“奪眼球”相比,寫作顯然是沉寂的、孤獨的。但就像“小說就是小聲地說”,寫作借此回歸到了它的本位。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還有人愿意堅持寫作,這本身不就是一種莫大的鼓舞嗎?我自身沒有標簽,也不怕標簽,因為標簽既然可以貼上,也可以撕下,那代表不了全部的我。
中國作家網:最近在忙什么?寫了什么新作品?
池上:最近在寫一個系列的小說,寫得很慢,但好在我不著急(反正我一直寫得很慢)。另外,我的新中短篇小說集《曼珠沙華》馬上就要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在此,也給自己的新書打一個廣告。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相關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