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菊的茶山》創作手記:杏花消息雨聲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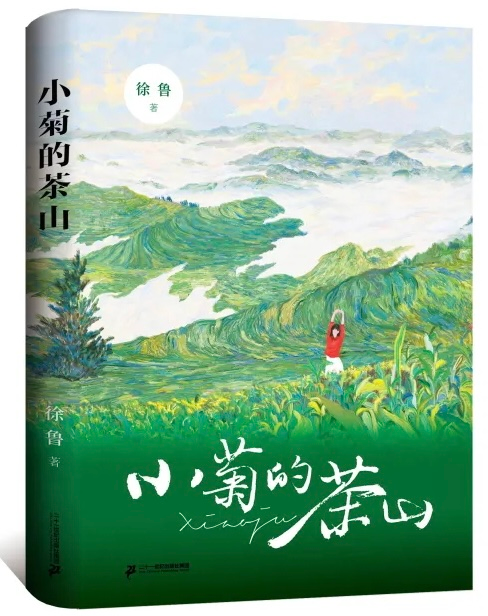
一、夙愿
2019年,一位素不相識的音樂學研究者、湖北科技學院音樂學院音樂系主任栗建偉博士寫信給我,說他正在做一個鄂東南民間文化的研究課題,他把自己撰寫的一篇長篇論文初稿發給我看,征求我的意見,論文題目是《陽新縣文化館鄂南民間音樂工作研究——以徐魯的文學記載為例》。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從沒想過,早些年寫下的一些幕阜山地域文化題材的文字(主要是散文),能成為民間音樂研究的素材。不過,栗老師的研究題目也透露出一點信息,就是我與幕阜山區、與鄂南陽新縣民間文化的淵源,著實不淺。
三十多年前我在鄂南陽新縣人民文化館工作過多年,所從事的是一種“烏蘭牧騎”的工作。我剛到文化館第一天,一位老館長、也是鄂東南民間文學專家梁萬程就諄諄教導我說:“我們是人民文化館,你來了,我們又多了一名烏蘭牧騎隊員!”他還給我解釋說,“烏蘭牧騎”的工作就是要深入到幕阜山區最偏遠的農村去,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勞動,簡稱“三同”。
幕阜山區橫亙在贛、湘、鄂三省交界處。我當時的工作之一,就是深入幕阜山中的窮鄉僻壤,去搜集民間故事、歌謠和小戲唱本,就像當年的格林兄弟深入德國偏遠的鄉村,去收集民間童話故事一樣,同時也給一些鄉鎮文化站和鄉村小劇團修改戲本,做一些創作和演出的輔導工作。這種身份當時叫“文化輔導干部”。除了收集和整理民間文學,還要經常送文化下鄉,要去輔導和組織鄉鎮和村里的業余文藝創作和群眾文化活動。比如,村里或者鄉鎮文化站要組織演采茶戲,如果正好我們這些人在場,還要臨時幫演員改戲本、寫幻燈字幕,幫著搭戲臺、搬道具、甚至給演員化妝,等等。遇到“三夏”和“雙槍”的農忙時節,就要挽起褲管,下田幫著割稻、栽紅薯秧、運送秧苗,等等。這是真正的“深扎”,也是完全意義上的“三同”,比現在的作家浩浩蕩蕩組成團去“采風”,要艱苦得多,也深入和扎實得多。
那時候,幕阜山區一些偏遠的小山塆還沒有通上電,需要走夜路時,房東就會舉著松明子或點上“罩子燈”,給我們引路和照明。在幕阜山區的崇山峻嶺間走村串戶、搜集民間故事和戲本的那些年,是我迄今為止最“接地氣”的一段生活。饑了餓了,走進任何一戶人家,都能吃到熱騰騰的、散發著柴禾氣息的鍋巴飯和老臘肉。渴了乏了,就猛喝一頓山泉水。翻山越嶺走累了,呼嘯的山風為我擦拭汗水。當年幕阜山區也還沒有實行禁獵,我也曾被允許跟著老獵戶去打過兩次獵,獵槍就是長長的火銃。有一次老獵戶打到了一只野物,他告訴我這叫“豹貓”,山里人又稱“飛虎”。現在,這些珍稀的野生動物當然都是當地的保護對象了。
鄂南地處吳頭楚尾,方言里猶帶吳音,而且保存著許多古雅的字音,比如把耕田叫“勸春”,玩耍稱為“戲”,穿衣稱為“著衣”,給客人添加酒水,叫“酙酒”,稱你為“乃”,稱我為“阿”或“吾”,稱他為“其”,把樹葉叫“木葉”,洗臉叫“抹臉”,棉背心叫“棉褡魂”, 下小雨叫“落細雨” 太陽叫“日頭”,白天稱“日分”,夜晚稱“夜分”,天亮叫“天光”,放牛叫“秧牛”,砍柴叫“斫柴”,選種叫“秧豆”。倘若遇到什么稀奇事或值得夸贊的場景,上了年紀的老人嘴里,瞬間就會蹦出了一兩個現在已經不大使用了、但在幕阜山區依然保存至今的文言嘆詞:“噫,好矣哉,好矣哉!”
理解力栽培下的東西,季節會使它們成熟。雖然離開了云遮霧罩的幕阜山區已經多年,但那里的草木和牲畜,它一年四季的雨絲風片,也時常縈繞在我的心頭。還有我所熟稔的那些茶山、竹林、橘園、稻田、山坳、河流、渡口、井臺、涼亭……也都在我的心底記憶和保留得清清楚楚,并且一直在溫暖地愛著和回憶著。所以近幾年來,我一直想寫一本類似沈從文的《邊城》和孫犁的《山地回憶》式的小說。《小菊》的完成,也算是了了我的一個夙愿。
二、文心
在創作之初,我這樣設想著:要努力去寫出一部帶著四月茶山的清新與明麗的色調,既能展現幕阜山區的地域風情之美和人性之美,又能呈現新時代鄉村振興的時代氣息的小說。
我很喜歡沈從文、孫犁兩位老作家那種半紀實、半虛構的小說文體。沈從文的作品暫且不說,我讀孫犁的《琴和簫》《荷花淀》《蘆葦蕩》《采蒲臺》《山地回憶》《蒿兒梁》《紀念》這些短篇,甚至到他晚年創作的“蕓齋小說”系列,其實很難分清,這是些虛構的小說,還是些真實的紀實故事。“我”(作者)自己的足跡、身影、聲音、行止、所思所感,散落在每一篇短篇故事的字里行間。《山地回憶》寫的是“我”在太行山區打游擊的日子里,有一天來到一個熟悉的小村外的小河邊,其中有一個細節:在河邊洗菜的小女孩端著菜走了,“我在河邊上洗了臉。我看了看我那只穿著一雙‘踢倒山’的鞋子,凍得發黑的腳,一時覺得我對于面前這山,這水,這沙灘,永遠不能分離了。”這樣的細節和感情,顯然是來自作者真切的經歷與體驗。
我對于幕阜山的感情也是如此。當我在暌違多年之后,重新站在富水河畔,看著暮色里的楓林渡口、茶亭,還有遠處的山嶺、田畈和一座座燈火初上的小塆……那一時間,我的心里也涌上了與孫犁在《山地回憶》里同樣的感受:這些都像是我的故園一樣,分別得再久,也永遠不會失卻和淡去那份溫暖、那份親切的感覺。我甚至感到,我和這里也是永遠不能分離了!
在這部小說里,我采用了孫犁小說的那種既是寫實的、又帶點抒情意味的散文般清新明麗的筆調,描繪了在全國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大背景下,贛湘鄂三省交界的幕阜山區的奮斗故事與現實風情畫卷。我試圖用云霧繚繞的青翠茶園、風雨百年的義渡渡口、農家書屋的燈光、飄飛在青山綠水間的采茶戲和采茶山歌、白云深處的朗朗書聲……構成了新時代山塆人家生機勃勃的日常生活圖景。小說的故事以生活在富水河畔楓林渡的阿通伯和他的女兒阿香與阿秀、外孫女小菊三代人的生活日常為主線,著力刻畫老一輩人對鄉土的眷戀與守護,新一代幕阜山少年的覺醒、奮進與自強不息,以及風風雨雨中永難泯滅、在鄉村振興的勁風中更加煥發的人性之美和如細流匯聚般的時代力量。
這樣的構想,這樣的文心,當然是明亮和美好的。但正如錢鍾書先生所言,我們常把自己的寫作熱情誤認為自己的寫作才能,自以為要寫成什么風格的,就意味著肯定會寫成、能寫成什么風格的。其實未必如此。小說是否達到了我自己所期望的效果,是讀者說了算的。
我很感謝二十一世紀出版社文學中心的談煒萍、王雨婷兩位年輕的編輯朋友,感謝她們耐心的等待和對我創作期間殷勤的照顧。好編輯總會把作者的作品視若己出。小說出版后,煒萍在《中華讀書報》上刊發了一篇書評《山鄉變革的故土戀歌》,其中有幾句評價洵為公允和中肯,也正好道出了我的文心與追求:“小說采取半紀實的敘事方式,循著主人公即作者的足跡,在散發著泥土與春茶氣息的旅程中,圍繞富水河畔楓林渡的阿通伯一家三代的生活經歷,全景展現了幕阜山近三十年來的發展變化。作者筆觸極具江南風情與韻味,但在這鄉土文化的探尋中,既充盈著作者濃烈的鄉土眷戀情愫,也隱含著作者客觀、冷靜的反思。”這也是我心目中的“理想讀者”。
三、人物
《小菊》出版后,我在微信圈里說道:“人間多奇葩,吾獨愛小菊。”雖是戲言,卻也道出了我對小菊這個人物的喜愛。作者寫小說,對于故事里的某些人物,自然也是視若己出,不愛則已,愛之彌深的。
《小菊》是一部兒童小說,小說里的主人公之一,就是小菊、小芬、萬新福、水芹等新時代山區的少年形象。他們是一群傳承清新樸素的采茶戲的少年人,也是未來的幕阜山區新生活的主人。尤其是小菊,我想通過這個小姑娘的形象,讓讀者看到新時代少年朝氣蓬勃、志存高遠、敢于擔當的精神特征,以及在鄉村振興的時代洪流中,這一代少年對于家鄉的山河、歷史的認知與熱愛。
小菊的性格跟她的媽媽阿香一樣,有點“愛憎分明”“嫉惡如仇”。她對自己的同學、從小患有肌無力疾病的小芬的幫助,視若己任,和同學一起組成了“愛的小船”行動小組,表現出一種堅毅的擔當勇氣。在小菊、韓叔叔等人的影響下,原本有著強烈的自卑心理的小芬,也像一棵獲得陽光照耀、雨露滋潤的小樹,漸漸舒展開了自信的枝丫。我在小說里寫到一個情節:坐在小船上,小菊和小芬這一對親密無間的好伙伴,東一句、西一句的,又打開了說說笑笑的話匣子。“我”一邊幫著阿香撐船,一邊默默聽著她們有一搭、沒一搭的交談。接著就是兩個小姑娘的長長的一大段對話。這時候,小船即將到達對岸,晨霧正在悄悄散開。我想,從兩個小姑娘的這段對話里,不難感受到新時代少年的那種不從流俗、奮發向上和獨立思考的精神。
除了小菊、小芬、萬新福、水芹等新時代山區的少年群像,我在小說里還塑造了駐村第一書記、工作隊隊長、退伍老兵韓燕來,文化站長劉耀煌,楓林渡口兩代撐渡人阿通伯和阿香,采茶戲傳承人阿秀、肖冬云、小玉,大學生喜子,還有文娟、紅菊、紅菱等年輕一代的形象,展現了他們為守護美好的鄉土文化、改變山區的落后面貌付出犧牲和艱辛、自強不息的奮斗故事。
肖冬云、阿秀、文娟、紅菊這一代年輕人,在艱辛的山區環境中長大,有的為了追求自己的夢想,忍受著委屈,離開山區去往遠方,進入了燈光炫目的城市。雖然是生活在城市的底層和角落里,但是只要不虛度自己的年華,只要腳步走得真實、踏實,他們就不僅分擔了這個時代的風霜和艱辛,也分享了這個時代給他們帶來的進步和收獲。我在小說里書寫了她們各自的故事,同時也透露出“我”的一種最深切、最質樸的感情:從心底里祝愿新一代幕阜山的孩子們,祝愿那些離開了家鄉的小山塆,散落在他鄉的角角落落的幕阜山的年輕人,在我們這個日新月異的時代里,都能生活得快樂和幸福一些,并且都能平平安安的,莫要叫老家的阿爸阿媽、阿公阿婆們擔驚受怕。
在駐村工作隊隊長和退伍老兵韓燕來、文化站的老站長劉耀煌、從擺渡人變身為農家書屋創辦者的阿通伯這些人物身上,讀者也可看到日新月異的新時代為古老的山區帶來的新觀念、新變化和新氣象,感受到一種春潮漫卷、山溪奔騰般的時代力量。在風風雨雨中永難泯滅的質樸的人性,又在鄉村振興的勁風中煥發出新的光彩。我也希望能在緩緩展開的山鄉風情畫卷中,閃耀出一種永恒的人性之美,寫出人性的光亮與溫暖、質樸與堅韌。
四、風俗
因為曾在幕阜山區生活和工作多年,對幕阜山區的地域風習、文化風情和人情世故,有一些切身體驗和積累,所以,我在小說里也寫了不少屬于地域文化和風情的內容與細節。例如陽新采茶戲的守護與傳承,稻場上的采茶戲演唱,“鄂南落田響”等插田號子演唱,采春茶時飄飛在層層綠崖和茶梯之間的采茶歌,還有對哭嫁之夜等場景的描寫,都屬于這一類情節和細節。
我在小說里寫到春工忙忙的早晨,伴著一陣陣朗朗笑語,韓燕來請來給阿通伯家幫忙開園采春茶的小嫂子們,像仙姑下凡一樣,一個個駕著飄繞的晨霧,裊裊娜娜地絡繹而來。這時,有的老爹看著街子上突然出現了這么多“仙姑”,情不自禁地發出了在這地處古代吳頭楚尾的幕阜山區,依然保存至今的文言嘆詞:“噫!好矣!好矣哉!”阿通伯更是喜得合不攏嘴,笑著對騎著自行車趕過來的燕來說:“燕來喲,你請來的茶姑,個個賽過仙女,怕盡是挑長得好看的要,不好看的不要咯!”我在小說里,嘗試適當采用一些鄂東南和贛北的民俗與風習,呈現幕阜山區的淳樸風情與美麗鄉愁,也有意無意地添加了不少對山塆人家一些獨特的方言遺存的重現。
也算是一種緣分,這部小說的編輯團隊的煒萍、雨婷兩位編輯老師,少女時代皆在幕阜山區度過,因此對小說里的方言、風習細節皆能莞爾會心。“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我想,這同樣是我在創作時對讀者們暗含的一種期待。
因為是有意追求一種散文或散文詩般的明麗與恬淡風格,所以,《小菊》這部小說與我前幾年寫的《羅布泊的孩子》《追尋》相比,并不以大開大合的故事見長,而是用一些鮮活的和散發著泥土與春茶氣息的細節描寫,撐起帶有鄉土韻味的敘事,從緩緩展開的風情畫卷中,去寫出人性的善良與美好、溫暖與堅韌,去呈現出春溪奔騰、細流匯聚般的時代力量。
最后,再次感謝煒萍、雨婷這個文學團隊的耐心等待和悉心照顧;感謝中國作家協會把這部作品列為2022年度重點作品扶持項目;感謝著名小楷書法家唐傳林先生(他也是《小菊》里的那位駐村第一書記、退伍老兵、先后擔任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駐村工作隊隊長的韓燕來的人物原型)為本書題寫書名。
2021年,我出版了長篇小說《爺爺的蘋果園》,是以烏蒙山區的脫貧攻堅為背景的;2022年出版的《小菊的茶山》,以幕阜山區的鄉村振興為背景。《爺爺的蘋果園》是我創作計劃中的“美麗鄉愁三部曲”的第一部,《小菊的茶山》是第二部,2023年將會完成這個三部曲的第三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