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忱談枕邊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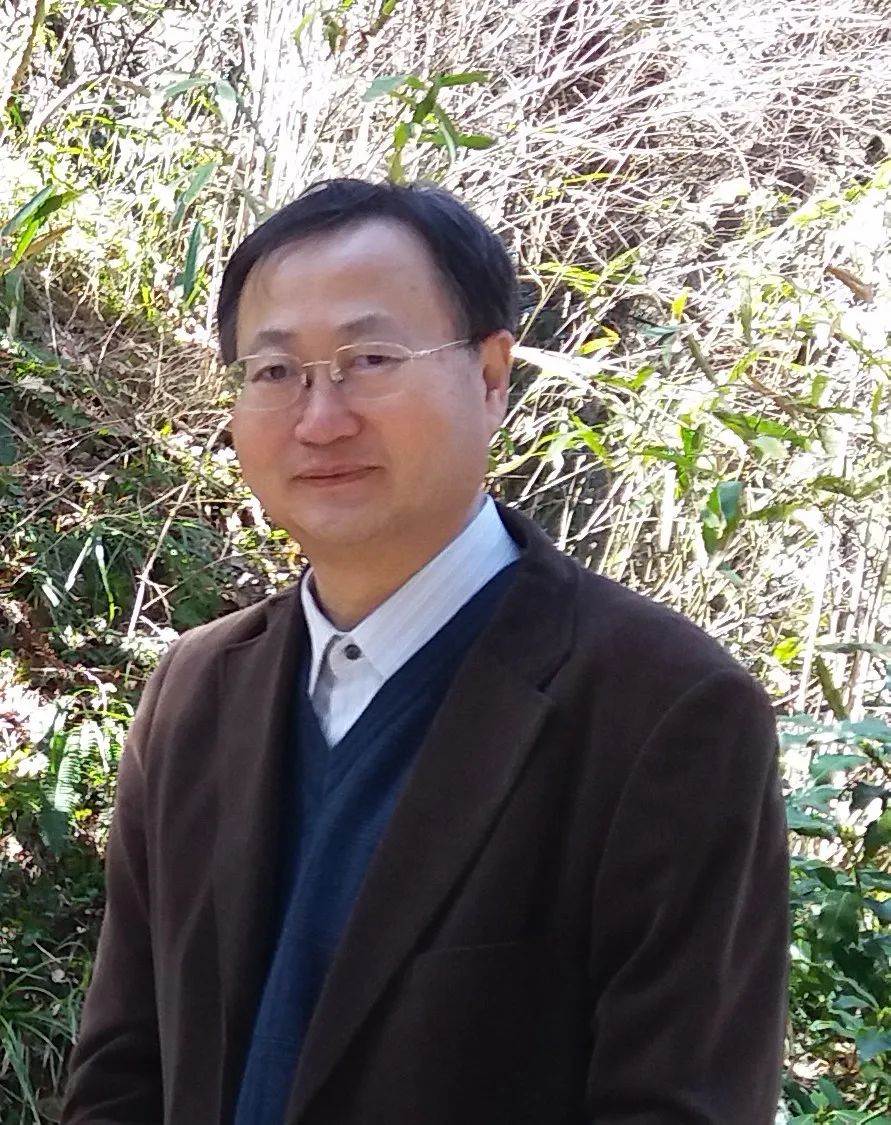
王中忱
中華讀書報:您的枕邊書有哪些?您認為什么樣的書適合作為枕邊書?
王中忱:枕邊讀書其實是一種奢侈,而在我能讀書的時候,絕無享受這樣奢侈的條件。我出生于東北松遼平原腹地的一個村莊,在我祖父那一代,整個村子識字的人屈指可數。我算是比較幸運的,我四叔讀過師范學校,在鄉村小學教學,他有一木箱藏書,平時總是很珍貴地鎖著,但對我一直很慷慨,尤其是過春節的時候,還會同時多借幾本給我。那就是我的節日盛宴。我哥哥比我高三個年級,他或借或買,總能搞到一些小說,讀完了就轉給我。
讀中學在“文革”期間,學校里本來不大的圖書室也關閉了,難有公開借到的書,但四叔的藏書箱仍在,哥哥也仍然有辦法找到一些書,《水滸傳》《西游記》《三國演義》《儒林外史》《紅樓夢》等幾部小說名著,確實都是在這一時期讀的,并且每一部都反復讀了多遍。還曾走過十多里路,到一位同學家借到線裝的《論語》《孟子》拿回家里抄錄。不過這些書都是坐著讀的,那時我的家鄉還沒有電,晚上點油燈睡土炕,沒有臥讀的條件,并且因為家里永遠有干不完的農活和雜活,家長并不鼓勵甚至很反感我們讀閑書,我們怎敢把書堂堂皇皇地放在枕邊?
讀枕邊書,是上了大學以后的事。中文系的學生,好像無論是哪所大學,貪戀在宿舍臥讀都勝過去課堂正經聽講,我也不例外。后來留在學校教書,有了工資,生活必需開支之外大都用來買書,買回來書,大都要躺在枕邊翻看一遍,然后再選必要的精讀,所以,在我看來,除了大開本的圖冊,其他普通開本的書都適合做枕邊書。而隨著關心的領域和興趣不斷變化,我的枕邊書也不斷變化,沒有哪本書一直放在枕邊反復讀。
中華讀書報:給予您精神上最重要的支撐的書有哪些?
王中忱:這個問題比較難回答。我讀書比較雜,從很多書里汲取到精神營養,從一般所說的經典著作,到民間故事和歌謠,都讓我感到忘我的愉悅,也都曾給我不同方面的啟迪,這些書綜合起來形成我的“精神支撐”。但在不同的年齡段讀書重點確有不同,年輕時候熱衷讀文學作品,后來興趣逐漸轉到理論著作,然后是歷史類和社會科學類的書,在經過了多學科閱讀之后,最近重新回到了文學。
中華讀書報:在現代文學研究上,您也有很多成就,比如對丁玲的研究,《重讀晚年丁玲》一文曾影響很大。您經常重讀作品?選擇重讀的作品有哪些?
王中忱:我確實是從中國現代文學開始走進學術研究領域的,成就完全談不上。我經常重讀作品,有時是因為感到有些作品所牽連的文學史問題需要重新討論,以前重讀“晚年丁玲”是如此,最近重讀茅盾的小說也是如此。但有時卻不是為了直接的學術課題,而是為了一些更廣泛的思考和困惑,最近重讀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就是想從歷史縱深和人心機微處去了解俄羅斯和歐洲。
中華讀書報:我對您早年的求學經歷很感興趣,在日本求學的幾年,您閱讀最多的書籍是哪些?您在《現代文學路上的迷途羔羊》一書中提到,自己對日本文學的興趣緣自尾上先生。他在讀書方面對您有怎樣的指導?
王中忱:我在日本求學的時候其實已經人到中年,此前在大學教過書,在文化出版機構工作多年,專業范圍主要在中國現當代文學領域,理想的職場規劃應該是沿著一條熟悉的路走下去,但我這個人比較隨性,尤其是在能夠從日文原文閱讀文學作品的時候,直接感受到詞語和音節的微妙律動,敘述語調的曲折變化,從此就欲罷不能。在日本文學課堂上尾上先生的鼓勵給了我信心,但在讀書方面并沒有給多少具體建議。當時日本的大學對學生基本是放養,這也適合我的個性,完全憑著興趣自由漫讀,后來集中到了左翼文學和新感覺派文學,特別是中野重治和橫光利一的小說,還有前衛性詩歌。同時也一直關注二戰以后活躍于文壇的作家,特別是“戰后派”一脈,如大岡升平、堀田善衛、大江健三郎等。概言之,我關注的范圍是日本的現當代文學。
尋求讀書指導,其實并不限于所讀大學的課堂之內。當時我們幾位同學組織過讀書會,一起研讀評論家吉本隆明的《對于語言而言美是什么》,這本書迄今沒有中譯本,在漢語讀書界鮮為人知,但在1960年代的日本讀書界風靡一時,可說是一本當代的經典。
中華讀書報:您曾獲《世界文學》翻譯獎(2001年),是翻譯什么作品?能否談談您的翻譯理念?比如選擇什么樣的作品翻譯,有何標準?
王中忱:翻譯的是大江健三郎的短篇小說《環火鳥》(日文原題《火をめぐらす鳥》),是時任《世界文學》編委的許金龍先生約稿,文字上也經過他的反復敲打。說來慚愧,盡管我很熱愛文學翻譯,但由于學校里各種雜務纏繞,實際很少有時間用于翻譯,自然完全不敢奢談“翻譯理念”。但如果繼續翻譯小說,我愿意選擇有思想深度且在敘述方式和語言表現上有新探索的作品。怎樣把原作的“探索”在漢語中體現出來,讓讀者通過譯本也能感受得到,這是文學翻譯的難題,也是讓譯者保持翻譯熱情的動力。
中華讀書報:上世紀90年代初,您從日本回國,托運了幾十箱書,都與日本文學相關。能說說都是什么書嗎?在您的收藏中,最珍貴或最有紀念意義的是什么書?
王中忱:我1989年4月赴日留學,1992年3月回國,那時候辦理護照簽證等出入國手續非常煩難,充滿不確定性,我不知道以后是否有機會再到日本,而我又想把已經開始了的日本文學的學習繼續下去。對比日本的中國研究,當時中國的日本研究基礎薄弱,圖書資料也非常匱乏,我搜購的書主要是日本近現代文學作品和相關的研究著作、辭書等。
我買書不是為了藏書,從收藏的角度說沒有什么珍本善本可言,但在書店里,當遇到期待很久的舊書,比如梁啟超、魯迅那一代人曾經讀過的版本,或者完全沒有預期卻讓人見了就移不動腳步的新著,那種興奮和激動,過后也難以忘卻。對我個人來說,這樣買來的每本書都很珍貴,有紀念意義。
中國和日本文化交流的進展超出想象,后來我多次去日本學習、教書和從事學術研究,無論長期還是短期,每次回國肩背手提的行李里占分量最多的仍然是書。而隨著研究領域的擴大,買書的范圍也從文學擴展到了思想史和文化史。2020年4月我從京都倉促回國,國際郵遞因新冠疫情停止營運,買的書都放在了客座研究的機構里,最近才由研究所的朋友寄到北京。拆開郵寄紙箱,看到兩年前一本一本買來的書完好歸來,真是又驚又喜,感慨萬千。
中華讀書報:這些書至今還在您的書架上嗎?很想知道您如何整理書架?那么多書,怎么收藏?怎么清理?
王中忱:這些書分別放在家里和學校研究室的書架上,大致按主題分類擺放。因為書架已經擠得滿滿,也有一些書裝進了紙箱里,需要的時候再拿出來,所以過一段時間確實需要整理一下,把某一專題的書歸攏上架或下架。研究生們可以到研究室借閱,他們自行管理。總之,這些書都在用,還說不上藏。
我也陸續把一些書送給學生和青年老師,但有時擔心會給他們添麻煩,因為現在大家都缺少放書的空間。書有聚有散,能夠散到想讀的人那里就好。這也可以說是一種清理吧。
中華讀書報:您對大江健三郎、加藤周一等研究頗多,能否談談您和日本作家的交往?您發現他們對于中國文學的了解是怎樣的情況?
王中忱:作為翻譯者和研究者,我和大江先生、加藤先生見過面談過話,但不能說是交往。他們都是我尊敬的前輩,能有機會親接謦欬,從感性層面接近他們的思想和文學,和只讀文字文本大為不同。
加藤曾長期旅居法國。大江畢業于東京大學法國文學專業。他們的知識背景帶有濃重的歐洲色彩,但他們都尊重漢文圈的傳統,如加藤在《日本文學史序說》里把近代以來被日本的文學史家放逐了的漢文寫作放置到重要位置。同時,出自對近代日本“脫亞入歐”論和對亞洲鄰國侵略歷史的反省,他們都積極參與了二戰之后第三世界作家發起的文學運動,如亞非作家會議。
加藤和大江都對魯迅有深刻理解,大江還特別關心中國“新時期”以來的文學。我曾親眼看到大江對照英文、法文、日文譯本閱讀莫言的小說,那樣誠摯用心,非常讓人感動。
中華讀書報:2021年9月,您在清華大學日新書院2021級開學典禮的致辭上,曾引用《無用知識的有用性》《我的幾何人生》等闡述自己“人文學是具有大用途的知識”的觀點。您經常會為學生推薦書嗎?
王中忱:我一般不給書院學生推薦閱讀書目,因為每門課程的老師都會開列書單。有時聽到學生抱怨說書讀不過來,我會說要注意讀書方法,但也不過是廣泛瀏覽和專精研讀相結合之類的老生常談。
基于自己的教訓,我會提醒學生注意培養扎實的讀書能力。書院設有《說文解字》研讀、古文字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等課程,還設有拉丁文基礎、基礎梵語等教授歐亞古代語言的課程。先賢說:“讀書須先識字”,開設這些課程,就是希望同學們在年輕的時候練好童子功,將來能夠從原文直接研讀中外經典。
研讀經典是人文學術的基礎,但讀書不能也不必總是正襟危坐,我也愿意鼓勵學生們憑著興趣去廣泛閱讀,不預設所謂研究目的,涵養性情,全面提高素養,這同樣是重要的。
- 浙江“新時代鄉村閱讀季”在湖州啟動[2022-06-22]
- 陸建德談枕邊書[2022-06-22]
- 朱永新:我是行動的理想主義者[2022-06-20]
- “從《異時之夏》看科幻長篇小說的創作”主題分享圓滿結束[2022-06-14]
- “書香之城”的“打卡”嘗試[2022-06-10]
- 陳眾議談枕邊書[2022-06-09]
- 城市副中心圖書館帶來智慧化新體驗[2022-06-07]
- 北京建投書局國貿店:線上訂單增長60%[2022-06-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