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孟祥:《講話》指引下的新說書運動
1942年5月間,毛澤東同志親自主持召開了延安文藝座談會,發表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不覺八十年過去了,當年,《講話》指引下的新說書運動仍歷歷在目。
《講話》發表以后,伴隨著新秧歌運動的不斷深入發展,專業文藝工作者向民間藝術學習的熱情不斷高漲,一個波瀾壯闊的新說書運動,便很快在延安開展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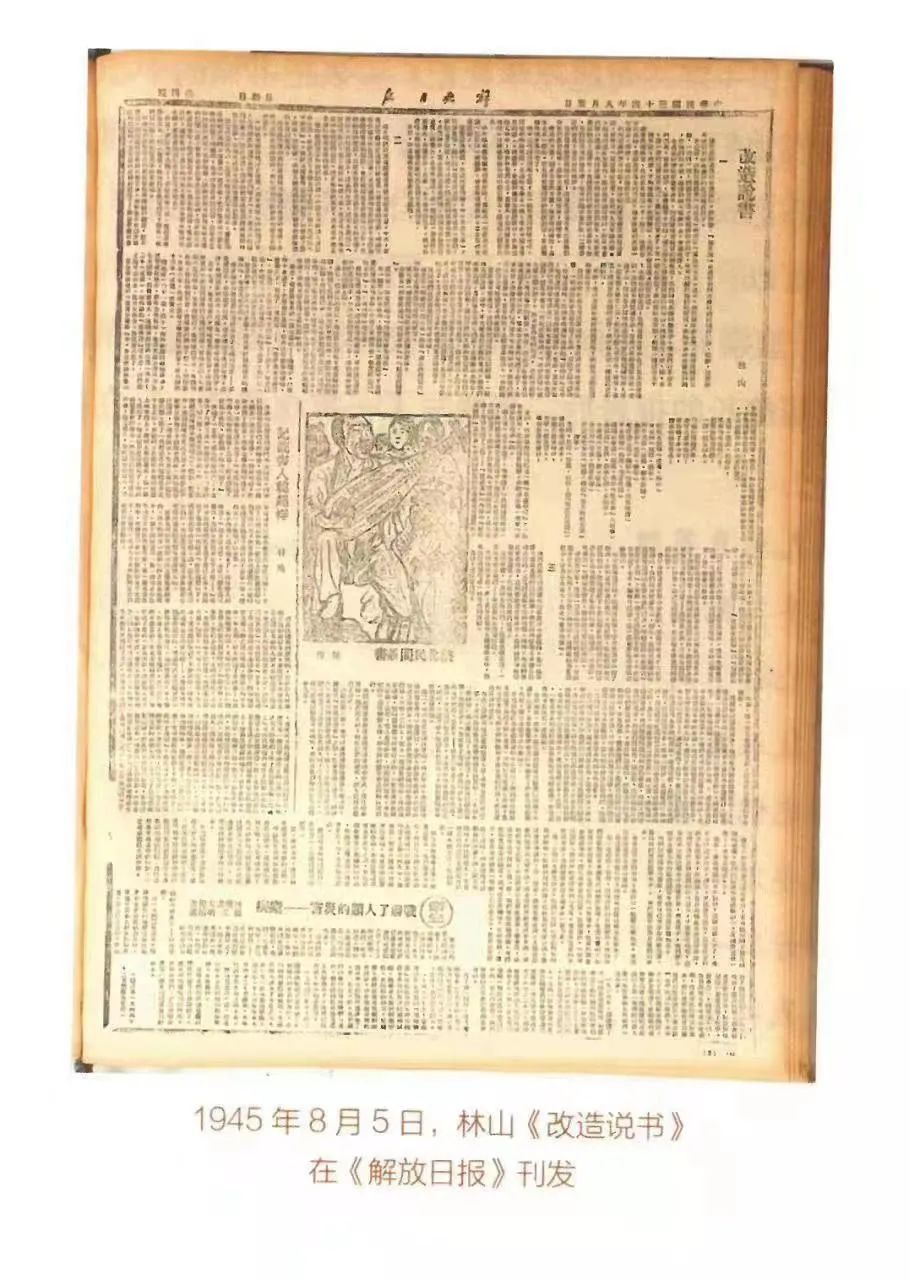
陜北的新說書運動,是在邊區文協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它首先得到西北文聯主席柯仲平的支持。1945年4月,邊區文協成立了說書組,由詩人林山領導。安波、陳明、柯藍、高敏夫、王宗元等同志,都先后參加了說書組。大約經過兩個月的實踐,逐漸探索出一條路,這就是:團結、教育、改造民間藝人,啟發、引導、幫助他們編新書,學習說新書和修改舊書。在具體做法上,首先是個別訪問,選擇對象,培養典型,然后通過他們來聯絡、推動其他說書人,并且采用個別傳幫帶和辦訓練班等方式,擴大說新書的影響。
文協說書組首先發現并培養了韓起祥。他們對韓起祥的思想、生活、創作才能、演唱藝術以及在群眾中和說書人中的影響等等,進行了深入而具體的研究,采取多種方式,提高他的思想水平和創作方法。
韓起祥在文協說書組的耐心幫助下,在短短的4個月內,思想上和藝術上有了飛躍提高。他在自編的《說書宣傳歌》中唱道:“文協、魯藝、縣政府,獎勵我來說新書,新書說的是什么?一段一段教育人。自編新書編不好,希望大家要批評!要知編了多少本,請看后面有書名:《紅鞋女妖精》《反巫神》《四岔捎書》《掏谷搓》《吃洋煙二流子轉變》《王五抽煙》《閻錫山要款》《血淚仇》《中國魂》《合家樂》《王志成吃元寶》《張家莊祈雨》。編的新書還不多,常編常說常增加,希望一般說書人:學習新書要實行!”不久,韓起祥又創作了頗有影響的《劉巧團圓》和《張玉蘭參加選舉會》等曲目。于是說書組不失時機地帶領韓起祥在延安辦起了第一個說書訓練班。隨后,又在米脂、綏德、清澗、延長、延川、子長等地舉辦說新書訓練班。當時,全陜北有失明藝人483人,經過訓練改說新書的就有273人。像綏德的石維俊、三邊的馮明山、延安的劉之有、常栓等,先后創作、改編了《烏鴉告狀》《地板》《平鷹墳)《抗日英雄洋鐵桶》等新書。此外,陳明的陜北說書《平妖記》,李季的說書《卜掌村演義》,孔厥的唱本《人民英雄劉志丹》《一家人彈詞》,戈西的說書《老麥菁偷麥》,拓開科的練子嘴《鬧官》等,也都受到群眾的好評。
韓起祥的演唱轟動一時,僅1946年9月,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就連續8次發表了他的新作品并報道了他的藝術活動。特別是毛澤東、朱德請他去說書,更使韓起祥的名聲遠揚。

由于韓起祥帶頭編演新書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熱烈歡迎,再加上黨報和林山等同志的大力倡導,陜北的新說書不到兩年的時間,就在全邊區形成了一個普遍的運動。不久,這一運動又在晉綏、晉察冀、冀魯豫、山東、蘇皖等全國各個解放區開花結果。尤其是冀魯豫解放區成績更為顯著,在冀魯豫邊區文聯主任王亞平的領導下,認真執行毛主席對舊藝術“既不卑棄,亦不投降”的態度和“推陳出新”的方針,有步驟有計劃地對舊藝術進行了改革,總計受訓的老藝人達千人以上,除對舊劇、舊說唱進行審查和整理改編外,還創作了新說唱詞上百篇。像王亞平的《張鎖買牛》、李剛的《二元成親》、沈冠英的《未婚妻勸夫參軍》、孟漢英的《濟南第一團)等,都是當時膾灸人口的曲藝佳作。邊區文聯還編印出版了大眾讀物《新地》半月刊,在邊區新華書店發行。
解放區的新說書運動,從1945年春到1949年7月全國第一次文代會的召開,在歷時4年多的時間里,據初步統計,僅廣大民間藝人的曲藝新作,就有上千篇。他們無論是吹拉彈唱,還是說新編新,都有大的突破和創新,成為農村新文化的重要陣地。
《講話》指導下的新說書運動,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首先,是思想改造和藝術改造相結合。從具體的藝術改造做起,結合思想改造,互相作用,互相提高,進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改造過程中,還注意及時給予鼓勵和表彰。譬如:對藝人編演的新曲目進行評獎;優秀的作品給予發表的園地;對典型人物及時進行宣傳報道等等。這樣既能提高民間藝人對思想改造和藝術改造的積極性,又能進一步鞏固所取得的成果,還能擴大新說書運動的政治影響。
其次,知識分子與民間藝人相結合。新說書運動的興起,打破了千百年來文人與藝人的長期隔閡,第一次使二者完全結合起來。解放區革命知識分子與民間藝人的結合,是以共同的革命目的為基礎,所以他們的結合是自覺的、同志式的。只有這種“同志式”的結合,才凝聚著革命的戰斗情誼。像林山與韓起祥的結合、王亞平與沈冠英的結合、何遲與王尊三的結合。而這種結合,正是在《講話》精神的感召下進行的。
二者的結合,使現代曲壇煥然一新,它大大推動了新說書運動的興起和發展。民間藝人與革命知識分子結合,不僅接受了進步思想,在藝術創作上也接受了新文藝的表現方法和寫作技巧。而知識分子通過與民間藝人結合,一方面指導著民間藝人和民間藝術的改造工作;另一方面也不斷地從民間藝術中吸取營養。詩人艾青在《解放區的藝術教育》一文中講:“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后,解放區文學藝術的成績,主要是學習民間得來的。例如秧歌、腰鼓、年畫、新的歌曲、大量的快板、說書、大鼓詞.....”。
再其次,新文藝與民間文藝相結合。《講話》發表以后,廣大文藝工作者通過深入火熱的現實生活,思想感情與工農兵打成一片,文藝創作也實現了民族化、大眾化。在這一過程中,說唱藝術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趙樹理的小說。他的成名之作《小二黑結婚》,最早是以“現代故事”來發表的。稍后的《李有才板話》,更是以他杰出的“板話"藝術,贏得中外讀者的贊賞。他把說唱藝術與小說藝術融為一體,成為解放區民族化、大眾化的一面旗幟。應該說,在解放區的作家群中,受民間藝術的影響是巨大的。像馬烽、西戎的《呂梁英雄傳》,孔厥、袁靜的《新兒女英雄傳》,王希堅的《地復天翻》,邵子南的《地雷陣》,徐光耀的《平原烈火》,康濯的《黑石坡煤窯演義》等等。這些作家或作品,或向曲藝學習結構形式,或向曲藝學習評書筆法,或向曲藝學習接近群眾的口語化語言,或向曲藝學習塑造人物的成功經驗。而這些學習和運用,對于促使小說的民族化大眾化,是至關重要的。
新說書運動對詩歌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李季的敘事長詩《王貴與李香香》,是采用了陜北“信天游”的格式,阮章競的長詩《圈套》,則自稱是“俚歌故事”。至于張志民的敘事詩《王九訴苦》和《死不者》,那簡直就與快板無甚區別了。與此同時,詩人王亞平則把鼓詞視為“唱詩",而“孩子詩人”苗得雨,干脆就把大鼓詞收進了自己的詩歌集。還有陶鈍的長篇說唱《楊桂香鼓詞》,馬少波的快板《嵩潛莊》等。這種“曲詞合一”的藝術實踐,正是新文藝與民間說唱藝術相結合的產物。

1950年,韓起祥(左)與陜北說書《劉巧團圓》記錄整理者高敏夫(延安魯藝人)合影
此外,現代說唱藝術還對戲曲乃至繪畫都產生了影響。眾所周知,最早的歌劇《白毛女》是根據民間傳說故事和民歌小調改編而成的;陜北說書《劉巧團圓》曾影響了評劇《劉巧兒》的移植改編。新秧歌傳到東北以后,又與二人轉合二為一,從而產生了二人轉秧歌劇。在晉察冀,相聲與戲劇相結合,出現了一種“相聲喜劇”。在冀魯豫,墜子與戲曲相結合,于是出現了一種“墜子戲”。在山東,快板與小調相結合,又涌現出“快板小調劇”。在陜甘寧,說唱與繪畫相結合,便產生了一支“藝術輕騎兵”新洋片。
說唱藝術一方面促進了新文藝的民族化與大眾化,另一方面新文藝又給說唱藝術以影響。像小說《小二黑結婚》《呂梁英雄傳》《烏鴉告狀》《平原烈火》《晴天》,戲曲《白毛女》《血淚仇》,詩歌《趕車傳》等,先后被說唱藝術所改編。文學藝術的這種相互滲透和相互交融,正是《講話》發表以后,文學藝術繁榮發展的重要標志。
新說書運動的最大功績,就是培養和造就了一支無產階級的曲藝隊伍,并為社會主義新曲藝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新說書運動的領導核心和中堅力量,正是由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像林山、安波、陳明、柯藍、高敏夫、趙樹理、陶鈍、王宗元、馬烽、西戎、何遲、王亞平,以及王尊三、韓起祥、沈冠英、畢革飛、楊星華、曹永山等,他們都是優秀的共產黨員作家和民間藝術演唱家,有的還長期擔任黨的文藝領導工作。這批具有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先進分子,滿腔熱情地投入到新說書運動的行列中來,其本身就具有極大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它改變了曲藝隊伍長期以來渙散無力的局面,代之以共產黨員為先鋒的無產階級曲藝隊伍的形成。這支曲藝新軍,既是新說書運動的開拓者,又是社會主義新曲藝的建設者。
回望歷史,展望未來,不忘初心,滿懷希望,繼續沿著《講話》指引的方向不斷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