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天驥:賞析古詩詞,不要停留在“金圣嘆式”評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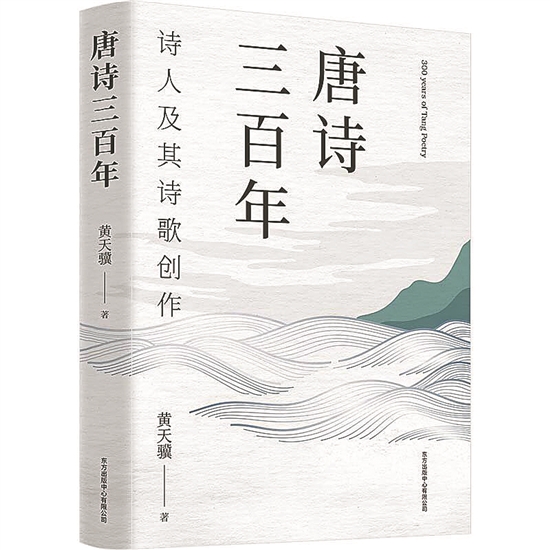
著名古典文學研究專家、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黃天驥新書《唐詩三百年——詩人及其詩歌創作》近日出版,通過解讀唐代32位詩人的35首代表性作品,呈現了有唐一代詩歌精華風貌。
該書可謂黃天驥教授從教六十余年來詩歌創作與研究的結晶。黃天驥教授幼承家學,后又從詹安泰、黃海章等前輩學習詩詞,在教學研究生涯中,雖然以戲曲為主,但也長期講授詩詞,并出版過《黃天驥詩詞曲十講》《詩詞創作發凡》《冷暖室別集》等。
日前,黃天驥老師接受羊城晚報記者專訪——
不能脫離時代背景研究古典文學
羊城晚報:《唐詩三百年》的寫作緣起是什么?為何是“三百年”而非“三百首”?
黃天驥:這本書其實并非出于一個宏大的寫作計劃,只是從偶然的單篇文章開始的。2019年初退休后,我住在校外,當時在做一個戲曲的題目,研究了一半因為資料欠缺暫時擱置了,一些學生就說讓我寫一些關于唐詩的短文章。
1956年,我從中山大學畢業并留校任教,主要方向是古代戲曲,但也一直從事古代文學史的教研工作,所以寫唐詩對我來說也算熟悉。
一開始寫的時候并沒有按照年代給詩人排序,后來成書的時候才發現把作家的年代排下來,可以看出唐詩三百年走過的歷程,其實這也跟我研究詩詞一向的思想有關:對任何一篇詩詞或者一個詩人的評價,都不能脫離所在的時代背景。因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面貌,個人情感的抒發跟時代有著密切的聯系。
所以我總要求自己做古典文學研究的時候,不能只看樹木不看森林,也不能離開森林去看一棵樹木。唯有如此才能準確理解每一篇作品真正的意義和技巧。
羊城晚報:《唐詩三百年》和市面上眾多此類出版物有何不同?
黃天驥:現在賞析唐詩,很多人都會把詩歌中的某種精神抽象出來,比如李白詩中表現出來戰勝困難的自豪,然后讓大家從詩中找到學習的力量,或者單獨抽出來某個詞進行賞析,我覺得文藝作品不能這樣解讀,這是非常機械的教條主義式的做法。
如果說我這本書有什么不同,可能就是我不僅要寫唐詩如何好,更要說明好在哪里、怎么寫出來的。從古代到現在,很多人賞析古詩詞往往停留在“如何如何好”,金圣嘆評點式,缺乏文學理論層面的分析。我不敢說我自己寫得就有多好,但是如果能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對同一首詩的理解,我覺得就夠了。
羊城晚報:這么多年游歷唐朝詩人及其詩歌精神世界,有何感觸?
黃天驥:小時候讀唐詩根本讀不懂,就是背誦。我很小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都是我祖父叫我背唐詩,但是記憶力很好,《長恨歌》等都能背得爛熟。
在人生不同的階段讀唐詩感受都會不一樣。比如唐詩中最常見的《登鸛雀樓》,字面上看誰都明白,所以很多人把這首詩當成風景詩來看,氣勢宏大,視野開闊,我小的時候就是這樣理解的,但是現在完全不這樣看,這首詩根本就不是風景詩,而是一首哲理詩,只是借著風景來寫。
一個經典的文本,在不同年齡階段理解是不同的。就像一個外國的漢學家所說,每過20年《西廂記》就應該重新研究一遍,我覺得這個道理是對的。如果一個作品像一張白紙一樣明白清晰,那可能是蹩腳的作品;好的作品往往會給人以神秘感,這才有味道,才會耐人尋味。
再也沒有第二個李白、杜甫
羊城晚報:在新書中,您不止一次提到了詩人對個人價值的認知,您對唐代詩人對人之價值的認知如何評價?
黃天驥:我覺得中國古代詩詞一個很重要的價值,就是不同時代的知識分子都力圖要表現出人的價值。比如常見被貶之后寫詩發牢騷,其實就是肯定自己的價值,我這么有才能為什么不重用我?為什么這個社會讓我無法發揮自己的才能,無法實現自己的理想?這個牢騷其實就是對個人理想價值的一種追求,唐詩里面就有很多這樣的作品。
李白、杜甫都有著強烈的個體意識,個性很強,這也是他們能寫出如此偉大的詩歌的原因之一。像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鮮明表達了他個人的意志。詩人如果沒有這種意識,不注重個人的存在價值,就很難寫出好的作品,寫的可能是淪為口號式的作品。
羊城晚報:您覺得唐詩取得如此輝煌成就的原因是什么?
黃天驥:兩個方面。從社會來看,如果一個社會是開放的,它的文藝作品、文藝思想、對現實的批判和感受往往是放得開、寫得深的,而唐代就是這么一個時代。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里,唐代是最開放的社會,而且神奇的是,唐代越艱難的時候越開放,像安史之亂時期,經濟大破壞,人民生活非常痛苦,但是當時的社會能夠接受各種不同的文化,開放到連當朝的皇帝都可以批評。從藝術技巧來看,唐代剛好接受了近體詩的寫法,既注重語言的韻,也注意平仄的安排,也就是音節的對立統一。這也是詩歌發展到非常成熟的時候才會出現,開放的社會疊加藝術本身的突破,造就了唐詩在中國文學史上不可逾越的地位,再也沒有第二個李白、杜甫了。
羊城晚報:對當下的文學創作有何啟示?
黃天驥:要從個人視角去看時代,而不是為了寫時代而創作。當你從個人視角出發,也不用擔心有沒有呈現時代,因為一個人的遭遇、情感、感受都是無法脫離時代的,所以寫出來的作品自然能表現出時代的精神。到底什么是時代精神,說起來就很廣了,不是幾句話能概括的,但是能夠把那個時代人民普遍的愿望、情感表達出來,就是好的詩歌。
繼承傳統文化勿忘“優良”二字
羊城晚報:您在研究古代文學時會受到西方文學理論的影響嗎?
黃天驥:會的。中國文學理論的核心是“我注六經,六經注我”,評論家同時是讀者,既要把古人的經典說清楚,也可以從主觀的方面去闡釋經典,為我所用,這是中國傳統的文獻注釋方法。我的老師詹安泰先生曾下定決心“三年不讀線裝書”,大量地研讀政治和文藝理論著作,一心想提高理論水平,加強對中國古代文學發展規律的研究,改變“評點式”的鑒賞方法,這對從舊時代過來的文史研究工作者來說,是十分必要的。當時讀的那些文學理論,雖然有的比較教條主義,但是有一點很重要,訓練了我們的邏輯思維。
但是也不能盲目使用西方文學理論,比如符號學,某一個形象出來后,經過共同認可變成一種概念性的東西,就是符號,每個民族都有,中國也有。我們不把這作為分析文學的主要手段,因為中國文學理論不會把整篇作品都看成是一個符號的表達,這是中西方文學理論重要區別之一。
羊城晚報:學習、研究古代詩詞有什么現實意義?
黃天驥:對我們中國人來說,要進一步認識到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和偉大意義,增強我們的民族自信心,這在當下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現在,西方文明值得我們學習,但也不能忘了中國的古代文明,我們有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社會標準、社會規范,文學上也有一套表現人物性格、感情的方法,如果不繼承下來,慢慢淡化,將來怎么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具體到古代詩詞,語言凝練,有韻味,尤其舊體詩基礎好的作家,像魯迅、郁達夫、汪曾祺等,他們寫的散文、小說就不一樣,那種詩的韻味游走在字里行間,余味無窮。
羊城晚報:中國傳統文化的創新與發展也面臨一些難題和挑戰。
黃天驥:這個問題現在恐怕難以解決。其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學,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和興奮點,這是必然的,這樣才會進化,所以過去的人對古代詩詞記得比較多,現在的人只記得一部分,這是自然的。語言環境、社會環境都變了,對古代文學的態度也會發生變化。所以不一定要強求,順其自然即可,我們做研究的告訴大家什么是好的,然后感興趣的人自覺去學習就可以了。不過在繼承的時候,千萬別忘了“優良”二字,傳統文化里也有不少糟粕,不是什么都要繼承。要學會甄別和篩選,哪怕是李白、杜甫、王維、白居易,也并非全都是優秀的作品。
羊城晚報:現在很多家長學前教育都是讓孩子背唐詩,您有什么建議?
黃天驥:小孩子背誦唐詩可以不求甚解,而且也沒一開始就深刻理解的必要。你先背下來,再慢慢琢磨,這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太早告訴小孩子詩歌背后的意義,給他定了一個框框反而不妥。我知道現在中小學課本中的古代文學作品多了,要求孩子們背誦,這是好事,可以培養對古詩詞的審美和語感。
- 倘佯在“古典的春水”間[2022-03-30]
- 《古典的春水:潘向黎古詩詞十二講》新書發行 邂逅最美古詩詞[2022-03-15]
- 從23首詩詞出發 攀登“大春秋”[2022-02-25]
- Z世代在網上追更古詩詞講解時,究竟在追什么?[2022-02-24]
- 二十四節氣:古詩詞里的“時間美”[2022-0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