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鋒·異托邦·后人類:中國科幻文學的“可見”與“不可見” ——宋明煒《中國科幻新浪潮》
編者按
在當代海外中國科幻研究中,宋明煒教授創造性運用的“新浪潮”(New Wave),已經成為具有導引性的關鍵詞。借助這個術語照亮“中國新科幻”的“幽暗”之處的炫目輝光,論者在這個文類的深處發現了具有“先鋒”“叛逆”“顛覆”等多種屬性的暗能量,進而視之為八十年代“新啟蒙”的延續。汪曉慧博士的這篇書評,很好地體現了“新浪潮”這個“認識裝置”的威力。比起一板一眼的歷史考述,一個包羅萬象而又立意鮮明的概念,顯然更能為當代中國科幻文學營造富有沖擊力和吸引力的整體形象,更能引起到中流擊水的學術豪情。但這只是起點。如果說“八九十年代之交”以來的中國科幻文學以甚至超越主流文學的精神強度介入了社會歷史,那么它們,以及它們的創造者,究竟以何種方式與后革命/后冷戰/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和世界的社會歷史發生了怎樣的血肉關聯?它們繁復各異甚至判然有別的技術觀、人性論和世界想象,是在寂寞中自組織,聽將令而齊齊殺出的伏兵,還是本身就構成了一個高技術社會的精神分裂癥候之隱喻?這股“新浪潮”與已經理所當然地消散并被忘卻的“前浪”或“舊浪”之間,或者說,“中國新科幻”與“中國舊科幻”之間,是了無牽掛,還是藕斷絲連,又或是,薪盡火傳?我們期待著更多的討論。
科幻小說的復興是中國文學邁入新世紀后最重要的現象之一。在從文學體制邊緣走向關注中心的過程中,科幻文學作為一種歷史政治寓言的潛力逐漸顯露,其間龐大、復雜、相互抵牾又相互勾連的詩學問題也浮出歷史地表。作為國際科幻論壇中首屈一指的批評家和中國科幻海外傳播的重要推手,宋明煒對中國科幻文學中的詩學問題保持著深刻關注與敏銳洞察,近十年來陸續發表一系列評論文章,見證和記錄了中國科幻文學再次勃興的歷時性過程。
宋明煒新著《中國科幻新浪潮:歷史·詩學·文本》(以下簡稱為《新浪潮》)收錄其中二十篇影響較大的科幻論述,以“新浪潮”為關鍵詞,直面既往科幻研究多以作家作品為中心、相對零散而缺少整體性創新的理論難題,從歷史眼光和詩學維度切入科幻研究,開拓性地梳理和發掘作為“他者”的科幻小說在文學空間、現實言說和主體意識三個維度上建立的“新坐標系”及影響。從“新浪潮”出發,無論是科幻文學的自我認知,抑或是當代主流文壇對科幻這一文類的認識,都發生了重要而意味深長的轉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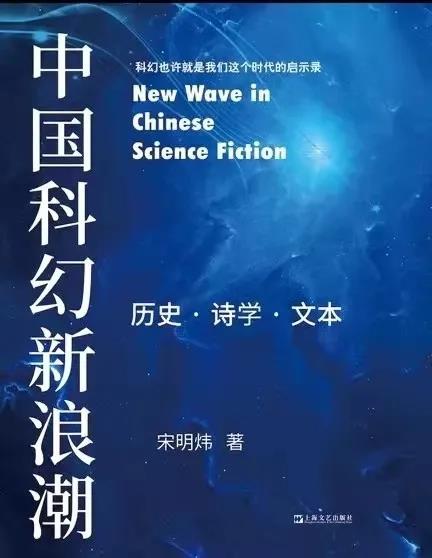
《中國科幻新浪潮:歷史·詩學·文本》
一、“新浪潮”的內涵與特征
世紀末以降,社會經濟與信息技術急遽發展,文化傳媒方式多元分化,中國社會思潮轉向的同時,主流現實主義文學卻逐漸與社會現實脫節,這些因素都促成了科幻文學在世紀之交的復興。《三體》《北京折疊》獲得雨果獎,《流浪地球》熱映,使得中國科幻文學這支“寂寞的伏兵”1走進大眾視野。不同于一些研究者將這場科幻熱類比為英美科幻史上曾出現的“黃金時代”,宋明煒獨辟蹊徑地將科幻文學的第三次復興形容為一場近似于超新星爆發般的“新浪潮”,著意研究當代科幻文學書寫中反叛傳統創作套路、標榜先鋒前衛、揭露黑暗未知的叛逆一面。
2013年,宋明煒在《文學》雜志中首次提出“中國科幻的新浪潮”這一說法2,以其指稱科幻文學對傳統文學形態的突破。在其后的論述中,他不斷夯實“新科幻”與“新浪潮”的理論細節和文本支撐,著重考察九十年代以來科幻異軍突起現象中的詩學價值。宋著認為,中國科幻新浪潮萌芽于八十年代末,興起于九十年代末,并在新世紀前十年逐漸發展成熟。它的出現最早可以追溯到1989年。那一年,劉慈欣寫下了他的第一部長篇科幻小說《中國2185》。盡管這部小說迄今為止并未公開發行,但它“以宏偉瑰麗的想象,將八十年代知識精英的理想,重現于‘另類歷史’的構想之中”,成為新浪潮中不可忽視的起點。其后,韓松、王晉康、星河、潘海天、趙海虹、陳楸帆、夏笳等人延續擴展了這種帶有嚴肅思考意味與先鋒精神指向的精英式科幻寫作,逐漸形成一股顛覆傳統科幻文類成規的創作力量。盡管這些作家的創作旨趣、審美偏向、敘事風格不盡相同,卻都在某種程度上選擇以曖昧復雜、不拘一格卻都具有某種分明意指的筆觸介入社會歷史,呈現出與現實或對應或悖離的異托邦世界,由此構成新浪潮的核心特點和寓言維度。
借用“新浪潮”(New Wave)為論述的內在精神邏輯,難免會讓研究者想起英美科幻文學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新浪潮”概念。但需指明的是,宋明煒所界定的“中國當代科幻新浪潮”實際上已經與“英美科幻新浪潮”產生較大區別。盡管這兩者都指向某種打破傳統、具有前衛色彩的人文科幻創作模式,但相較于后者以心理學、社會學、宗教和社會諷喻為核心的實驗性敘事立場,中國科幻新浪潮則更大程度上呈現出一種多元而外向的格局。換言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西方“新浪潮科幻”是類型文學在歷時的發展過程中試圖自我突破所形成的迭代式內部革新;而在宋著所界定的中國科幻新浪潮中,類似的前衛先鋒意識早已突破類型文學內部,它對話、繼承、叛逆、超越的對象更多指向占據文壇主流的現實主義傳統及其中難以言說或被長久忽視的“異境”。
科幻文學的核心命題之一是對于“現代性”的闡述。正如吳巖所說,“研究科幻文學如果不從‘現代性’著手,就不能真正接觸它的內核”3。當代科幻作家繼承魯迅以來的“五四”啟蒙思考和八十年代文學中的先鋒批判精神,立足于對中國現代性問題的反思而產生的本土化想象,自覺不自覺地在小說中融入社會問題和科學思維,借此返照社會現實,創造出了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科幻文學樣式。這亦是中國當代科幻區別于西方科幻新浪潮最鮮明的特質之一。
在這股新浪潮中,劉慈欣、拉拉、寶樹等作家筆下的作品有著鮮明的技術頌歌傾向、宏大崇高的民族精神表達以及向史詩傳統回歸的新古典主義氣質;韓松的寫作風格具有強烈的先鋒特質,文字晦澀曲折、意象破碎扭曲、人物形象混沌不清,在鬼魅混沌的隱喻中折射現實歷史的種種鏡像;更年輕的作家陳楸帆等人跨越西方新浪潮的寫作階段而則將關注點放在控制論、信息技術、虛擬現實、人工智能等相關話題上,創作了一系列兼具本土化想象和后人類意味的賽博朋克作品。西方科幻曾經歷的幾個發展階段被不同作家借鑒吸收,共時地出現在中國科幻新浪潮中,構成當代文學場域中一股多元龐雜、充滿活力的潛流。
正如宋明煒強調的,當代科幻中所產生的先鋒敘事和異質書寫不僅是百年來中國科幻文學發展歷史中的一股“新浪潮”,也“對中國文學的主流造成了沖擊”,更應當被視作“當代中國文壇的一個新浪潮”4。因此宋著中“新浪潮”一詞或更應當取其字面引申義來理解,它指的是中國科幻文學從邊緣走向主流、從中國走向世界過程中所產生的現象級影響。由此,我們不難發現,宋明煒所建構的“中國科幻新浪潮”是一體兩面的:在敘事層面,它指的是中國當代科幻在主題、內容、世界觀等方面對既往文體的實驗性顛覆;在思想層面,它包含從現代性、本土性和全球性角度出發的詩學探索,并最終提出關于當代科幻言說的三個核心議題。
二、“孤獨者姿態”與“未完的革命”
《新浪潮》首先討論的是新科幻在當代文學史上的“坐標”和“定位”問題。回顧中國科幻百年來的發展歷程,由于政治傾向、社會思潮等諸種原因,盡管科幻文學曾數次繁榮,但其發展代際之間并無直接繼承與接續關系,而是形成了如同斷代史般的在精神上或有共通、但在文學書寫上卻各自獨立的局面。當“中國科幻文學史從來都是斷裂而非續接”的論段普遍流行,科幻作為“一支寂寞的伏兵”幾乎成為被反復強調的確論,宋著卻將當代科幻置于自“五四”至八十年代以來文學發展的整體脈絡中考察:在解構科幻小說存在于文學譜系邊緣的“孤獨者”姿態之余,亦試圖合法化重寫科幻內部曾被文學霸權與政治潛意識刻意壓制和遮蔽的啟蒙意識和先鋒精神。
盡管對于新科幻復興的時間起點并無定論,但評論家們大多同意將其定位在1990年前后。5頗有意味的是,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恰恰是當代主流文壇“最為沉寂”的時期之一。6“五四”以來所倡導的理性批判精神作為現代文學的核心命題被消解和擱置,宏偉的啟蒙論述幾乎銷聲匿跡。主流文學中的先鋒精神被流行文化收編,文學的地位也因此而迅速邊緣化后,文學場域中“完美的真空”7卻給予科幻文學萌發的機會。
啟蒙主題在新世紀以科學和幻想的方式重新歸來。以劉慈欣、韓松、王晉康等人為代表的“新生代科幻作家群”(即“第三代”)及其后的“更新代”8直接汲取了從魯迅到八十年代文學中的思想話語與批判姿態,以開放而新奇的姿態續接先鋒精神。通過對傳統文化的指認與顛覆、對技術的重審與祛魅,那些帶有嚴肅思考意味的科幻創作將新時期“以信息化、法治化和富裕化為特征的新愚昧,以及科學-政治拜物教帶來的身心壓迫”從潛流中拔擢至敘事層面,在技術背景和后現代維度中不斷回應、展開和創造啟蒙論述的新內涵。
吳巖認為,“從梁啟超和魯迅開始,中國的科幻文學發展出現了一個兩極性的文化空間。”9在梁啟超一極,未來暢想沿著科學上行而到達全新的形而上的哲理境界,譬如《新中國未來記》所描繪的諸種畫面,體現了基于宏偉視野的樂觀愿景;而在魯迅一極,科幻作為一種思想和工具沿著社會等級下行,被納入日常并滲透到生活的幽微細節之中,并以此抵達國人精神深處。顯然,宋明煒將“新浪潮”的精神源頭定位在魯迅一極。他認為,新浪潮興起,梁啟超式的光榮與夢想雖然也在,但是“對于劉慈欣、韓松等作家來說,魯迅代表了一種真正開啟異世界的想象模式。”10
魯迅及其精神作為“五四”文學革命留下最重要的文化符號和遺產,其筆下諸如“鐵屋”“看客”“昏睡”以及“救火者”等一系列詞匯在近百年文學書寫中反復出現,其含義已經從隱喻上升到明喻層面。新生代科幻作家將魯迅勾勒的中國視景加以延伸,以奇詭想象出入于虛擬的真實和寫實的虛幻之中,探勘現實以外的幽暗淵藪。宋明煒認為韓松是對魯迅有最自覺繼承意識的科幻作家,他在小說中創造的隱喻總在有意無意回應百年前的文化命題。以韓松的《乘客與創造者》為例,這是一個典型的發生在“鐵屋內”的故事,并忠實地呼應著魯迅的“吶喊”。小說中,人類生活的“世界”是一架在永夜之中飛行的波音7X7,封閉空間中充斥著黑暗頹廢、腐爛死亡的氣息。技術抹去乘客們的記憶,飛機里的人忘記了自我身份,對于周遭一切熟視無睹,“這世界上一切都無所謂”。盡管“啟蒙者”試圖幫助乘客逃出牢籠,但絕大多數人依舊冷漠麻木,寧愿殉身火海。更為可怖的是,少數有清醒覺知的乘客最終跳下飛機逃生,早已在地面等待他們的卻是一群持槍士兵。
在魯迅的鐵屋敘事中,鐵屋是有限的空間。驚起昏睡者,或有打破鐵屋而闖出去的希望,仁人志士們堅信等候在鐵屋之外的將會是與“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截然相反的事物。而在當代科幻敘事中,“鐵屋”卻失去邊界感,鐵屋內外空間的關系變得更為復雜。變異的技術放大了桎梏,鐵屋進化成層疊異形,主體從較小的囚籠內部逃離,卻奔赴進入更廣闊的鐵屋,導致絕望之外還是絕望。這一切無不彰顯著科幻寫作者焦慮的潛話語:技術進步與精神解放之間并不直接對應。走出“鐵屋”后,啟蒙話語在現代科技和后人類語境中非但遠未終結,反而化為深入宇宙肌理的無物之陣,充斥著無處不在的悖謬與迷茫。新浪潮科幻作家在技術文明背景下重審“五四”文學革命,這些“德先生”與“賽先生”的遺民態度相較于先輩卻更為矛盾,甚至充滿質疑的虛無。恰如魯迅所說,“于天上看見深淵。于一切眼見中看見無所有”,新浪潮中,一面是對啟蒙話語被遮蔽后導致的未完成狀態的懷疑、憂慮和悲哀,另一面是對光明、希望和自我意識歸復的極端渴求——這種分裂、焦慮與不確定恰恰是魯迅留下的精神遺產,也是重審啟蒙價值與現代性的第一步。
如宋著中所言,如何界定科幻與現代文學傳統之間既斷裂又續接的關系,是“我們如何理解科幻的想象模式為文學帶來的新奇的沖擊力”11的關鍵。質言之,在“新浪潮”的論述框架內,無論是策略性地把魯迅提到中國科幻的時間軸上,抑或是提出“《狂人日記》是科幻小說嗎?”之類的問題12,其實并非為得到某種確定答案,而是試圖在習以為常的文學史論述中重新定位科幻這一被遮蔽的“孤獨者”,同時彰顯科幻文學對先鋒精神與未完成之文學革命的續接與突破。
三、從“現實一種”到“異托邦想象”
科幻文學與現實言說之間的復雜關系是《新浪潮》試圖闡釋的另一關鍵詩學論題。宋明煒認為,科幻小說看似是具有強烈未來式、距離現實最遠的文類,實則卻與現實有著最緊密的關系。它的寫作對象看似是不存在的事物,但卻通過構造出迥異于日常生活且具有高度復雜性的“異托邦”,揭示了表象之下更為深層的“真實”。這種“宣稱說出真相的現實主義與看似與現實無關的科幻小說之間看似不可能的結合”造就了中國科幻史最曲折的言說維度,亦成為“新浪潮”的美學核心。13
在論述中,宋明煒回避了以“科幻現實主義”這樣的混搭術語來簡單指稱科幻與文學、與現實之間的關系,而更多將分析重點放在“科幻小說是如何在詩學意義上建立具有真實性基礎的語義、修辭和文本性”這一問題上。借用福柯的異托邦理論,宋明煒指出了尤為重要的一點,即科幻小說文本本身作為語言空間就是一種異托邦的構造,它以極度陌生化的題材和敘事建構了超越現實的“看的恐懼”,直接指涉那些人們不敢睜眼去看的異樣真實和令人恐懼的真相,從而揭示現實層面內外的復雜向度。
晚清以來,由“未來中國自立自強”這一政治愿景所驅載的烏托邦敘事和技術樂觀主義一直主導著科幻寫作模式。從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到吳趼人《新石頭記》,從莊鳴山《生活在原子時代》到葉永烈《小靈通漫游未來》,無不如是。
其間為數不多的例外或只有老舍的惡托邦寓言《貓城記》。一個世紀后,世界政治面貌發生深刻變化,在“中國夢”和“和平崛起”等政治構想下,當代科幻所建構的異托邦早已超越單純的未來寓言式的烏托邦/惡托邦,它復雜而尖銳地內嵌于當下存在之中,成為現實中國的轉喻場域,在邏輯上與真實世界發生既耦合又悖離的深刻聯系。
一方面,科幻異托邦從不回避認知上的真實性與現實感。這種真實性未必已經在現實層面成立,但卻必然或多或少建立在已有的認知邏輯、科學原則或擬科學思維之上。大量極具真實感的細節描寫起到“增強現實”的效果,使得科幻小說中超越日常邏輯的鏡像異世界具有強烈的說服力。無論是黃土高原上貧瘠落后的西部鄉村和留守兒童生活現狀(劉慈欣《鄉村教師》),還是充斥著斑斕暈影和惡臭氣息的東南沿海垃圾島和宗族制下困獸般的新人類(陳楸帆《荒潮》),科幻故事中無不填充大量真實社會歷史細節作為背景,一切恍如現實鏡像。于此般鏡像描寫中,作家們將日常細節中或詭異或反常的細節提純,準確切入現實中難以言說的幽暗一面,通過不斷重組各種文化元素、科技因子和政治愿景,構造出一個個被隔離、被治療、被規訓的異托邦空間,將對現實的反思融入對異世界的總體性構想之中。
僅僅討論異托邦是如何以虛構空間和另類視野再現已然存在的現實顯然是不夠的,它更作為與真實空間相對的“他者”而存在。“異托邦”的意義存在于它與現實之間曲折的轉述關系,其結構性目標是通過反抗和揭示“看的恐懼”來挑戰人們習以為常的大眾想象和現實秩序。于是乎,另一方面,異托邦又極度重視和強調創造認知上的陌生性,試圖以略微超前的時空姿態反身回刺現實,完成對認知世界的重構。蘇文·達恩將科幻定義為“認知上的陌生化”,其中的核心是奇觀與新奇事物(novum)。科幻小說所創造的異托邦恰恰是不斷被構造又不斷被瓦解的奇觀。
通過提供對現實有差異的另類認知和解讀,異托邦將“深藏在我們時代中、不為我們在日常經驗層面所感知的某種特征、某些力量釋放出來”。科幻作家筆下創造的二維“異世界”與三維“現實世界”有某種互文性聯系——拼湊文字碎片,便能得到通往真實世界的地圖——此間種種異象充滿了荒謬變形、無處不在的未知性和不確定性,恍若夢魘。這一敘事特點在韓松的創作中尤為鮮明。通勤路上,擁擠地鐵忽然失常,沿著鐵軌永不停駐地前進,將乘客帶去未知的地下世界,畸變和殘食如藤蔓般纏繞著眾人(《地鐵》);大地震后,建筑師發明了混合著廢墟和人類尸體制成的環保再生磚,以撫慰震后人們心中傷慟,再生磚中回響著的死者耳語和低泣竟意外使人沉迷,以至于人們不斷尋找新的災難(《再生磚》);平靜夜晚,人們卻傾城夢游,真相竟是政府為實現發展既定目標,決定放棄人民睡眠和做夢的權利,令睡夢中的人夜夜在夢游中完成額外工作任務(《我的祖國不做夢》)。在追求富強的現代化發展語境中,宏偉的“中國夢”畸變為鬼魅般的奇體中國。科幻小說打開書寫中國發展現狀和人們普遍心理狀態的新面向,它挑戰已有的“感覺結構”14,以技術化方式將細微而明確的社會事實轉化為極度陌生的景象和體驗,將超越性的抽象理念嵌入社會生活,對現實產生強大沖擊并持續重塑感覺結構和日常認知。異托邦建構可被視作科幻言說中的重要方法,“新浪潮”由此提煉出講述中國乃至世界“可見的正面”與“不可見的反面”的隱秘符碼,并追問其作用與意義。
四、“人的存在”與后人類狀況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科幻小說天生帶有世界文學的意味。它超越了國家政治身份,在光年尺度上思考人性與人類生存的終極問題,體現了“不可思議的崇高一面”。自圖靈測試以后,后人類主義思潮愈發旗幟鮮明地挑戰傳統人本主義對人的定義。當后人類主義在談論“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How we became posthuman?)”15的時候,實際上指向的是“什么是人”/“人何以為人”的本體論問題。以賽博朋克為代表的科幻文學想象中所描繪的“信息去身化”、“賽博格具象化”和“人類義體化”等現象無疑是這一思考后科技時代的新變體,諸類研究也幾乎都將后人類的倫理難題等同于賽博格的困境。
然而,“科幻新浪潮”中的“后人類問題”指向一種更為復雜而廣泛的“自我-他者”二元對立結構。宋明煒并未將后人類難題局限于“自動化控制機體,機器和有機體的雜糅體,現實和虛構的混合體”16對人的存在本身的挑戰,而是將研究視野進一步擴大,延伸到科幻對于人類未來多種形態與生存境遇的凝視與想象。他敏銳地捕捉到后人類狀況之下透射出的更深層問題,即同類與異類、自我與非我之間的“差異性”。自我與他者在差異之中互為觀照、互相馴化,從性別、階級、宗教、國族乃至物種等多個角度體現著“新的主體建構、政治身份和文化認同”17。由此,人類重新定義自我主體身份,改寫自我建構規范。
宋明煒在論述中擴大了后人類的內涵邊界。《新浪潮》中,“后人類”一詞不僅包括“黑客帝國式”的人工智能和控制論中的虛擬意識與去身化主體,也包括從瑪麗·雪萊《弗蘭肯斯坦》中的怪物到威爾斯《時間機器》中的地下人,從伊格言《噬夢人》中的生化人到劉慈欣《微紀元》中的微人,從韓松《紅色海洋》中的海底人到陳楸帆《荒潮》中的賽博格。后人類以不同形象一再出現,然而不管它的分身幻象為何,都包含同一認識基礎,即后人類主義是“對以自我為中心的人本主義信念的質疑和消解”,“不確定性和無限性挑戰著人文主義對于整體和諧的信念,瓦解了人文主義樂觀精神下的理性主義和自我決定。”18
宋著將科幻作品對后人類的態度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面對差異和未知的恐懼,另一類是對因差異而受難的他者近乎宗教感的同情,這兩種態度既矛盾又融合。19前者來源于人類中心主義面臨挑戰時而產生的普遍危機意識。正如福山所憂慮的,受現代技術裹挾的人將逐漸淪為信息和數據符碼化的后人類,人性悄然異化,“我們將站在人類與后人類歷史這一巨大分水嶺的另一邊,……卻沒意識到分水嶺業已形成,因為我們再也看不見人性中最為根本的部分。”20但這一觀點依舊是建立在傳統人文主義話語之上,始終未能突破人類中心主義所導致的認知盲區。而作為思想前沿的后人類形象傾向于在差異中重新結構對人和人性的定義,隨之而來的第二種態度則是在理解、包容差異的基礎上產生的超越性認同。它使得構筑一個更為和諧的“世界命運共同體”成為可能,亦是新一代中國科幻作家處理的重要命題。
在“更新代”中,陳楸帆或許是最具有全球視野和后人類書寫自覺的科幻作家之一。借由跨越性別、階層乃至物種的異視角通感與意識共情手法,陳的作品往往將懸置的人類感覺內嵌于他者的感官和生命體驗之中,毫不避諱地暴露出后人類狀況中的諸種倫理困境,并在極端異化和沖突中獲得對世界的再理解。無論是以人造子宮體驗原始的生育痛苦來跨越性別認同之差的行為藝術(《這一刻我們是快樂的》),或是在意識上切入巨型機械的網絡神經而完成了從垃圾人到賽博女神的非我身份覺醒(《荒潮》),甚至是以消泯自我意識為代價融合入其他物種智慧意識的生命體驗(《巴鱗》),陳楸帆筆下的故事無不證明著在對“差異”的包容和重構中蘊含著另一種平等想象個體、人類、世界命運共同體的可能性——這恰如宋明煒在書中所寫:“我們如何理解人,取決于我們如何看待非人”,“我們如何理解他者,關系著我們如何理解自己。”21也正因科幻對“差異性”葆有長久關切,使它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文類。
中國當代科幻正以某種奇特的方式向前行進:一面開啟嶄新的黃金時代,另一面又衍生出頗具顛覆性的新浪潮,兩者齊頭并進、雙生共存。正如《三體》中地球向宇宙發出廣播而顯露坐標,當中國當代科幻唱響古老地球之歌時,也正以跨越光年的速度向全世界廣播本土作家對宇宙存在的嚴肅思考。
事實上,如何定義科幻文學,如何定義“中國科幻的‘中國性’”22,這些問題迄今尚無定論。不同類型的科幻在“科學性”“未來性”“敘事性”“現實性”23四個向度中不斷游移,其內部張力所帶來的豐富可能性本能地拒絕任何一種欲將其符號化、秩序化和固型化的理論批評。正因如此,作為國內第一部科幻小說評論專集,《中國科幻新浪潮》的可貴之處恰恰在于它并未試圖建立某種統蓋全局的科幻詩學。就論述內容而言,作者策略性地選擇將科幻的“敘事性”和“現實性”作為分析重點來建構科幻小說的中國闡釋,在系統介紹世紀末科幻新浪潮興起始末、探討中國科幻文學發展譜系的同時,分析中國科幻的先鋒性、想象力、創造性之于世界的意義。
誠然,在這本十余年來陸續發表文章的結集中,其中難免出現一些重復甚或矛盾的痕跡。但這正是作者在提出新理論過程中留下的“未完成的仍在進行中的”思考痕跡,亦是其對新穎觀點不斷篩選、淘洗、打磨、統合的另一種證明。24以“新浪潮”一詞形容科幻敘事的氣勢,不僅體現了宋明煒對科幻在當下引起關注之“此刻意義”的洞見和發掘文學新質的學術敏感,更顯示了他試圖打造“極具中國特色的科幻詩學”25和創新理論格局的雄心。
本文原刊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2021年第6期
作者簡介
汪曉慧:1995年生,浙江臨海人。曾在《揚子江文學評論》《當代作家評論》《中國比較文學》等期刊發表評論文章,另有小說發表于《鐘山》。
注釋
1:2010年,科幻作家飛氘曾在“新世紀十年文學”國際研討會上就當時的科幻文學景況做過精妙的比喻:“科幻更像是當代文學的一支寂寞的伏兵,在少有人關心的荒野上默默地埋伏著,也許某一天,……會斜刺里殺出幾員猛將,從此改天換地。但也可能在荒野上自娛自樂自說自話最后自生自滅,將來的人會在這里找到一件未完成的神秘兵器,而鍛造和揮舞過這把兵器的人們則被遺忘。”
2:宋明煒:《中國科幻新浪潮》,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268-269頁。
3:吳巖:《科幻文學論綱》,重慶:重慶出版社,2011年版,第218頁。
4:劉亞光,宋明煒:《如何理解“中國科幻新浪潮”?》,《新京報書評周刊》,2020年7月23日。
5:科幻作家、評論家王瑤(夏笳)在博士論文《全球化時代的恐懼與希望:當代中國科幻文學及其文化政治(1991-2012)》中亦將“清污”運動以后科幻小說再出發的起點定位在了1990年前后。
6:宋明煒:《〈叔叔的故事〉與小說的藝術》,《文藝爭鳴》1999年第5期。
7:宋明煒:《中國科幻新浪潮》,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268頁。
8:對于中國當代科幻作家的代際劃分參見《中國百年科幻史話》,董威仁編著,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9:吳巖:《科幻文學的中國闡釋》,《南方文壇》,2010年第6期。
10:宋明煒:《中國科幻新浪潮》,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200-202頁。
11:宋明煒:《中國科幻新浪潮》,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70頁。
12:宋明煒:《中國科幻新浪潮》,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201頁。
13:宋明煒:《中國科幻新浪潮》,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270頁。
14:[英]雷蒙德·威廉斯:《漫長的革命》,倪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頁。
15:[美]凱瑟琳·海勒:《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劉宇清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16:[美]唐娜·哈拉維:《賽博格宣言》,陳靜譯,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14頁。
17:宋明煒:《中國科幻新浪潮》,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256頁。
18:宋明煒:《中國科幻新浪潮》,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166頁。
19:宋明煒:《中國科幻新浪潮》,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256頁。
20:[美]弗蘭西斯·福山:《我們后人類的未來:生物科技革命的后果》,黃立志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序言。
21:宋明煒:《中國科幻新浪潮》,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12-13頁。
22:王瑤:《火星上沒有琉璃瓦嗎——當代中國科幻與“民族化”議題》,《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9期。
23:張朔:《中國當代科幻小說研究芻議》,《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
24:在即將出版的英文科幻理論專著《The Fear of Seeing》(《看的恐懼》)中,宋明煒對這些觀點和動態思考進行了更為成熟透徹的系統性總結。
25:王德威:《想象世界及其外的方法》,《讀書》,2020年第3期。
- 性別?寓言?烏托邦——劉慈欣《三體》中的文化啟示與后人類想象[2021-1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