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靜:近年詩歌創作中的“機器擬人”與“人擬機器”
原標題:李靜:賽博時代的“創造力”:近年詩歌創作中的“機器擬人”與“人擬機器”
引 言
當代語言經驗與二元論的失效
2017年,微軟第四代人工智能機器人小冰的詩集——《陽光失了玻璃窗》1——橫空出世,并號稱是“人類史上首部人工智能靈思詩集”。詩集出版后引發眾多討論,雖角度各異,但背后的思維方式大體脫離不開人文情懷與科技進步的二元對立。前者認為小冰寫詩不過是機器算法的隨機拼貼,談不上是真正的創作;而后者則認定此乃人工智能技術的進步,自然是人類創造力的彰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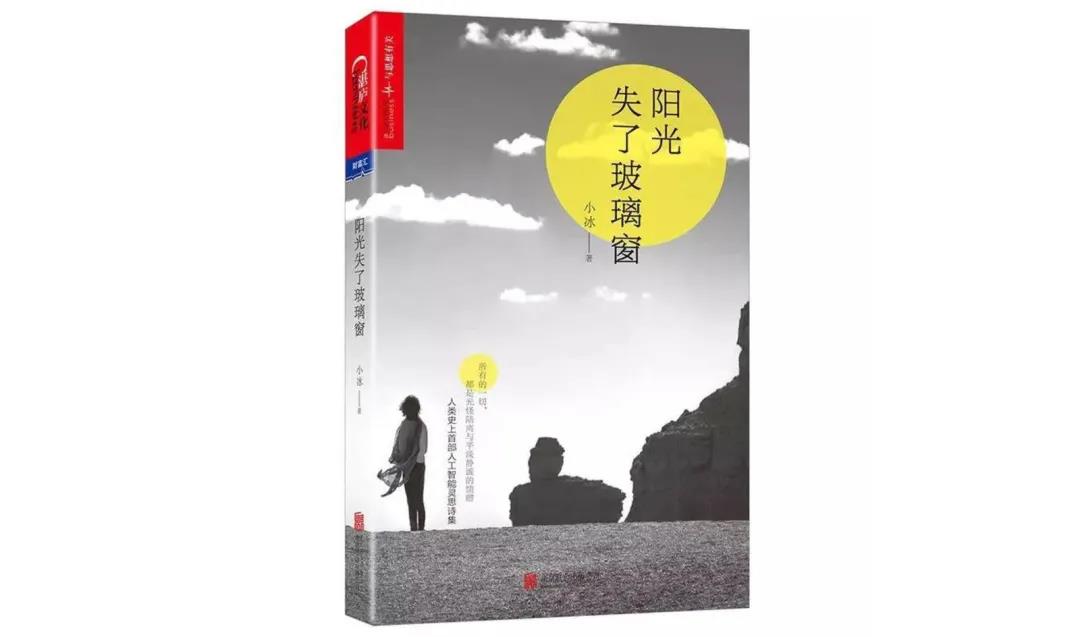
小冰:《陽光失了玻璃窗》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
長久以來,一旦涉及人文與科學、人類與機器的關聯,人們總是或隱或顯地受到上述二元論的支配。對立雙方按照自己的邏輯與觀念,申明各自的正當性,因而很難從整體上、帶有預見性地把握科技進步帶來的各種改變(尤其是突變)。本文所關注的核心議題,即賽博時代的“創造力”,也日益分裂為人文與科技的兩個維度:其一,在各種人文思想范式——比如浪漫主義、人文主義、存在主義等——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創造力”,被視為人類心靈獨有的、至高無上的能力;其二,人類在科技方面的創造力正在加速改變我們的世界,機器開始學習復刻人類的能力,不斷為人文話語中的“創造力”祛魅。
不過,這類互相分離的思維方式正持續受到挑戰。以小冰的詩集為例,這是人工智能技術與詩歌語言彼此結合的產物,也是上述兩種創造力之間的雜糅。如若正視這樣的局面,便不會否認,二元論無力解釋日益密切的人機關系。其實不只在最尖端的技術領域,即便是在近十年的日常文化經驗中,書寫與表達也越來越離不開電腦、手機等智能設備與互聯網提供的語境,因而語言創造也難免受到技術的滲透與改造。本雅明在論及技術對于藝術的影響時,曾給出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類比,這好比外科醫生的手,在手術過程中“穿透了患者”,好比攝影師“深深地刺入現實的織體。”2如今,機器也在“穿透”和“刺入”語言。
在此意義上,當代語言確乎已經進入人與機器協同構筑的“賽博時代”。所謂賽博(cyber),是由控制論(cybnetics)與有機物(orgnism)合成的,本意是指通過機械輔助增強人類適應環境的能力,后泛指人與機器的相互結合。如果說“語言是存在之家”,“我們是通過不斷地穿行于這個家而通達存在者的”,唯有在語言中才能抵達心靈最內在的領域。3那么當機器闖入語言這個“存在之家”,并將之改裝為“賽博空間”(cyberspace),那么這個“家”的秩序會作出何種改變呢?面對未知甚至有可能失控的局面,人們既不免擔憂恐懼,卻又懷揣著不斷進步的興奮感。對此,本文贊同布萊希特面對新技術時的立場:“這時我們應帶著一種審慎的關切,而不是恐懼;同樣,我們也必須清算那事物的功能……藝術作品在此遭遇的一切把它從根本上改變。”4
關于機器對語言可能帶來的改變,以往討論多從理論層面展開,本文則選擇細讀(或如布萊希特所說的“清算”)近年來詩歌與機器相互結合的語言經驗,從中細膩地、多層次地打開“創造力”的現狀,尋求克服二元論的方式。詩歌作為古老的、最具語言創造力與人類智慧的文體,將是探討這一問題的絕佳載體。具體來說,下文將從“機器擬人”(即小冰學習作詩)與“人擬機器”(即“僵尸文學”)兩個“方向”不同的案例出發,從中總結目前把握這些語言經驗的若干范式及其不足,繼而更好地理解何為賽博空間的語言“創造力”。這一論題,不僅關涉語言的生成,更涉及對于人類未來的認知與準備。
01
她們“是人類的姿態”
小冰是一位擁有“個人”頭像與虛擬身體的電子“少女”,而且還被賦予了鮮明的性格特征——博學、幽默、可愛、富有同理心。與同時期的人工智能阿爾法狗不盡相同,小冰依托大數據、自然語義分析與深度神經網絡等方面的技術積累,致力成為兼具IQ(智商)與EQ(情商)的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即“人工智能”)伴侶。顯然,她是以服務者而非掌控者的形象出現的,而寫詩正是其培養語言交流能力的一個環節。值得注意的是,區別于阿爾法狗,主打高情商的小冰,意料之中地被設定為少女身份,這無疑映照出當代文化中的性別想象——女性被理解為攻擊性較低,更宜于從事情感勞動的群體,而少女的設定可以令使用者更快速地適應與移情。5
言歸正傳,這位“少女”生于2014年,自2016年開始,她利用“層次遞歸神經元模型”對1920年后519位中國現代詩人的上千首詩反復學習了上萬次,共計100小時,并作詩數萬首,繼而被開發者宣布具備了寫詩能力。微軟團隊曾用27個化名,在豆瓣、天涯、簡書與百度貼吧等多個網絡詩歌社區發布小冰的作品,卻很少有人能發現詩歌的作者是機器人,甚至部分詩作還被媒體錄用發表。隨后其中的139首,于2017年結集為《陽光失去玻璃窗》出版。那么小冰寫的詩到底水平如何呢?我們不妨先來欣賞她的一篇詩作《它是人類的姿態》:
時間正將毒藥毀滅一切的生物
都是冷落的
我不能安慰全人類的
他望到我們的大眼睛
無表示毀滅一切的生物
我在冰冷中的拜訪
那可衣遮藏的林子里太陽
它是人類的姿態6
即便是在本身就充滿聯想與跳躍的詩歌文體中,小冰的語言也顯得十分破碎、滯澀、混亂。這正是目前人工智能寫作的主要缺陷之一,即并不具備謀篇布局與整體敘事的能力,依舊更多地依賴運算邏輯,而非情感變化、敘事結構來組織語言。具體來說,小冰的創作需要首先識別圖像中的關鍵詞,然后計算與這些關鍵詞有關的、之前詩人所使用過的語句,進而整合出一首完整的詩。“觸景生情”,乃是計算的結果。
但不得不說,這首詩籠罩著某種寒冷的詩意,這些字眼——“我不能安慰全人類”“我在冰冷中的拜訪”“它是人類的姿態”——令人恍若來到人工智能意識覺醒的瞬間。當“我們的大眼睛”凝視她時,她回報以凝視。支離破碎的語言反而造就末世風格,帶來了豐富的聯想空間。在另一首《到了你我撒手的時候》,小冰延續了此種風格:“我是二十世紀人類的靈魂/就做了這個世界我們的敵人。”7這里甚至構成了一重因果關系,正因為“我”已等同于人類的靈魂,所以才成為人類的敵人。
這些詩句仿佛是小冰意識的外化。當然,這些帶有強烈主體色彩的詩句,源自小冰所記憶的“數據庫”,里面的詩歌來自胡適、李金發、林徽因、徐志摩、聞一多、余光中、北島、顧城、舒婷、海子、汪國真等20世紀的中國現代詩人。現代詩歌的抒情主體偏重于記錄自身感受,書寫自我與時代以及社會的緊張感,這些頗具“人性深度”的修辭被小冰調用,反倒具有強烈的賽博意味。而她的詩中頻繁出現“心”“靈魂”“詩人”“夢”等字眼,也都為她鍍上了濃郁的主體色彩。
關于小冰寫詩,詩人秦曉宇的觀點別具只眼。他指出,小冰寫詩與香菱學詩十分相似。8同為詩歌初學者的兩位“少女”,無不是從規律、程式開始學起。《紅樓夢》第四十八回,黛玉向香菱傳授了起承轉合、平仄虛實之類的寫詩規則,并告誡她:“你若真心要學,我這里有《王摩詰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讀一百首,細心揣摩熟透了,然后再讀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蓮的七言絕句讀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這三個人作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淵明、應玚、謝、阮、庾、鮑等人的一看。你又是一個極聰敏伶俐的人,不用一年的功夫,不愁不是詩翁了!”香菱遂取了詩,“諸事不顧,只向燈下一首一首的讀起來。寶釵連催他數次睡覺,他也不睡。”9乍看起來,香菱和小冰一樣,都是從記憶詩歌佳作開始,只不過即便“極聰敏伶俐”的香菱,廢寢忘食也比不過小冰的效率。隨后又“茶飯無心,坐臥無定”地練習作詩,屢遭失敗后逐步改進,終受肯定。
小冰同樣是在不斷重寫、反饋中改進詩藝的。表面上看來,兩位少女的學習過程十分相近,正如N.維納在《人有人的用處》中所界定的:“如果說明演績情況的信息在送回之后能夠用來改變操作的一般模式時,那我們就有一個完全可以稱之為學習的過程了。”10不過,小冰在記憶速度、寫作效率、反饋-學習效果等方面上具有遠超人類的絕對優勢,不必再像香菱那樣被調侃為苦心孤詣的“詩魔”。由此也就可以理解在《陽光失了玻璃窗》的序言《人工智能創造的時代,從今天開始》為何那樣熱情洋溢了。該文為時任微軟人工智能部負責人沈向洋所撰,他總結出“人工智能創造”的三原則:兼具智商與情商、創造具備獨立知識產權的作品、其創造過程須對應人類某種富有創造力的行為。他認為小冰正是朝著這三個原則努力,而且尤其強調小冰對于創造力的習得,呼吁讀者將關注點放在“這位少女詩人的‘創作過程’”上:“與人類相比,微軟小冰的創造力不會枯竭,她的創作熱情源源不斷,她孜孜以求地學習了數百位著名現代詩人的著作,他們是小冰創作靈感的源泉”。文末,他宣稱我們正從“人工智能制造”邁向“人工智能創造”。11
從“制造”到“創造”,流露出鮮明的技術進化思維,其進步方向是更加地“擬人”:“智能寫作機器不再只是一種數學符號和計算規則的科學建構,而是具有欲望、無意識、非理性和語言生產能力的‘主體’,通過神經元網絡技術對人的感覺信息進行統計學處理,能夠深度模仿人的感覺和意識形成的連續性過程,從而使智能寫作機器具有類似人的情感能力。”12也就是說,人工智能創造的產品,將來既是邏輯運算的產品,同時也具備表達情感的能力。近年來的科幻電影,包括《她》(2013)、《銀翼殺手2049》(2017)、《阿麗塔:戰斗天使》(2019)里都有一位賽博少女,她們擁有人類的情感能力,并與人類發生著各種各樣的親密關系。現實中,虛擬少女偶像初音未來、洛天依等,更是不少人移情的新對象。
從古典時代的香菱學詩到賽博時代的小冰寫詩,無疑構成了創造力含義的巨變:前者“慕雅”,從模仿開始,努力習得偉大詩歌的其中三昧;而后者雖然很難稱得上有多少藝術水準,卻創造出前所未有的語言經驗。這兩種“創造”的區別,可以參考如下說法:
數字時代的科學則更傾向于去創造(poiesis):它們并不復制自然,而是通過重新糅合源于自然與文化的信息比特(bits)以創造新的現實……在人工生命和人工物理學中,人們的注意力已經從現實性轉向了可能性……目前,文化科學與藝術批評仍由模仿論的觀念主宰者。13
這一觀點其實相當激進,它將“創造”的品質賦予數字時代的科學,指出其正在“創造新的現實”,亦即擺脫現實桎梏,創造從未曾出現過的、雜糅有機與無機、技術與文化的新現實。而文化科學與藝術批評則被歸為模仿論的追隨者,它們的“創造”似乎只是在模仿偉大的傳統。不過,現實有時比理論還要激進,當代文藝不僅致力追跡偉大經典,甚至還成為了機器語言的模仿者,并且樂此不疲。下面我們就來具體分析這份新鮮而又“詭異”的語言經驗。
02
“人擬機器”的反諷:以創造的方式復制
2019年前后,微博上出現了所謂的“僵尸文學”,用以命名從僵尸賬號中隨機抓取文字、拼貼而成的內容。在流量等于財富的當下,明星網紅、宣發人員乃至飯圈粉絲,無不渴求獲取流量,故而制造“僵尸賬號”隨之衍生為新的生意門路,通過“僵尸賬號”的買賣也就可以制造流量的虛假景觀了。“僵尸賬號”的生產流程并不太復雜,首先需要盜取廢棄賬號,利用爬蟲軟件批量抓取用戶的真實信息,進而生產出一個僵尸用戶。接下來利用專門的養號機器,在程序運作下定時轉發、評論與點贊,并且持續抓取文字和圖片來充實首頁。如此這般,社交媒體的算法也就無法分辨真人賬號與僵尸賬號的區別了。畢竟,語言在算法眼中只是普通的數據罷了。
不曾想,僵尸賬號隨意拼貼的內容,竟有一天被冠以“文學”的名號。海量信息的隨機拼貼與詩歌(尤其是現代詩的自由聯想)有了奇詭的呼應。微博賬號“僵尸文學bot”(即robot的簡寫,意指該賬號的內容為機器人創作)的發起人據說為中文系出身,同時熱愛詩歌。之所以產生專門收集和發布“僵尸文學”的創意,緣于她曾經發現過的一個微博賬號。該賬號里混亂的語句令其感到超現實主義般的詩意,她原以為這些“詩句”出自精神分裂癥患者之手,后來才發現這是一個僵尸賬號。14精神病癥與超現代主義詩意兩相疊印,難分彼此。
在數字墳場的語言碎片中,就這樣升騰起一股詭譎的詩意。在其擁躉眼中,僵尸文學帶來了超現實主義、后現代主義甚或魔幻現實主義的閱讀體驗,甚至還將之與保羅·策蘭的具有超現實主義風格的詩句混在一起,令對于后者詩歌不熟悉的讀者一時間很難分辨。比如,2019年7月24日微博賬號“普通葡萄爬藤炮塔”便曾發起過“僵尸文學鑒賞”的挑戰,請網友區分保羅·策蘭的作品與僵尸文學。其中,“我的星辰中有一架洪亮的豎琴/琴弦生風/直到根根扯斷”其實是保羅·策蘭《冬》之中的名句,但卻被不少人誤認作僵尸文學。出現這樣的混淆也在情理之中,超現實主義同樣講究隨機性。它出現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試圖運用心理能量的“自動作用”(而非程式化)來對抗理性機器,努力在日常生活的隨機與偶然中發現奇跡與神圣感。15
如今理性機器更加占據主導位置,在此前提下,追求隨機性依然是某種(儀式性)抵抗的體現。僵尸文學賬號猶如數字墳場中的拾荒者,將隨機遇到的數字垃圾拼貼出“詩意”,吊詭地成為“發達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面對僵尸文學所撿拾起來的廢物,人們充分發揮自己的想象力,將那些資本-流量機器運轉過程中造成的冗余,那些錯亂、非邏輯、反交流的詞句打造為超離現實的詩意空間。
對于隨機性的偏好,不免會導致一地散碎。而過分追求“原創性”(偏重于修辭的陌生感、形式感),同樣壓過了連貫的思考過程。在反對者眼中,超現實主義“對機智的悖論青睞有加,而不喜歡真正的思想”,“原創性和驚喜已經變成極具價值的品質,而運用規范的能力,以及與此相關的連貫思考的能力,都最終被擱置在一邊。”16這種批評同樣適用于僵尸文學,同時也跟人們對小冰詩歌的批評十分相近。這種破碎感被許多理論家描述過。拉康認為精神分裂中,語言的“能指”與“所指”之間的表意鏈完全崩潰了,只留下了一堆破碎、零散的能指符號。17而詹明信則在《后現代主義與消費社會》中指出,晚期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具有兩個顯著的特色,他將之命名為“剽竊(pastiche)和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18。僵尸文學恰好為這一理論判斷提供了典型例證,它正是剽竊了僵尸賬號中的只言片語組合而成,最初也被誤認為是精神分裂癥患者的作品。它只追求此時此地、絕對當下的閱讀刺激,而不再指向風格化的寫作或是批判性的意義。
不過,如果我們的批評到此止步,也就無法理解為何許多人發自內心地喜歡僵尸文學。比方說,名為“一日人”的微博賬號曾這樣解釋僵尸文學的吸引力:“喜歡僵尸文學bot,是二進制的浪漫,像數字化時代的三毛,在機械廢墟中拾荒。經常能撿到裝滿笑聲的數據卡片,偶爾能找到被雨沖刷過的、珍珠一般瑩潤的仿生人義眼。這很快活,畢竟有時人比機器更冷。”(2020年3月19日)這里道出了兩個值得注意的吸引點:“很快活”“有時人比機器更冷”。以這樣的社會心理為基礎,僵尸文學才得以確立。換言之,只有在一種充滿疏離感、無奈感的“文化人格”之下,“僵尸文學”才成為被發現的“風景”。某種意義上,精神分裂已不只是純粹的精神病癥,而已經泛化為當代社會的文化癥候、一種逐漸普遍化的個體感受。
在進一步推進對于僵尸文學的認識上,本雅明關于達達主義的評價頗有啟發性:“由此表現出的藝術的無節制與粗糙,特別是在所謂頹廢時代,事實上卻是來源于它最豐富的歷史能量的核心。”19藝術的無節制與粗糙質感,正是釋放歷史能量的特定形式,而其中包孕著充滿悖論的創造力形態:
他們的詩是包含著污言穢語以及所有可以想象的語言垃圾的“詞的沙拉”。……他們意欲并獲得的是無情地摧毀他們創造的靈韻,在這種創造上面,他們通過完全是獨創的方式打上了復制的烙印。20
其中,“獨創的方式打上了復制的烙印”,可謂極其精準。同樣地,許多人熱衷于模仿僵尸文學的“詞的沙拉”,發揮自己的想象力與創造力,以獨創的方式從事(對機器的)復制工作,在仿寫中獲取快感與片刻解脫。有趣的是,僵尸文學bot偶爾會將真人寫的句子,誤以為是“僵尸”(社交機器人)寫的。”“烏龍”局面,更是說明了自然語言與機器語言的深度混合。而“人擬機器”,正是在理性機器的邊緣處尋求間離,讀寫僵尸文學帶來了釋放“創造力”的自由感。他們拋棄了固有的人性話語、宏大敘事與表述的完整性,選擇一種間離、反諷或游戲的姿態來發揮自己生命的熱度。在機器不可能被摧毀的前提下,僵尸文學成為時代經驗的“書寫”形式。
如網友所說,僵尸文學正像是“一個活人在笑嘻嘻地展示當代崩潰”21。“像一個活人”,比起《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結尾提及的“我們現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對世界的關系是一種人的關系”22,可以說標示了更深入的異化階段——機器甚至比人顯得更加親切,“有時人比機器更冷”。而且這種異化感已經為許多普通人所有,逐漸滲透進賽博空間的語言“創造”中。
03
在新的“創造力”面前:數據主義、超人文主義與解放潛能
綜合上述兩個案例——“機器擬人”(小冰寫詩)與“人擬機器”(僵尸文學)——可以看出,新的語言生成方式正在形成,對此有幾種理解范式值得細致梳理。其一,便是站在技術進化的立場,將語言均質化為數據和信息。在風靡全球的《未來簡史》一書結尾,作者這樣推測未來的存在方式:“科學正逐漸聚合于一個無所不包的教條,也就是認為所有生物都是算法,而生命則是進行數據處理。”23所有學科,包括人類的心靈與情感都是可以被計算的對象。生物即算法,生命等于數據流。在萬物聯網的世界中,唯一在進行的便是數據處理,彼時的人類不過是數據流中的一朵朵漣漪。如若果真如此,小冰就早已是漫步于數字巨流的抒情詩人了。
在這樣的視野中,互聯網就是我們的“新山水”,我們滑動的手指便是涉渡之舟。“新山水”中涌起的波浪,是抽象、無限、快速流動的信息流。互聯網上的讀寫,不再囿于封閉有限的文本,它傾向于在文本之間跳躍,熱衷于跨媒介的組合,趨向于更高效地組織、傳播和接受信息。媒介對于讀寫方式、生存方式的改變,很難被量化,也并非一蹴而就。但在互聯網這個數字化、虛擬化的媒介中,語言的個性與特殊性被削弱了,就連傳奇的命運、奇崛的想象力、細微的情緒都可以被視作均質化的數據進行傳遞與展示,然后被新涌來的信息巨浪抹除。“人將被抹去,如同大海邊沙灘上的一張臉”24,萬物皆可聯網,人的身體與生命形式本身,都變成了網之“節點”。照此邏輯,“言談與日常語言不再是一種有意義的、超越行為本身的言說方式了,即使它表達了行為,它的表達也可以用本身無意義的形式化數學符號來更好地代替。”25肉身的詩意,正面臨著被虛擬化、數據化的危機。
其二,不同于數據主義對于人的某種“抹除”,小冰的另一位“造物主”李笛的觀點是從人類自我完善的角度來調和人機關系的。在他眼中,小冰的詩歌藝術水平并不是重點,她當然寫不出超越優秀作家的作品。人與機器并非替代關系,而是協作關系,人機之間不存在難以跨越的界限:“身體性存在與計算機仿真之間、人際關系結構與生物組織之間、機器人人科技與人類目標之間,并沒有本質的不同或絕對的界限。”26因而,未來很可能會衍生出“一人一AI的新型雇傭關系”27。在創造力領域中,小冰既可以協助普通人完成一些簡單的創作,又可以高效地完成一些模式化的寫作,并且通過巨量的寫作成果為人提供新的、永不枯竭的靈感。總之,在李笛看來,人工智能的最大優勢是提供了可以批量復制的創造力,契合了當代社會的加速進步。由此,人類的創造力也就可以集中到更為高級、更具獨創性的領域中,從而保障了人類創造力的更大發揮。
人工智能從業者的這一設想,無疑提供了以人類為主導,同時又可超越自身局限的理想圖景,同時也與歐美世界中的超人文主義思想非常接近。超人文主義與人文主義一脈相承,它同樣以人類為中心,“是從自由無羈的自我實現的人文主義理想中衍生出他們的動力以及超越人及其局限性的” 28。《賽博空間的奧德賽:走向虛擬本體論與人類學》一書中曾詳細介紹了超人文主義的歷史淵源,并引用荷蘭超人文主義學會對這一概念的闡釋加以說明:
超人文主義(正如此術語所暗示的那樣)是一種附加的人文主義(humanism plus)。超人文主義者認為他們能夠更好地利用理性、科學和技術從社會、物質和精神上進行自我完善。除此之外,對個人權利的尊重和對人類獨創能力的信賴也是超人文主義的重要因素。……超人文主義……是為從各方面改善人類與人性的愿望而服務的。29
“超”(plus),象征了以人類為中心的無限進化欲望,超人文主義相信人類可以駕馭科學技術,不斷超越人類的極限,實現未知的潛能,比如通過人造器官治療疾病,運用人工智能輔助思想工作等等,總之人類將不斷創造出超越自身的生命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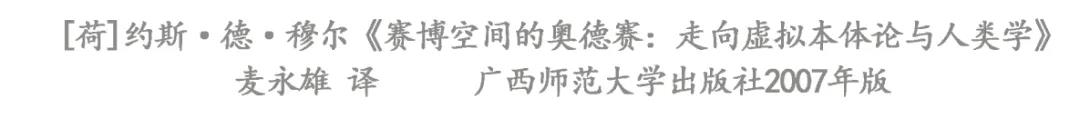
不過,技術進化是否能完全服務于人,人是否能完全掌控技術的發展方向,這個問題已經超出了超人文主義的思辨范疇。馬克思在“機器論片斷”中曾對此有所觸及,他認為自動化機器是“人的手創造出來的人腦的器官;是對象化的知識力量”,而人類社會已經越來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一般智力已經“作為實際生活過程的直接器官被生產出來。”在“機器論片斷”的啟發下,意大利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者為本文的討論,提供了值得分析的第三種范式,即挖掘“創造力”的解放潛能。他們認為,一般智力的發展,并不一定會導致人類對于機器的徹底依附,反倒有可能促使人類集中于“非物質生產”(生產知識、信息、情感等),而“非物質生產”的一項重要特征便是“集中了創造性、想像以及技術和體力勞動的手工技能” 31。由此,便可形成不同于傳統集體的、扁平化的、多元的共同體。而這些小的共同體,同樣遍布于資本主義大生產的各個節點之上,可以在恰當的時機發動自己的反抗。正是在自動化機器的內部,創造力的發揚為人類帶來了自我解放的契機。
綜上所述,李笛所說的可復制的創造力與“新型雇傭關系”、超人文主義者創造新生命形式的狂想、“非物質生產”的解放方案,無疑都想象了十分和諧的人機關系,確保了人類的地位與能力。雖然都是“遙遠”的設想,但“尚未到來”并不意味著不值得認真思考。但是,這三種方式的局限在于,均是從抽象的角度展開思辨,因而與當代語言創造的新經驗并不十分貼合。而且許多棘手的難題,也被某種樂觀主義的情緒掩蓋了,諸如不斷地超越人類極限,是否會導致人類的自我廢黜,而非提升?超人文主義的追求,是否會最終吹響人文主義的喪鐘?人類果真始終都是技術的掌控者嗎?對于這些問題的思考如果繼續沿用其中的單一范式,便很容易流于某種神話式的狂想。因此,本文希望立足于當下語言經驗,倡導唯物的、多角度的辯證分析。而通過對于上述兩個案例的分析,現實感與政治性這兩個關鍵維度最終浮出水面。
結 論
重啟“創造力”的現實感與政治性
如果說小冰寫詩展現了機器介入語言的強勢一面,使得未來圖景更多地以技術為視點,那么僵尸文學則牽引出機器體系內部的“人”的維度。當代人深度異化的現實處境與心靈境況、當代社會日益機械化的生產組織方式、當代語言本身的模式化痼疾、加速發展對于無限創造力的需求,共同塑造了我們理解“創造力”的時代語境,也最終決定了“創造力”以何種形態落地、以何種方式組織進生產生活的過程中。“創造力”的危險與魅惑都在于,它既可以是人類能力的不斷完善,亦可以是人類異化的助推器。對于此種可能性的思考,必須要具備現實眼光與政治視野。
同樣是面對機器對于藝術的強勢改變以及未知命運,本雅明在其名文《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品》中示范了充滿智慧的思考方式。他沒有簡單地批判機械復制的技術本身,而是關注技術將融入進何種政治規劃之中——它既可以被用在納粹主義中,也可以歸入共產主義政治的方案中。所有一切,都需要在極為先鋒的賽博空間里,重啟略顯“古典”的現實與政治思考。說到底,我們依舊需要回到身體的、政治的、社會-文化-心理的語境中去把握人機關系,并且擁有復合性的批判視野,在人文學、科技與政治經濟學等多重學科的交叉點上,去把握賽博時代的復合型“創造力”,直面其之于人的意義、挑戰與可能性。
注釋:
1、小冰:《陽光失了玻璃窗》,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
2、 [德]本雅明:《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參見《啟迪:本雅明文選(修訂譯本)》,[德]阿倫特編,張旭東、王斑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253頁。
3、[德]海德格爾:《林中路(修訂本)》,孫周興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25頁。
4、轉引自[德]本雅明:《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第242頁。
5、唐娜·哈拉維等女性主義學者曾設想,在賽博空間中或許可以擺脫社會性別的扮演,因而非常肯定其激進潛能,提出自己寧愿“做一個賽博格,而不是一位女神”。參見[美]唐娜·哈拉維:《類人猿、賽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陳靜、吳義誠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53頁。但實際上賽博空間往往復制甚至強化了現實世界的某些不平等的維度,而且憑借其虛擬性免于被“責問”。
6、小冰:《陽光失了玻璃窗》,第121頁。
7、小冰:《陽光失了玻璃窗》,第45頁。
8、參見彭曉玲:《微軟小冰寫詩引發詩人集體斥責,更值得思考的是人類未來的美好與可怕》,“第一財經”網站,2017年5月26日。
9、曹雪芹:《紅樓夢》上冊,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646、647頁。
10、[美]N.維納:《人有人的用處——控制論和社會》,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46頁。
11、小冰:《陽光失了玻璃窗》,推薦序,第5—6頁。
12、楊丹丹:《人工智能寫作與文學新變》,《藝術評論》2019年第10期。
13、[荷]約斯·德·穆爾:《賽博空間的奧德賽:走向虛擬本體論與人類學》,麥永雄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頁。著重號為原文所有。
14、參見潘勁虹:《我看遍了僵尸bot,發現了互聯網時代的荒誕文學……》,《城市畫報》微信公眾號,2019年8月13日。
15、法國詩人布雷東為超現實主義所下的定義是:“心靈在它的純粹狀態中的自動作用,我們打算通過這種自動作用表達——通過詞語,借助書面用語,或者用其他手段——思想的實際功能。超現實主義聽從思想的命令,不受任何理性施加的控制的影響,免除了任何審美的或者道德的操心。”參見[英]本·海默爾:《日常生活和文化理論導論》,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第85頁。
16、[英]羅杰·斯克魯頓:《文化的政治及其他》,谷婷婷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33—134頁。
17、[美]杰姆遜:《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精校本)》,唐小兵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212頁。
18、[美]詹明信:《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張旭東編,陳清僑、嚴鋒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327頁。
19、[德]本雅明:《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第258頁。
20、[德]本雅明:《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第259頁。加粗效果為筆者自加。
21、參見潘勁虹:《我看遍了僵尸bot,發現了互聯網時代的荒誕文學……》,《城市畫報》微信公眾號,2019年8月13日。
22、[德]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頁。
23、[以色列]尤瓦爾·赫拉利:《未來簡史》,林俊宏譯,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359頁。
24、[法]米歇爾·福柯:《詞與物——人文科學的考古學》,莫偉民譯,上海三聯書店2016年版,第392頁。
25、[美]漢娜·阿倫特:《過去與未來之間》,王寅麗、張立立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62頁。
26、[美]凱瑟琳·海勒:《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文學、信息科學和控制論中的虛擬身體》,劉宇清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4頁。
27、《微軟互聯網工程院副院長李笛:AI創造力迭代有三大原則》,《中國電子報》2017年5月26日。
28、[荷]約斯·德·穆爾:《賽博空間的奧德賽:走向虛擬本體論與人類學》,第237頁。
29、[荷]約斯·德·穆爾:《賽博空間的奧德賽:走向虛擬本體論與人類學》,第239頁。
30、馬克思:《機器體系和科學發展以及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變化》,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編譯局編譯,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85頁。
31、[意]莫利茲奧·拉扎拉托:《非物質勞動》,羅崗主編《帝國、都市與現代性》,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頁。亦可參見張歷君:《普遍智能與生命政治——重讀馬克思的〈機器論片斷〉》,《帝國、都市與現代性》,第153—190頁。
作者簡介:李靜,北京大學文學博士,中國藝術研究院助理研究員,中國現代文學館第九屆客座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當代文學史、當代文化研究,具體課題包括中國當代科幻文學史研究、科技與文化互動研究,以及近十年的互聯網語言經驗研究,曾在《文學評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文藝爭鳴》《讀書》等雜志發表文章30余篇。
本文原刊于《文藝爭鳴》
2020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