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國華:科學與情感——漢語科幻詩談屑
嘉應黃公度算是晚清特別推崇“奇技淫巧”的詩人。所謂“技進乎道”,他不僅“吟到中華以外天”,關心異域事物,而且寫下了這樣的詩:
星星世界遍諸天,不計三千與大千。
倘亦乘槎中有客,回頭望我地球圓。[1]
寫詩之時,黃公度正好乘船從日本橫濱前往美國。大概遠渡重洋的稊米微身之感刺激詩人的詩思逸出小小寰球,使詩人想出天外,詩里所寫的槎中客,轉譯成現代漢語的表達,說是“星際人”,肯定不算拉郎配。詩人說天上有很多星星,多到不是佛書所說的三千大千世界所能描述的,這可以理解為詩人所看到的“世界”不再是佛書所描述的世界,而是從新的知識構型中看到的全新的世界。
因此,他所設想的“倘亦乘槎中有客”,那槎中客自然不是神仙和佛陀,而是別一知識構型之下的幻想人物。這一幻想中的人物與“地球”相對應而成立,而神仙和佛陀都是相對于蒼天、大地而成立的。地球和蒼天、大地,分析起來有很多相關處,但它們屬于截然不同的知識構型,是沒有疑義的。那么,那個“回頭望我地球圓”的槎中客,就只能是一個和“我”這樣的地球人相對的、在宇宙星辰間穿越的“星際人”,一個擬想中的球外智慧生物。這意思大概不難理解,不易理解的是詩背后的科幻思維。也就是說,公度此詩是科幻詩,是在新的知識構型下展開的對于人、地球和宇宙的幻想。詩中的“星際人”雖然還被包裹在道教神話典故的重衣中,但其回望的標的不再是鰲戴山抃的方形大地,而是懸浮在空中的圓形地球,表現出明顯的異質性。這種異質性不僅是與道教神話相比而言的異質性,而且更重要的是,是與地球文化相比而言的異質性。
已有的語言,像是一件借來的衣裳,呈現著表面的相似性,但因為詩歌背后的思維已經不是屈原式的“天問”,相似的表面之下,異質彰彰。不過,這并不是說黃公度是從異質性的原則出發而想象“星際人”的存在。恰恰相反,詩人的幻想遵從的是相似性原則,他設想宇宙星辰中有與地球人類似的智慧生物存在,但其能力遠遠超過地球人,能夠在星際旅行。黃公度還不知道后世送給“星際人”的是宇宙飛船、UFO等星際交通工具,只是幻想“星際人”在星際乘槎旅行。在這里,詩人的科幻思維撐開了古典漢語的表達空間,使得原來致密的神話結構出現巨大的豁口,以騰挪出容納“地球圓”在語詞編織中的位置。
但是,黃公度并不是一個自覺的科幻詩人,或者說,雖然偶有想出球外的壯舉,詩人的寫作仍然更加緊貼大地、緊貼古典漢語的傳統。在《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一詩中,詩人雖然清楚地知道“舉頭只見故鄉月,月不同時地各別”,但感慨的乃是“九州腳底大球背,天胡置我于此中”。[2]公度之前的詩人吟月,雖然在感情的作用下會覺得“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將故鄉的月亮想象成另一月亮,但并不是在實體的意義上認為那是另一輪月亮。他們的典型態度是萬川印月的,認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認為“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月亮是同一輪月亮,時空是同一的時空,連看月亮的心情也是一樣的心情,彼此以月亮為橋,形成一種共通的感覺結構。
而“舉頭只見故鄉月,月不同時地各別”的表達,將古典的時空體從一致性想象中分析出來,時間是不同的,空間也是不同的,那么,月亮難道不應該是不同的月亮嗎?但詩人卻認為月亮仍然那枚“故鄉月”,是同樣的月亮。這種看法背后延續的與其說是萬川印月、古今一月式的古典情感,不如說關聯的是新的物理知識,即月亮是地球唯一的衛星。因為月亮是地球唯一的衛星,所以詩人雖然處在“月不同時地各別”的時空之感中,卻仍舊認為舉頭所見的月亮乃是故鄉的那一枚月亮。但在新的知識構型中意識到無法“一夜鄉心五處同”的詩人,雖然在相歧的時空中重新確認了月亮的同一性,但對地球的理解卻并沒有多么明顯地越出古典傳統的軌范。
當詩人說“九州腳底大球背”時,一方面固然呈現了地球作為球形物的存在,另一方面則以“腳底”一詞表明,地球雖然是球形的,但它仍然在人的“腳底”,詩人仍然是腳踏實地的。既然詩人仍然是腳踏實地的,那就意味著懸浮在空中的、無法區分上下左右的球體被當成了可以進行上下左右區分的大地來理解,地球仍然以大地的方式存在。而因為地球仍然以大地的方式存在于詩人的感覺結構之中,于是太平洋舟中望月的詩人發出的天問就是“天胡置我于此中”,他在大地上,像古典的詩人一樣,向天發出了疑問。在這種天、地既相互勾連又相互對立的感覺結構中,黃公度離那個擔心天會塌下來的杞人,那上古時代的悲觀的人類,其實是不太遠的。
而在這樣的邏輯中,即使是一些有機會比黃公度擁有更為完備的科學知識和環球旅行經驗的當代詩人,似乎也沒有走得太遠。比如下面這首詩:
七夕夜的星際穿越
(寫給小曼)
一架紡車把天琴座光芒纏繞進不眠夜
遙遙相對的小陽臺上,幻聽者憑欄
并沒有看真切,藍色太空圍攏的
伊大嘉
——她是否又在讓快進的梭子
趁著黑快退?正當暑夏繁星
全都倒映在樓下游泳池,被一小朵
烏云般黝暗的胖墩兒救生員
用一根細竹竿一顆顆戳滅
織機上她拆散
不打算完工的愛的新樂章
化為烏有的也是舊樂章;用白晝之弓
她每天奏彈的,也是無限往昔的音塵之
舊絮
喜鵲們倒沒有因此而厭倦,星際人
更殷勤,想要把未來所有的此時此刻與
此情此景,充注銀河間往還擺渡不已的
航天船。幻聽者隔空再去想象
救生員拋出
游泳池圓月的一小半之際,尤利西斯
恰在歸途,會遭遇怎樣險阻的歌喉
天琴座光芒將一架紡車纏繞于不眠夜
*
而他用的是高倍望遠鏡。掠過游泳池
他的觀察,輕易刺穿了大海的灰皮膚
確切地,攫奪大海深藍的血
并且,他可以
隨便叼取更為理想的無限天青色
經由任意伸縮的鏡筒,它們會溢滿
完善于翱翔的心室和心房——主動脈弓
向右的泵,開始急切奮力地搏動
(……比附的情人節催促閃電
被戳滅的倒影,又要聚集起新的烏云
盡管已經不再是雀鳥,宇宙空間站
還是喧嚷著人神間架橋,依舊允許
胖墩兒救生員膨脹黝暗。而閃電
閃電——閃電催促比附的情人節)
他是否真的來自天鷹座?來自比基尼姑娘
一邊在沙灘上吃著燒烤,一邊感動的
那顆星星?——正當一對翅膀打開,正當
服務于寂寞的男公關凌空,扯住一根
時光線頭,像收回風箏般把不眠夜卷攏于
一張吧臺上清亮的金酒
奏彈者端起了
水晶杯盞,打算接著……話說下一回
2014[3]
這樣一首寫于2014年的詩,從詩題《七夕夜的星際穿越》開始,就展現出在古典與現代、神話與科幻之間寫作的質地。“七夕”是一個古典的符碼不用多說,而“星際穿越”則是2014年風靡全球、譽滿天下的一部科幻電影的名字,恐怕難以否認,詩人的寫作肯定受到了科幻電影的刺激。事實上也正是如此,《七夕夜的星際穿越》重寫的是與郭沫若《天上的街市》一樣的牛郎織女的愛情神話,但與郭沫若相比,就表現出了科幻氣質。在郭沫若的想象中,在天街上游蕩的牛郎織女,除了“街燈亮了”的表達增加了一點現代工業生活的人間氣息,“提著燈籠在走”的男女既是古典的,也是神話的,其中有幻想的味道,但簡直毫無科學的氣質。郭沫若的宇宙大概比黃公度還要古典,雖然一個是用白話寫作,一個是用文言寫作。

郭沫若
《七夕夜的星際穿越》與郭沫若拉開了距離,詩里出現了“星際人”,而且“星際人”“想要把未來所有的此時此刻與/此情此景,充注銀河間往還擺渡不已的/航天船”,詩人的想象借助“航天船”,試圖擺脫大地的牽引。如同電影《星際穿越》中的人物需要借助航天工具才能進行“星際穿越”一樣,詩人也需要借助“航天船”這樣的現代科技事物才能擺脫古典傳統對詩歌內在秩序的牽引。但是,應該說非常遺憾的是,電影配備給航天工具的一整套現代科學知識,如蟲洞、黑洞等,而詩人配備給“星際人”的除了“航天船”和“宇宙空間站”,不過是一系列大地上的事物,其中最具有象征性的是“望遠鏡”。對于伽利略來說,望遠鏡只不過是大地上的神的子民用來尋找神之蹤跡的工具,它完全屬于地上的人們,而且貼得過于緊致。這在《七夕夜的星際穿越》中,幾乎沒有任何變化,類似“而他用的是高倍望遠鏡。掠過游泳池/他的觀察,輕易刺穿了大海的灰皮膚/確切地,攫奪大海深藍的血”的表達,不僅沒有超越伽利略的意圖,而且將望遠鏡的方向從宇宙轉向了大地,需要通過科學幻想才能理解的宇宙,被比喻成與大地上的人有切身之近的大海。在這個意義上來看,《七夕夜的星際穿越》雖然受到電影《星際穿越》的刺激,表現出相比郭沫若《天上的街市》而言的科幻氣質,但與其說它是一首科幻詩,不如說它是一首反科幻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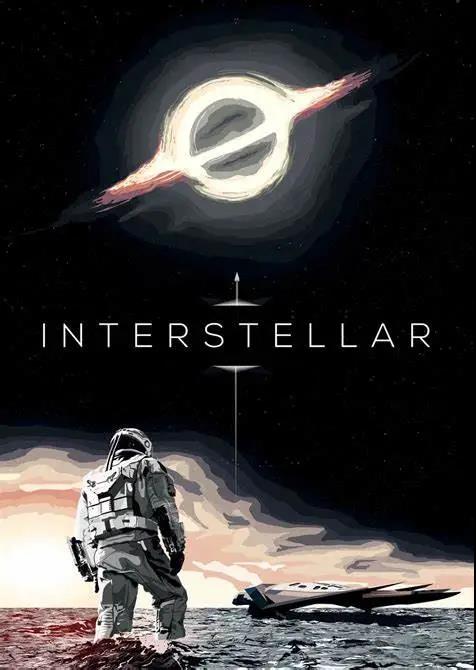
《星際穿越》
也許正因為如此,詩中才會出現“盡管已經不再是雀鳥,宇宙空間站/還是喧嚷著人神間架橋”這樣的表達。宇宙空間站就像是給人間的牛郎和天上的織女提供相會場所的鵲橋,這種想象力也是驚人的,但以宇宙空間站置換鵲橋,詩中另有各類舍不得棄置的“喜鵲”“尤利西斯”的語詞,則表明詩人的想象秩序并沒有因為現代科學而發生變革。他只是換了幾幅插圖,故事仍然是古典的故事。甚至與古典的純凈相比,《七夕夜的星際穿越》還多了現代人的粗俗和愛欲。比如詩第一段后面的幾句“正當暑夏繁星/全都倒映在樓下游泳池,被一小朵/烏云般黝暗的胖墩兒救生員/用一根細竹竿一顆顆戳滅”,將浩瀚星空裝置在“樓下游泳池”,救生員“用一根細竹竿”就能將星星“一顆顆戳滅”,精彩是夠精彩了,粗俗也是夠粗俗的了。而當救生員再次出現在詩尾,與吃燒烤的比基尼姑娘、服務于寂寞的男公關和清亮的金酒綴系在一起,就在欲望化的現代人生活場景中凸顯了現代人的粗俗和愛欲。這個粗俗和愛欲的世界要顯現,當然要將星星““一顆顆戳滅”,要從浩瀚星空落到地面,要從星際穿越落到情人間的交換溫柔。與那心系大地而憂天傾的杞人相比,這個當代詩人似乎并沒有從現代科學獲得什么有意思的想象力,他沒有借助科學進行幻想,而是站在原地打轉,幻想科學。他甚至都沒有心系大地,只是心系一汪淺淺的游泳池罷了。
而且,如果讀到另一位當代漢語詩人的極有關聯的詩,即《反科幻詩》,會發現當代詩人不僅站在原地打轉,而且反對借助科學進行幻想:
我們就如此安于落后的人類軀殼
寄生在落后的二十一世紀
身披纖維但始終渴望皮肉摩挲取暖
不嫉妒同性也保持與異性的溫柔和平
做愛之后依舊像野豬般感傷
做夢時依舊抱緊床沿如紙莎草靈船
失眠便以更落后的巫術比如白酒和煙葉
來挺過獨自面對沉甸甸的星空
我們大多數仍然不懂和虛擬的靈魂較量
混淆光年與余生為一樣的短暫
對大地上遍布的蟻穴、天空中
擁擠的祖先視而不見
我們哭泣時流淚的毫升
與巴比倫陷落時她們哭的差不多
沒有忘記在淚水中放鹽來防止它凝結
沒有忘記在翻動書頁的時候小心翼翼
就跟你們在未來檢索我們的全息影像一樣
你們沒有忘記加密我們的詩來防止悲觀
和那個世紀末我們哭的差不多
你們撤離地球時你們放棄服用控制絕望的藥
對星云間遍布的陷阱、黑洞邊上
掙扎的探險船視而不見
混淆三島由紀夫與魯迅為一樣孤獨的運動員
你們大多數仍然不懂和神調情
獨自面對被傳送軌道切割的星空時
甚至沒有多少巫術比如圣經和搖滾來抵擋夢魘
做夢時被電子羊一點點吃掉腦中光纖
做愛之后忘記關掉二進制的呻吟
與一個外星染色體交換快感編碼之后突然想
問一問它的父母們是否依然存在于某個坐標點
它們摩挲是否足以溫暖你們穿越的光年
偶爾想想落后的二十一世紀
那些小人兒用一生與速朽的肉體達成和解
為純粹的虛空增加21克的重量。
2015.10.31[4]
這是一首比《七夕夜的星際穿越》更深地卷入了科學帶來的想象的詩,它想象了人類的后代借助某種交通工具撤離地球的一些情況。這種人類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后人類特征,他們“做夢時被電子羊一點點吃掉腦中光纖/做愛之后忘記關掉二進制的呻吟”,所謂“腦中光纖”和“二進制的呻吟”都意味著人類的生物性身體已經被人工智能改造,而“與一個外形染色體交換快感編碼”這樣的表達也說明人類的后代與外星智能體交流的方式詩是類似于人工智能的方式。那么,這種可以稱為人工智能型的后人類,他們是高于作為祖先的“我們”的嗎?詩人明確認為“你們大多數仍然不懂和神調情/獨自面對被傳送軌道切割的星空時/甚至沒有多少巫術比如圣經和搖滾來抵擋夢魘”,這也就是說,人工智能型的后人類,雖然具有更加發達的科學和技術,但是無力“抵擋夢魘”,反而不如“我們”。而“我們”,因為擁有“圣經和搖滾”,擁有“更落后的巫術比如白酒和煙葉”,卻是足以“挺過獨自面對沉甸甸的星空”的,足以在悲傷和絕望中“為純粹的虛空增加21克的重量”。在這里,人類和后人類的對照,其實延續了中國現代史科玄論戰中玄學派的思路。玄學論者認為科學不足以解釋人類的靈魂問題,甚至認為科學不僅不能解釋人類的靈魂問題,而且還會造成人類的精神空虛。
人工智能型的后人類與“我們”一樣盲目,“我們”是“大多數仍然不懂和虛擬的靈魂較量/混淆光年和余生為一樣的短暫/對大地上遍布的蟻穴、天空中/擁擠的祖先視而不見”,而他們是“放棄服用控制絕望的藥/對星云間遍布的陷阱、黑洞邊上/掙扎的探險船視而不見”,二者生存的處境極其相似,盲目的情狀也極其相似。看起來,科學和技術什么也沒有改變,但人工智能型的后人類卻沒有了人類的巫術,喪失了靈魂。因此,詩人要反科幻。詩人進入科學的邏輯進行了一番幻想之后,卻發現科學之前的那些被科學反對的事物,如宗教和巫術,才是能使人類得救的,這的確是一首反科幻詩。因此,假如不去考查詩人的科學理解的成色,而是僅僅去理解和解釋詩人為什么站在原地打轉、不借助科學進行幻想的話,那么,就只能說,對于一些當代詩人來說,他們樂于站在科學的對立面,以對立的方式馳騁科學開辟的場域。這些當代詩人筆下的科幻詩,不管安插進了多少科學的詞匯,其實都不過是一些眷眷于大地的寫作,甚至還不如黃公度筆下的槎中客,能夠將地球文明相對化,在相對化中尋找到某種重新理解大地的維度。在這個意義上,當寫下《七夕夜的星際穿越》的詩人在另一首取名《宇航詩》的詩里寫“在萬有引力彎曲的想象里/穿過宇宙學幽渺的針眼”時,一定要更加關注詩的結尾是“透過盥洗室舷窗的黎明遞送宇航詩”,[5]它幻想的邏輯起點仍然不在科學那邊,而在大地上,而且貼得過于緊致。
有必要進一步強調的是,《反科幻詩》比《七夕夜的星際穿越》更加赤裸裸地表現了對粗俗和愛欲的世界的迷戀。它雖然把圣經和21克的重量作為宗教、信仰、靈魂的符碼編織進了詩行,但更加信任的是“皮肉摩挲取暖”,并因此“安于落后的人類軀殼/寄生在落后的二十一世紀”。《反科幻詩》就像是一首愛欲的說教詩,而且顯得很粗俗,過于明顯地強調了人類軀殼和皮肉摩挲的重要。如果說黃公度的槎中客幻想,像是一只飄離大地的熱氣球在萬有引力的作用下,始終心系大地,是“偶開天眼看紅塵”,《反科幻詩》人工智能型后人類的想象,就像是面對一場宇宙災難的驚懼反應,龜縮在大地浮塵之中,是心即宇宙的愛欲版。科學技術大概還沒有帶來什么真正的宇宙災難,但關于宇宙災難的驚懼反應已經在詩人的幻想中出現了。從理解科學與詩的關系的角度來說,詩人的腳步未免走得太急了一些。
但這也許就是漢語科幻的特點。比如這些年名滿江湖的劉慈欣《三體》,其主人公羅輯就是風流放蕩之輩。劉慈欣毫無疑問是漢語科幻的主動力之一,但他在科幻世界中展開的基本邏輯與《反科幻詩》的作者卻有異曲同工之處,道德訴求都處于一種原始、自然的狀態。也許,科幻作者都免不了會認為,科學作為具有反自然性質的知識構型,當其發展離原始、自然狀態愈遙遠時,就愈需要喚醒人類原始、自然的記憶,以之為救贖的路徑。

《三體》
的確,經歷過二戰的現代人與之前的人類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原子彈在日本升起的蘑菇云以及日后世界的核均勢恐怖讓人很難不想到科學和技術可能帶來的災難,那不是個體倫理問題,而是人類作為一個龐大的種群如何重新與自然建立關系的問題。人類存在的本質是什么呢?是可以以科學進行解釋的部分,還是科學無法解釋的部分?初次面對現代科學帶來的新世界的黃公度,在百年之前,他大概是相信科學可以解釋的部分即是人類的本質。而對當代漢語詩人來說,當他們對科學和技術表達意見時,就往往是批判性的,甚至是否定性的了。批判和否定也許真的是必要的,如果能給予科學和技術的探索一定的坐標和倫理的參照,那么,就算詩人的腳步未免走得太急了一些,倒也不是無益的。不過,詩人的腳步所奏響的大地上的自信,那種對于愛欲的迷思,也不是不應該批判的。人類大概還是過于相信愛欲的力量,連所謂硬科幻的典范之作《星際穿越》,也未能免俗。在電影中,受困于另一維度的父親所以能與地球上的女兒溝通,除了借助萬有引力的知識傳遞信息,就是無法知識化和信息化的愛。無法知識化、信息化的愛,的確具有穿透維度的能力嗎?這應該不過是一種愛欲的迷思吧?在這個意義上,回憶李白《夜宿山寺》一詩是必要的。李白寫:“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
對于未知的恐懼,使詩人詩中的想象有了天然的邊界和秩序,詩人因此在謙卑中感覺到了超乎一己之知識和理解的原始、自然的狀態,這是一種默契,遠比大聲說出什么要動人。從比喻的意義上來說,這也就是科幻世界流傳的黑暗森林的古典漢詩版。宇宙是一片茫無邊際的黑暗森林,里面活躍著不同的生物種群,當彼此處于大寂靜的狀態時,相安無事。一旦有聲音出現,打破了寂靜,聽到聲音的種群不一定會感到欣喜,也許會感到恐懼。一旦感到恐懼,就容易出現自衛式的暴力,朝著聲音開一槍;而那一槍,也許就是毀滅的一槍。因此,就算借助天文望遠鏡看見億萬光年之遠,有光帆駛來,你也不一定就要歡欣鼓舞,發出聲音。此之謂“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適度的敬畏,大概是可以破解愛欲的迷思的。
至于緊貼大地的問題,是無可如何的。因為人類終歸是地上的種群,只要真正的星際旅行尚未成為現實,就只能以地球為唯一的家園,緊緊貼在大地上。譬如最近風靡漢語世界的《流浪地球》,當地球災難將臨,人類的辦法便是帶著地球一起去流浪。如果拋開以科學為基礎的基本設計不談,《流浪地球》實在不過是“雞犬升天”故事的科幻版。魯迅說:“我們有一個傳說。大約二千年之前,有一個劉先生,積了許多苦功,修成神仙,可以和他的夫人一同飛上天去了,然而他的太太不愿意。為什么呢?她舍不得住著的老房子,養著的雞和狗。劉先生只好去懇求上帝,設法連老房子,雞,狗,和他們倆全都弄到天上去,這才做成了神仙。也就是大大的變化了,其實卻等于并沒有變化。”[6]經魯迅一解釋,地球上的人類,再怎么想出天外,也仍然是地球上的人類,漂浮在云天的時候,他們是要把大地弄到云天上去的。

《流浪地球》
如果說《流浪地球》作為一部電影,當它影像呈現想象時,不得不更多地借助人類既有的經驗,只能做有限的變形處理,那么文字是否能做到更多呢?至少從漢語科幻詩來看,文字似乎也沒有做到更多的。例如對現代科學和技術興致盎然的詩人吳望堯,他在1978年寫了一組科幻詩,詩題《科幻組曲》,下轄《光子旅行》《時光隧道》《太空城市》等題,每一題背后都有具體的科學理論支撐。《光子旅行》的理論支撐是“最接近地球銀河系的仙女座,離我們二百萬光年,但根據‘相對論’,我們仍可以接近光速漫游宇宙,可是當你歸來,只長了五十五歲,地球卻過了三百萬年”,但詩人最感興趣的卻是“許你便是 神/從自己的家里出去/而變成飛碟的神/回到地球”。[7]詩人不知道接近光速的宇宙漫游能發現什么球外文明、河外文明,只能幻想光速漫游也不過是拋出去的飛去來器,在時空的錯愕中“變成飛碟的神,回到地球”。如果科學影響下的文明真的是呈直線發展的,三百萬年的時間大概不是不能發展出識別三百萬年前出發、而現在歸來的“神”不過是史前的人,就像劉慈欣《微紀元》所寫的那樣,微紀元的人類對于此前的宏紀元的人類是了如指掌的,怎么可能呼為“神”呢?這就意味著,詩人雖然借助科學馳騁幻想,但神話的思維更深地制約著他詩思的展開。他的《科幻組曲》不管離大地多么遙遠,借助了多么高深的現代科學理論,如果不能從神話的范型中掙脫,就仍然無法從大地生產的有限經驗中建立不緊貼大地的幻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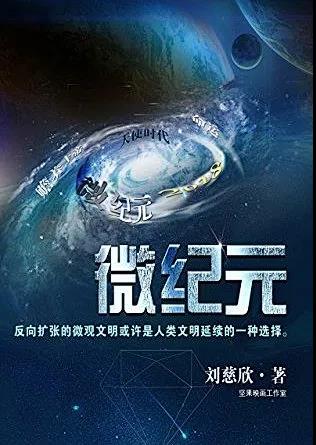
《微紀元》
而且,吳望堯是樂觀的詩人,他遵從相似性的原則,認為“時光隧道”的那一頭有“他們”,“他們”將“先鋒十號”看作“只是沖出太陽系的”“一只孩子們玩的紙的飛標”,但“我們的子孫仍會努力/來訪問你們,從時光的隧道”。[8]看起來,詩人認為“他們”是可理解的,也是可接觸和親近的,宇宙并不是一片茫無邊際的黑暗森林。詩人甚至幻想,“在龐大的太空城市 熱鬧的空間站/正有無數的智性生物 舉著彩色的旗幟/歡迎來自太陽系的那個叫地球的居民”,[9]這簡直是把星際移動當成了民間聯歡,確實是不能更樂觀了。從歷史的角度看,吳望堯的樂觀似乎帶有某種1970年代的具體特點。這從《科幻時代》1979年的一首《并非詩人的幻想》可見一斑:
小序
我曾經有過許多幻想,
把它當作幾何的圖形,
我相信未來的科學,
會對它一一作出求證。
一
每當打開那香水的瓶蓋,
滿屋就聞到一股芬芳,
瞧那么小小的一個瓶子,
能夠把那么多香味儲藏。
為什么不能有那么個瓶子,
白天從太陽那里收集光亮,
等到了晚間打開瓶蓋,
室內就亮過那燈火輝煌!
二
春天的柳絮在空間飄游,
那么自在,那么輕松,
它利用空氣的浮力,
來托起自己的行蹤。
如果我們穿上特殊的衣裳,
也能像柳絮在空間浮動,
那么,只消拿一把扇子當槳,
我們將逍遙云端來去如風!
三
電流既然能傳導聲音,
為什么不可以傳導氣溫?
必定有一把導溫的鑰匙,
能夠打開這神秘之門。
要是南北交織的電線,
像傳聲一樣把冷熱載運,
南方的酷暑會自膏退隱,
北方的嚴冬將溫暖如春。
四
矛盾的雙方構成事物,
這是辯證法的基本原理;
我們既然知道地球有引力,
必能找到抵消引力的東西。
我設想我們乘坐的車輛,
在沒有引力的情況下騰空而起,
讓地球的自轉代替行車,
萬里外的目標奔來眼底![10]
除了樂觀的情緒,這是和吳望堯的詩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種詩。盡管如此,還是必須首先看到,在1970年代的漢語文化中,科學被認為是足以解釋和解決一切的,那是對科學感到充分樂觀的時代。《并非詩人的幻想》一詩,雖然通篇都是詩人的幻想,但詩人卻敢于堅稱“并非詩人的幻想”,就是因為“我相信未來的科學,/會對它一一作出求證”。再看詩人“幻想”展開的邏輯,有的是從香水瓶儲存香味這樣的人工現象出發,有的是從春天的柳絮在空中飄蕩這樣的自然現象出發,有的是從電流傳遞聲音這樣的物理現象出發,還有的是從辯證法的基本原理出發,應該說,邏輯的起點都是不夠科學的,至少是不符合當時既有的科學認識的。因此,詩人說“我相信未來的科學,/會對它一一作出求證”。從科學最早萌生的邏輯和科幻文藝作品最早出現的一些情況來看,《并非詩人的幻想》可謂典型的科幻詩。但是,“未來的科學”要“對它一一作出求證”,卻是困難的。雖然太陽能現在已經得到廣泛應用,但以太陽光為光的室內照明并未實現。至于“特殊的衣裳”、運載冷熱的電線和沒有引力的車輛,雖然不能說沒有類似的發明正在應用,但離詩人所幻想的科技創造的日常生活情況,還遙不可及。這也就是說,“環球同此涼熱”和“坐地日行八萬里”都還只是詩人的浪漫想象,都還只是一種隱喻,并沒有因為詩人對“未來的科學”樂觀自信,而兌換為現實。某種特定時代的樂觀情緒,也許足以在科學的指引和影響下,打開漢語詩的一些空間,建構一些獨特的詩歌類型和情緒,但也仍然不能擺脫大地浮塵的遮蔽。即使是幻想擺脫了萬有引力,詩人的世界也還是緊緊圍繞地球而轉,不過是“讓地球的自轉代替行車”而已。
科學作為一種獨特的知識構型和思維范型,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改造漢語和漢語詩學,也許是一個很大、很有價值的論題。從上述一些漢語科幻詩來看,即使是在相對集中和極端的文學形式實踐中,漢語和漢語詩學發生的變化也是有限的。這也許是因為漢語具有強大的韌性,始終模塑著漢語詩人的思維和表達,也許是因為科學與神話、巫術、宗教的關系,也不是那么容易切割的。不管是從怎樣的路徑出現的,科學似乎總是在激發或喚醒漢語詩人對于神話、巫術和宗教的記憶,使他們的幻想總是在科學與神話、巫術、宗教的羈絆中展開。在這樣的層面,也許很難說是漢語詩人的科學知識和素養不足,從而很難嚴格按照科學的邏輯展開詩思。因此,當黃公度的月亮仍然是那枚“故鄉月”,當代漢語詩人的世界紛紛圍繞地球而轉,甚至于轉而乞靈于神話、巫術和宗教之時,關注科幻文藝的人們,也許不妨想一想,科學原不過是人類文明的一個分支而已。即使是信仰科學者,也難以切割出一個純粹而完整的、叫做“科學”的對象來吧。
本文原刊于《廣州文藝》2019年11期
注釋:
[1] 黃遵憲:《黃遵憲集》(上卷),第150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2] 黃遵憲:《黃遵憲集》(上卷),第159-160頁。
[3] 陳東東:《宇航詩(外一首)》,《山花》,2015年第23期。
[4] 廖偉棠:《春盞》,第244-245頁,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6年。
[5] 陳東東:《宇航詩(外一首)》,《山花》,2015年第23期。
[6] 魯迅:《且介亭雜文·中國文壇上的鬼魅》,《魯迅全集》第6卷,第156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7] 吳望堯:《吳望堯自選集》,第118頁,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
[8] 吳望堯:《吳望堯自選集》,第119-120頁。
[9] 吳望堯:《吳望堯自選集》,第121頁。
[10] 轉引自郭曰方、方竟成選編:《中國科學文藝大系?科學詩卷》,第126-127頁,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