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簡續存》是《張中行全集》最大亮點
來源:文匯報 | 劉德水 2019年10月14日07: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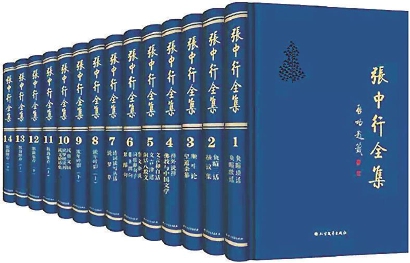
《張中行全集》,北方文藝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
《張中行全集》已于今年8月出版面世。從去年初動議,到如今洋洋14卷編成,僅一年多時間,由此可見出版社效率之高。展卷之際,不禁憶起先生,想到與本書的種種因緣,感慨不已。
《全集》兩種處理方式
去年4月,北方文藝出版社宋玉成社長來京,說已征得張中行先生家人授權,準備啟動《張中行全集》的編輯工作,請我協助云云。我自然應允——當年多得先生教誨,迄無萬一之報,能為《全集》出力,于情于理,我都責無旁貸。
張先生的文章,1996年曾匯編為《張中行作品集》六卷,由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1997年5月,先生的回憶錄《流年碎影》付梓;1999年3月,又把零散篇什編為《散簡集存》(編者徐秀珊,經先生過目獲首肯)。這八卷,是先生在世時編成的較全的集子。但也有缺憾,此前先生的文字結集,交叉的很多。一篇文章,此書收了,另一本書也收。
編文集須避重。避重,可采用的方式很多,例如保留原來結集的全本,將未入集的散篇續作編為“集外文”。《張中行作品集》就采用這種方式。但有些集外文用了既有書名,如《月旦集》《橫議集》。文章兩本書重收的,其中一本以“存目”方式呈現。如《黃晦聞》,在《負暄瑣話》中“存目”,文章則入《月旦集》。
另一個缺憾,是當時很多友人以為,《負暄瑣話》是先生最早出版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而《月旦集》是先生1995年把“負暄”系列及后來專寫人物的文章收到一起編成的。如要“存目”,該保留《負暄瑣話》全本,而在《月旦集》存目。這種處理方式似乎更好。
此次編《全集》,遇到同樣問題。在處理方式上,借鑒了作品集的經驗,已結集成書的,如《負暄瑣話》《負暄續話》《負暄三話》《順生論》《禪外說禪》《佛教與中國文學》《文言和白話》《作文雜談》《文言津逮》《詩詞讀寫叢話》《流年碎影》《散簡集存》《說夢草》(詩集)以及當年我為先生代筆的《閑話八股文》,都收入其中。這是易于處理的。
棘手的是后來的續作,有些入其他文集出版,有些散見于報刊。《全集》采用兩種方式處理,一是沿用先生生前的書名,如《談文論語集》《望道雜纂》《橫議集》《民貴文輯》等,對于重復的篇目,吸收上面所說意見,保留了《負暄瑣話》等代表作的全貌,而在其他書冊里“存目”;二是散見于報刊、未入集的,另外編輯《散簡續存》,分上、下兩冊(第十三卷、第十四卷)。
如此處理,出版社還有一個想法,每卷書的厚度大致差不多。這樣,最后編成14卷,收入了目前能見到的張中行先生一生所寫的絕大部分文字。
《散簡續存》編輯著力最多
《張中行全集》最為突出的亮點,也是編者著力最大的,是編輯《散簡續存》。
《續存》共兩冊,上冊收錄張中行先生1946年—1948年在天津《新生晚報》刊登的全部專欄文字。這些都是他在北京四中教書之余,應報紙主編、好友張道梁先生之邀而寫。其中“周末閑談”專欄刊文24篇,篇幅較長;“一夕話”專欄刊文326篇,篇幅較短。
當年先生健在時,我曾詢問這批文字,先生說本來都有存報,捆在一起,后來被家人當舊貨處理了。我那時想去圖書館查閱,先生未允。我以為有什么違礙或顧慮,比如與現在思想不一致,先生說沒有,只是不愿讓我“費那個力氣”。
這次為編《全集》,我在國家圖書館查到《新生晚報》的膠片,出版社予以全部復制,花費大力進行整理。其間也遇到一些疑難,就是那些文章所處欄目相同,文風一致,但署名往往不同,如“行健”“行”“健”“藍”“聞”等,到底是否先生手筆?編輯問我,我一一做了答復:張先生當年用筆名“張行健”,見張道梁回憶錄《往事九十年》中《悼張中行》一文。這個筆名,1964年先生所寫小冊子《中學語文課本文言課文難字的補充注音和注釋》(文字改革出版社)還曾用過。
此外,先生外祖家姓藍,當年曾以母姓,取筆名“藍聞”,還求金禹民先生刻制一方“藍聞之印”。這是我買到《金禹民篆刻作品選》拿給先生看時,老人指著里面的印章親口告訴我的。
從這批文字,可窺見張中行先生早年思想、文風的樣貌。果如先生所言,并沒有什么“違礙”,思想與后來并無不同。相反,從這些長則數千言短則百余字的雜文隨感里,隨處可感覺到,從那時起,先生就有著強烈的反專制思想,與晚年毫無二致。
當年先生逝世,筆者與張厚感、李世中二位先生一起撰寫訃文,就有這樣的話:“他提倡民主與科學,反對專制,重視知識學習,強調教育對人的啟迪作用。他繼承儒家‘民貴’思想,又富現代理性精神,時存悲天憫人之懷,多有洞明世事之智。”
而先生的這批文字,當時頗受“有關方面”的伺察和非議。1946年11月4日所購南星《松堂集》扉頁上,先生有記云:“日暮返家,接天津信,云老爺的狗將砸報館,因報上有些雜文不規矩。莫非狗亦知文?總之,網是更密了。”(見先生晚年所作《扉頁記語》)文中“有些雜文”,當指先生的文字。
盛年已顯大家氣象
張中行先生文筆簡潔而老辣犀利,嬉笑怒罵則自然成文。
人說先生晚年才“暴得大名”,其實“暴”字用得不確。先生盛年之筆,早已顯出大家氣象。其晚年之得大名,其“實”來有所自,絕非偶然。僅舉一例,可見一斑。
請看1947年11月6日,在《新生晚報》署名“行”的“一夕話”(專欄):
《情理》人日常處世要講情理,情理者,出乎真情,即合乎道理之謂也。這或者就是中國醫生所贊揚不疊的誠字。誠則靈,不誠則不靈。
美國副國務卿克萊頓辭職,理由是因為妻子有病,這假使是在中國,一定就要說成媽媽有病了,因為必須這樣,才能合于傳統觀念的孝。而其實,孝與不孝,自然只有天知道。
干政治喊愛民亦是如此,愛到人民都餓干了,還在喊愛民,誰信?此之謂不誠則不靈。
在這個時代,情理顯然比口號更可貴,更重要。(行)
話是家常話,理也是家常理,可是一經聯系當時現實,就能體會到平實語言背后豐富而深刻的含義,“其辭微而其指極大”,其中實在有凌峻的風骨。
語云“嘗一臠而知一鑊之味”,這一篇,口味還算輕的。比這重的,還大有文在。因此,被“老爺的狗”視為“不規矩”,也是良有以也。
倘說這版《全集》的貢獻,我想,僅這一本,對熱愛張中行先生文字的讀者來說,就功不可沒。張先生倘九泉下有知,也會首肯吧。
還有《續存》的下冊,分為兩部分。
前一半是1949年前的,包括1945年先生主編《上海論壇》,親自操刀,在僅出的三期上所寫的三篇時政雜論;《大地周報》第四期刊登的一篇雜論;《文藝時代》1946年第一卷第四期刊登的一篇雜文。比較集中的是1947年,張中行先生以一人之力,為續可法師主編佛學刊物《世間解》,共11期,第一期的“發刊詞”,每期的“編輯室雜記”,均為先生親筆所寫。此外,他還親自下水,寫了《關于度苦》,刊在第二期。
這些資料的獲得,還要感謝先生的外曾孫劉立維先生。一年前,他得知我正在搜集先生的資料,遂寄來《世間解》全部11期復印本。以此之故,這部分資料,未費吹灰之力就得到了。
后面一部分,是先生未入集的散篇文字。有早期的,如1946年12月出版的雜志《文藝時代》刊登的書信體散文《寄MP》,這篇收在姜德明先生編《如夢令:名人筆下的舊京》一書。當年,我曾攜書去說夢樓(先生書房),問張先生“MP”是誰。先生告訴我,是王夢白,名伯英,他的同窗老友。還告訴我,文中的“N”,是詩人南星。
當然,這部分篇什,大多是先生晚年作品,有些在發表后從未入集,如為北京五中語文組論文《采薪集》寫的序,只在該書刊出。又如《悼鄧云鄉》,是1999年4月,先生在河南鄭州司家莊小住,我在電話里告之鄧云鄉先生逝世的消息,他聞聽后寫了這篇滿懷深情的悼文,發表在同年5月1日《文匯讀書周報》。年底,先生患病住院,這些零散篇什就散佚在報刊了。
還有一些,如先生為親家(四女婿王鏞之父)王云樵先生所編《謎語新編》所作序文,收在自印本中,由家屬找出,提供給編輯。
若非多方齊心合力,是找不到這么多篇章的。
遺珠之憾終究難免
《張中行全集》第六卷,收錄的全是語文方面的著作。
《作文雜談》先后有人民教育出版社、中華書局單行本,此外還有《詞組和句子》《非主謂句》《緊縮句》三本專著。這后幾本是上世紀50年代末,為配合中學語法教學而寫,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詞組和句子》,署名張中行,毫無疑問是先生著作。《緊縮句》筆名“向若”。《簡略句、無主句、獨詞句》署名郭中平,1984年再版改名《非主謂句》,署名張中行。
這里就有疑問:“向若”是誰?“郭中平”何以變為“張中行”?記得《流年碎影》有相關記載,一查,固然在《稻粱謀》一節里,先生明言,這三本是為多掙稿費以養家糊口而寫。“向若”是筆名,“郭中平”是人教社語文室郭翼舟、張中行、呂冀平三人各取一字作為筆名(文字則全由先生執筆)。這樣,三本小書,就無可爭議地進入全集。
當然,鉤沉輯佚,即使網密也不免于疏漏,遺珠之憾,終究難免。后來知悉,還有散佚文字未能收全。如據周實先生回憶,《書屋》1997年第六期曾刊有張中行先生《多信自己,少信別人》一文,本次未收。此外,《現代佛學》《語文教學》雜志也應刊載先生不少文章,本次均未及梳理。
當然,最大的遺憾,是缺少“書信集”——那是一項大工程,需要耗費更多時日和精力。有人說這套《全集》不全,也不是毫無道理。
但是,語云“靡不有初”。我們就把這個不全的《全集》,當做一個“初”,那就可以期望于將來,也能像《汪曾祺全集》,由最初的北師大版而后來的人民文學版,日日以進,版版以新。
最后想說的是第十四卷結尾,附錄了我編的《張中行年表》和《張中行著作系年》。這兩篇,尤其《年表》,是先生逝世后,為遣哀思,我整理讀書筆記及與先生交往日記,把有確切時間可考的有關先生的大小事情,做了一個系年梳理。因材料所限,實在稱不上是“年表”。本來是提供給出版社做編輯參考的,承蒙不棄,居然得附驥尾,實在汗顏無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