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大典》殘本兩岸重現記
來源:中華讀書報 | 肖伊緋 2017年05月10日1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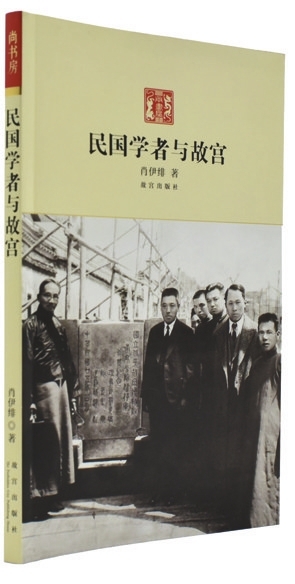
《民國學者與故宮》

葉恭綽(1881-1968)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永樂大典》書影

《永樂大典戲文三種》,1931年“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出版,沈尹默封面題箋。
◎前世今生
《永樂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命太子少師姚廣孝和翰林學士解縉主持,歷時四年,于永樂六年(1408)修成的大型類書。參與編校、謄寫圈點者三千余人,輯入古今圖書七八千種,包括經、史、子、集、釋藏、道經、戲劇、平話、工技、農藝等,搜集極為宏富。至永樂六年(1408)冬成書,全書編成目錄60卷,正文22877卷,裝成11095冊,總字數約3.7億字,皇帝賜名為《永樂大典》。
大典成書于南京,書成后未能刻板,只抄寫一部。永樂十九年(1421)朱棣遷都時,命令撰修陳循挑選文淵閣藏書,共裝100柜,與大典正本一起運至北京皇宮。大典到京,貯于文樓,其他100柜圖書則暫存左順門北廊。正統六年(1441),北京文淵閣建成,于是將左順門北廊的書運入閣中,大典則仍貯文樓。正統十四年(1449),南京文淵閣不幸失火,大典所據原稿及所藏其他圖書均付之一炬,蕩然無存。自此,貯于北京皇宮文樓中的大典遂成孤本。
嘉靖三十六年(1557),北京宮中失火,奉天門及三大殿均被焚毀。明世宗朱厚熜擔心殃及附近的文樓,嚴令將《大典》全部搶運了出來。為了預防不測,他還決定重新抄錄一部副本。此事擱置了幾年,嘉靖四十一年(1562)秋,才召選書寫、繪畫生員109人,正式開始抄繪。重錄前,世宗與閣臣徐階等經周密研究,制訂出嚴格的規章制度,謄寫人員早入晚出,登記領取大典,并完全依照大典原樣重錄,做到內容一字不差,規格版式完全相同,每天抄寫三葉,不得涂改,也不允許雇人抄寫。這些嚴密有序的舉措,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正本的原貌。重錄工作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明世宗辭世時尚未竣工,直到隆慶元年(1567)四月才算大功告成,共費時五年。
明朝滅亡之后,《永樂大典》正本已不知下落,或稱殉葬永陵,或稱毀于李自成戰火,總之是再沒有于世間重現過。世人所能見到的《永樂大典》都是嘉靖年間抄錄的副本,《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也正是這嘉靖年間的副本之一。只不過,這一卷所輯錄的全是古典戲文,記錄的是原汁原味的宋元劇本,非常珍貴、至為難得。
其實,《永樂大典》卷一三九六五至一三九九一都是記載宋元劇本的,共計二十七卷之多。《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這一卷,只是統歸為“戲”字號、凡二十七卷中的一卷,而且還是其中的最后一卷,是一部已經損失嚴重、很不完整的殘本,但卻是目前所知唯一存世的《永樂大典》“戲”字號殘本。
◎遷臺秘史
《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何時遷往臺灣,遷臺歷程又有著怎樣的坎坷磨難?它是怎樣歷經四百年劫難而又重現于世的?所有這一系列疑問,無疑皆凝聚著深沉厚重的國家記憶,理應為后世所銘記。
據史料記載,大典嘉靖副本貯藏于皇史宬配殿約150年,到清雍正年間被移貯翰林院敬一亭。從此,這部內府藏書開始被清廷朝臣們頻繁借閱,也因之不斷遺失并遭受各種破壞。乾隆三十八年(1772)修《四庫全書》曾利用此書,清查時發現已缺失2422卷,約1000冊。
清代嘉慶、道光間,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統志》時又利用大典,這期間由于監管制度不嚴,又被官員大量盜竊。此外,咸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到野蠻破壞和搶劫,丟失大典更不計其數。其中,尤以英軍搶掠最多,將其作為戰利品運回該國。光緒元年(1875)修繕翰林院建筑時,清查所存大典已不足5000冊,實際缺失已達6000冊以上。
另據記載,光緒二年(1876),清查大典庫存數量之后短短一年時間,翁同龢入翰林院檢查大典,竟只剩下800冊。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翰林院成為戰場,大典除戰火焚毀破壞以外,還遭人為搶劫,翰林院所藏大典副本至此全部化為烏有。各國將搶劫的大量文物古籍盜運回國,大典從此散布在世界各國圖書館和私人手中。《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可能就在此時遠渡重洋至大洋彼岸的英國。直至1920年,葉恭綽(1881-1968)赴歐洲考察實業,在倫敦一間小古董鋪里,意外發現并購回了這一冊大典殘本。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后,華北局勢動蕩不安,政府下令古物南遷。北平圖書館已將敦煌寫經、古籍善本、金石拓片、輿圖及部分珍貴的西文書籍裝箱后,存放在天津大陸銀行等較為安全的地方。可能也恰在此時或稍早,葉恭綽也將自己從英國購回的《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秘藏于天津租界銀行的保險柜中,以此避免意外發生,確保國寶不再流落異邦。
當時北平圖書館僅藏有60冊《永樂大典》,并沒有收藏《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但曾專門派人據此卷抄錄了一份副本留存,當時主持抄錄副本工作的趙萬里(1905-1980)是國學大師王國維的同鄉兼門生,是著名文獻學家,精于版本、目錄、校勘、輯佚之學。時任北平圖書館善本部采訪組組長的他,正著力訪求各類流散民間的珍貴古籍,因見部分《永樂大典》遺失海外,國內無存,甚為痛心,便有意將境外之《永樂大典》進行抄錄,以補館藏不足。葉恭綽從英國回購的《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當然引起了趙的重視,他迅即組織人力,對原本進行了精心的“景鈔”。所謂“景鈔”,也即“影鈔”,是近于影印效果的一種人工復制,即是按照原書原有行格、篇幅、字數、字體進行全方位的一比一復制,類似于現代復印技術。
值得一提的是,趙萬里可能還是國內最早撰文、專門介紹《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學者。趙氏所撰《記永樂大典內之戲曲》一文,并附有一頁珂羅版書影,刊載于《北平北海圖書館月刊》第2卷第3、4號合刊的“永樂大典專號”之中,是年為1929年。這期“專號”中,趙連撰三篇論文,一為《永樂大典內輯出之佚書目》,二為《館藏永樂大典提要》,第三篇即為《記永樂大典內之戲曲》。可以看到,在綜述他所經歷的《永樂大典》收藏、訪求、研究史中,專列一文來探討《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中的相關內容,足見其對這部大典殘本的濃厚興趣。
趙萬里對館外《永樂大典》的訪求、抄錄副本工作從1930年代一直持續到1950年代,在歷時近20年的抄錄工作中,經其組織抄錄的這些《永樂大典》副本本身也已極其珍貴,絕大部分均難得一見,獨具文獻價值。從現存的趙萬里所抄副本情況來看,大部分為紅格謄抄本,但并非所有副本均采用原比例復制的“景鈔”。究其原由,無非有兩種。一是所據原本已不是明代嘉靖寫本,而是清代各類官方或私人的過錄本,沒有必要“景鈔”;二是原藏者不愿意提供原件,或時間倉促,沒有足夠的主客觀條件予以“景鈔”。
可以說,正是由于葉恭綽的慷慨無私、趙萬里的高度重視,才合力促成了《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景鈔本的誕生,這一景鈔本也成為北平圖書館的重要館藏之一。在這一景鈔本的基礎之上,又陸續有若干種仿鈔本、精鈔本誕生,均是館方或者學者再次錄副的結果,其中一種還于1954年輯入鄭振鐸(1898-1958)主持編印的《古本戲曲叢刊》初集,這個“影之再影”的影印本,成為大陸戲曲研究學者能夠比較容易用到的工作底本,也幾乎就等同于葉氏所藏的原本。那么,葉氏所藏的原本,此時又身在何方呢?
事實上,在北平圖書館景鈔本誕生之后,國民政府決意古物南遷之前不久,1931年5月,由北京大學馬隅卿等人發起的“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又主持鉛字排印了《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此書就是以北圖景鈔本為底本校印的。為什么沒能用葉氏所藏的原本作底本校印,或者說為什么不直接以原本影印出版,恐怕與當時原本根本就沒在北京有一定的關系。其實,葉恭綽本人早有將原本影印出版、以廣流傳的想法,并沒有深藏不露、秘而不宣的意思;他還為《永樂大典戲文三種》親撰跋文,簡述了原本發現經過,也提到“亟愿此書流通”“影印姑待他日”云云;在馬隅卿等以北圖景鈔本為底本校印出版之際,他表示“樂觀其成”。
或許,由于葉恭綽已經預料到了戰事的危急,此時已將《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轉移秘藏。此舉雖然讓后來的學者們未能一睹真容,一時也未能采取影印原本的出版方式,不得不以景鈔本為底本來排印出版,這多少有些遺憾,但畢竟保全了國寶,在行將來臨的戰亂中及時做出了果斷抉擇。
1933年5月,國民政府教育部電令北平圖書館將宋元精本、《永樂大典》、明代實錄及明人文集挑選精品南遷,以防不虞。接電后,北平圖書館即將包括《永樂大典》在內的善本典籍運往上海,存放于公共租界倉庫。原先同時秘藏于天津銀行的《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是否也隨之南遷,不得而知;此時葉是否已經將此書捐贈或售予北圖,也無從考證。但有一點確是可以肯定的,《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隨后踏上了飛赴美國、轉遷臺灣的旅途。這從時局的演進與葉氏的生平事跡來看,都可以做大致的推定。
原來,1937年“八一三”事變以后,上海淪陷,不久歐戰爆發,國內局勢進一步惡化,存放在上海的珍貴圖籍也因之受到嚴重威脅。北圖代理館長袁同禮(1895-1965)和上海辦事處代表錢存訓(1910-2015),通過駐美國使館與美國聯系,決定將這批善本再做挑選之后運往美國寄存,此次選取的3000種圖籍中就有60冊《永樂大典》。這批精之至精的善本,于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運抵美國,由美國國會圖書館代為保管。1965年,這批善本又全部轉運臺灣。
與此同時,葉恭綽也在為保護國家文物不遺余力。抗日戰爭爆發后,上海淪陷,他準備避難香港,臨行前,秘密將珍藏的7箱文物寄存在公共租界英商美藝公司倉庫,其中就有國寶毛公鼎等重器。抗戰勝利后,這批當時由軍統局秘密保護的國寶,全部轉交南京中央博物院保存。此外,葉氏還將大批珍貴古籍和文物直接捐獻給圖書館、博物館。1943年,他將藏書906種3245冊捐贈上海合眾圖書館;其珍藏的文物則或捐贈、或出售,盡歸北京、上海、廣州、蘇州、成都等相關文化機構收藏,如《鴨頭丸帖》歸上海博物館,《楝亭夜話圖》歸吉林省博物館,等等。可以看到,所有這些在抗戰后才露面現世的,均沒有留在葉手頭的珍貴文物、古籍,早在抗戰前或抗戰中就已經由他精心籌措、苦心操辦,分散保存于當時國民政府的各類文博機構之中了。而其中獨獨未見的《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可能是唯一有資格、有便利、有機會登上避難美國國會圖書館專機的葉氏舊藏之一。
再來看1949年從香港回到北京的葉恭綽。他更為積極地從事文博事業,經其手鑒定、搜求、購藏、捐贈的文物古籍不計其數,但《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始終未再露面,他本人也從未提及。唯一合理的解釋只能是,在抗戰前后,《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已經不再屬于他個人,無論是其捐贈、售予或戰時托管,這冊書已經屬于“國家財產”,登上了飛往美國、轉遷臺灣的航機。
關于《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在抗戰前后的蹤跡,以及最終運至臺灣的這段歷程,筆者的上述推測與判定后來得到了初步證實與進一步的厘清。據臺灣學者汪天成教授考證,現藏于臺灣“國家圖書館”的《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是當年由“中央圖書館”通過中英庚款董事會,以保存文獻名義購入典藏的(詳參:汪天成《〈永樂大典戲文三種〉的再發現》,《戲曲藝術》季刊2010年第1期)。也即是說,當時的國民政府確實是從葉恭綽手中購得了《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使之從私人藏品化身為國之重寶,歷經國難種種,終將其轉運至臺灣。
但與筆者推測略有出入,也更為傳奇的是,《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當年并未搭乘飛赴美國的專機,而是滯留在了香港,未能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轉運出去。隨著香港被日軍攻占,它與中央圖書館寄存在港的大批善本古籍,還曾被劫往日本,抗戰勝利后方才重回南京。1948年,此書終于得以與中央圖書館大批善本古籍一道遷往臺灣,珍藏至今。
◎失蹤傳聞
1934年12月,《燕京學報》第九專號刊印了一部名為《宋元南戲百一錄》的專著。書中附印了一頁珂羅版影印的《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題為“永樂大典小孫屠戲文”。這是繼北平圖書館景鈔本、1931年排印本《永樂大典戲文三種》面世之后,《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首次向公眾以一頁書影的方式展露真容。相信對于普通學者、讀者而言,《宋元南戲百一錄》讓他們第一次看到了《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原始影像,雖只有一頁,卻也著實令人驚喜。但殊不知,這一頁“真容”也并非真容,只不過是北平圖書館景鈔本的首頁而已,因為仿照原本“景鈔”得十分逼真,很容易讓人誤以為就是原本。
當然,讓學者們激動的不可能只是一頁影印圖案,更為重要的是,時年36歲的作者錢南揚(1899-1987),就此開始深入研討一個專門的學術概念“南戲”,并為之摸索考證了七年之久。在書中,他確證了南戲曾經存在的形態與特征,而且還把后來有遺存內容的劇本一一羅列概述。
到1979年10月,已經80歲的南戲研究專家錢南揚,終于完成了其南戲研究里程碑式著作《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注》。他在“前言”中不無感慨地提到學界中流行已久的《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失蹤傳聞。他寫道:
《永樂大典》自卷一三九六五至一三九九一,凡二十七卷,收戲文三十三本,詳連筠簃刊本《永樂大典目錄》。這本《戲文三種》,乃是僅存的最后一卷。此書已流出國外,一九二○年,葉玉甫(恭綽)先生游歐,從倫敦一小古玩肆中購回,一直放在天津某銀行保險庫中。抗戰勝利后,不知下落。現在流傳的僅幾種鈔本及根據鈔本的翻印本,可惜見不到原書了。這次校注,即據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的排印本。
錢南揚可能是為數不多的曾經見到過《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或者至少親自查閱過北平圖書館景鈔本的知名學者。但他仍然沒能逐一查閱、使用并研究《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全部內容,這也是無疑的。否則,他不會在《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注》的工作底本上退而求其次,選擇“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的鉛字排印本。這個鉛字排印本的底本,乃是北平圖書館景鈔本——錢氏的工作底本,實際上已經與原本隔了兩層“紗”。換句話說,錢的學術研究,沒能拿到最接近原汁原味的“原本”,從古籍校注角度而言,“純度”當然還不夠,多少還是有些遺憾的。頗具意味的是,這部與《宋元南戲百一錄》出版相隔已45年之久的著作之中,仍然在卷首插印了一頁北平圖書館景鈔本的《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由此可見,包括錢南揚在內的大陸學者們對該書原本的珍視與關注,隨之而來的遺憾與困惑,也因此縈繞半個世紀,揮之不去。
《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注》出版之后20年,1999年,與錢南揚師出同門,同為曲學大師吳梅弟子的王季思(1906-1996),組織編撰的大型叢書《全元戲曲》終于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在編校出自《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元代劇本“宦門弟子錯立身”時,他也感言:“本劇原與《小孫屠》、《張協狀元》一起,存于《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中。由于原書遺失,故這次整理,以《古本戲曲叢刊》影印的鈔本為底本,參以錢南揚《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注》本。底本原不分出,為閱讀方便,從錢本分為十四出。”以上這些感言得以公開出版刊行之際,90歲高齡的王季思也已于三年前逝世。他在書中的這番感言,也成為中國學術界最后一次確證《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失蹤的說法。
這時,距離葉恭綽從英國購回《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已經整整80年過去了;距北平圖書館景鈔本之誕生,也已經近70年了。但凡有可能親自看到過、抄錄過、校印過、研究過、接觸過《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中國學者皆一一作古。葉恭綽、趙萬里、馬廉、胡適、吳梅、傅惜華、唐圭璋、馮沅君、任中敏、譚正璧、錢南揚、王季思等,皆相繼走完了自己的生命歷程,而《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的下落依舊還是個謎。
隨之而來的閱讀與研究狀況是:在中國學者視野中,《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已經失蹤70年了,只有極少數人能看到北平圖書館景鈔本;接下來,“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的排印本也不多見了;再接下來,只能查閱《古本戲曲叢刊》中的“影之再影”的影鈔本;到最后,錢南揚所著《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注》成了最為常用的通行本。
◎重現臺灣
距錢南揚所著《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注》出版之后30年,2009年11月21日至22日,南戲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南京召開。臺灣嘉義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汪天成發表《〈永樂大典戲文三種〉的再發現》論文,報告了一個驚人的發現:《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即《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明代嘉靖年間內府重寫本)并沒有失蹤,現藏于臺灣“國家圖書館”(即原“國立中央圖書館”)。
原來,臺灣學術界也曾根據錢南揚所言,一直持《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已經失蹤的觀點。但汪天成坦言“一直還心懷僥幸,希望能再看到原書”,寄希望于在大陸或海外尋求原書。接下來,一次因備課查尋資料的偶然機遇,竟意外讓這冊“失蹤”已近一個世紀的國寶重現。他在論文中激動地寫道:
后來在備課時,因為要講到包背裝,需引用臺灣“國圖”的《術語圖說》來解說,可是一點開之后,圖例竟然是《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一,我頓時愣住了。由于是遠景看不真切,于是趕快去查“國圖”的館藏目錄,結果真找到《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一,而且看到了更清晰的圖。就這樣我還不放心,特地再到“國圖”去看了微片和原書,確定真的是《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一。
驚喜之余,出于學者的審慎,汪天成再次逐頁逐字檢閱原書。由于擔心這并不是明代原本,而是另一種未經著錄的景鈔本,他甚至于核對了明代原卷抄錄者呂鳴瑞名下的現存所有《永樂大典》抄錄筆跡。他將《永樂大典》卷六六六、卷二二三七、卷七三二四、卷七五一八、卷七六七七、卷八九一〇、卷一二三六八、卷一九七九一等多卷字跡逐一核對比照,最終確定了他在臺灣“國家圖書館”中見到的《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正是明代嘉靖年間內府重寫本,也就是當年葉恭綽從英國購回的原本。
此時,已經被中國學術界宣稱“失蹤”達80年之久的《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終于重現于海峽彼岸。據汪天成初步研究,這部原本的內容,與此前流行于學術界的各個版本均有較大差異,無論是景鈔本、排印本、影印本、校注本還是各類輯選本,都存在或多或少、程度不一的錯訛與脫漏,這給學術研究帶來的負面影響是持續而且深遠的。可以預見,《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在臺灣的重新發現,將重新厘清相關研究中的一些誤區,重新建立起新的、更為精確的研究路徑與方法,這必將掀起新一輪的相關研究熱潮,誕生新一批的學術研究成果。這次神奇發現《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的學術價值,當然毋庸置疑。
(本文摘自《民國學者與故宮》,肖伊緋著,故宮出版社2017年2月出版,定價:36.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