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冷靜的歷史是無法失落的遺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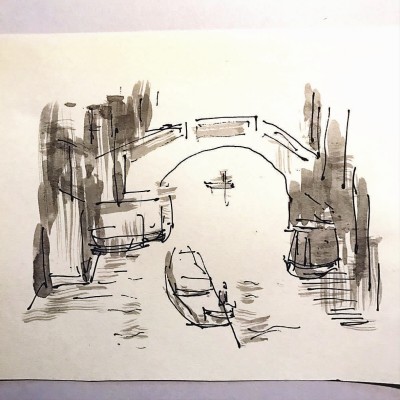
作家金宇澄繼長篇小說《繁花》摘得茅盾文學獎后,日前推出非虛構力作《回望》雜糅個人記憶、家族歷史和時代風云
這是一部紀念“我的父親母親”的記憶之書,也是作家回望歷史后的回聲。繼長篇小說 《繁花》 摘得茅盾文學獎后,金宇澄的又一力作 《回望》 日前出版。書寫父輩故事,如何避免流于一地雞毛,又能窺見歷史的鮮活面貌? 金宇澄的做法是,采用我、父親、母親三種不同的敘事角度,交織大量信件日記等私人記憶,展開枝蔓叢生的講述。
“三個部分相互有重合,也有間隙,線條不一致,我覺得這種狀態蠻好。就像我們聽一個人說這件事,換一個人講,說不定又是另外一種說法。”金宇澄昨天在接受采訪時說,記憶與印象,就像泥土中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須,有枯萎和干癟的過程,“如果你疏忽它的特殊性,它們將消失,而冷靜的歷史,僅是巨獸沉重的骨架,或許是無法失落的遺跡。在這一點上說,如果我們回望,留取樣本,是有意義的。”
就在日前的思南讀書會上,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毛尖評價說,《回望》在某種意義上可看成 《繁花》 的前傳,從大體的時間線來看,《繁花》開始的部分是 《回望》 即將結束的地方,兩本書合起來幾乎跨越了整個20世紀。一些被歷史長河所裹挾的細節,如涓涓細流般重新被找了回來,站在河岸的人,無法忽略水面閃爍的歲月光影。
三重視角交錯,編織有體溫的家族敘事
《回望》 的雛形,是2015年第5期 《收獲》 刊發的專欄文章 《火鳥:時光對照錄》。金宇澄在文中回望了父母的青春———曾叫作維德的進步青年,從故鄉江蘇黎里小鎮走出,抗戰前夕加入中共秘密情報組織,他與愛好文藝的進步女大學生邂逅,歷經生死離別。父輩的前世今生、舊時大家庭的盛衰起伏,交織成帶有個人體溫的家族敘事,在作家隱忍的文字中汩汩流淌。
“我常常入神地觀看父母的青年時代,想到屬于自己的青春歲月。”
父親去世后,金宇澄常陪母親翻老相冊,舊影紛繁,牽起綿綿無盡的話頭,他請母親講一講舊照片,記下時間和細節。《回望》 采用我、父親、母親三重不同的敘事角度,作家刻意保持了三段記憶之間的某些差異,保留了一種“在場感”。對于上一輩故事采用這種交織的復述,金宇澄坦言,他的寫作常常“瞻前顧后、下筆踟躕,習慣被七嘴八舌的聲音和畫面切斷”。在一次次梳理中,父輩經歷的細節,油然融入到作家少年時期的記憶碎片里,金宇澄提到他喜歡的導演楊德昌,尤其難忘電影里父親的形象,“一直記得在影片的咝咝聲中,那個長期獨坐不動的寂寞身影”。
在《收獲》 雜志副主編鐘紅明看來,金宇澄的非虛構充溢著小說家筆法,“是一種文體的自覺和清醒,透著精心和講究。更重要的是思想的力量,以及他對知青年代的反思,對那階段生存的展現和充分的認知,我覺得超出了我所讀過的同題材作品”。在她看來,回望,很樸素的一個動詞,似乎低到塵埃里的姿態,但那是要經歷怎樣的傷痛與滄桑,才會擁有澹泊澄澈的覺悟? 至少,金宇澄寫出父母一輩的信仰與抉擇,而不是大時代可有可無的點綴。此時,記憶的重要價值浮出水面:讓歷史變得似乎觸手可及。
同樣以上海敘事見長的作家小白,在《回望》 里發現了很多隱秘的細節。比如書中寫到在提籃橋監獄,父親聽到了日本兵散步時唱的俄文 《伏爾加船夫曲》,而不是 《櫻花樹下》,讓他覺得驚異。又比如講述當年太湖的強盜來到小鎮,三里長的店面由西向東傳來乒乒乓乓關“排門板”的巨響,驚濤駭浪般的強盜沖進當鋪,搶走一格格抽屜,把里面的銀元倒進船艙,抽屜扔棄河里,水面上飄浮的全是抽屜。“這種仿佛電影一樣的聲響與畫面效果,非常高級,令人過目不忘。”小白說。
“開放式寫作”,讓讀者深度參與互動
《回望》 第二章正文中,穿插了大量書信、父親筆記、日記摘抄、互動百科的詞條解釋,以及種種著作摘錄節選,各種背景聲涌入,幾乎是以一種眾聲喧嘩的方式,四面八方地呈現大時代里的豐富細節。看似碎片化,也正是金宇澄獨具匠心的所在。“這種方式有不確定的效果,每個讀者都可以根據不同線索,生成自己的認知判斷,我不想按照一般的傳統的習慣,把幾大塊材料來做清清楚楚的整合,這會失卻一些原生的味道,可揣摩的空間也顯得狹小。”由此,《回望》 形成一個開放式的結構。
選擇開放式的形態,部分來自金宇澄對當下閱讀習慣的判斷。他愛看五花八門的書評、影評,去年有本火透了的《S.》 讓金宇澄覺得“有意思”,“小說形態本就有多元樣式,書頁間夾雜照片、明信片,甚至羅盤,每一頁空白處,有各種顏色筆的筆記和對話,多線索并行,營造出好奇與解密的閱讀氛圍”。金宇澄認為,讀者是聰明的,所以“作者只需要考慮如何豐富自己的表達,請讀者選擇答案;作者甚至不妨‘懶’一些,多點留白讓讀者想象”。
不難發現,比起一般創作立場的“自我”,金宇澄格外留意讀者與創作的即時呼應。長篇 《繁花》 最早便是在弄堂網連載,他化名在論壇上碼字,每天更新一節,讀者追看、跟帖、評論,“這種互動,其實就是以前西方傳統的客廳、沙龍式閱讀,作家寫出一段,當天念給熟悉的友人聽的,即興分享對作品的看法”。作家木心說,小說家是享樂主義者。在金宇澄看來,“享樂”多了一重意味,那就是全身心投入到這一“讓人消遣與感動”的游戲中,饒有趣味地不斷試探文本的彈性與余味。
采訪問答
金宇澄:文字風格最好是排他的
問:新書《回望》扉頁上題詞“獻給冬的孤獨,夏的別離”,又深情又蕭索,有何意味?
答:這是我按照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短章 《我的孤獨是一座花園》 (薛慶國選譯) 改寫 的。詩作譯文是:冬是孤獨/夏是離別/春是兩者之間的橋梁/唯獨秋,滲透所有的季節……我注意到前兩句所概括的意義:冬和夏,截然相反的兩極,是悲劇性的對立,很符合這本書的某種特質。
問:書中提到母親的那句話“在梳理記憶的這段日子里,她變得沉靜多了,正是記憶的價值所在”,比起辨析歷史,你是否更在意文學意義上的“留存”?
答:是的,文學更大的價值在于我能夠留住一些什么。也許是長期當編輯形成的某種敏感,我清楚這本書究竟敘述、梳理和記錄了什么。加上種種局限,這部非虛構作品里總是會出現空白,因此,我要把僅存的那些細節,進一步細化,做到細之再三,有種疊床架屋的效果,整體上才可以獲得某種平衡。
問:這部作品明明是非虛構敘事,為何還是透著小說家的運筆?
答:用哪種文字質地來表現作家所理解的樣式和內涵,這是非常重要的。文學其實和音樂美術一樣,必須顯示作者的個人特征,你要學會把自己和別人區分開,文字最好是排他的。即使是非虛構,同樣要有個性化的樣式和內涵。
問:從《繁花》到《回望》,你強調的“在場感”一直很明顯,對一段段歲月的截面敘述畫面感十足。這種內在勾連會延續到你的下一部作品中嗎?
答:我確實一直注意畫面和在場感,喜歡簡練與克制。不過,目前還不清楚下一部作品會是什么,因為我不是有計劃、有慣性的作者。我當了近30年小說編輯,編輯心態更占上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