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伍迪·艾倫談喜劇
來源:文學報 | 蘇妮娜 2016年12月16日14: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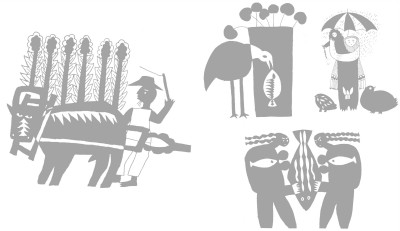
一
藝術家所談論的藝術,不大容易帶入研究者的“問題閾”。不過,他們?nèi)匀换卮鸩⒚嫦蛄艘恍┗镜膯栴}。越是大藝術家,其思考越接近本質(zhì),對既有觀念或補充或背叛。我們只能認為這些思考的來處是創(chuàng)作行為的“倒逼”。黑澤明的書名為《蛤蟆的油》,一方面是笑話自己像自不量力跑去照鏡子的蛤蟆,被自己的丑陋嚇壞了。另一方面,他是說,蛤蟆身上最珍貴的就是“油”,“油”就是不管多么惶恐,人們總會“反思自身”,從走過的路當中倒逼出思想性的經(jīng)驗或經(jīng)驗性的思想。
伍迪·艾倫的談話錄也是如此。伍迪·艾倫非常典型,但伍迪·艾倫卻不可復制。他以獨樹一幟的喜劇電影成名,跟好萊塢無數(shù)聰明性感時尚的面孔聯(lián)系在一起,但他最愛的卻是緩慢安靜質(zhì)樸的歐洲電影,熱愛冷僻的伯格曼,他淡定、客觀地看待希區(qū)柯克和卓別林這些更成功、更適合成為學習對象的好萊塢老前輩們,甚至還有點挑剔。他語調(diào)平實,散發(fā)出一股子老文青冷靜的聰明。他的電影被稱為悲觀主義者的喜劇,不過,他寧可用現(xiàn)實主義者來稱呼自己。
《伍迪·艾倫談話錄》一書是伍迪·艾倫和埃里克·拉克斯跨越30多年的對話,涉及到電影的所有方面,仔細讀來,相當于《認識電影》這一類電影入門書的實踐操作版。不過我最關心的是,對“喜劇電影是什么”這個問題伍迪·艾倫做了怎樣的回答。作為中國的讀者和觀眾,我知道,在某種意義上,伍迪·艾倫的喜劇范式不屬于當下的我們,但他的看法中可能包含著喜劇的走向,某種程度上是在完成對喜劇的背叛——至少是對既有模式的背叛。這是一個刷新認識的機會。
二
從17歲開始,伍迪·艾倫就靠寫作各種各樣的笑話為生,他是天生的段子手,越到現(xiàn)場越能即興發(fā)揮。不過正是這么擅長講笑話的家伙一本正經(jīng)地告訴我們,電影中好笑的東西并不是段子、包袱和笑料本身,這個判斷才顯得那么有說服力。合理的笑料,產(chǎn)生在人物的性格當中。這么說吧,若人物不成立,則笑點無意義。
“是的,比方說你看《愛德·沙利文秀》的那些寫手,讓觀眾大笑一陣之后就消失了,隱去了,因為他們的故事和笑話背后沒有可信的人物。他們的臺詞在紙上很好笑,人們是覺得臺詞不錯所以開懷大笑。但是笑料的最高價值是作為表現(xiàn)人物的媒介。”這樣的觀點,對于我國的喜劇是很有啟發(fā)的:萬萬不能覺得搞個喜劇就是攢很多段子。要知道,“笑點”的達到是需要多種條件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物性格的構成。
笑點的可貴在于它內(nèi)在于人物性格的表現(xiàn),或者說,正是因為人物處于困惑的關鍵點上,他的內(nèi)在特質(zhì)一下子釋放出來了,那是影像中人的尷尬、局促、狼狽的時刻,或是荒誕、錯位、無可奈何的時刻,笑總是在這里產(chǎn)生。伍迪·艾倫比較自己和黛安·基頓:“我充當了一個油嘴滑舌的喜劇演員,而她則塑造了一個人物。”“盡管鮑勃·霍普滔滔不絕地說過無數(shù)俏皮話,讓人們記住他的卻是霍普這個形象。我忘了他的笑話也不會忘了這個人物。”無疑,他把塑造人物看得比制造笑點重要,他追求的并不是把人們逗笑的那個時刻。
三
習以為常的看法是,喜劇允許膚淺,或是喜劇必然膚淺,因為滑稽可笑意味著對深度模式的消解。不過這個觀點似乎對伍迪·艾倫并不完全適用,甚至制造了某種關于喜劇認識的混亂。你能從他前后幾十年說過的話中感到矛盾:一方面他對自己的搞笑才能運用裕如,頗為受用;另一方面,他又強調(diào),如果不是為了別人,而是為了自己,他喜愛的是那些深刻、內(nèi)在、不無悲涼的深度模式電影。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伍迪·艾倫在用一生時間擺脫他身上那個17歲成名的段子手形象。因為對段子、笑點的過分強調(diào)無疑是反敘事的。偉大的喜劇應該同時也是偉大的敘事作品,并不會為了博觀眾的一笑,就放棄戲劇本身的任務。真正好的喜劇應該做的,是有把控的“喜感” ,而比這更高的要求是:“可能笑話本身一點也不好笑,但寫出來讓某個特定的演員去演,就會無比搞笑”——笑意已經(jīng)不需要在文本中直接給出來,也不僅僅是紙上創(chuàng)作的人物性格的一個方面,而更存在于表演本身,也就是演員參與構成之后,成立于一個人物的邏輯內(nèi)部。這是伍迪·艾倫提到的“喜劇性格”“性格幽默”的存在。
我們常說,一個幽默的人,他本身并不可笑,甚至比誰都嚴肅,可就是能讓人不可抑制地發(fā)笑。伍迪·艾倫認為:“你只能在前面正經(jīng)話允許的范圍內(nèi)去做笑話……你不能先從笑點做起,而要考慮人物在那種情境中到底會說什么。”當人物身上的荒誕感成立,觀眾被“撩”到主動在人物身上找“笑”,演員不需要表演幽默和笑,他只要繼續(xù)在性格的軌道上行走,這一切就是可笑的。把性格寫到這個程度,包袱、笑點、段子,統(tǒng)統(tǒng)已經(jīng)被超越了。這是高階的喜劇。
關于今天的喜劇,伍迪·艾倫說:“我們生活在一個精神分析時代——沖突變得內(nèi)在化而不再像多年前那樣是外在可見或是電影化的。沖突的程度越來越細微,在這種現(xiàn)代程度的沖突中心理因素起決定作用……毀滅的種子埋在你自身,這是很難用喜劇的形式加以表現(xiàn)的。”
沖突內(nèi)在化,而非外在化,這不僅僅是喜劇,更是現(xiàn)代藝術共同面對的一種表達困境和表達需求。
當代故事、尤其是當代喜劇最應表現(xiàn)但又不夠自覺之處,就是它們對城市的表達。在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喜劇人物和喜感模式都來自鄉(xiāng)村,來自東北、西北的鄉(xiāng)村,或許還有小部分來自地域特征明顯的城市和城鎮(zhèn)。但我們的城市是鄉(xiāng)村的放大版,喜劇總是從這個“鄉(xiāng)俗”的意義上呈現(xiàn),人們自動地從地域的差異性方面去尋找生活或故事的可笑之處。然而,這種方式會越來越不適用于缺少區(qū)隔、打破疆界的當代生活。
或許從這一點出發(fā),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伍迪·艾倫為何如此“常青”:公寓、花園、商場、醫(yī)院和咖啡廳里的故事,是一種普遍的故事來源。我們需要的陌生感和熟悉感,都不再能從地域文化中汲取。不管鄉(xiāng)村表達多么熟稔,鄉(xiāng)村之根已經(jīng)斬斷,電影、戲劇、小說,對應于更廣闊的現(xiàn)實經(jīng)驗的是城市生活。
伍迪·艾倫是熱愛城市的。一個熱愛歐洲電影,不喜歡快速的鏡頭切換,并且?guī)缀跏亲猿暗卣f現(xiàn)在的電影中對話太多的人,其實并不喜歡過那些電影中的生活。他的生活,只能是在人群聚居的地方。他曾在英國南安普頓的鄉(xiāng)村買了一幢非常漂亮的房子,用盡心力裝修完后,只入住了一個晚上,他便突然醒悟到“這不是我待的地方”,于是給會計打了個電話:“把房子賣了吧”,然后帶上妻子回到城里去。他會遵從他所拍攝的城市來調(diào)整劇本和拍攝方式,正如他會為了一個角色的演員更換而更換這一切——或者我們可以這么說,他攝影鏡頭下的城市,是一個重要角色,也許比其他角色重要得多。“我猜我還是人行道、麥迪遜廣場花園、飯店和書店的產(chǎn)物——你知道,就是街市的感覺。”
四
對伍迪·艾倫這樣悲觀主義者的喜劇,羅杰·伊伯特說:“一位善良的牧師眼睛瞎了,一位聰明的哲學家從窗戶跳下,而我們笑著,可能并不會為之哭泣。這是伍迪·艾倫有史以來最絕望的一部電影,但是你越想,越覺得它滑稽。”
伍迪·艾倫是個清醒的無神主義者,他的喜劇直指“無神世界中人們要憑借什么活下去”這個哲學命題。也許對大多數(shù)人來說,悲劇才是關乎存在的嚴肅思考。但伍迪·艾倫指給人們看:喜劇同樣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