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 民族文藝 >> 文學評論 >> 正文
大抒情與神圣世界
http://www.tc13822.com 2014年11月02日14:08 來源:中國民族報 劉大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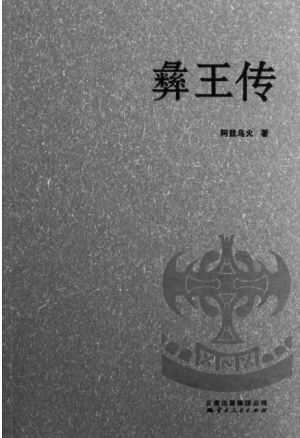 作者:阿茲烏火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3年5月
作者:阿茲烏火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3年5月詩言志、詩緣情,一向是中國傳統詩學的主流。到了現代,中國當代詩歌在朦朧詩之后,有了種種新的探索。口語、身體、日常化……這些路向成為重要的詩歌議題,它們總體上顯示了當代社會詩意的喪失,日常生活的審美化,以及散文時代的到來。詩歌似乎越來越理性化,技術化,瑣碎化。
然而,在這些時髦命題的背后卻隱藏著一股洶涌的潛流——絕大部分不曾進入主流批評視野的少數民族詩歌依然在保守的面孔下,執著地進行浪漫主義式的抒情。他們或者帶著集體狂歡的激情,要為瀕臨消亡的族群文化留存記憶;或者在想象的幻境中,點燃逝去意象的盛大焰火。來自烏蒙山區的彝族詩人阿茲烏火屬于前者,他的漢文名字叫李騫。他是文學教授,屬于彝族的文化精英。當他起意為彝族傳說中的祖先、王者、英雄、神靈創作一部長詩時,是為了完成心中的情結:既訴說本族群的璀璨往事,歌頌英雄祖先的業績,又抒發帶有共通性的情感。
我們向世人講述彝王
其實也就是講述我們自己
這是每一個彝族人神圣的責任
只有這樣 即使幾萬年后
我們的子孫才不會丟失這一段記憶
阿茲烏火在長詩《彝王傳》的最后卒章顯志,點明自己寫作的緣由。這首長詩分為上、中、下三篇,分別為“橫空出世”、“繁殖之神”、“六祖分支”。從內容上看,這首詩是以傳說中的彝王阿普篤慕的事跡為線索。然而,恰如阿茲烏火所說:“這首長詩不是以敘事為主,而是一首帶有神性色彩的抒情長詩。詩中的彝王只是生命的一種直觀體驗形式,而非歷史中的偉人。應該說,我筆下的彝王更接近彝族民間口頭傳說中的王者,他是一個無所不能、自由自在的神靈。”
這種抒情與上世紀90年代之后,詩人趨于個體化、肉身化的自我撫摸不同,而是傾向于一個宏觀、博大的抽象主體。這是一種“大抒情”,指向的是共同體的同情共感,提倡的是更為廣泛的普遍價值——那些在日益平庸、精細、功利、工具理性化時代行將就木的,對于血性、威武、勇猛、豪放、犧牲、苦難、超越的渴望。
少數民族詩人作家的寫作,往往帶有很強的代言意識,無論自覺或者不自覺,作為一個族群的文化精英,在書寫涉及族群歷史、文化、社會時,總有一種共同體意識,而很少個人主義式的表述。在現代性沖擊中的回歸祖靈,可以視為一種無可奈何的退守性思路。然而,這是站在啟蒙式理性規劃視角下的審視。如果換個立場,站在彝族的主位,那么這種尋根則具有尋找遺落的價值的意味。
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在《詩人何為》一文中,把普遍技術化的“世界時代”,標識為“世界黑夜的貧困時代”,認為處身“世界黑夜”中的人類,總體正在經受“世界歷史”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阿茲烏火筆下的“彝王”,通過自己生生不息的繁殖力、蓬勃有力的播撒力,讓暗夜中頹敗潰散的人群重新得到光明。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跨越空間與文化差異的共通。人們遭遇的是同樣的命運,在摸黑找尋出路。“彝王”雖然只是一種中國邊地族群的信仰和圖騰,卻具有全人類的價值。
這種大抒情復活的是某種小傳統,通過頌歌式的抒情營造出一個超驗世界,穿透了世俗和現實,完成對神圣性的復活。在科技、資本、消費主義日益強勢的氛圍中,弱勢個體的自我出現分裂、流散和支離的局面,靈光消逝,大抒情則起到了彌合與修復作用,讓自我在對于祖靈代表的共同體中圓滿、充實、完整,接續了斷裂的歷史,重建一個世界。因此,對《彝王傳》這部作品不能僅僅從通行的文學審美予以審視,它實際上是一種精神檔案和文化表達。從文化復興的角度來看,該書也提供了多樣的思想資源。
網友評論
專 題




網上期刊社


博 客


網絡工作室
